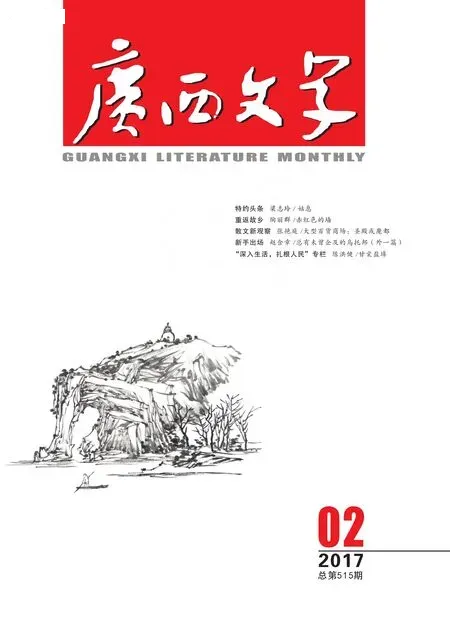三奔波
短篇小说·明 媚/著
当最后一辆牛车碾过茬固岭的石拱桥时,西边的太阳掉了下去。那辆用铁条焊成的牛车,黄土坯悠悠地很不情愿地从车上震落下来。在这条石子路上,只剩下一个黑影在游移;只剩下一种咿呀的声响,间或老牛的吭鼻声;只剩下一种秋凉般的寂静,散落在同样黑黑的蔗林里。
三奔波解开了牛绳牛轭,那头老牛慢悠悠地向牛房走去,牛尾巴像一条软软的辫子在屁股后面左右甩动。他接着从牛车上扯下两把牛草,步履轻快,好像要给自己的老婆送饭那般殷切。脸上淡淡的笑在白牙下不露声色,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自己的心思。老牛,老婆,只差一个字。老牛不能变老婆,老婆也不能变老牛,可他知道,有了老牛,他的老婆就一步一步走进他的梦里。这头怀孕的老牛,再过几个月就会生下一头小牛,养两三年,一出手,三四千元,他三奔波再买回一个壮实的老婆,日子就甜美了。可惜了三十五个春秋里,他的青春和他的积蓄被三个外乡女席卷而去,还留下了一堆活债。他也得了一个雅号“三奔波”。买来的三个女人都只在他的房里待了一个月,正盼着有人叫一声爹,女人和梦想就如一缕烟销声匿迹了。再拼搏一年,所有的甘蔗收成后,债就还完了,三奔波这么想着。牛犊出生之后,美丽也来的。
三奔波笑笑,那口白牙灿烂。在灯光照射下,他的脸膛还是像刚出炉的红薯一样黑。他老爹佝偻着腰,在门下看着他。爷俩向来就不大一起说话,他老爹瞧见他回来,好像安了心似的自个到房里躺去了,也不看电视。三奔波把衣服脱了,一身的黑亮,腰带扎得像只挂在树上的青蛙似的。三奔波吃完饭,洗了个澡,躲在房里看电视。门关死,床尾边还挂着几件女人的衣服,那是上次的老婆跑时没来得及带走,已过去一年了,衣服上满是灰尘,可是他还是舍不得把这些衣服丢掉。
秋收了稻子,媒婆就来到了三奔波家。一来就三人,一个老女人,她嘴唇边长着一颗大黑痣,她是专做联络人营生的邻村的大姑妈。一个中年妇女,陪着待嫁女人来讨价还价类似经纪人的女人。一个不大不小的女人,三十左右的样子,矮墩壮实的女人。大姑妈当然把三奔波的老爹叫到一旁,颇有耐心地讲解女方的情况。也就是死了老公,那边很穷,过不下去了,没有儿女拖累,是个干活的能手。末了还问一下他三奔波的老爹,是否有心要啊。有的话就选个好日子,迎进门来。迟了其他人看上的话就没得说了。女人当然和三奔波在房里看电视,他们言语不通,只能这么傻坐着、干笑着。中年妇女会讲点普通话,算是一个翻译员。可三奔波结结巴巴地对不上话,只能不时地斜溜一下坐在凳子上的女人。女人,就是他的梦,就是他俯贴在这片黄泥地上的全部诗意。
三个女人走后,却还留着特有的味道,鲜活地笼罩着这个沉闷的家。这个味道,导引着三奔波向狂想的甜美奔去。三个女人走后,三奔波的老爹望着墙上的积善堂,祖宗在上,他的双眼却愁结暗淡。夜里,父子俩交换了意见,把稻子卖了,把牛卖了,凑起来也有六千多了。再压压价,争取五千块把老婆买到手。剩下的一千多摆上几桌请一些亲戚来吃餐饭,再给点女方陪送人员的来回路费,满打满算,也凑合着够了。爷俩都觉得这样干实在。年底的甘蔗钱就拿来慢慢还债,对三奔波来说这是一个兴奋的计划。兴奋了,他就有劲了,第二天就张罗起买卖来。谷子先拉到镇上卖了,接着,也有人来把牛拉走了。邻居都笑他神经,没有了牛怎么种地呢?在石头混杂的黄泥地里,种甘蔗,种谷子,一头牛可以顶得上一辆拖拉机呀。你三奔波没有了牛可怎么干活?三奔波回答得挺轻松,我不会借啊?谁借给你呀?都忙,一出工牛不离人,人不离车。三奔波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没人借就去信用社贷款再买一头呗。你看他多豪情。
三奔波忙活了一周,夜里却睡得踏实了甜美了。没有了牛,他去干活只能徒步去了,也不用一边干活一边分神管牛了。早上出工时,往肩上扛一根尖头扁担,手上提一壶粥,再拿一把镰刀,便走入了茂密的甘蔗林里。除草,摘蔗叶,他样样能行。就算从四里开外的蔗地里一肩挑回两大捆蔗叶,他也是面上的笑容盖过咸涩的汗水。
村里的人都看惯了他的笑话,这样,三奔波在众人的心目中就扁了许多。可是他得忍啊,他要改变他的现状。别人有的,他要有,三奔波这么想着。刚好发生的一件事让三奔波得到了安慰,村里一夜之间被偷了五头牛。人们集结在商店门口议论纷纷,把罪过都归到了新修的一条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上。有了这条水泥路,贼们都在深夜开着后驱动或者小面的来偷牛。人们谈论叹息之余不忘点一下三奔波,卖牛卖得及时对路了。三奔波也嘿嘿地笑。
三奔波家没有狗,因为没人愿意到他家走动,也没人到他家喝个小酒。在别人眼里他家没什么好东西藏在家里。就算他家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来往的人都很少,狗也就没什么大作用。可一天晚上,本村的一个同样没有老婆和三奔波年龄相当的老男孩走进了他的家门。大家都是条件相当,自然就有了话题。老男孩叫四生,出了名的赌徒,他的到来,换成谁都会警觉地对待,可三奔波还憨憨地笑,叫:“四哥坐。”四生说:“老三,听说你准备娶老婆了。哪里人啊?合适的话,等你娶了,也让你老婆介绍一个给我。以后我们去丈母娘家就有了伴了,路上也就安全了。”三奔波笑笑:“四哥,我真有老婆了,肯定要帮你的忙,我也要两只阉鸡来吃啊。”四生说:“好好,如果你介绍给我成事,我给你八只阉鸡。”三奔波说:“说话要算话哦。”四生就拍着他的肩说:“我几时骗过你?都是本家兄弟,骗兄弟我不是人。”三奔波说:“等我成事了,一定请你喝酒。”四生说:“你又不喝酒,我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三奔波说:“我不会叫我老婆陪你喝呀?”四生就哧哧地笑:“老三,看来你真的要成事了哦。”三奔波露出白牙笑:“八字就差一撇了。”四生在他房里望了望,用手拨了拨吊在他床尾的几件女人衣服,眼神诡秘地对三奔波说:“老三,你都成事了,还骗老哥啊?衣服都有了。”三奔波傻傻地笑:“没有哦,都是以前的了。”四生就逗他:“老三,你小子也风流成性啊,娶了三个老婆的了。再添上一个,你就娶了四房太太了,真是一个老财主噢。”三奔波就眯眼呵呵笑,憨憨地说:“是哦,在村里也就是我一个,有这样的历史哦。”
四生点了一支烟,他给三奔波一支,三奔波不会,四生硬是往他嘴里塞,三奔波就抽了起来。四生说:“老三,告诉哥,你这回买这个老婆要多少钱。”三奔波说:“不知道哦,还要讲价的。”四生说:“那边要多少钱?”三奔波说:“可能要六七千吧。”四生说:“你不会讲价啊?找她身上的毛病来说啊。”三奔波说:“我见她身体也行啊,干活是有劲的就行了。”四生说:“你傻呀,把她买过来就是你的了。没买前,人家看的是你的钱。你有多少钱,自己有多大的承受力,要心中有数,不然,娶不到的。”三奔波就凑了过来说:“我不知道怎么讲价哦。我和女方的人又不通语言。”四生说:“有什么难?我帮你搞定。我全国各地都去过,他们还能说外星话?我就不信。”三奔波说:“真的啵。”四生拍胸脯说:“你再去时叫我,我帮你讲价。把价压低给你。”三奔波说:“真的啵?”四生说:“真的,什么时候去,我开车拉你去。讲归讲,你也要让我知道你的底价,到底压价到什么程度,你才能承受得起。”三奔波说:“我现在有六千八了。我和我爹商量好了,争取五千块能成事。剩下的钱,一些拿来摆几桌喜酒,一些再给女方路费和媒人费,这样弄就刚好够了。”四生斜眼听他说完,说:“这好弄,我一定帮你把事弄成。”这时,三奔波的老爹路过三奔波的房门,说:“三啊,早点睡啊,明天还要去摘蔗叶啊。”三奔波应了一声。四生起身说:“什么时候去谈,你叫上我,包你如意。”三奔波起身送四生,说:“你这么能说,到时说给你自己的话我可不同意的哦。”四生笑笑:“我们是兄弟,当然照顾兄弟在前。我有这么坏吗?抢兄弟老婆。”三奔波说:“那你在家等我哦。”
天刚有点灰亮,三奔波就抢在第一头牛迈过茬固岭的石拱桥时,第一个跨步过去。他要争取先把蔗叶摘完,再去相亲。不把蔗叶摘完,等到砍运的时候要多给别人工钱的。那些茫茫的蔗海,很快就把三奔波淹没了。走进自家的蔗地,三奔波找了个地方把备好的午饭放好。天凉了,不怕饭菜馊了,可以一心一意一捋一捆地把蔗叶摘下捆好摆在蔗垄沟里了。他动作利索地干着,心里只想一个劲地加油,平时一天只能摘三分地的蔗叶,这次他下决心要摘四分地。老爹不能帮他忙了,只能在家喂个猪,煮个饭给他吃了。想到有个老婆和自己一起劳动,那该多好啊。他就像一条冒着汗的野狗被藤蔓缠绕一样,奋力地撕扯着,努力撕开一条路……
夜色灰暗了,三奔波匆匆喝了两口粥,把摘下来的蔗叶抱出地头。天干物燥,还是把蔗叶搬出来的好,没有了牛也要把蔗叶挑回去当柴草煮饭烧水。他把蔗叶用绳子一捆,分散的蔗叶就被扎成了两垛。三奔波钻进扁担下时整个人都被蔗叶淹没了。他运运气,腰一挺就走了起来。那双破了洞的解放鞋踩在茬固岭黑黑的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山岭的上空。
忙过了这些天,三奔波的脸上被蔗叶划出了几个口子。他照镜子时,用雪花糕涂了涂。他一边涂一边想那事可不能拖了,第二天就是隔三赶集的日子了。他打算去理个发,就去媒婆大姑妈家把事办了。夜里,他去找了四生。四生说没问题,他用摩托车拉三奔波去。三奔波很高兴,终于找到一个帮说话的伴去了。上床睡觉前,他去问老爹要钱做路费。老爹解了两层裤带才把钱取了出来,三奔波就看到了一沓红红的绿绿的钞票。老爹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出来说:“带上五十块。买斤肉去。”三奔波说:“知道了,我想再剪个头发,要不要买果去噢?”老爹说:“不买,不知道成不成事。不浪费。”他这才知道老爹一直带着钱睡觉。
三奔波见到了那个嘴角有颗大黑痣的大姑妈,大姑妈已不像来他家时那么好说和热乎。大姑妈说:“三啊,你来得不是时候了。华加村有个人看上了我带到你家的女人,出价七千。”三奔波听大姑妈这么说,心都怯了,不知道怎么办了,笑容硬了起来,傻傻地说:“他有我这么好吗?”大姑妈哼了一下鼻:“人家家里有两层楼,三头牛,一架手扶拖拉机。关键那个女人也喜欢哦。”三奔波说:“还有其他的人吗?老一点我也要噢。”大姑妈说:“六十岁你娶吗?我识得几个人。”三奔波就不知道怎么答话了。四生扬扬手中的猪肉,瞪着大姑妈说:“你这个人怎么讲话的?等下我就让你把这块猪肉吃下去。”大姑妈瞟了他一眼说:“这个人是谁噢?是想娶老婆吗?想娶老婆这样讲话得的?”四生说:“我讲话明了给你听。你敢把那个女人嫁到华加村去,我就烧了你这个破屋。”大姑妈也不是省油的灯,只见她两片薄嘴皮张张合合,就像炒黄豆一样爆出一串话来:“死噢,娶个老婆把气发到我身上。这个是哪门子的道理噢?年轻人,成败要看两个人的缘分,不是我讲了算噢。你吓我有什么用?没有用哦。我费口舌去拉线先不要讲,还惹得人恨,我做这些好事是为哪个噢?你不得乱讲话哦,乱讲话被雷公劈的噢。”四生说:“不是你带人去,我和老三不会上门来看你。今天就把价讲好了,五千块。”大姑妈叫出声来:“五千块!不够人家的来回路费,还想娶老婆?”四生说:“你同意吗?又不是嫁你的女,你着什么急?好讲一点多给你两只阉鸡。不好讲,出街看到扫你一脚,要你躺床一个月,坐凳三个月。”大姑妈白了他一眼说:“我试着讲讲看吧。不行,也不要怪我啊。”四生说:“我还怕那个女的是骗钱的,得了钱就拍屁股走人。”大姑妈说:“你养得人家好,人家怎么会走的?”三奔波说:“我要她跟我去做工噢,我要看紧她哦。”大姑妈说:“嫁过去了就是你们的事咯,这种事,我管不得咯。”四生说:“反正你要好好讲,喊那女的来我们老三家。我们老三人老实,做工也做得快。”大姑妈摇摇头说:“那我试试看哦。”
从大姑妈家出来,到了集上,四生叫三奔波喝两杯。三奔波推不过就喝了,喝了他就醉了,醉了四生就把他背了回来,扔在了床上。三奔波的老爹见了就有点不高兴,拉着三奔波的耳朵说:“三啊,今日花了多少钱?事怎么样了?”四生说:“没有这么快,还得去一趟。没得和那个女人见面呢。”
之后的一天清晨,三奔波正打算再去老姑妈家探一下消息,他醒时发现睡过了头。同样睡得迷迷糊糊的老爹还没起床煮粥呢。他敲老爹的房门,老爹不吱声,便打开了门进去,摇了摇老爹。老爹醒来问什么事。三奔波说要钱。老爹解开裤带拿钱,发现一沓钞票全变成了天地银行的冥币。父子俩顿时傻了眼。老爹紧张地问:“钱呢?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哗啦地抖开假币,不停地翻找着,那老泪就流了出来。三奔波也木木地站着,嘴里喃喃:“放在哪了?放在哪了?见鬼了。见鬼了!怕是没拜过祖宗呢,早两天出门做事,没做错什么噢。”老爹嚅动着嘴唇:“钱被人偷了,被人偷了,被人偷了。”三奔波才紧张起来:“什么?被人偷了?怎么不见门口被撬?怎会又变成了假钱?”老爹说:“咒他祖宗十八代啊,平时我半夜都睡不着,昨夜怎么睡得这么死?一点响声都听不到噢。”三奔波说:“那我的老婆怎么办噢?去哪再找这笔钱噢?是哪个害人精干的?真应该出门被车撞死哦。”老爹在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一切。昨晚吃过饭,他就是像往常一样早早上床躺的,就是奇怪怎么睡得这么快了,而且半夜也不起夜了。
三奔波在老爹的安排下跑到镇上报了警。民警带着三奔波回来了,三奔波坐在面的改装的警车里东张西望很是好奇。民警了解了情况,做了记录,怀疑他们的食物被人做了手脚,要拿他们昨晚的食物回去化验。可那些剩饭剩粥已被拿去喂猪了。民警又检查了门锁,没发现被撬,结论为,是拿钥匙开门进去偷钱的。老爹问:“什么时候可以破案?要不然,贼就把我们的血汗钱花光了。”民警说:“我们尽力,尽快。”围观的群众都知道了怎么回事。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盼着破案,日子也过去了,甘蔗也砍了,债务也用蔗款还上了。劳累了一年,三奔波还是两手空空,连牛也没有了。春天的细雨蒙蒙地洒落在三奔波的头上,他正干着帮别人砍甘蔗的营生,也只能这么挣钱了。他老爹早早去求人家帮忙耕地,可人家也没有空啊。回家闷想之后,他决定去亲戚家借牛。
春耕刚开始,当最后一辆牛车碾过茬固岭的石拱桥时,三奔波从车上跳了下来,他到拱桥下洗净了手脚。虽然水有点凉,可他心里一笑,总算耕完了所有的地。他看看这头并不健壮的牛,在他家里待了十天,亲戚家的人就来看了三次,还说牛瘦了,叫快点还了。第二天,老爹就叫三奔波带了两斤猪肉和一百块钱去亲戚家还牛了。
春耕完后,三奔波的那颗心又闲不住了。他在想他未来的老婆啊,他在想怎么去弄七千块钱再买一个老婆,他在想着那些温热的感觉。眼见着过年时,村里面的小伙子一个一个从广东带老婆回来。有的还是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回来,他羡慕死别人了。这些人怎么这么有能耐?他在茬固岭的石拱桥下洗衣服时看到从广东打工回来的人出双入对,在商店里闲坐时看到人家小情人儿打情骂俏,他的心就痒痒的。他也想着自己应该可以去广东的,也会像他们一样找到老婆的。他想着心里就乐滋滋的。旁人也说他该去广东找老婆呢。特别是胖七婶,从广东回来的,说那边什么女人都有,三奔波愿意的话,娶个带小孩的都没问题,还免得被计生队拉去阉呢。听了胖七婶的话,夜里三奔波就睡不着了。他真想去开开眼界,他翻来覆去地想,老爹能让他去吗?他走后谁来养老爹呢?他不敢开口啊,怕被骂不孝。
在一个晚上,他说了想去广东找老婆的想法。以为老爹会反对,老爹说:“你想去就去吧,找个人带去。”三奔波说:“你在家怎么办?”老爹说:“只能叫叔伯们帮忙了。我一个人饿不死,几亩地的稻子够我吃很久咯。关键是你要带老婆回来,再不带回来,家里就断香火了噢。”三奔波得到了老爹的应允,就有雄心了,就看到了光明的前程。随后,他卖了几袋稻子,有了路费,和村里的一个中年男人去广东搞建筑打零工了。
没多久三奔波从广东回来。大伯告诉他:“你爹杀人了,用的是菜刀。”三奔波惊问:“杀的谁?”大伯说:“四生。”三奔波问:“为什么杀他?”大伯端着水烟筒喷了一口烟说:“四生偷了你家的钱,那六千块。”三奔波说:“怎么知道是他偷的?”大伯说:“四生赌钱输了噢,去偷敏八叔的钱,被追到蔗地里抓住,敏八叔家老六正准备娶老婆的钱哎。老六是个蛮种,不放过他,说剁了他的手,吓得四生尿裤子了,就什么都招了,包括偷你家钱的事。你爹知道后,去叫四生赔钱。四生不肯噢,他家里人也不管。你爹就收拾了他。”
三奔波探监见到老爹,老爹木讷的眼光碰到他时突然放光并悲戚地叫了一声:“三啊!”三奔波看到老爹皱纹深纵的脸紧紧撑着一双未闭的眼,他的泪就如洪水一样流泻出来。
后来,茬固岭的土坡上,多了一个崭新的坟。那些白纸条和那些散乱的脚印,撒了一地。三奔波手里还拿着一把锄头。
从此,茬固岭的石拱桥旁,多了一个孤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