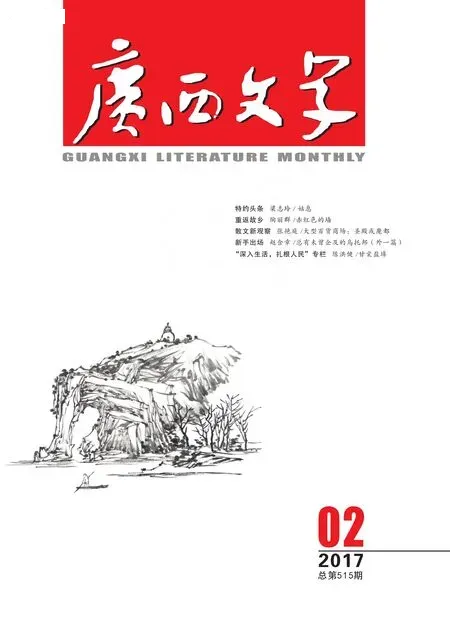翻 车
伍中正/著
那个冬天的下午有点特别,我意外地接到了村里发煤叔打来的电话。
要在往常,我是绝对没有很多电话的,尤其是发煤叔打来那么多的电话,就为一件事情,一下午用手机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以为他疯了。
这几年,我跟发煤叔的联系没有间断。每年中的某几天,发煤叔都会想起我来,跟我打几个电话,说些对我来说有点瓜葛或者无关紧要的事。在一个电话里,他从村里谁家的狗咬了人,谁家的主人不愿给被咬的人出打预防针的钱说起,接着说到那个叫苏和尚的兽医一刀子下去,把谁家发情的小母猪弄死了。在另一个电话里,他说那个叫海棠的女人在屋后设置了一张网捕那些飞来飞去的鸟,接着说跟村主任好过的女人拿着砖块砸了村主任家的窗户。
有一回,我对发煤叔说,你往后打个对我有用点的电话,在电话里说个对我有用的事,你看行不?我把这个想法说出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冲撞了发煤叔。
发煤叔好像听出了我的不耐烦,想跟我解释又没解释。最后,他在电话里保证,等有用的事到了,一定打电话给我。
发煤叔在电话里有些焦急地告诉我,说我原来承包的那块水田里翻下了一辆卡车,车主的一车沙卵石散落在田里。这回的事对我有用,肯定有用。
在电话里,发煤叔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恨不得加重语气。
我不知道发煤叔的手机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没电了。他说完这句,我就听不到下文了。
发煤叔的电话让我揪心了一会。同时,我觉得那个冬天的下午特别漫长。
车怎么会翻在我田里?我那块田里有史以来没有翻过一次车,是不是发煤叔搞错了?再说,我进城前,把路边的那块田让给了长富叔。就是车不小心翻在了田里,也应该找长富叔去处理。我还是觉得,发煤叔的电话对我没有一点作用。
过了一个小时,我又接到发煤叔的电话。发煤叔说,长富跑过去了,两条腿跑得很急。他跟车主撕破脸了要钱。不给钱,长富死活不让用吊车吊起来的卡车走。
话还没说完,电话里没有声音了。可能是发煤叔挂断了。
我还没有进城前,长富叔就看中了我的那块田。那块田挨近公路,水路好,种啥长啥,他愿意承包下来。长富叔提了两瓶酒还特意到我家来跟我说那块田的事。他跟我讲,要是进了城,无论如何,得把那块田让给他种。看着长富叔死心塌地要种那块田的样子,我答应了长富叔。
那年春天,长富叔就在那块田里耕种。一种就是好几年。
那天下午,我的电话好像就是为发煤叔准备的。
那天下午,发煤叔就只给我打电话。
发煤叔叔又一次打通了我的电话。发煤叔说,车翻在田里,压毁了田埂,田里还落了不少的沙卵石。长富平白无故地拿到了一笔钱。车主赔的那笔钱不应该长富拿,应该你来拿。
说完,电话又断了。
我觉得好笑,长富叔没有理由要车主赔啥钱,车主也没有必要给长富叔钱,他只要找几个人把那些沙卵石挑走,把田埂修好不就没事了?一个在外面跑运输的车主还找不到几个人?
我觉得长富叔是没事找事,弄不好还会出事。
果真出事了。
发煤叔的电话再次打给我时,我知道,翻车的事情真的闹大了,必须回去。
我在那个冬天的下午赶到了村庄。
在发煤叔家,我见他头上包着一层厚厚的纱布,从那层纱布上还能看到隐约渗透出来的血色。
发煤叔见到我,就赶紧替我出气。
发煤叔说,车翻在你田里,赔的钱只能你来拿,凭什么他长富就拿了?发煤叔的情绪仍很激动。
我不好对发煤叔说什么,安慰了他几句后我就见去见长富叔了。
我看见长富叔的左手明显地受了伤,从脖子穿下来的一根纱带吊着手臂。长富叔见我到来,就搬出椅子招呼我在禾场上坐下,那没伤的一只手再次搬了一把椅子出来。
长富叔说,这几年,感谢你让出那块田,让我从田里增加了收入。
长富叔接着说,车翻在你田里,我不能让你吃亏。我让那个车主赔了钱才走。钱,我帮你要回来了。
说完长富叔起身回屋。
长富叔再出来的时候,那只没伤的手上拿着一沓钱。
我一惊。
我平静了心情跟长富叔说,车翻田里,我不想要车主的钱。
长富叔激动地跟我说,莫蠢,车翻在你田里了,到手的钱,不要白不要!
我跟长富叔挑明,把钱退给车主。
长富叔不依。
我看了看天,村庄的黄昏就要来了。我急着要回城,没有时间跟长富叔多说。
我执意没拿他手上的钱。回来的时候,我听见长富叔在我背后骂我的声音:杂种,往后,老子不种你的田了。
那一刻,我没有回头。
在我入睡前,发煤叔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一看是发煤叔的电话,接了。我对着电话说,别打电话了。
发煤叔说,我的田里翻了一辆车,我不知道咋整。
我一下摁了电话,接着,关机了。
我小声地对着手机说,发煤叔,你爱咋整就咋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