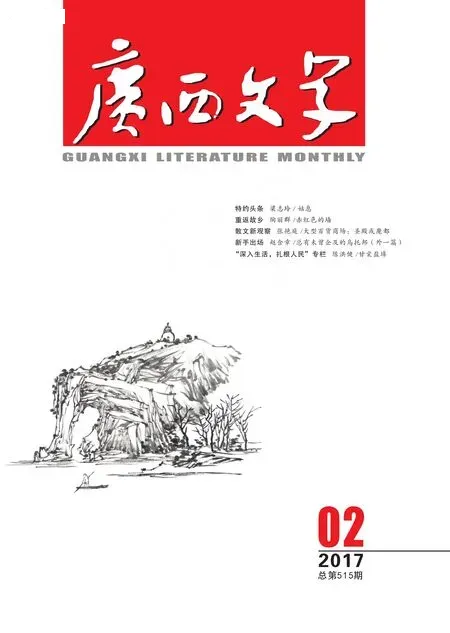总有未曾企及的乌托邦(外一篇)
赵含章/著
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让人猝不及防,我行走在氤氲的雾气中,下意识地把外衣裹紧了些。黯淡的天空化作深沉的底色,衬托出这个城市的疲倦。
我停在一个书店前,这是我此行的目的地,门外夸张的大幅海报宣告着这里正在开展换客活动。
书店的店主是我的老友,他曾跟我抱怨过经营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而我不曾想到已经举步维艰到直率如他都要通过与商家合作来维持生意。
书店是能让一座沉重笨拙的现代城市漂浮起来的生态系统,可惜倍道而进的快节奏生活正蚕食着这一隅轻盈。
我推开店门,讶异地发现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多。也许在这个辛辣奇突如电影般唰唰掠过的时代里,应接不暇的人们把复古也当成了一种时尚。
我和店主打了个招呼,懒洋洋地走到贴着交换告示的墙壁前,寻找着能让自己眼前一亮的物品。
“不好意思”,一个有点沙哑却很耐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其他人的喧嚣霎时间成了无关紧要的模糊背景。“可以用这个跟您的东西交换吗?”她递过来一张碟片,又指了指我手里拿的巴黎胶片摄影集。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接过那张《午夜巴黎》的碟片,不禁问:“我也看过这个电影,你很喜欢法国吗?” “怎么说呢?曾经喜欢过吧。”她看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不由微笑起来。“不如一起喝杯咖啡吧。”
在书店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坐定,她告诉我,她不久前刚刚从巴黎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去巴黎,不过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吗?”我问,她摇了摇头。
三年前,她在美术馆参观了一个以巴黎为拍摄主题的摄影展,她一直记得那个午后,阳光的薄片从玻璃窗上跌落,蝴蝶般轻快地跳动在一幅幅照片上,点亮了那些色彩鲜艳的小房子和巴黎街头悠闲的行人的眼神,她的视线所及之处皆是厚重斑驳的光影。她在美术馆里伫立良久,想象着此刻自己就站在巴黎的街道上,被迷人的法语发音围绕着,在蜿蜒曲折的小巷里迷失了方向,抬起头又看见了无数艺术家笔下戴着桂冠的埃菲尔铁塔。
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的世界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宽广。
“从小我就是一个父母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听着他们的安排升学、找工作、相亲,按部就班地生活。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我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那感觉就像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她的眼睛亮亮的,像落入了星子一般。
从前法国巴黎对她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但从那以后她开始努力地靠近它。
她学习法语,看法国电影,了解法国的一切,以至于她有法国留学背景的同事都惊讶于她对法国的认识。
后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法国男人,他们志趣相投,一起聊书、聊电影,谈论各自的生活。
有一次,他告诉她:“科西嘉岛的星空很美,我希望能与你一同分享。”那天她坐在公司的小隔间里,身边的人仍在反反复复地争论,自顾自地努力呈现自己的想法,却又不愿意停下来倾听,最后精疲力竭地发现彼此都从未抵达过对方的灵魂。而她从落地窗向外望去,看着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喧嚣不息,车灯亮起如一片燃烧的火海。她想象着自己是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望着日落汹涌、晚霞燎烈,转过身她看到那位法国男子,他们之间是轻轻回旋的风声和温暖的阳光。尽管仍在生活的漩涡中身不由己地挣扎着,她还是感觉自己抬起头看见了月亮。
“后来呢?”我不无好奇地追问道。
“后来啊……”她叹了一口气,无奈地笑了笑。“要知道生活不如我们想象的自由。”
一年前她的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住进医院的父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告诉她希望能在去世前看到女儿幸福地出嫁。
她看着病床上白发苍苍的父亲,终于妥协,和家里很满意的现任男友结了婚。
披上白纱的时候她忽然看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上漫天飞舞的梧桐叶,不禁红了眼眶。
后来父亲去世,她回归有轨电车般的生活,工作依旧繁重,还有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她也不再幻想在巴黎左岸开一家小小的书店。
直到不久前因工作需要她终于有机会在巴黎短暂停留。她站在蒙马特高地下,看着游人如织,喧嚣如潮水般翻涌不息,困住这座无助的城市。
人潮汹涌,过去的,经历的,熟悉的,一切的一切都如同一场盛大的幻象。
她想,这就是她心心念念的巴黎吗。
她觉得自己就像伍迪·艾伦镜头下的男主人公,感叹着巴黎再不复当年模样,被无尽的游客叨扰,那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此留下的痕迹都化作最好的旅游宣传素材。
如同电影中的角色们感叹着过去更好,她想她热爱的那一席“流动的盛宴”也许从来只是她用想象构筑的乌托邦,是她的梦想得以心安理得栖息的精神家园,而与现实中的巴黎毫无瓜葛。
“我想我只是被一触即碎的‘另一种生活’蛊惑。之前我喜欢说巴黎是我的精神故乡。其实没有什么精神故乡,只有未曾企及的乌托邦。”她望向窗外,阳光落在她海藻般漆黑浓密的头发上,“就像一场很长很长的美梦,在我从飞机上下来,站在巴黎的土地上的时候,终于完全清醒了。”
卡夫卡说,掉下去不可怕,可怕的是悬在半空。我想,就像认清了自己随波逐流的现状却无力反抗现实的人,只能在生活的虚空中苦恼着,叹息着。
这个想法就像一阵轻微的苦涩,掉落在我们两人之间。
“也许这样的乌托邦就是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鸿沟的桥梁,它相对于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存在。就像桃花源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刘子骥寻而未果的理想之地,正是不可企及成就了乌托邦。”我试探着说。
“可是我时常感觉,这更像现实失意者对于挫败的自我慰藉,就连感喟也是单薄可怜的。”她苦笑。
我便跟她说起我一个曾经的同学。
时间把这个飞扬跋扈的少年打磨成了没有棱角的笨拙模样,他在事业上一直很不如意,当年打游戏连战连胜的他却在生活的游戏规则里受缚,无法施展才华。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山了。我有些惊讶,虽然知道他一直很喜欢海明威,但还是觉得这个决定太过冒险。他却说,只是想为生活找到一个意义。
他回来后,我问他有什么收获。他告诉我他在山顶没有看到豹子,也没有感受到什么强烈的情感,只是觉得异常平静,涟漪一般在胸口慢慢漾开。下山的路上甚至会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那些平凡的日子没有在这个风雪之晨被凛冽的疾风吹得离他而去,而像浪潮卷起的流沙,一遍遍翻涌又退却,最后积淀成他现在的模样。
人总是趋光的,因为光总是被抽象成希望、方向和积极向上。
因而乌托邦总在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肯定中维持着平衡,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而绝对理想的生活方式从来就不存在。
她笑着说:“既然如此,要是人类没有那么多追求和欲望,不就能少一些痛苦了?”
“其实我很喜欢人身上这种层出不穷的欲望,就像我喜欢一本书,如果我能够买到它,就会很满足,即使我将来还想要更多的书。”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所以那应该是一个人心里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精神角落。因为不曾企及,也就从未失去。”
离开书店后,我带着那张《午夜巴黎》的碟片走在回家的路上,已是华灯初上,暮色像即将退潮的深海,汹涌而深邃,沉静而安稳。我站在立交桥的人行道上向下望去。不远处就是我年幼时爷爷奶奶居住的小区,如今那里曾经的平房早已散佚在时过境迁的灰烬里。我时常怀念小时候去爷爷奶奶家玩时看到的那种低矮古老的房子,仿佛一砖一瓦都嵌着厚重的往事,我也时常希望能够体验住在老房子里的那种澄澈明亮的日子,一切都很慢,仿佛什么都从长计议,是细水长流的安定和温暖,包裹着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阳光明媚的时候,爷爷奶奶会把棉被和衣服挂出来晒太阳,爬山虎在外墙壁上蜿蜒交错,一年四季都蛮横地绿着,不由分说地在阳光下伸展着纤细的卷须,一寸寸都在丈量生命的长度。小路两旁的木樨萦绕着甜腻温软的清香,隔壁的老婆婆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还有不知谁家养的猫常常在小区里灵活地蹿上蹿下。
而今,只有毫无特色的钢铁森林耀武扬威地占领一座又一座城市,城市扩张的爪牙吞噬了那些可爱的老房子,却孕育出一栋栋千篇一律的商品房。人际关系也像施工队垒起的沙砾一样,没有稳固的立足点,却总能听见响亮刺耳的脚步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愈加凸显,有时生活在同一层楼的人们也是彼此陌生。
生命的荒芜和惆怅,一直徘徊在那里,作为生活的大背景存在着。我们一直在以或轻浮或深沉的方式,对抗日常生活那无法消释的乏味的成分。不幸的是,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定居也好,换一份出乎旁人意料的工作也好,坠入爱河又脱身出来也好,不论人们如何去冒险,现实的镜子只是从不同角度映现同一张空虚、得不到满足的脸,像打开探照灯照见内心的茫然无措。
①优:腰痛、腿痛均消失,腰部运动无限制,可正常生活及工作。②良:腰痛、腿痛显著改善,腰部运动无限制,可进行轻微的工作。③可:腰痛、腿痛有所好转,但不能独立活动及工作。④差:腰痛、腿痛、运动功能等无改善,或加重。
我在混合着伤感和平静的失望中,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向往着那未曾企及的乌托邦。
不论世界美好与否,那些不切实际又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们总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理由。
这时,我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揪我的裤腿,我低下头,瞥见一个有点眼熟的身影。
我蹲下来好跟那双墨绿色的眼睛对视,“你也在这里呀,你的主人呢?”它“喵”了一声,仍然趴在我的腿边不走。
我不禁微笑起来。“那我们一起回家吧。”我抱起这只小猫,再次踏上了回家的路。
倘若再次遇见
我并不是一个能持之以恒的人,这在写文章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文章常常写到一半就倦于继续,那些文字便在时光中辗转,渐渐蒙尘。时常怀疑那些蘸满情绪的笔墨是否能构筑出一个平行的世界。而那些被遗忘在字里行间的角色,是否在另一个地方,有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如果,能再次与他们相遇。
他比烟花寂寞
他是我倾注了最多感情的角色。他演绎过很多人的人生,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我笔下的他已经三十四岁,人们说他的演技经过时间的沉淀日渐娴熟,他却觉得自己早已失去了刚开始接触演戏时的那份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投入。纵使他熟背过那么多台词,他却始终觉得他是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依着内心的感觉,如同在黑暗中行走。他三十四岁,人们觉得他风华正茂,他却觉得自己已经垂垂老去。
我一直想为他安排一场告别影坛的作品,却总也找不到方向。我第一次觉得,即使是我笔下的人物,我也无法完全理解。从他被我写出来的那一刻起,我就有鲜明的感觉——他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或者我的影子,他是那样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渴望去解读。我要做的不是创造而是记录。
我如果与他再次相遇,也许是在英国宁静的乡村。
他架着画架,认真地调色,我坐在他旁边,望着澄空上漂浮的云,保持着默契的沉默。作为一个演员,纵使把别人的故事演绎得精彩绝伦,也不一定能与自己的生活和解。
有家的波西米亚人
如果我能与那个行者再次相遇。
当我书写他的故事时,绿皮火车已经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在我的笔下,他乘坐最后一列绿皮火车,思念着一个人,从南到北。他一直在路上,了无牵挂,但在一次旅途中,他遇到了令他动心的人。可是按照故事发展,他应该和朝思暮想的人相见时,我却犹豫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为所爱之人停留下来。在年轻的时候,总有一些词汇让我们满心憧憬,比如流浪,比如在路上,比如吉普赛人。到后来,我们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放逐自己,不愿困于琐碎的生活小事,还是想要逃避日渐锋利的回忆。
如今,绿皮火车似乎又要回来了。
如果我再次遇见他,也许乘坐着经年后第一列绿皮火车,我问他是否还在思念,他并不回答,只是安静地望着窗外。耳机里的歌一遍遍循环。“是谁来自山川与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我可以选择将故事停止在这里,却不能使人生暂停在某一阶段。只是没有归宿,行走亦是荒凉。
只身打马过草原
尽管我相信笔下的人物具有自己的生命力,但毕竟都是我思想或心境的映射。
如果我能与藏匿在文字中的自己相遇。
那会在我垂暮之年,或是我决意不再拿起笔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她对我笑着,那复杂的笑容里有嘲讽、有怜悯,还有隐秘的支持。我与她相对而立,世界仿佛离我远去,我可以对它做鬼脸、吐口水或是给它一个耳光——怎样都行。在我的笔下,我可以是郁郁不得志的画家,可以是春风得意的诗人,可以是与琴为友的歌者。但是脱离了文字,我也不过是一个将一个又一个白日梦付诸笔端的平庸之辈。究竟哪一个世界更美好,文字中的世界,还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文字外的世界,深爱音乐的人还在发传单,迷恋绘画的人还在送快递。文字构筑的世界实现着梦想,但它并不真实。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