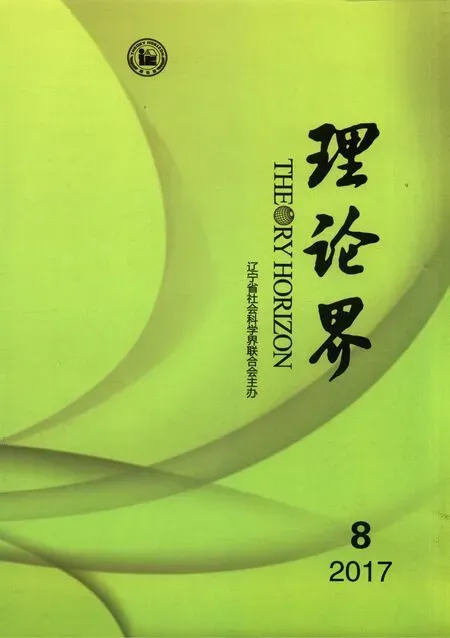皮尔斯指示符号内部次类划分问题探析
吕军伟
皮尔斯指示符号内部次类划分问题探析
吕军伟
皮尔斯于19世纪末首次提出指示符号概念,但未对该类符号之内部情况做深入探究。指示是人类认知及交际的核心方式之一,因无须反映所指对象之本质特征,指示符号极具语境依赖性及经济性。根据符号与对象间之关系,皮氏所谓“指示符号”可进一步分为:实物指示、实物——语言指示及语言指示,从实物指示到语言指示再到语言指称存在一个单向性符号连续统,该连续统体现出人类认知能力及意指方式之演化过程。
指示符号;次类划分;单向性;连续统
一、指示现象及指示符号
指示现象(Deixis)及其相关符号在世界各语言中普遍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Stoics)便已对指示现象及指示符号有所关注,该学派学者克吕西普(Chrysippus)以“与我们说出‘我’时相伴的指示”为例,认为:指示(Deixis),或指向所指对象(即我们自己),或是与说“我”者头部方向相伴的手势,实为一种肢体行为,该行为在说出含有代词的句子的同时,指出所指对象。〔13〕在英语中,与指示现象相关同为“指示”义的词语不止一个,如:index、indicate、denote、designate、demonstrate及deixis等等,且上述词语在相关研究中同被用以表示“指示”义,且难以分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术语混乱。
究竟何为“指示”?从“指示(Deixis)”一词之来源看,该词始自古希腊语,其基本意为“指(Pointing或Indicating)”。〔7〕〔8〕由此推知,所谓“指示”是一种意指行为,究其过程则主要涉及指示发出者(人),指示符号(指示行为的承载体),指示对象(物理对象),指示意图及其接收者,换言之,指示者根据其指示意图向交际对象指出其所指对象,不管指人、指物、指时间、指空间等等,虽然颇具差异,但都须基于或部分基于上述基本要素,而至于指示信息获取的管道,则兼有视觉和听觉。皮尔斯在对指示符号的论述中指出:〔2〕与指示现象相关的符号皆因其对象而成为符号,但二者之性质无任何联系,指示符号与对象间存在自然物理联系或动力学(Dynamical,包括空间)联系,二者形成有机对(Organic pair),且与指示符号与作为符号为之服务的那个人的感觉、记忆产生联系,指示符号在联系确立之后仅仅起标注(Remarking)该对象的作用。鉴于此,皮尔斯将日规或钟、风信标,手指、铅垂、灯塔、航标、呼喊、叫卖声、北极星、敲门声、名字、专有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这”、“那”)、关系代词(“谁”、“哪一个”等)、物主代词、全称选择词(如“任何人、所有、无、不论”等)、时间副词、方位副词、序数词(“第一、最后一个”等),以及介词或介词短语(如“在……左(右)边”等)等等,凡是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任何东西都作为指示符号。
皮氏之论述初步揭示指示类符号能够独立成类的本质特征,但指示符号如何确定其所指对象?与其对象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指示符号内部又存在怎样的差异性?语言介入的指示有何特性等等诸多问题须基于现象做深层次分析。
二、皮尔斯指示类符号内部次类划分
皮尔斯之指示符号类内部情况较为复杂,对于指示符号之意指关系,赵毅衡先生曾指出,〔10〕此类符号与对象之所以能相互提示,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从而让接受者感知符号即能够想到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从皮氏对指示符号的列举中可明显看出其将语言与非语言符号混为一谈,而二者虽有共性,但又存在本质区别,且异远大于同,故此有必要深入细究符号与其对象间的不同关系,进而对该类符号做进一步区分。
1.实物指示符
实物指示符号与其对象间存在明确的动力学或因果关系,故此即便没有语言相伴亦可完成示意过程,实现传达意图的目的,充当符号功能的是非语言的实物,皮氏所列举的“日规或钟、风信标,手指、铅垂、灯塔、航标、北极星、敲门声”等皆属于实物指示。在英文中“食指”被称为:“Index Finger”,即用于指示的手指。从“指示”之基本定义可见:指示实为一种行为,与人体的姿势或动作有关(如头部姿势、眼神、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等),最为典型的便是:以手指,示物,无需语言相伴便可借助于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完成表达意图的行为。
视觉和听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知世界、获取信息的渠道。纯实物指示传达意图的感官信道主要是视觉。因此,类指示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相互依存且关系简明,实物指示依赖于能够满足交际之视觉需要的光线,且对指示之各构成要素之在场性有较高的要求,除发挥符号功能的指示实物外,指示者、指示对象、接收者通常皆须在场,否则指示意图便无法实现。若视觉通道受阻,即便上述指示要素全部在场,单单依靠纯实物指示,也不可能完成指示达意的过程(当然可以通过交际双方共同的触觉、味觉、嗅觉经历,实现交际,如拿指示对象给对方尝试,但这已经不属于指示交际的范畴),另外对于不可视的抽象概念,如果没有其他辅助因素的介入,也很难通过纯实物指示得以传达。
因而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限制,实物指示并不利于交流中信息的传递及意图的表达,这也迫使实物指示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通过补偿实现交际。而在此情况下,作为人类另一条最为主要的信息获取管道——听觉,便不可避免地作为补偿因素被利用起来。这一转变,也便实现了听觉及声音的介入。
2.实物——语言指示符
通常而言,纯实物指示在人们的日常交际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明显,而更为普遍的是通过视——听觉来完成指示表意行为。从视觉到视——听觉,信息获取管道的拓展为指示意图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这也使得我们需要将眼光转向以视——听觉为主的:实物-语言指示。
所谓“实物——语言指示”是指信息获取是以视觉为主听觉为辅,在指示达意过程中,以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实物为主,与此同时有语言辅以明确或醒示指示意图的行为,此类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多存在一定的因果或邻接关系,或动力学(包括空间)联系,皮氏所列举的“指示代词(英语‘this/that’,汉语‘这/那’)”以及人称代词(英语“I/YOU”,汉语“我/你”)、方所词(英语here/there)、时间名词(英语“now”,汉语“现在”)等均属此类,实物——语言指示最为典型且重要的功能是:在日常交际中形成以指示主体为中心,以“IHere-Now”为原点构成指示场坐标系统,〔3〕由此来确立指示中心,包括言说主体,言说时位及言说方位,进而以指示中心为参照确立所指对象。实物——语言指示在日常交际中极为常见且使用频率极高,比如我们在通过手势等肢体动作或面部表情向交际对方指明某一对象时,为了表意更为明确或引起对方更多注意,通常会在指示行为产生的同时,伴随有“这、那”等代词抑或“嗯、喏、嘿、嗨”等拟声词。与纯实物指示相比,实物——语言指示也同样需要有能够满足交际之视觉需要的光线,且同样要求指示者、指示符号、指示对象、传达对象四要素皆须在场,否则指示意图也同样无法实现。但所不同的是:基于听觉的语言虽然仅仅作为辅助手段介入,但使得指示行为表达意图更为明晰。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纯实物指示在不同场合中其表意有效性会收受诸多因素的限制,也并非纯实物指示辅以简单语词便可以在所有场合均可以正确表达指示意图,尤其是在指示对象众多且彼此区别特征不明显的情况下,例如指示者欲通过指示向交际对方指明穿着相同制服的一群陌生人中的某个人,此时,单单依靠手势以及与之相伴的“那、他、喏”等词语,对方依旧不会明白其到底想指明的是哪一个,此时,如若欲实现指示意图,则会通过描写摹状等途径辅以更多的语言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本处于辅助地位的听觉信道以及语言信息之作用,则必然被凸显,以致必不可少。
3.语言指示符
对于实物指示与语言指示间的关系问题,从发生学及儿童个体语言行为发展角度看,儿童在习得语言之前便已经可以借助简单实物指示(如手势、眼神、表情等)表达其意图,但却分不清近远指“这/那”以及基本人称指示“我/你/TA”,由此可以推知:实物指示先于语言指示。指示表意行为是否可以脱离实物借助于语言独立完成?根据日常经验,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交际双方必须已经习得一种共同的语言且在具体交际中有共知的信息背景,例如:
A:今天来的 这/那 个人是个骗子。
B:是的,他 说的 那些 东西压根就不存在。
如若满足上述条件,纯语言指示便可以实现。所谓的纯语言指示,指的是:在指示之对象实物不在场的情况下,依靠交际双方的共知背景信息,仅仅借助于语言来实现指示意图传达的行为,此类符号与其对象间关系较为复杂,每种语言都有一套划分及标记指示场的符号,并构成一个指示符号系统,其在划分、标记及形式化指示场的同时,构建起一个相对区别的关系网络,〔11〕并以此区分场内在场及场外缺场对象。指示现象所涉及的符号往往数量有限,但分工明确,具有极强系统性,这些符号与其对象间的关系则通常是以指示中心(话语主体、时位及方所等)为参照,根据所指对象与指示中心之相对关系得以确立,具有一定的理据性和主观性。皮氏所列举的“(第三)人称代词(如英语‘He/She/It’,汉语‘TA’)、关系代词(‘谁、哪一个’等)、物主代词、全称选择词、时间副词、方位副词、序数词以及介词或介词短语等属于该类。与纯实物指示相比,纯语言指示除了指示符号由实物变为纯语言外,信息获取管道已完全依赖于听觉,先前光线及视觉之限制,也随之消失,即便在漆黑的夜晚单单借助于语言也可以完成指示交际行为。这也使得指示表意之范围得以扩展,尤其是指示对象的扩展,单纯的实物指示如欲以抽象的事物、概念或思想等而言作为指示对象,则必须基于先前所做的描述及铺垫,也就是在说,指示发出者事先需要对所指对象做以描述,使对方在心理上对所指对象有一个基本认识,亦即形成共同信息背景。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实物指示之必备条件之一的在场性,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纯实物指示要求指示发出者、指示符号、指示对象、指示接收者五要素皆必须在场,而在场性对纯语言指示约束则相对降低,指示对象实物可以不在场,但作为补偿,交际双方需对所指对象有共同的背景信息,其中便包括对指示对象之相关信息的心理唤起,只是与一般心理概念不同,所唤起的仅仅是不反映对象之本质特征的时、空存在信息,因此,语言指示符号表意具有极强的语境依赖性。
三、从实物指示到语言指示再到语言指称——指示符号系统内部连续统分析
对于指示现象而言,从最基本的以视觉为主的实物指示到仅仅依赖于听觉的纯语言指示,构成了整个指示系统的两极,而在交际使用中,无论是哪一极,单纯出现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最为常见的则是介于两极之间的实物——语言指示,因为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使得单单依赖于一种途径不能准确或迅速有效地实现指示意图,多种途径和资源的结合,往往能够彼此互补,大大提高指示表意的效率及准确性,在标记所指对象的同时,将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从前文皮尔斯对指示符号的界定和研究可以看出,其所关注的是广义指示符号,即包括实物指示符号和语言指示符号,或者说语言指示符号和非语言指示符号。实物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皮尔斯之探讨并非以语言符号为范本,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其对指示符号之本质的把握侧重于实物指示符号,但同时皮氏亦觉察出实物指示符号与语言指示符号间存在差异。皮尔斯之后,其学生莫里斯(C.W.Morris)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基础上,从一般符号学的角度进一步对符号进行了区分,莫里斯(2009)认为:〔14〕关于一个对象的符号,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可以仅仅使指号的解释者注意到这个对象,另一端却可以在这个对象本身不在当前的时候使解释者考虑到这个对象的所有特性。而在这两极间存在着一个可能的符号连续统(Continuum),在该连续统中关于每一个对象或情况的各种程度的符号过程都可以表现出来;而且关于“一个符号的所指谓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实际等同于“究竟对象或情况的什么特性仅因符号载体物的出现真正被考虑到了”这一问题。〔4〕
从实物指示到语言指示中间有诸多过度或连续状态,指示系统的两极与语言系统表示事物的两种基本方式:指示和指称,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随着表达内容的复杂化和抽象化,借助于实物表意的局限性势必凸显,由此促生语言系统生成和介入,在此实物——语言指示阶段,语言成分的出现仅处于辅助地位,直至人类在认知层面具备抽取和把握事物或对象之本质特征能力后,所谓关于对象的概念才逐渐产生,语言指称这一更为高级的表意手段才能产生,正因可以把握对象之本质特征,借助于对象之概念及语言便可在对象不出现的情况下,实现表意和交际过程。因此,符号连续统体现出人类在认知和表达手段上的演化过程:
在皮氏符号学体系中,专用名词也被划归到指示符号的行列,从上表可见,这一做法并非无理之举,专有名词与指示符号间存在着诸多共性。从实物指示符号到通称符号,实现了

从依赖时空的在场到不在场,从受限到无限,从对认知对象之概念从无到本质抽取,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过程。在该过程中,无论是认知对象的量问题,还是其质问题,都在发生变化,而质的成功抽取最终实现了认识事物过程中的范畴化。上表中亦蕴含着一种单向性,即从实物指示到通称存在单向依存关系。实物指示与在场性密不可分,而随着在场性的减弱及消失,表示事物之方式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强,就单个符号而言,对语境的依赖性则逐渐减弱。指示符号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在场性的制约,而指称符号则可以做到。正是与在场时空因素的密不可分,指示符号在言语交际中才可以在不必抽取认知对象之本质并形成概念的情况下,指示欲指对象,进而完成交际。这也恰是指示符号极具语境依赖性之原因所在。
此外,正如语言世界是物理世界的反映,语言世界的在场性同样是物理世界在场性的折射,所不同的是,语言世界的在场性并非要求作为指示对象的实际物体在场,而是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单位(如词语、句子、语段等)须与指示符号在一定范围内同现,以使得指示符号通过回指或照应(Anaphora)等手段能够寻找并确定其所指对象。
四、余论
指示是人类核心表意方式之一,典型指示过程通常包括五个要素:指示发出者、指示符号、指示对象、指示意图及其接收者。从指示发出者产生指示意图到选择指示方式发出指示行为,到指示接收者看到指示发出者的指示行为借助于在场诸因素理解其指示意图,存在一个交流的过程。指示发出者及接收者是能够思考具有思想的人;指示对象可以是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具有不同维度的一切;指示符号作为指示行为承载体,无论是实物还是语言,其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指示意图的产生及指示接收者对指示意图进行分析识别则是交际双方的个人心理行为;指示作为一种表意行为,其从产生到完成所经历的过程必然经历一个时间跨度,即本身具有矢量。指示现象必然涉及四各方面,即人物、事物、(人物或事物所处的)空间和时间,此四方面是指示系统形成的物质基础。语言指示符号介于实物指示和语言指称两种方式之间,在意指方式上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之研究目前尚不够明朗,而对于汉语指示现象所涉及的语言符号问题(如指示系统边界、层级及内部小类等),则有待基于汉语事实做进一步系统性探究。
[1]孙蕾著.指示语语义特性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
[2]Peirce,C.S.ed.by J.Buchler.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M].N ew Y ork:D over Publications,1955:108、101-102、107-114.
[3]K arl Bühler,Trans. by Donald Fraser Goodwin.Theory of language: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M].A msterdam:J.Benjamins Pub.Co.,1934/1990:93-95、117-119.
[4]C.W.M orris.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4-5.
[5]H usserl E.Logical Investigations(V ol.1)[M].London:Routledge & Kegan,1970:269.
[6][意]乌蒙勃托·艾柯著.符号学理论[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7]Lyons J.Semantics,V ol.2[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636.
[8]Levinson S.C.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54.
[9]Thomas A.Sebeok,Signs:A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Second Edition)[M].Toronto:Universit of Toronto Press,2001.
[10]赵毅衡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82.
[11]吕军伟.语言符号模型的发展与语言指示符号问题研究[J].北方论丛,2012(4):62.
[12]丁尔苏.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20.
[13]Brad Inw ood.The Stoics[M].Cambridge: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2003:89.
[14][美]C.W.莫里斯著.莫里斯文选[M].涂纪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1.
Study on the Subordinate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of Peirce's Indexical Signs
Lv Junwei
Theconceptof “index”wasfirstputforwardbyCharlesSandersPeirceattheend ofthenineteenthcentury,butPeircedidnotmakefurtherexplorations.Indexisoneofcore methodsofhumancognitionandcommunication.Asthereisnoneedtoreflecttheessential featuresoftheobject,indexicalsignsarehighlycontext-dependentandeconomic.Accordingto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signanditsobject,indexicalsignscanbefurtherdividedintothree types:objectindex,object-languageindexanddeixis.Thereisaunidirectionalcontinuumfromobject indextoobject-languageindextodeixis,whichreflectstheevolutionprocessofhumancognitive abilitiesandideographicmeans.
indexical signs,subordinate classification,unidirectionality,continuum
H0
A
1003-6547(2017)08-0103-06
指示是人类认知及交际的基本手段之一,其无须形成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抽象概念,便可以完成交流,相对于指称等其他意指手段而言,指示表意更为经济实用。儿童在习得语言之前亦会通过手指指示来表达其基本意图。语言系统中指称词语与指示词语之区分先于名词、动词两个基本词类的区分,且该区分在不同语言中具有相当普遍性。〔1〕“指示符号(Index)”概念的正式提出发端于19世纪末的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S.Peirce),其将凡能引人注意的任何东西皆纳入“指示符号”类,〔2〕致使指示符号外延宽泛,但因皮氏旨在阐述其逻辑学思想,对于指示符号内部情况,如符号次类划分、符号层级、次类关系、语言指示符号与非语言指示符号之差异等等诸多问题,并未过多关注,且在其指示符号阐述过程中多处前后矛盾。〔2〕
皮氏之后虽不乏学者谈及指示符号,如比勒(Bühler K.)(1934)、〔3〕莫里斯(Morris C.W.)(1938)、〔4〕胡塞尔(Husserl E.)(1970)、〔5〕艾柯(Eco U.)(1976)、〔6〕莱昂斯(Lyons J.)(1977)、〔7〕列文森(Levinson S.C.)(1983)、〔8〕西比奥克(Sebeok T.A.)(2001)、〔9〕孙蕾(2002)、〔1〕赵毅衡(2011)〔10〕及吕军伟(2012)〔11〕等等,但整体而言,学界对指示符号的认识仅停留于基本概念,〔12〕对于上述问题依旧缺乏系统的深入探析。鉴于此,本文拟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基础上,尝试对皮尔斯所谓的指示类符号内部情况做进一步分析。
本文系广西教育厅2015年度高校科研项目“基于指示视角的汉、壮语代词体系比较研究”(K Y 2015Y B017)、广西大学2014年度科研基金项目“基于指示视角的汉语代词体系研究”(X G S1405)、广西大学2015年度青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语言指示符号系统性及意指特性研究”(X BS16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吕军伟,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白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