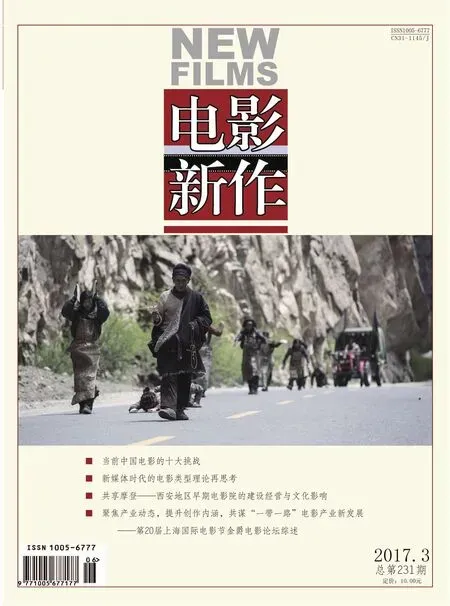《闪光少女》:类型范式的复合跃进与代际冲突的价值平衡
程 波
《闪光少女》:类型范式的复合跃进与代际冲突的价值平衡
程 波
《闪光少女》题材新颖,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产电影在“二次元”青春少女音乐喜剧这种复合类型上的空白。电影的剧作扎实而且均衡,导演和表演呈现也让人耳目一新,其不仅开拓出类型范式“复合跃进”的态势,把青春与喜剧,青春与音乐,音乐与喜剧有机地综合为了一个整体,而且自觉地采取了在代际冲突中保持价值平衡的策略,将年轻人前沿的价值观理解为一种有价值的理想。在全球化时代彰显中华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电影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呈现了传统文化当代化、年轻化的可能性,也把主流价值观对青年成长的规训更多地以相互理解的方式“愉快地”表达了出来。
类型范式 二次元 青春片 代际冲突 价值平衡 传统文化
《闪光少女》的出现,给人们的一个直观感受可能就是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前些年国产青春片在的某种范式:怀旧,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的中年人(特别是中年男人)带着中庸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追忆青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妳》《将爱情进行到底》《中国合伙人》《少年派》《匆匆那年》等都是在追忆青春,在怀旧的消费性里,青春的疼痛、喜悦,甚至打架、堕胎、离别这些戏剧性的标配都显得有些隔靴搔痒。李玉的《万物生长》曾经力图打破这种范式,但客观上似乎更多的只是在通过一种黑色戏谑的方式表达出“破”的一面,并未建构出一个更具有“观众缘”和“当下感”的“立”的一面。
《闪光少女》的编剧鲍鲸鲸是当年票房和口碑双赢的影片《失恋33天》的编剧,其女性视角及对年轻人的当下生活独特的切入角度在《闪光少女》里再一次得到了体现。不仅如此,影片在故事和影像层面类型感十足,在青春片的基础上综合了喜剧、以ACG(动画、漫画、游戏)为载体的二次元文化、少女电影、音乐片等类型因素。如果说类型电影的发展规律往往是“范式跃进”(也就是说某个经典电影创造了某种类型电影的经典范式,然后在众多模仿者和反叛者之后,直到产生一个新的经典电影,承载了一个带有明显创新和跃进式的新范式,如此延续。)式的,那么《闪光少女》在国产青春片的类型里,就是通过“复合跃进”而成的新范式。电影的剧作扎实而且均衡,导演和表演呈现也让人耳目一新,其不仅把青春与喜剧、青春与音乐、音乐与喜剧、传统文化与二次元文化有机地综合为了一个整体,而且自觉地采取了在代际冲突中保持价值平衡的策略,在主题层面将年轻人前沿的价值观理解为是一种有价值的理想。青年成长以小反抗,大认同,象征性“破”和实体性“立”的方式达到最终的价值平衡,进而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呈现了传统文化当代化、年轻化的可能性,也把主流价值观对青年成长的规训更多地以相互理解的方式“愉快地”表达了出来。

图1.《闪光少女》
一,类型范式的复合跃进
当青春的主体从身体里住着中产阶级的中年男人的男孩,变成一个活在当下就是她自己的少女,青春闪耀的光似乎才用对了光源。《闪光少女》里的女主角陈惊是一所音乐学院附中学扬琴的学生,她的男闺蜜油渣是打民乐大鼓的。陈惊喜欢上学校里的钢琴王子,想向他表白,却因自己学习民乐而被奚落,学钢琴的帅师哥甚至压根都不知道什么是扬琴。她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注意她,也为了争口气,决定组织一支民乐队。开始没有人愿意参加,直到她和油渣在学校里找到了四个住在一个宿舍的“二次元”少女,特别是一个网名叫“千指大人”的古筝达人。乐队经过开始阶段的不和谐,以在动漫展的演出为拐点小试牛刀,竟然在网上火了起来。陈惊以为这次师哥就会高看她一眼,没想到再次表白却带来更大失败和羞辱。可是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原本作为爱情工具的民乐队,竟然在失败的挫折中转变成了理想和励志的目的。民乐从“工具”到“目的”的转变,也正是这群年轻人成长的表征。经过了与西洋乐学生们意气之争的斗琴、经过了与校方不合理的权力规训的抗争,化解了各种矛盾,闪光少女和她的二次元民乐伙伴们一起上演了一场充满青春热血的华彩乐章,陈惊也发现油渣这个一直在她身边的人才是真正欣赏和喜欢她的人。
这是当下在场、不追忆怀旧的青春,创作者和制片方在宣传口径上称之为“反类型青春片”,也应该主要是出于这一点。所谓“追忆怀旧”指的是青春的缅怀、青春的回忆,站在普遍主流人群立场上的,是从过往者和中年人的视角去回顾、追忆曾经的青春。所谓“当下在场”,是指用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叙事方式来突显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青春。电影《闪光少女》直接就采取的是用一种客观视角顺叙的方式,没有“隐藏叙事人”,也没有现实和回忆中跳进跳出的“开关”。青春、爱情的表达透明而又超脱,青春不再是一味的苦涩、悸动和悔恨,而是充满了自然幽默、励志阳光的气息。
不过很明显,《闪光少女》依然有着明显的青春片的类型特征:女主角和男闺蜜的核心人物搭配,主角与乐队群像的人物设计,青春的励志与成长,校园热血与时尚文化,从矛盾到和解再到大团圆的结局,这些都是青春片的元素。只是不怀旧了之后,这些元素本身的价值会在现在进行时的语境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而且,“二次元”文化的加入,也使得青春具有更年轻更接地气的感觉。青春不仅是二次元,还有力图理解二次元但又不完全沉入的2.5次元,以及二次元眼中的三次元世界。这种差异虽然明显,但似乎在青春里又有共存共生的可能性,而且在矛盾和共存中,可以开拓出一大片讲述青春的新领域。这一文化元素的加入,也使得青春片类型范式有了一块新鲜坚实的向前跃进的踏脚石。
《闪光少女》闪耀的是不仅是青春之光,还有喜剧和音乐之光。新世纪以来,大陆喜剧电影的主要范式是“底层喜剧”,虽然这其中的发展轨迹和个体差异比较复杂,但往往是以消费底层尴尬甚至苦难,进而或产生出疯狂色彩(疯狂系列喜剧)、或建构黑色意味(《追凶者也》)、或凸显悲喜剧之美(《钢的琴》)为主要途径。青春校园喜剧成功的尝试在国内的大银幕上并不多见(有些是通过网络大电影的载体在进行),而在美国和日本,麻辣而又热血的高校往往是青春的舞台。《闪光少女》的主人公陈惊和油渣,就是校园里的一堆麻辣活宝,他们一出场干的事听着就有创意还可乐:在琴房用饮水机的储水槽吃火锅,拿烫发夹子烤鸡翅。陈惊努力争取了一个翻谱员的工作就为能坐在钢琴王子旁边,然后伺机表白。当然,不分时间场合向错误的对象的表白失败了,表白中的性别和环境的错位,显得很有喜剧效果。原本来自三次元的陈惊和油渣在与二次元少女四人组的交往中,也在相互奇观化的身份认同的错位中呈现了很多笑料,一个“手办”(动漫人偶)的梗就显得新鲜而且有效。民乐与西洋乐学生之间的相互争斗,乃至在陈奕迅饰演的视察领导的眼皮子底下斗琴的片段,不仅热血而且麻辣。闫妮和耿乐客串陈惊的父母,勾勒了陈惊的前史,以及她与扬琴的缘分,这都是在嬉笑之中完成的。青春校园喜剧里的成长感,没有通过残酷青春或者黑色幽默来完成,而是把成长呈现为从“无害的反抗”和“无因的隔阂”发展成了“有趣的和解”的过程。
在《闪光少女》中,音乐作为类型元素同样十分重要。“歌舞青春”是一种有效的范式,但歌舞片的成本和文化语境的限制,使得歌舞片这一类型在大陆电影里很少有人去触及(《如果爱》已经过去多年了),更不用说在青春校园电影里全方位地采用歌舞片的类型元素了。但《闪光少女》去除舞蹈,保留音乐,将音乐放在几个不同但相关层次上进行处理,形成了独特的效果:在故事和主题层面,让民乐成为叙事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并让它贯穿二次元和三次元,与西洋乐形成对抗并最终走向和解。音乐的复合型与青年性,交织了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和爱情的纠葛形成了隐喻性的呼应。在叙事层面上,著名音乐人梁翘柏担任电影音乐制作人,不仅完成了《星星月亮》这首主题歌和全部配乐,也对作为叙事载体的乐队演出、斗琴、最终高潮演出进行了整体安排。在音乐的表演和制作层面,演员不亚于专业民乐手的排练和表演,符合音乐节奏的剪辑和精良的制作都很好地支撑了有关音乐的叙事和主题。
所以,三种主要类型元素的交织呈现为一种青春片类型范式“复合跃进”的态势,把青春与喜剧,青春与音乐,音乐与喜剧有机地综合为了一个极具创新性和吸引力的整体。
二,代际冲突的价值平衡
对青春片来说,常规性的主题总会涉及成长中的权力与规训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往往又集中体现为代际冲突,也就是说,作为父母、老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父辈”与作为孩子、学生、青年亚文化等非主流价值观的“下一代”之间的冲突。《闪光少女》并非作者感十足的艺术电影,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商业类型电影,但它处理这一冲突的方式既不是粉饰式的回避或迎合,也不是意气用事般的沉溺或对抗。在真实、贴切、有趣地表现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同时,也把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差异甚至对抗表现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对抗的结果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而是在一个更大的价值体系里,平衡了其中的冲突与隔阂,在青年成长中完成了价值观的和解,进而呈现出年轻人有个性、有承担、有梦想这种奋发有为的励志图景。这种有意识的价值平衡,也让电影有了更大的代际和文化的兼容性,甚至“少女一闪光,大叔也心仪”。

图2.《闪光少女》
在价值平衡的具体策略上,《闪光少女》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自觉意识和有效手段。
电影巧妙地引入了“二次元”这一对年轻人有影响力、相对时尚前沿的价值观的载体。影片的主人公陈惊并非是一个身处二次元或完全拥抱二次元的人,她提供了一种相对外部但可能跟普通观众更一致的视角,在走近的过程中从误解到了解二次元。配角里的四个二次元少女,她们形象和性格也有差异,但在迷恋ACG、宅、人际交往方式独特等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在外人乍一看来,有些古怪和奇观化,但随着陈惊的视角带着观众和她们走近,观众发现她们都是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坚持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似随性但却十分坚毅、善良与美好,这一点与普通人无异。据说制片方为了防止对二次元文化产生误解和扭曲,在剧本和人物设定阶段进行了调研,并且让二次元文化的“业内人士”把关。电影不是为了代言或批判某种文化或价值观的,但在《闪光少女》中,二次元文化(ACG的虚拟世界)与三次元文化(现实世界)发生了短暂的冲突后,融合成了兼容的平衡体,就像剧中六人组成的民乐队的名称一样——“2.5次元”。
《闪光少女》有一个价值观上的预设,即二次元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民乐)是如此天然而又没有矛盾地存在于这群少女身上。客观说,这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也契合了主流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以及年轻人成长在某一个向度的期望。电影对于这一前提没有交代其成因,其有效地为故事中的价值平衡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的意图却十分明显。讨论这样的预设是否具有社会基础,是否有先入为主之嫌似乎有些过于严肃和苛求了,采用这样的策略,给了电影中的“下一代”超越“父辈”期望的、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即便是良好的愿望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更何况,在电影里,当陈惊因为爱情表白失败,准备放弃乐队甚至民乐的时候,二次元少女们斥之为“叛徒”;学校校长屈服于市场,准备停止民乐招生的时候,是二次元少女们如《死亡诗社》里挽留老师的学生们一般,一个个站上桌子挽留传统文化的存在。在这样的设置里,年轻人的个体的理想与爱好,同作为“下一代”承担民族文化的传承统一在了一起。在斗琴维护民乐尊严、发掘使用“编钟”等桥段里,他们甚至做得比“父辈”还要好。所以,前面的预设具有这样的意味:“下一代”在玩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认真地在玩,并不像“父辈”想象甚至误解的那样玩物丧志或无所事事,他们在追求快乐、个性和理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也承担了传承的责任。也就是说,这样的“下一代”是可以让“父辈”们放心的。
围绕这一价值平衡的策略,电影还把一些具有呼应性的价值冲突也纳入到了视野之中,并让之趋于平衡。
首先是女性视角的问题。陈惊作为女孩主动表白,受挫后领悟到女性个体的独立性的重要;四个二次元少女和陈惊一起建立乐队,屡有挫折也没有放弃,女孩间的友谊越挫越深;油渣作为陈惊的男闺蜜、作为“千指大人”的崇拜者表面上围着女孩转,但实际上起到了两性关系中介和平衡的作用;校长作为男性长辈,被利益牵着鼻子走,学校的规训机制也有偏颇之处,人为制造了青年人的相互争斗和隔阂,直到女孩努力获得了更高的权力认可,进而获得了公平和追逐梦想的自由。闪光少女的视角既是古灵精怪的、又是轻松愉快的,还是感性温暖的,这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影片的基调。
其次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电影策略性地先将强势得宠且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西洋乐和少人问津有些老土的民乐对立起来,并将之与陈惊爱情纠葛中的权力关系对应起来,“钢琴王子”结合了两种强势,显得“面目可憎”。但实际上观众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对抗并不是正反两种价值的对抗,而是为了表达平等和尊重的重要性,为了走向和谐的铺垫。油渣在陈惊第二次表白失败后,为陈惊出头和“钢琴王子”发生了一次直接冲突,他说,你要出国继续学习钢琴,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伤害陈惊。扬琴和钢琴同宗,没有天然的尊卑之分,你出国学西洋乐,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音乐,只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音乐,当你对西方人这么解释来学西洋乐的理由时,不是更酷吗?这段表达,在电影中堪称华彩。共存与融合消解了假反派,也拆除了挡在民乐与西洋乐之间的那道铁门;斗琴看似在“斗”,但实际上展现了音乐本身魅力,连《野蜂飞舞》和《百鸟朝凤》之间还有个无缝对接的契合点;最后的高潮演出,民乐队也是在交响乐队尽释前嫌的帮助下完成的。
在当前中国电影增速放缓同时迎来产业升级契机的背景下,类型化发展策略也需要更具有深入性和本土化的能力。《闪光少女》没有大投资,也没有耀眼的明星,但因其综合创新的努力和对青春片范式“复合跃进”的推动,最终完成了品质上乘的作品,这极具启发意义。更进一步说,《闪光少女》在商业主流和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规训下,在电影内部以“小反抗,大认同”,以及象征性“破”和实体性“立”的方式最终达到了价值平衡,同时在电影外部努力做到消费性与作者性的平衡。这些方面,《闪光少女》因为十分难得,也应具有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样本价值。
本文系2017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及2017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项目成果。
程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