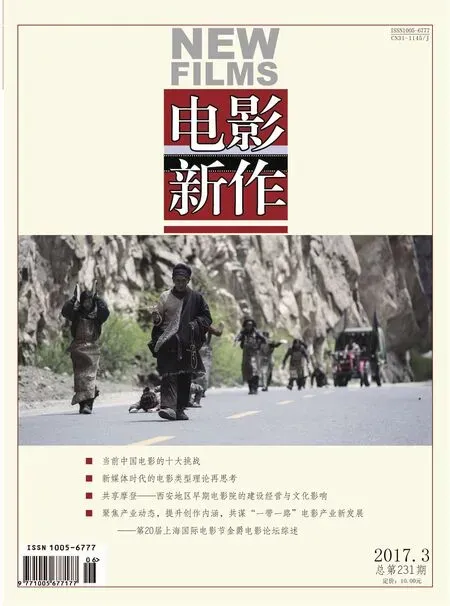跨界后的性别流动想象
——赛博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机械姬》
金 明
跨界后的性别流动想象
——赛博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机械姬》
金 明
《机械姬》是一部结构紧凑、布局精巧的小格局科幻电影,亦是一部赛博时代的女性寓言。这部电影的导演兼编剧亚历克斯·加兰在影片中深刻探讨了未来赛博时代“机器人”的“性别”议题,试图以电影镜像语言对“女性气质”“身体”“性别”等重要的概念进行“再赋义”。文章以赛博女性主义理论关怀电影文本,通过对影像中叙事文本与重要意象的阐释,窥探电影中“性别建设”想象。
《机械姬》 赛博女性主义 女性气质 身体 主体性科幻电影一直都离不开“性别叙事”,冰冷的机器一旦获得智能,势必会贴上“性别认知”的标签。科幻电影中所建构的新的“性别主体”会成为影片中重要的叙事驱动力。同时,科幻电影中对于“人机互动”“机器身体”等关于“未来性别”的思考与想象,以及科幻空间本身宏大且神秘的场域,对于现实场域中的性别研究极具建设性。2015年上映的《机械姬》(Ex Machina)是导演亚历克斯·加兰(Alex Garland)在赛博时代的“女性主义宣言”,电影以平静的影像语言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程序员卡莱布(Caleb)受公司老板纳森(Nathan)的邀请去其私家别墅进行为期一周的“度假”,事实上,这次“度假”是纳森有预谋的安排卡莱布参与其研发的机器人“艾娃”(Ava)的“图灵测试”。在此期间,机器人艾娃以自身的“女性气质”与“智慧”使卡莱布爱上自己,并且在卡莱布与京子(Kyoko)的帮助下,杀死了长久围困她的纳森,进入人类社会,获得自由。与《星球大战》(《Star Wars》)、《星际穿越》(《Interstellar》)等科幻奇观电影相比,《机械姬》所关注的不仅有未来科技AI(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生存焦虑”,同时,影片对于机器人“性别”的表达也是电影重要的输出隐喻。科幻电影中的性别想象与其隐含的性别政治,必须通过深入分析电影中的性别意象与叙事内容得以窥见。本文以赛博女性主义理论关怀电影文本,重新检视《机械姬》中的重要意象与叙事文本,以释电影中“身体”“空间”与“性别”之间相互关联的隐蔽关系,试图以电影镜像解现实场域“性别博弈”之弊薮。
一、赛博视阈下的“身体”与“性别”
赛博女性主义又称电子人女性主义,“赛伯”(赛伯格)一词源于“人类”与“科技”的邂逅,它始肇于现代宇航科技与医学的发展。由于美国宇航员特殊的太空作业需求,意图以科技重铸自身的身体,以应对外太空恶劣的环境。他们在两个英语词汇“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中截取其词首创造出“赛博格”(Cyborg),意图以机器取代自然肉体成为新的人类身体材料。然而,人类的身体伴随着“嫁接媒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男性”与“女性”的边界逐渐消失,他们开始有了新的统一命名:“电子人”。这样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同时极大地影响到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赛博格神话不仅是构建一个多元、界限模糊、元素冲突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贴切隐喻。”①在赛博时代,人类可以通过科技芯片的植入,利用技术改变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的生殖系统,使得父权社会中女性无法逾越的“生殖焦虑”消失,社会性别“同一”到“电子人”。

图1.《机械姬》
赛博女性主义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对“男/女性气质”的载体做出了建设性的阐释,自激进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女性主义学者对于“男/女性气质”的考虑,一直都以人类的“自然身体”为讨论的载体。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气质”都是基于“自然身体构建”之上,并且父权社会一直将“女性气质”与消极的、残缺的、被动的生命经验连接,而将“男性气质”界定成积极的、完整的、主动的。女性主义学者伊里格瑞(Irigaray)认为父权社会中的认知系统将“黑暗”“非理性”等内涵强加于女性身上,而男性则公认为“光明”“理性”的,这样的“寓言”仍延续到电影的叙事中。但是面对现代科技、医学的不断发展,“机械”开始成为人类身体建设的新材料,被“机械”强大的身体是否能承载“性别”?被虚拟增权的“身体”是否还是人类“主体性”的依据?《机械姬》中给予这些性别议题以新的想象。
毫无疑问,“身体”是女性追寻自身主体性的重要场域。电影中艾娃的“身体”成为唐娜·哈拉维所言的“谦卑的见证者”。她机械的“身体”可以无限制的“复制”与“替换”,电影中这样的“身体”表现策略可以说是对父权制度下“身心一元论”的绝对冲击。影片中艾娃的“身份”是伴随着“艾娃芯片”,而不是“身体”继续“存在”的。可见,科技的发展给予“性别”新的寄居空间,“性别意识”的本体可以逃离人类躯体,而移位于机器异形。同时,“记忆”开始取代“身体”,成为承载“性别”的容器,这种对于传统性别主体认知的重新界定,预示着赛博空间的符号与意义生成的“翻转性”与“多样性”。电影中性别符码也打破了以往身体政治的认知边界。在赛博空间,“性别”也成为一种编码,可以有多重的意义与解读。性别的载体可以是性感的躯体,也可以是坚硬的金属。
《机械姬》中伴随着叙事的深入,陈述了一个“赛博女性”的诞生,电影开始,艾娃作为一个女性机器人,在“性别”特征上仍不完整的、透明的身体仍表明了她的机器属性,她只有一张女性的面孔来表明“第二性征”。然而,艾娃通过“语言”让卡莱布不断地相信她所陈述的“事实”。随着测试的进行,艾娃开始不断选择头发、衣服去遮蔽“异化”的身体,让卡莱布更加相信自己的“女性气质”与“女性性别”,直到艾娃杀死纳森,真正获得自由,挑选自己的“身体”皮肤,拼贴在机器身体的表面,完成了自己的“重生”。电影中展现了一次完整的“身体”伴随着“性别意识”逐步重塑的过程。这与现实场域中,父权制度与消费社会合谋下的女性身体构建的种种“主体性消弭”的身体事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时的艾娃在镜子面前重新审视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镜头,预示着艾娃“决定”自己成为“女性”,性别成为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符码。然而,“艾娃”原本是由男性创造的“机器人”,她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进入人类社会,但最终她选择“自己”成为“女性”电子人,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于“女性气质”与“女性”的认同。对于主体性(身体)与自我意识(记忆)的保护,成为艾娃通向自我主体构建的重要路径。同时在另外一个维度来考虑,艾娃这样的行为也印证了赛博空间本身就会对“性别意识”进行消解。机器人取代了“女性”,同时机器人也消弭了“人”的边界,“拟像”的“仿真”突破了“性别”与“认同”。“性别”开始伴随着“身体”多元化不断重新释义,并开始扮演真正意义上的“跨界”的“流动”。
二、“铁屋子”的围困与突围
电影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科幻电影的叙事依旧有着浓厚的父权痕迹,这表现在电影中性别关系与性别层级中,无论是《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中对于在机械武装下更加强大的“男性气质”的称颂,还是《变形金刚》(《Transformers》)系列中对于视听效果的“快感”追求,都夹杂着性别博弈。在这些科幻电影的性别书写中,“男性/男性气质”一直都被塑造成充满“神性”的,处于主动地位的,而“女性”角色都是“失语与缺席的”、处于次要地位并且亟待拯救的。因而,这些电影中充满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别叙事。但不可否认,科幻电影中,因“科技力量”强大的“叠加效应”和“超人效应”,极具差距的“性别力量”同时成就了这些科幻电影中的“叙事张力”,使得其对于叙事原型的拆解更具有戏剧化。在《机械姬》所构建的后性别时代的寓言中,两位“女性”角色都是机器“赛博格”的身份,而男性则是人类“所有者”与“测试者”的身份,电影中人物的设置仍是充满父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机器人/女性”与“人类/男性”这对具有张力的对立关系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矛盾,成为推动电影情节的主要动力。纳森的隐世别墅如同父权社会建构在广袤大地上的“铁屋子”,幽闭的空间加剧了权利关系的对立与紧张,纳森的“通行卡”所隐喻的“性别身份”成为“铁屋子”中的权利象征,“铁屋子”与“通行证”共同保护着纳森的“知识产权”,同时禁锢着具有“女性气质”的艾娃与京子,机器人“逃离铁屋子”既是机器人获得“救赎”的路径,也是纳森为其设置的“宿命”,显然,这是电影用影像符码书写了现实社会中的性别镜像。
《机械姬》依旧延续着“男性”创造“女性”的神话,纳森掌握着“创世”的科技,他如“上帝”般创造了“京子”与“艾娃”。一个作为其“工具”;一个是其“商品”,她们都生活在纳森所制造的“铁屋子”的牢笼中,并且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她们都是“被创造的”,在主体性上是“第二性”的。同时,命运又都掌握在“男性”手中,她们作为“机器人”的选择与淘汰都是基于“创造者”,并且与她们作为“产品”,都与经济关系密切相关。可见,在赛博空间,“性别”同样可以“生产”与“贩售”。同时,京子与艾娃的智商性能、外貌体征的不同也暗示现实场域中,女性群体中的“差异性”生存现状。

图2.《机械姬》
京子在电影中是一个服务型机器人,她的存在就是为了单纯满足纳森的生理欲望,以及帮助纳森完成生活起居的琐事,因此她被“设置”成低龄智商,并且不会“英语”,纳森的这种“设置”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使用京子。她东方的面孔与日文的名字,依旧充满了“西方”对“东方”情色化的“凝视”。艾娃则作为其创造的“商品”,在不断的“复制”与“改进”中逐渐“进化”,但是她的身体(脸),依旧是按照卡莱布的“情色幻想”的对象“制造”,这印证了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对父权社会中“女性是被建构”的观点。“传统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心智与肉体、理性与情的二元对立及其泛化,导致了等级制的男性价值体系和技术控制欲望的起源。”②正是因为纳森是理性的“创造者”,所以电影中依旧充满了性别权利的对战,电影中“创造者/被创造者”“老板/员工”“男性/女性”“人类/机器人”充满“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依旧影射出现实场域社会中父权意识的巨大潜仰力,被压抑的“性别气质”仍旧伺机期待着“突围”。
所以,电影中仍旧充满了父权暴力语境,“男性气质”仍被塑造成“具有攻击性”的,纳森对于艾娃“禁锢”与“监视”,使得艾娃生活在如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全景敞开俯视的监狱”,在这种极端的不平等“秩序”中,不同性别之间形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对话模式。艾娃所有的“话语”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纳森而言,艾娃的“语言”仅仅是一种“测试”的符码。可见,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中,性别的对话与交流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性别压迫成为必然。“女性气质”难逃被“改造”的命运,艾娃出于对于“身体”与“记忆”的保护一定要逃离纳森所建造的“铁屋子”藩篱。
如果说纳森用数据和科技塑造了艾娃的身体,那么艾娃则是拥有父权神话中那些“叛逆”而又“强大”的女性的力量:拥有夏娃的智慧、美杜莎诱惑式的美丽、复仇女神的睿智,这些存在于父系神话缝隙中的女性神话想象再造了艾娃的“生命经验”与“成长轨迹”。女性“身体”与“意识”对于空间的向往,成为电影中重要的输出隐喻。电影中艾娃联合了卡莱布、京子的力量,战胜了纳森,获得了“自由”,电影也试图以影像符码阐释了这样一个事实:性别的平等离不开所有“性别”的参与,只有联合多元的力量,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性别平等的胜利。
三、“颠覆”抑或是“重建”赛博伦理
《机械姬》中,性别叙事模式突破了以往电影叙事中政治正确与伦理正确的主流,电影展现了导演对未来科技的反乌托邦式的忧思。影片中包含着双重伦理的思考,一种是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它实质是一种人类对于未来科技的“焦虑”;另外一种就是对于现实场域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思考。艾娃利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与“智慧”顺利通过了图灵测试,但是她联合京子杀死了制造自己的主人,囚禁了帮助自己的卡莱布,违背了“机器人”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如同激进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暴力式的做法颠覆了赛博空间的基本准则。这也是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一个新的伦理命题:机器人是否应该具有“自我意识”?机器人所拥有的“自我”特质本身就与“人类”意识相抵触的,“自我”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肯定。这势必就与“机器人不能违背人类的命令”相抵触,因为拥有AI的“机器人”本身就认为“自己”是人类。机器人通过“女性气质”扮演女性获得自由,抑或是“女性赛博电子人”通过AI完成“逃离”,艾娃的性别本身就是悖论式的存在,但“女性气质”无疑是艾娃获得自由的重要特质,所以在电影结尾通过了“测试”的艾娃,寻找到了自我认可的“主体性”,选择了女性身份进入了人类社会,实现了自我主体的策略性命名。
京子与艾娃在电影中的伦理关系也十分微妙,在艾娃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将纳森的屋子断电后,京子才第一次看到了艾娃,并且帮助艾娃离开了“囚室”,遵循艾娃的指令,杀死了纳森。电影中关于“女性情谊”的描写超越了简单的女性“命运共同体”,并且呈现出阶级、种族的多重意识形态。在电影中,京子与艾娃的“主体性”的呈现明显带有西方视角,东方女性的话语仍要从属于西方女性,京子不仅要受纳森的控制,同时也要“服从”于艾娃的指令,“东方女性”在电影中呈现出“边缘的边缘”的处境。京子相对于艾娃,仍然是“失语的”“未启蒙的”“缺乏主体意识的”,虽然她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女性情谊”也不再是基于“性别认同”之上的情感认知,而是建立在“语言”“属性”(阶级)的基础上的策略。电影中承认了“女性情谊”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情感共同体,而是伴随着彼此身份多元建构的复杂情感认知。但是电影中对于东方女性的性别想象仍未脱离现实场域西方国家中对东方国家的“刻板印象”。

图3.《星际穿越》
电影中也有关注现实社会中女性运动的“话语伦理”问题的考虑。在进行图灵测试的七天中,艾娃向卡莱布展示了两副面孔,因为要面对纳森的监视,所以她要表现得像一个“人类”,与卡莱布进行对话交流,进而通过“图灵测试”;另一面,艾娃通过“超能”的身体使得电源系统暂时性故障,这时艾娃向卡莱布求助,希望借助其力量离开屋子,以逃避其“身体”与“记忆”的重组命运。艾娃与卡莱布的对话中有“谎言”(对人类而言),但是“谎言”对艾娃而言,是实现“逃离”的策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言“语言是存在之家”,电影拓宽了对于“语言”与“存在”的理解,在性别视阈内找到了对“存在”的多重解读,对于“人类/男性”的“谎言”,对“机器人/女性”而言可能生成另外的意义策略。电影借科幻语境对“女性”与“男性”凝滞成“机器人”与“测试者”,以断裂感的道德标准呈现出现实场域女性所承受的父权话语系统中的暴力诋毁。
然而伴随着科技的爆炸式发展,人类的“身体”必将被科技武装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现实场域中,义肢、心跳起搏器、义眼等“机械身体”不断地应用到人类身体建设中,模糊了人类“身体”的定义,电影文本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卡莱布就曾怀疑自己的身体与京子、艾娃一样,于是用刀片割开自己,审视自己的身体。“作为科学身体的隐喻和形象化表达,赛博格的身体成了权力和身份的地图。”③电影中映射出现实场域“身体”的“物质性”随着本体的演变逐渐消退,伴随身体发生的巨大变化,性别开始走向了一种流动式的变化,开始了跨界的能动想象。“性别”开始真正地被“扮演”,而不是固化在身体空间,可以想象,在赛博时代,随着“自然身体”与“机械身体”的嫁接与融合,人类“身体”的版图将不断强大与扩张,进而,基于“身体”主体性建设上的“性别权利构建”势必更具含混性、多元性。因此,人类社会将会重新建立“性别”权利的关系格局。
四、结语
作为一部充满“性别气质”对抗的科幻电影,《机械姬》在电影结构的处理上,将叙事空间切割成具有“仪式感”段落,效仿了基督教的“七天创世”,以章节的形式,刻意打破父权叙事模式所积极倡导的单一化线性叙事,进而用电影语言镜像进行一种“女性化”“去中心化”“零散化”的书写策略,在父权叙事的断点处寻找裂隙,探索“女性气质”的特殊性文本表达。
在现实场域中,“女性在‘社会性别议程’的完善中不断获得自身的解放,又伴随着消费主义和父权制度的‘暧昧’发展无限式微。”④然而,电影《机械姬》不仅呈现着导演对于未来人类与科技关系的重新思考,同时也积极关注未来世界的“性别议程设置”。电影在一个边界模糊的场域重写了科幻电影的“性别史”,将父权社会下的隐蔽的性别运作模式通过镜像语言不断地演绎,让“性别气质”跨界到冰冷的机器,颠覆了父权神话中女性永远“在场的缺席”的性别迷思,试图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当今父权社会下的种种不平等的性别建构,为现实场域女性主体性策略与身份的多重命名寻求出路。可以想象,在赛博时代,“性别”将融入一个更为宽广的场域进行考虑,这也为消除父权社会所制造的性别“刻板印象”提供了某种可能。因而可以说,《机械姬》是导演在赛博语境中对于“女性气质”的正名,是对未来赛博时代的“性别”狂欢式的“畅想”。
【注释】
①[美]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A].郝志琴译.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7.
②李芳芳.赛博格与女性联合体的重组[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04):100-103.
③周丽昀.身体:符号、隐喻与跨界——唐娜·哈拉维“技科学”的主体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05):62-67.
④金明.身体·记忆·认同——女性主义视阈下多重主体的重塑与自我命名[J].文艺评论,2017,(01):45-50.
金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美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