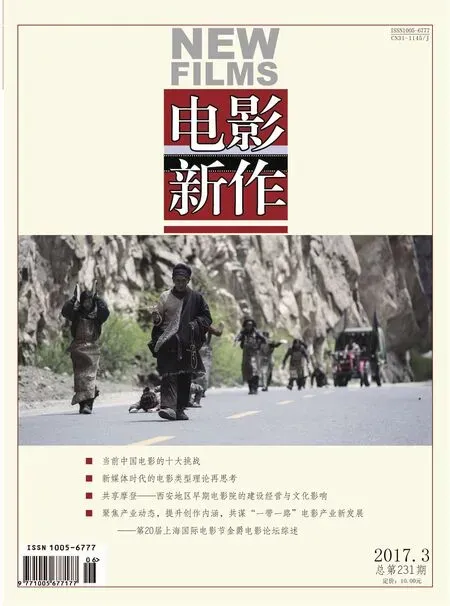《八月》:情感因果式、90年代氛围与“释父”情怀
齐 伟
《八月》:情感因果式、90年代氛围与“释父”情怀
齐 伟
在2017年上半年的电影市场中,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八月》是旨趣独特的影片。情感因果性主导的叙事语法、80后的个体经验浸润下的90年代中国想象和“释父”情怀是这部影片三个显著特点。本文尝试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该片的影像世界,展开对以上三个特点的分析与读解。
《八月》 叙事 90年代 “释父”
累计票房433.3万元①,影片《八月》并没有因为其斩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而票房大卖,“惨淡”似乎已经成为这部影片的又一个标签。与其他被贴上“艺术电影”标志的影片一样,《八月》的院线“可见”显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包容与多样,而其票房“惨淡”也暗示了当下中国内地主流观众的趣味指向。但是,票房的失利并没有将《八月》淹没在这个动辄单片票房过亿甚至过十亿的“奇迹”语境中,鲜明却不单调的黑白影调、浓重却并不弥散的80后个人自传色彩、表面松弛却内里紧张的90年代气氛,都使得导演张大磊的这部大银幕处女座显示出了“可看性”与“耐看性”的电影质感。
导演以浓重的个体经验与情感记忆慢条斯理地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关于90年代中国的故事,让那个在当代中国史述中看似并不具有鲜明转折意义,实则暗潮涌动、格局分化的时空格局可辨可感。影片的别致之处在于:用一个正在被“召唤”的个体视角瞥见宏大叙事无暇顾及的大变革时代,以及其中“不足为道”的父辈们,在冲突“禁用”的叙事动能之下满载个体情感与成长经验。黑白影调的色彩处理是导演关于童年记忆的色彩还原,表面看似毫无生气,但是导演将男主角小雷及其周遭人“放置”在90年代的某个八月的时空器皿中反复测量,看似凌乱无序的叙事碎片与时光流淌却也浸润着温情。可以说,它是一部潜藏着,或者说弥漫着“释父”情怀的小品文。
一、情感因果式与《八月》的叙事语法
《八月》是一部80后导演的处女作,青涩显而易见之余,也为“导演”的实验与实践让渡了巨大的艺术探索空间。在今天中国内地主流电影市场中,除却类型、明星和奇观制造等策略外,一部影片情节是否紧凑严谨,符合罗伯特·麦基的“故事”范式,或者更通俗地说,“笑点”的布局是否合理,“尿点”的控制是否得当,俨然是票房大卖或今天评判电影“可看”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对于很多观众而言,《八月》的叙事结构松散,甚至是零散的。从夏日三口之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用餐的影片开场段落,到博士酒楼宴请小雷上重点中学这个八月家庭中最大的事情得以解决,再到黑白镜像中的母子两人坐在家中观看始终不肯“低下高贵头颅”的小雷父亲消失在着色的影像纵深处,观众似乎无法在106分钟的观影中获得视觉奇观带来的即时快感和强烈戏剧性冲突诱导的解读趣味。这部电影既没有青春电影中常见的男孩儿间因力比多爆发而外化的打斗段落,也无时代变革映衬下人物与人物间的显性戏剧冲突,更无精巧设计的跌宕起伏与剧情反转,某种由戏剧性主导的电影经验和解读范式在这部电影中显得无所适从。
可以说,作为一部进入电影院线的剧情片,《八月》是“不可看”的,因为它并不是传统的戏剧式影片,即它不是一部由镜头间、场景间和段落间紧凑有序排列推演、由事件间逻辑清晰,结构上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渐次展开的情节因果律主导的。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它具有极强的“可看”性,因为它的情节结构方式是“情感因果”式,写实主义的。从影片的整体叙事语法来看,导演摈弃了观众熟悉易懂的、商业电影创作中惯用、规范的情节推演模式,而选择了一种需要充分调动或考验观众审美知觉的情节结构逻辑——“情感因果”式,即影片情节结构是以人物的情感逻辑为结构,或者说以人物(小雷)对于周遭世界(人物/环境)的选择与互渗所带来的潜在情感变化来统一和把握的。影片《八月》中镜头间、场景间和段落间的选择、组合和连缀,不是以某种显见的“设计”为观众所知,而是以人物情感逻辑呈现。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小雷家、姥姥家、制片厂、电影院和家属院等是导演考察小雷成长(情感/情绪变化)变化的主要场景/段落,也是影片叙事功能的承载。进一步说,在这些并未出现明显的戏剧冲突的主要叙事空间中,小雷在一旁观看父母间、长辈间,以及三哥们的表演,而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雷。例如,博士酒楼宴请之后,在父母骑车带着小雷回家的夜路上,母亲问小雷“为什么要上三中呀”时,小雷回答“因为三中的校服挺帅的,还配一根像三哥那样的皮带”。小雷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父母的期许,但却是小雷的,因为这是三哥们的“表演”烙在小雷成长中的情感烙印。同样的例子还有影院门口韩胖子父子与小雷父子巧遇的那场戏。在这场戏中,一边是韩胖子对小雷父亲的盛气凌人,一边是聊天后手握双节棍的小雷追打韩胖子的儿子。可以说,小雷对于韩胖子儿子的追打绝非是少年间的打闹,而是父亲身上某种情绪在儿子小雷心理和行为上的某种显影。因此,这类影片的情节分析不是侧重辨析镜头/场景/段落间的组合是否符合情节因果性,而是着力于考察人物的情感如何统摄及影响它们的择取与联结,以及这背后显示了人物何种情感状态和走向。
众所周知,人物是影片情节编织的核心牵制元素之一。在大多数戏剧式电影中,人物的出场或离去是服务于情节的延展。而影片《八月》则是以是否契合主要人物小雷的情感转换逻辑来择取与设计人物。对于谙熟“情节因果律”观念的观众而言,这些细碎甚至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及镜头是可以删减的,因为它们并不参与叙事,是不具有意义的可有可无。但是,对于片中的人物小雷而言,他们都因参与了其个体成长,或者说在剧中人物小雷的童年情感结构中具有不容抹杀的印记而具有意味。例如在影片中,小雷家对面楼里的姐姐曾经出现在他的梦中或是他偷窥的对象,但又在小雷的生活中无缘由地消失。这些段落是在暗示一个12岁的少年在稚气未脱与奔向成长过程中,开始感知异性吸引力的情感表征。而与影片中小雷父亲相比,在整部影片中不时出现的三哥也是“父亲”,或者更确切地说承担着小雷成长和情感转变中的“代父”功能。影片中的三哥并未参与影片主体叙事,但却具有“代父”意味。对于小雷来说,不论是坐在胡同口瞥见“三哥”和一众兄弟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还是观看“三哥”们勒索中学生的腰带,抑或说电影院里偷看前座喝着啤酒搂着女朋友的他们,那种三哥身上透漏出的“父亲”权力既是压迫和威胁,同样也激发了他“变成”父亲的精神动能。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出场与离去都是服务于小雷的情感变化。
不过,我们的确无法用传统戏剧式结构去理解这些散落的段落或人物,但导演却是用剧中那个话语并不太多,情感细腻丰富且正在起着变化的小雷的“情感因果”串联起了整部影片。简言之,《八月》的情节组织方式是导演将其自身的某种90年代情感经验赋予小雷及其情感,进而使剧中人物小雷微观的情感变化具有特殊的结构意义。在今天电影创作逐渐成为电影工业化生产的语境下,《八月》是不具有可复制价值的,但却也是不可代替的。其原因就在于它是导演对个体经验的唤醒、感知和提炼,并统一于影片人物的情感系统中。当然,这种情感因果律主导的叙事语法并不是这部影片所独有的。大多数以“艺术电影”之名聚合起来的影片在叙事层面上都带有这一组织原则,而这也是艺术电影需要或值得解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90年代氛围:个体经验与被括起的“空间”
无须讳言,90年代、国企改革和导演自传式既是《八月》显见的影片标签,也为影片解读圈定了清晰的文本标志。导演张大磊一再强调这部影片的自传属性②和情感/情绪导向,“在《八月》里,我想表达的,其实抒情的分量更多一些”③;也并不意图明确地通过虚构一间“影像实验室”去拷问“90年代中国想象”这一宏大命题,“对90年代,我没有特别理性地去判断和分析,我的认识,还是站在我当时的角度,也就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角度。”④但是,敏感的观众还是体察到影片中弥散着的、浓重的90年代氛围。那么,90年代氛围究竟是什么?它是“后革命”时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重启甚或加速,市场/市场经济的真正降临成为90年代最显著的历史事件。而其裹挟而来的意识形态深刻地介入,甚至改变了一系列社会关系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不过,与弥漫着金钱逻辑的汾阳县里小武们的无奈与无望,以及《钢的琴》衰败的烟囱下,陈桂林们以工人之名对抗物欲与商业大潮时的浪漫与荒诞不同,《八月》中的90年代中国并不宏大,而仅仅是弥漫在12岁少年小雷某一个暑假生活片段,以及他眼中父辈面对改革时代的无奈、隐忍与承受的“氛围”。
事实上,影片中的90年代氛围首先是导演张大磊个体成长经验中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导演在影片中并不旨在“渲染”作为身外之物存在的时代氛围,而是这种氛围本身就是由其个体成长经验与90年代中国两者间发酵沉淀后的情感/情绪复合转生。在影片的具体处理上,导演把小雷置于“前景”,将90年代置于“后景”。对于小雷们来说,尽管“90年代中国”并没有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个体身上,但是一种面目并不全然清晰而又无法逃脱的氛围。这种氛围是与姥爷坐在电视机前聆听关于国企改革的“主流”发声,是在姥姥院子里下岗后的舅舅对小雷母亲聊起“三十年工龄都换成毛线了”和小雷父亲口中“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的“个体”无奈与无力,也是父亲和舅舅酒醉后在街头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每日每夜工作忙”般的中国式情绪宣泄。
不过,这种前后景的氛围处理并不是界限清晰的,或者说小雷并不是一直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表面上看,或者大多数时候小雷都不占据这些叙事段落的核心位置,他跟观看影片的观众一样,仅仅是观看和观察身临其境的父辈们的反应与表现,但是影片中一些看似无意的情节设计和场面调度却也暗藏着小雷的“介入”,或者说这一时代氛围对于他的影响。例如,在影片26分钟左右那场母亲在与舅舅聊天的段落处理中,母亲和舅舅始终是占据视觉中心的位置,小雷和妹妹孩子般无忧无虑地玩耍看起来是在大人们谈正事儿的叙事中心之外,承担着叙事“背景”的作用。但有趣的是,在随后母亲与舅舅关于一沓钱的推搡中小雷突然进入房间,闯入“大人的世界”。他不仅将钱塞进舅舅的上衣口袋,而且坐在门外楼梯上若有所思地听着姥爷和舅舅间关于“如何理解国企改革”的谈话。其有意味之处恰恰在于导演看似割裂了大人们和孩子们的世界,但是却精巧地通过细节处理将一个时代的“氛围”嵌入一个少年的成年经验中。
尽管导演一再宣称这部作品带有显著的“个体经验”色彩,我们也不否认导演的个体经验在这部影片中的核心地位,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个个体经验是独属于张大磊/小雷的吗?或者说,导演真的在完成一部个人的影像自传吗?如果这部电影并不是彰显“个体”的话,那么导演在《八月》中如何实现将“个体”经验转换生成为80后的集体经验呢?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导演的做法是将地域特征放入“括号”,进而将个体经验泛化为80后一代人的90年代集体经验。这一点也是该片“90后氛围”处理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
对于这一特点的概括是源自于我们反复阅读影片后的疑问:导演为什么刻意规避和弱化导演个体经验展演空间和影片主要拍摄地的“呼和浩特”,而将大多数的情节和段落置于家庭/家族、工厂、街头、酒馆等地域标志并不显著的空间?进一步说,如果不是导演有意识地在影片第13分钟左右插入一个小雷游泳证的特写镜头的话,观众几乎无法察觉到这部影片的空间指向。这种迥异于贾樟柯式的“汾阳”情结和张猛式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着迷。与贾樟柯和张猛的空间“符号化”给予影片的叙事动能和意义增殖相比,《八月》的空间遮罩处理显得刻意而有意味。这种处理大致呈现为“泛化”与“窄化”的双重意味。所谓“泛化”是指为了凸显影片的表意指向是“小雷们”的,而非“小雷”的。换句话说,将地域空间辨识度降到最低一方面是为了更聚焦于小雷在那个已逝去的90年代某个八月碎片化的生活经验背后牵连的细腻情感变化和成长,而在地域空间独特性被抹平与擦除的语境下,观众更容易进入小雷的个人情感世界,进而在他的某些经历中稀释出观众与小雷共享的90年代青春成长经验。而“窄化”则指将地域空间收缩到家庭/家族空间。呼和浩特是一个独特且显著的地域标志。如果影片过分凸显它,反而会容易过分牵制影片中小雷个体成长经验的共享性。而将影片的空间锁定在家庭/家族,甚至工厂、街头等空间的话,看似空间被窄化,但它却更容易唤起“小雷们”的童年经验和集体记忆。当然,这种由于影片空间设计上带来的“泛化”和“窄化”都是与导演某种清晰的表意诉求密不可分的,“影片中呈现的社会变迁,仅仅是背景,没有强调它的目的,主要是讲家庭,讲人。”⑤
三、“我”的位置与“释父”情怀
尽管我们在前文论述中反复提及小雷及其情感走向在《八月》的叙事系统与意义表征中的重要性与核心地位,但小雷却并不是影片的“主角”。正如导演张大磊坦言,“小雷不是主角,但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因为我比较熟悉他,他的视点决定了我们能看到谁的生活。随意,我想以他为主,他闲着的时候在姥姥家,看到的就是姥姥家发生的事;他回到制片厂家属院,看到的就是三哥的事。”⑥也就是说,小雷仅仅是影片为我们展演的90年代国家/家庭、改革话语的发令/承担等核心二元关系结构中的“第三者”。
不论是影片多次出现的在小雷家,父母关于制片厂改革后父亲的出路等问题讨论的场景,还是在姥姥家,大人们围绕长期卧床的太姥姥忙前忙后,而小雷却在窗外观看与玩耍,抑或是在博士酒楼,父母为了小雷升学宴请而他却在酒楼门口看似若无其事地打台球的场景中,他都不是叙事/行动的发出者或直接承担者。作为这部影片的文本策略之一,这种“第三者”的位置设计看似赋予了小雷叙事人的身份,以及某种场景段落的视点依据。但如果对这些段落进行细致辨析便会发现,小雷是以在场的缺席方式参与进这些叙事段落/场景。换句话说,在影片的很多段落中,机位与摄影机的视点择取、场面调度及人物关系的展开又都不是以小雷的在场为视点依据的。这一吊诡的视点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将影片中的小雷(“我”)有限度地放逐于90年代中国改革话语发出/承担的历史进程之外。而“有限度”则意味着未完全,即它同时规定了处于成长中或“观看”中的小雷的“准主体”位置。例如前文分析影片26分钟左右那场母亲在与舅舅聊天的段落处理中小雷的“闯入”便是如此。
无疑,小雷的“准主体”位置一方面意味着他尚未完全成为被“询唤”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作为“第三者”的小雷,其大部分的行为方式都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并未获得主动性的“观看”。当90年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国企改革渗入这个不具名城市的制片厂和家庭/家族时,小雷父亲们而非小雷是直接承受者。在诸如小雷家、姥姥家或酒楼中父辈们那些无奈与无力感的表演,并不是因为小雷的在场而出演。进一步说,小雷仅是90年代中国改革进程/话语、家庭/家族变迁的旁观者,而隐忍的小雷父亲们是那个变革时代的见证人和承担者,同时也是《八月》中真正的“主角”。这一“主角”是小雷和我们“观看”时的视觉和叙事中心,也是子一代对于父一代的认同。在影片结尾处姥姥家拍家庭合照的戏中,小雷右臂提起的动作既意味着为家庭已经在外打工的父亲的缺席,同时也意味着父亲形象在小雷心中的体认与在场。而影片结尾字幕升起的“谨以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同样证明了这一判断,暗示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张大磊们的“释父”情怀。
而《八月》中的这种情怀并非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孤证。无独有偶,曾经以“叛逆”而成为80后一代精神偶像韩寒,在其票房大卖的新片《乘风破浪》中显露出的“父子和解”旨趣与《八月》的“释父”情怀形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无疑,与弗洛伊德式的“弑父情结”及其在文本运作层面的普泛性和普适性不同,张大磊的“释父”也好,“国民岳父”韩寒的“父子和解”也罢,其选择是带有80后一代人鲜明的感情烙印的,是不再年少轻狂的80后们尝试精神自梳时尝试与父辈达成某种情感与历史和解:今天,长大成人的这一代人已经成为“父亲”,甚至是学会成为“父亲”时,对自己曾经叛逆的“弑父”冲动的心理校正。他们以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体认”的方式重新认识和发现父亲。这种心理校正既意味着子一代与父一代的和解,也意味着子一代的身份更迭。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八月》更像是一部情感充沛、满怀“释父”意味的小品文,而非旨在把握90年代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改革“阵痛”的铭文。只是,当个体经验遭遇历史时,一种90年代氛围改革阵痛便自然在父辈们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被12岁的小雷“观看”的同时,也潜在地影响着他的青春与成长。导演正是抓住这一点,以一个12岁孩子的情感变化/成长话语贯穿,既完成了子与父的历史和解,也缝合了弥漫在90年代整个时代的国家与家庭承担的双重“阵痛”。
【注释】
①票房数据参见艺恩电影智库“CBO中国票房”,http://www.cbooo.cn/m/655812。
②张大磊在谈及《八月》的创作缘起时说:2008年有一个夏天午后,我回到姥姥家,就像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个环境。那天特别有感触,看着母亲用小勺给躺在床上的八十多岁的姥姥喂饭,感觉恍若隔世。1994年的夏天,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床,姥姥也是这样扶着她的背。中午吃完饭,我坐在姥姥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晒着太阳,突然感觉时间慢下来了,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很多童年的记忆浮现,像在电影里,像梦一样。我希望把这个感觉抓住。参见张大磊、李春:《“这部电影其实就像我的一场白日梦”——〈八月〉导演张大磊访谈》,《当代电影》2017年第5期,第20页。
③参见张大磊、李春:《“这部电影其实就像我的一场白日梦”——〈八月〉导演张大磊访谈》,《当代电影》2017年第5期,第21页。
④同③,第20页。
⑤同③,第20页。
⑥同③,第21页。
本文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互联网+’语境下电影社会舆情分析及判断”(项目编号:GDT1604)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齐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