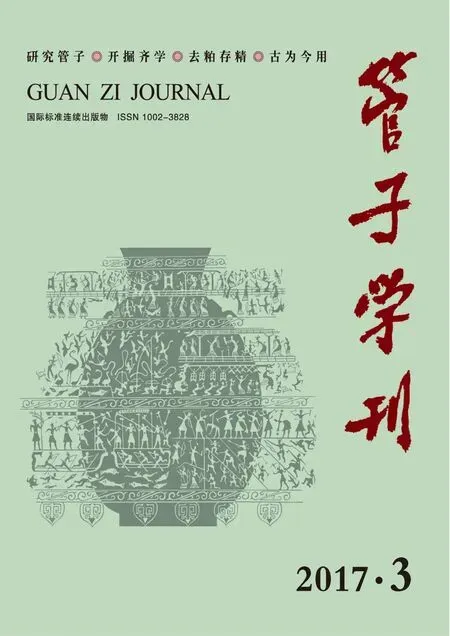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
郑邦宏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4)
新出土文献研究
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
郑邦宏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4)
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由来已久,有成功,也有失误。对那些失误的案例,虽已有学者注意,但目前学界仍没人作较为全面的总结。我们从出土文献自身的讹误、时代地域性差异、文字考释成果的可靠性、通假字、偏旁义近通用字、用字书写习惯、不明词义误校、重视语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出土文献;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
引言
古书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文字发生讹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其中的形近字。古书的文字如发生讹误,文义则晦涩难通,习者或不达其义,或失之千里,这不利于古书的释读和传播。因此,对古书中形近讹误字的校订,是整理古籍的重要工作。这一方面,前贤时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东汉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其中就有对古书中形近讹误字的大量校订。《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尹》,今本的“吉”,正作“”,即“诰”。可证郑注之确。而郑注“吉,当为告”,则是对“吉”为“告”之形近讹误字的校订。
然而传世古书中仍有大量形近讹误字未能校出,而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文献保留着文字原来的书写面貌,且有不少可与传世文献对读,这为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提供了新的材料,带来了新的契机。近些年,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成为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就包括大量古书形近讹误字的校订。如裘锡圭先生据金文“引”与“弘”形近,指出今本《尚书·大诰》“洪惟我幼冲人”、《多方》“洪惟图天之命”的“洪”,本应写作“弘”,而“弘”为“引”之形讹[1]45-49。陈剑先生据战国文字“安”与“女”形近,指出《礼记·乐记》“宋音燕女溺志”(《史记·乐书》“燕女溺志”)的“女”为“安”之形讹[2]121。陈雄先生根据上博简、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对读,指出今本《周易·解》“解而拇”的“而”为“亓”之形讹[3]454。
当然,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应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有学者就此已做过一些讨论,我们尝试再作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出土文献自身讹误
与传世文献相比,出土文献入土后未经后人改动,更接近古书的原貌。学者也多认为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加可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出土文献在传抄前代古书时有可能已有讹误。单就字形而言,形近讹误字在出土文献中就比较常见。如裘锡圭先生就特别强调:“我们在释读楚竹书的时候,应该把竹书中有错别字这一点牢记心头。如果遇到错别字而不能辨明,就会无法理解或误解文义。”[4]377冯胜君先生则指出:“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文字上的错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与地下出土的简帛古籍材料对读,有时能够纠正一些仅靠传世典籍不易发现的讹文。但需要注意的是,地下出土的简帛古籍中也同样存在各种类型的讹文,如果遇到抄手水平不高的情况,其讹文的数量甚至会大大超过与之对应的传世典籍中讹文的数量,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形近而发生讹混。”[5]153
如今本《礼记·缁衣》“慎恶以御民之淫”的“淫”字,上博简《缁衣》同,而郭店简《缁衣》作“泾”,郭店简整理者指出“泾”为“淫”之形讹[6]129。
今本《老子》三十二章“民莫之令而自均焉”的“而”字,帛书《老子》乙本、北大汉简《老子》同,而郭店简《老子》甲本讹写作“天”[6]112;楚文字“天”“而”字形相近,极易讹混。参之文意,郭店简的“天”应为“而”之形近讹字。
今本《周易·遯卦》“无不利”的“无”字,上博简《周易》作“亡”,二字音近可通,而帛书《周易》讹写作与“无”形近的“先”。
《国语·吴语》“乃阖左阖”的“左”字,慈利竹书作“右”。陈送文先生依照文意,并结合礼制和字形,指出慈利竹书的“右”为“左”之形讹[7]522—523。“右”“左”,战国、秦汉文字字形都较为相近,易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皆有二字讹混之例。
由上可知,出土文献中讹误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形近字。我们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时,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不可盲信出土文献,而轻视传世文献。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盲信出土文献,那就极有可能将今本原来的正字改成了讹字。
二、时代性、地域性差异
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一定要弄清其与古书之间的时代性、地域性差异。关于这个问题,冯胜君先生曾有很好的讨论[5]51-55,此节我们主要参考冯说。简而言之,就时代性而言,应注意出土文献与古书的成书年代或写定年代之间的关系,如不能用先秦文字的字形来校订成书于西汉或更晚的古籍中的字形讹误;而所谓地域性的差异,主要是指战国时期各地域之间的文字异形。
于省吾先生曾据金文的“上”作“二”,认为《韩非子·存韩》“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的“王一”乃“王上”二字连书[8]361。所谓的“连书”,就是“共用笔划”,即“王”下面的横画与“二”上面的横画共用笔划。
《韩非子》的写定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与金文的时代相距较远,冯胜君先生指出:“在战国晚期以后的文字材料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例写作‘二’形的‘上’字。因而,‘王上’不大可能讹为‘王一’。”[5]51-53换句话说,“王”与“上”在战国晚期不可能有共用笔划的现象,也就不可能讹作今本的“王一”,因此,于省吾先生据金文的字形来校订《韩非子》是不可取的。解放后,于先生修訂《双剑誃诸子新证》时,将这条考证删去,可能他已认识到其中的问题。
《淮南子·要略》“族铸大钟”的“族”字,于省吾先生据金文、陶文的“陶”多省作“匋”,其与“族”形近,认为“族”为“匋”之讹[10]409。冯胜君先生指出:“‘族’‘匋’二字的形体也的确有相似之处,但这反映的也只是西周晚期的现象,《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所用字体应为汉隶,从字形上说,与西周金文了不相涉,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根据这样的对比材料推导出的结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5]53冯说可从,金文与《淮南子》并不存在相关性,以金文来校订汉隶更是没有任何依据。


只有弄清出土文献与古书之间的时代性、地域性差异,才能正确地运用出土文献对古书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用先秦、秦汉文字对古书形近讹误字的校订,时代性、地域性的问题就更为重要。
三、文字考释的可靠性
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正确的文字考释结论是一大前提,如果文字考释站不住脚,那么,以此为依据作出的校订的科学性可靠性便无从谈起。

据此,有学者认为《周易·萃·爻辞》“引吉”应为“弘吉”,“引”为“弘”之形近讹误字,如高亨先生说:“《尔雅·释诂》:‘引,长也。’是引吉犹云长吉永吉矣。但余疑引当作弘,形近而讹。《尔雅·释诂》:‘弘,大也。’弘吉与大吉、元吉同义。殷虚卜辞屡言弘吉,即其证也。筮遇此爻,大吉无咎,故曰弘吉无咎。”[12]289
于豪亮先生受睡虎地秦简“引”字启发,指出甲骨文中旧释为“弘”的字,其实就是“引”字,他说:“秦简的写法同甲骨文、金文的写法相同,帛书的写法也同甲骨文、金文的写法极相近。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以前都将这个字释为弘,根据秦简和帛书,可以肯定这个字是引字,不是弘字。”[13]74。
无论从字形,还是训诂角度考虑,释为“引”确为不易之说。现在,学者多持于豪亮先生说。如此,原来《周易·萃·爻辞》“引吉”不误,学者将其改为“弘吉”反倒是错误的,这是对正字的误改。

总之,文字释读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的科学性可靠性,如果以误释的文字来校订古书,则极有可能将古书的正字误改。
四、通假字和偏旁通用字
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有时将通假字、偏旁通用字也误认为形近讹误字。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以避免这一方面的错误。
《尚书·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的“劝”*为讨论方便,此处“观”“劝”皆用繁体。字,《礼记·缁衣》引《君奭》作“观”。于省吾先生说:“劝作观;宁作文,皆以形似而讹,《礼记》所引是也。”[9]229而在于先生之前,王国维已说:“劝与观,似从观为长。”[17]252。郭店简《缁衣》引《君奭》亦作“观”,正与于、王二氏相同。但于先生讹字说似不可从,“劝”“观”都从“雚”得声,二字音近可通。且字形上,虽二字都从“雚”,但“见”与“力”的字形差异较大,不易致误。廖名春先生就曾指出:“‘观’,《礼记·缁衣》同,古文和今文《尚书》皆作‘劝’。两字音同,故可通用。从楚简和文意可知,‘观’当为本字。”[18]115“观”“劝”应是通假关系,而并不是形近讹误字。
今本《尚书·金滕》“惟朕小子其新逆”的“新”字,清华简《金滕》作“亲”*为讨论方便,此处“亲”用繁体。。对此,扈晓冰先生说:“郑本作‘亲迎’,马本作‘亲迎’,简本亦作‘亲逆’,故今本‘新逆’当为‘亲逆’。新与亲,字形相近易讹。”[19]12扈先生以“新与亲,字形相近易讹”,殊误。“新”“亲”,音近可通。二字相通之例,出土文献与古书中皆常见。
汉印有“湿成丞印”“湿成左尉”等印文,而“湿成”,《汉书·地理志》不见,仅西河郡有“隰成县”。罗福颐先生据汉印指出“隰”为“湿”之形讹[20]。湿,古音邪母缉部字;隰,古音书母缉部字。二字韵部相同,声母发音部位相近,音近可通。赵平安先生亦认为此印文的“湿”通《汉书》的“隰”,是通假字,并指出《谷梁传·襄公八年经》“获蔡公子湿”的“湿”,《释文》“湿本又作隰”[21]。“湿”与“隰”应是通假关系,而不是形近讹误字。
汉印有“窒中宣”“窒中宰”“窒中光”“窒中遂”等印文,陈直先生据此指出《汉书》“清简侯室中同”的“室”为“窒”之形讹[22]68。冯胜君先生赞同陈说,并以此为利用汉印订正人名例[5]79—80。然讹字之说并不可信。室,古音书母质部字;窒,古音端母质部字。二字韵部相同,声母同属舌音,音近可通。古代复姓“窒仲”,汉印或作“窒中”,或作“室中”*此蒙魏宜辉先生提示。。而古书中“室”与“窒”亦有通假之例,如《论语·阳货》“恶果敢而窒者”的“窒”,《释文》“鲁读窒为室”[23]563。因此,“室”与“窒”二字应是通假关系,而不是形近讹误字。退一步讲,“宀”“穴”义近偏旁通用,也不当以讹字处理。
通假还关乎用字习惯的问题。所谓的用字习惯,指人们记录语言时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哪一个词的习惯[24]464。出土文献与古书的有些形近字,二者可能只是用字不同,不存在谁正谁误的问题。出土文献保留着文字的用字习惯,凭借出土文献,我们得以了解古书的用字习惯;对学者以往将有些用字习惯当作讹字的问题有新的认识。

不能否认“荥”“荧”字形确实相近,有发生讹误的可能。但语音上,“荧”和“荥”,二字都是匣母耕部字,读音相同,可通。这样,古书中“荥阳”一词的“荥”为“荧”之讹的说法就值得怀疑。
施谢捷先生在吴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然则‘荥阳’之得名与‘荥泽’有关,‘荥’本来应该作从水的‘荥’,秦汉以后或作从火的‘荧’,则属于同音借字。至于后世文献中作‘荥’或‘荧’,只是反映不同时代或不同书手的不同用字习惯,并不存在孰是孰非。‘荧阳’在战国时还可以写作‘萦阳’(参‘萦(荥)昜(阳)氐马’玺说明)。”[28]117
冯胜君先生说:“后来,在战国玺印、陶文中又发现了地名‘荥阳’,‘荥’字写法与古书中的记载相合。但这仍然不能推翻段玉裁等人的结论,原因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荥阳’这一写法虽然有可能比‘荧阳’古,但却不一定合于《史记》《汉书》等古书成书年代的用字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求古,其结果很可能是反失其真。”[5]97-98
冯说“但这仍然不能推翻段玉裁等人的结论”值得考虑,因为段玉裁等人的讹字说是不可从的。我们认为,即使“荧”是《史记》《汉书》等书的用字习惯,其与“荥”也不是讹误字的关系。它们只是用字习惯的不同,而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

汉印中有“槀侯相印”印文,韩彦佶先生据此认为《汉书·地理志》“稾城”的“稾”,“当为‘槀’,传抄时将‘木’讹作‘禾’所致”[31]51。其实“槀”从木与“稾”从禾也是偏旁义近通用。古文字中从木、从禾通用。《汉书》“稾城”之“稾”从禾应不是“槀”的形近讹字,二者应是异体字的关系。
另外,学者有时将文字的某种书写习惯也当成了形近讹误字,也应引起注意。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有一枚西汉印“平旳国丞”,罗福颐先生据此印指出《汉书·地理志》“北海郡属平的县”之“的”为“旳”之讹[20]。
赵平安先生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旳,后世文献一般从白,是在日的基础上加上一撇,是为了字势的需要。日旁变成白后,仍具表意作用。由旳变为的,应是形义两方面一起作用的结果。”[32]236赵说可从,“旳”写成“的”是字势的需要,是一种书写的习惯,并不是讹字。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多见,我们这里只顺带提及。
古书的通假现象很普遍,如果以通假能够解释清楚的现象,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以讹字立说。而偏旁义近通用也是古文字中常见的现象,古书的抄本可能存在一字各写通用偏旁的不同字形,若后世的整理者对其中的一些字未作统一,就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异体现象。但它们并不是讹误字的关系,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五、不明词义而误校
有些词义,文献中用例少见。学者不明词义,文意说解不通,因而以讹字立说,联系形近字,将其误校。
《诗经·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中的两个“比”字,前人的解释存在差异[33]33-34。于省吾先生从押韵的角度,提出“比”为“从”字之讹[34]19-20。此说影响很大,学者多信从。谢明文先生从字形和异文角度出发,认为“克顺克比”的“比”其意当和《国语》“比于诸弟”之“比”相同。《国语》韦注训“比”为“亲”,似较毛传更为贴近文义[35]19-20。蒋文先生在谢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从文意和字形两方面详细论证了于说不可靠,指出“克顺克比”的“比”当作“辅佐”“配合”解[33]35-36;“比于文王”的“比”,蒋先生以为应从朱熹之说,将“比”训为“比至”[33]39。要之,无论从文意,还是字形,于先生的校改都是没有必要的。既然“比”的词义本就能将文意解释清楚,就不烦改字。
《清华简(贰)·系年》“曾(缯)人乃降西戎”(简6)一句,学者解释或有不同,张新俊先生提出新说,以“降”为“徵”之误字,并以此指出《国语·周语中》“王降狄师以伐郑”的“降”同样也是“徵”之讹字[36]。王辉先生不同意张说,认为韦注训“降”为“下”可信,古书常用“下师”或“下兵”表示出兵,“降狄师”及简文“降西戎”之“降”应如韦注所言,意为下,与“下师”“下兵”之“下”意思相当。《系年》“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意即缯人于是发西戎之兵进攻周幽王,可见“降”自可通[37]488-489。并且,王先生还指出“降”“徵”二字讹混是有条件的[37]489-490。王说甚是。“降”,《说文·□部》:“下也。从□,夅声。”由甲骨、金文可知,其造字本义即人从高山走下。“降”,训“下”,古书常见。联系古书“下师”“下兵”之“下”的训释,于文义即可通,不烦校改。
词义是繁复的系统,由本义到引申,是发散的。对一些文句的校读,我们不能因为常用的训释不通,即用讹字立说,对其进行校改,以免误校。
六、重视语法研究成果
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必须符合语言事实,语法的检验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有些形近字,它们的语法功能恰有相同的方面,而其中一字的语法功能后世罕见,一些学者不知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将它们视为讹误字。
《周易》各本“有孚”一词常见,但用字不同。上博简《周易》作“又孚”,今本《周易》作“有孚”,帛书《周易》作“有复”。而各本又见“厥孚”一词,不过用字也不同。上博简《周易》作“氒孚”,帛书《周易》作“阙孚”,今本《周易》作“厥孚”。由于楚简“氒”“又”二字形近,这让人对“厥孚”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张新俊先生怀疑《周易》各本的“氒(厥)孚”应为“又(有)孚”,“氒(厥)”为“又”之讹[39]。
袁金平先生不同意徐、张之说,指出学者的研究早已证明“有”有代词的用法[40]370-377。其中,以裘燮君先生的研究用力最多,裘先生指出:“在殷商卜辞、西周金文、《周易》、《尚书》和《诗经》等先秦早期文献中,有字可以用为第三人称代词、一般性指示代词和特指代词。”[41]304并对先秦早期文献中“有”的代词性用法作了很好的梳理,例证丰富,结论让人信服,其中有对“有孚”一词的分析:“《周易》‘有孚’一词中的‘有’,从‘有’字在先秦早期的特殊用法来看,‘有’字宜释为特指代词,相当于‘其’,表示‘那个’的意思。‘有孚’是‘那个筮象’的意思,‘有’字指代‘有孚’所在的某卦某爻,如‘有孚颙若’的‘有’,就是指代《观》卦。”[42]103
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有”有代词性的用法是可以确定的。这样,“厥”与“有”就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也就是说,《周书·立政》的“克厥宅心”和金文的“克又(有)宅心”,《周易》各本的“厥孚”和“又(有)孚”“又(有)”并不是“厥”的讹字,只是用了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不同的词“又(有)”与“厥”而已。
又如今本《系辞上》“加乎民”的“乎”字,帛书《系辞》作“於”。张玲玲先生认为今本的“乎”为“於”之形讹[42]23。当然,说“乎”为“於”的形讹,应是“於”作“于”形。定州汉简《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乎学”的“乎”字,汉石经本、正平本作“乎”,阮本、皇本则皆作“于”,韦扬先生认为阮本和皇本的“于”为“乎”之形讹,因二字字形相近[43]。
以上两位先生的订改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知道,作介词是古汉语中“乎”的常见用法,其语法功能与“于/於”相当。各本的异文,只是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不同虚词的替换,没有必要认为是讹误字。如果“乎”“于”二字为讹误字的话,那么古书中“乎”“于”相讹之例何其多也。
对古书形近讹误字的校订,一定要考察二字的语法功能是否有相同的方面;如果有,二字的不同可能只是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两个词的替换,而不是形讹。
结语
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必须把握好一些准则,或者说应重视其中一些应注意的问题。不然,就极有可能将原本的正字改成了讹字,将本不是形讹关系的字当成了形讹字。上面所讨论的几个方面,是我们对学者在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希望为我们以后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提供一些借鉴,以避免不必要的失误。
[1]裘锡圭.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M]//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陈剑.说“安”字[M]//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
[3]陈雄根.《周易》零释[C]//古文字学论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4]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M].裘锡圭学术文集(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
[6]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7]陈送文.慈利竹书和《国语·吴语》对勘(两则)[C]//古文字研究(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
[8]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M].上海:上海书店,1999.
[9]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于省吾.释弘[M].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于豪亮.说引字[M].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J].考古,1963,(8).
[15]郑刚.战国文字中的“陵”和“李”[M]//楚简道家文献辩证.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16]郭永秉.续说战国文字的“夌”和从“夌”之字[M]//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7]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8]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C]//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19]扈晓冰.清华简《金滕》篇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0]罗福颐.史印新证举隅[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1).
[21]赵平安.秦西汉印的文字学考察[C]//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22]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79.
[23]高亨.古字通假会典[M].董治安整理.济南:齐鲁书社,1989.
[24]裘锡圭.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M]//裘锡圭学术文集(第4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5]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M]//金文文献集成(第1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
[26]牛济普.荥阳印陶考[J].中原文物,1984,(2).
[27]吴振武.释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官印[C]//中国文字(新24期).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
[28]施谢捷.古玺汇考[D].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29]黄灵庚.楚辞异文辩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30]苏建洲.出土文献对《楚辞》校诂之贡献[J].中国学术年刊,2005,(27).
[31]韩彦佶.汉印地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2]赵平安.秦汉印章与古籍的校读[C]//出土文献(第3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
[33]蒋文.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与解读[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34]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5]谢明文.《大雅》《颂》之毛传郑笺与金文[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6]张新俊.清华简《系年》“曾人乃降西戎”新探[J].中国语文,2015,(5).

[38]徐宝贵.关于金文“克明又心”及“保业氒秦”的释读[C]//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9]张新俊:《周易》新证一例——“厥孚”可能是“有孚”之误[J].开封大学学报,2005,(1).
[40]袁金平.新蔡葛陵楚简“大川有”一语试解——兼论上古汉语中“有”的特殊用法[C]//语言学论丛(第2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1]裘燮君.先秦早期文献中“有”字的代词性[C]//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42]裘燮君.“有孚颙若”考释[C]//语言学论丛(第2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3]韦扬.定州汉简本《论语》校读札记[J].现代语文,2009,(10).
2017-03-05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两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 15ZDB095) 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 批面上资助( 2017M610854) 的阶段性成果。
郑邦宏( 1985—) ,男,广东汕头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汉语史。
K877
A
1002-3828(2017)03-0094-07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3.15
(责任编辑: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