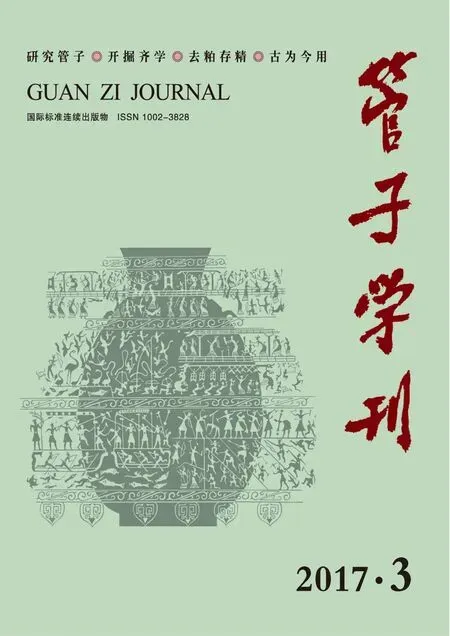先秦阴阳五行观念的政治展开:以稷下为中心
李 震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稷下学研究
先秦阴阳五行观念的政治展开:以稷下为中心
李 震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阴阳五行观念深刻地形塑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气质取向。在先秦,阴阳和五行原本彼此独立,各自经历了长期的意义演变进程,从自然话语一步步转为人事政治的法则,政治意涵不断丰富、增强并固定化,最终在稷下学中实现了融合。五行观念的一支与阴阳观念合流,形成了《管子》四时教令的体系,在哲学上实现了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恰当安顿;另一支则催生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阴阳五行影响下的稷下政治学说,构成了先秦政治哲学的重要形态。
阴阳;五行;政治;稷下
在秦汉政治原则和政治话语的构建中,纵论“天人之际”的阴阳五行观念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冯友兰先生指出:“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当时阴阳家之空气,弥漫于一般人之思想中。”[1]8事实上,阴阳五行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如此显明的政治维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展开过程;而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之学*关于稷下学的外延,学界意见不一。为方便讨论,本文参照白奚先生在《稷下学研究》中的分法,将以《黄帝四经》《管子》为代表的黄老、道法家言和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言统称为稷下学。参见白奚: 《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文化争鸣》,三联书店,1998 年,第67-68 页。,则可称为上述过程之枢纽。自古史辨以来,对于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观念,学者已有不少典范性的研究*例如: 梁启超: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顾颉刚编《古史辨》( 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343-362 页; 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古史辨》( 第五册) ,第404-617 页; 钱穆: 《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古史辨》( 第五册),第617-630 页; 陈梦家: 《五行之起源》,《燕京学报》,第24 期,1938 年12 月; 孙广德: 《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1-57 页; 乐爱国: 《〈管子〉的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管子学刊》,1994 年第1 期; 庞朴: 《一分为三: 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 年,第56-77、114-139 页; 王继训:《先秦秦汉阴阳五行思想之探析》,《管子学刊》,2003 年第1 期;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62-72 页。;但具体到阴阳五行观念如何从自然含义一步步展开为政治话语,以及这一演变过程的哲学根据,似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以稷下学为中心,分析阴阳五行观念政治意涵的发展脉络和不同观念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理解阴阳五行观念的复杂含义和先秦政治哲学的思想面貌,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战国时期论阴阳五行者不限于稷下,本文仅择取两种观念彼此有结合者加以论述。如《易传》言阴阳而不言五行,不涉及两种观念的结合,故本文从略;类似地,《五行篇》言“五行”但不言阴阳,且其论述已经逸出了原有五行学说的问题意识,本文亦不作讨论。
一、阴阳五行观念的起源与初步展开
对于先秦阴阳五行观念的讨论,须从厘清其源头入手。秦汉以来,阴阳、五行二说多并称并用,其实却各有源。我们先来看阴阳观念的发展轨迹。
(一)阴阳
根据学者的考释,甲骨文中已有阳字的用例,为地名;阴字未见。及至金文,阴阳二字都已出现,但尚未连用。这一时期的阴、阳,主要是作为地名、诸侯名和方向义而被使用[2]4-5。
传世文献中,阴或阳在《易经》《诗经》和今文《尚书》中已经有所出现。根据梁启超的考定,所有用例均指现象或形象之物,属于阴、阳的基本义和初步引申义,不具抽象意义,故“商周以前所谓阴阳者,不过自然界中一种粗浅微末之现象,绝不含有何等深邃之意义”[3]347。既然尚未成为一种抽象概念,这种意义上的阴阳也就不可能与政治发生某种固定的关联。
及至《左传》,情况开始有所变化。阴阳开始被连用,用来指称某种抽象的物质,并与人事相联系。如僖公十六年春: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4]1808-1809
在这则著名的材料中,叔兴认为阴阳是引发反常现象的原因;从其与宋襄公的问答来看,在时人的观念中,政治丧乱也被归因于阴阳的作用。但这里的阴阳究竟何指,尚不清楚。在《左传》后文中,阴阳的含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昭公元年医和答晋侯问,有“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4]2025之语,可知阴阳乃天所生之气。医和认为,阴阳对人事的影响在于“淫生六疾”,即其气过盛则会使人罹患疾病。
除了阴阳并举之外,《左传》中另有许多阴阳分言的例子,含义与此类似。如襄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4]1998
当春无冰,应寒而暖,故言“阴不堪阳”。由此言“宋郑必饥”,是用岁星位次和分野之说来判断人事吉凶。又如昭公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4]2106
据杜预注,日食为阴胜阳,水属阴,故梓慎以为将雨;而昭子则认为阴胜阳而不能尽克,郁积的阳气必然反来克阴,故言将旱。
总结以上诸例可见,在《左传》中,阴阳被看作是两种彼此对待的物质性的气,其对立运动关联着人事吉凶。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以阴阳言人事,往往是根据天文、天象或以天文、天象为佐证来立论;推测的内容多为偶发性、关键性的事件,如丧乱、饥荒、旱灾;推测吉凶的人物基本为史官或医官*上古巫史医卜之职相通,“推天象以明吉凶”正是巫史的职责所在。司马迁《报任安书》述西汉太史之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可以看作巫史之职的余裔。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2页。。这说明:在《左传》所记述的春秋时期,一方面,阴阳已经成为一种可用来描述天象的抽象的物质概念,并以“推天象以明吉凶”的方式参与到政治解释的构建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构建又是初步的、不成熟的、非常制的,因为阴阳所能解释的事件种类仍然十分有限,解释只用于“变”而不用于“常”,且相关解释并未主动、自觉地将阴阳消长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原则加以运用。
与《左传》相似,《国语》中也有以阴阳之气推定人事吉凶的例子,如伯阳父以“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5]26论地震与西周衰亡,等等。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与《左传》不同,阴阳在《国语》中具有了某种贯穿天道与人事的普遍法则的意味。《国语·越语下》载范蠡答勾践语:
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5]578-579。
将“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作为一种行政的原则,表明阴阳被看作天地的法则,能够且应当被应用于人事政治,成为理政用兵的标准。“因以为常”的说法更强调出这样一种意涵:阴阳不再仅仅是判断偶然事件的根据,而成为了行为的固定准则与施政的基本模式。《越语下》又载范蠡论兵法:
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5]584-585。
在这里,阴阳消长既是天道盈虚的本质,同时也是攻守的依据和进退的范式。“用阴”“用阳”“阴节”“阳节”说明,阴阳已经成为兵法谋略中的固定概念,其含义与强弱、刚柔相近。范蠡所论兵法在具体内容上可能远有所本,未必是直接由阴阳观念演绎而来;阴阳观念在兵法中的应用,更像是对既有兵学经验的理论总结和重构。阴阳对兵学的重构表明,作为天道范畴的阴阳已经被有意识地运用于人事的实践中,成为一种固定的行为原则。这种“本天道以立人事”的思考方式,与《左传》“推天象以明吉凶”的方式已大有不同。后面会看到,稷下之学强调刑德须与阴阳相应,在一定意义上正可看作范蠡之说的延续与发展*如果我们相信范蠡化名陶朱公而居齐的故事,那么,这种延续性便更多了一层实证的意味。。
(二)五行
所谓五行,指金木水火土。既有研究指出,金木水火土虽然已经部分地出现在了甲骨文和金文当中,但五者并提的说法和五行的概念此时都尚未成型[2]19。目前可见最早言及五行的例子,是《尚书·甘誓》和《洪范》。《甘誓》载夏启语: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4]155
《洪范》载箕子答武王问: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4]187-188
《甘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含义难解,梁启超疑当解作“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3]350。我们认为,《甘誓》“五行”的提法仍与金木水火土有关,但可能主要是指五行之官或五行之祀,这在下文可以看得更加明确。
与《甘誓》相比,《洪范》的意义显然更加清晰。所谓五行,孙星衍引郑玄注云:
行者,顺天之气。
又引《白虎通·五行篇》:
五行者,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6]294。
五行即指天地所生的五类“气”或自然物,因其流行,故谓之“行”。我们注意到,与阴阳不同,五行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某种与人事无涉的纯然的自然物,而是生活生产所需的物质材料和基础。《洪范》在历数五行的名称后,又列举了其特性和味觉,正是指出五行在人伦生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的生产作用。这提示我们,在《洪范》中,五行与其他八畴一样,并不简单是对于自然的客观解释,而是“彝伦”的一部分,是建构合理的人伦秩序所必须使用和安排的事物。五行得当与否关乎人事兴衰,人君如能合理安顿五行,则“彝伦攸叙”;如不能,则五行汩乱,“彝伦攸斁”,君王“殛死”。
《左传》亦言五行。与《尚书》相比,《左传》进一步明确了五行为人所“用”的意涵。郤缺以水火金木土与谷并称六府,子罕所谓“天生五材,民并用之”[4] 4008、4336,皆属此例*关于五行与人事的关系,《国语》也有所说明。《国语·鲁语上》载展禽之语:“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更重要的是,《左传》特别突出了五行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答赵简子云: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4]2107-2108。
这里,五行被认为是天地所生,理想政治植根于对于五行的恰当使用的基础之上。五行具体地表现为五味、五色、五声,执政者通过祭祀、服饰、音律等方面的礼乐创制,对五行加以合理利用。这种利用同时也就是对于人伦秩序的成就,五行与人事政治明显地勾连在一起。
在《左传》的另一处,五行被明确地与官职、祭祀关联起来。昭公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献子问,云: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4]2123-2124。
按照蔡墨的叙述,夏商以来,五行之事各有官掌,掌事之官称为五行之官或五官。五官称职,则“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甘誓》所谓“威侮五行”,当即指凌侮五行之官而言。如果说前引子大叔之语体现了五行观念在春秋时期政治观念与事务中的影响,那么,此处蔡墨的说法则更加凸显出五行观念对于当时宗教意识的塑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1911,我们可以说,在稷下学出现之前,五行观念已经深入到了人伦生活的核心层面。
除了上述政治和宗教意涵之外,春秋时期五行说的另一发展,在于五行次序观念的明确出现。庞朴先生曾列举出历代典籍所见五行的九种次序[7]127-128,其中最为重要且与稷下之学关联紧密的,是五行相生、相胜两种次序*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前引蔡墨“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即五行相生之序的变形;而《左传》中以五行占星的例子以及《孙子·虚实》[8]125-126与《墨子·经下》[9]319“五行无常胜”的说法,则为五行相胜之序提供了佐证。这些材料表明,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五行相生相胜观念。
五行相生与五行相胜两种次序的理论意义,在于充分揭示出五行概念内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后世五行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展开,正是这一内在丰富性的具体化。下文可知,战国稷下学中两种主要的政治学说——四时教令与五德终始——即分别以五行相生和相胜为其理论范式。这表明,尽管春秋及以前的五行观念尚较为初步,五行在人事政治中尚未获得足够丰富的理论展开,但其基本内涵已然具备,这就为五行观念在稷下学中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阴阳观念的合流提供了基础。
以上,我们梳理了阴阳五行观念从产生至春秋末年的意义演变趋势,重点突出了其中政治意涵的展开过程。阴阳、五行的本义均指自然事物,但在演变过程中,二者与人事政治的关联逐渐增强:阴阳首先被理解为作为天象基础的物质性的气,用以推定人事吉凶,进而被认为是贯穿天道人事的普遍法则,成为了固定的政治行动原则和施政模式;五行被看作人伦日用的基础,参与了政制设置和宗教观念的建构,并表现出相生相胜的秩序,这种秩序为其进一步的政治展开提供了前提。可以看到,在阴阳五行观念长期发展、政治含义不断展开的基础上,一种新的、综合性的政治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二、稷下学中阴阳五行观念的政治展开
将关注点从春秋移至战国,我们可以发现:阴阳五行观念在政治上得到了更加普遍的施用,并逐渐走向合流。这一特征在齐地稷下之学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一)阴阳与五行的合流
稷下学阴阳与五行的合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阴阳、刑德和四时之间建立起系统的关联;然后,五行通过四时与阴阳相配。其间,阴阳五行学说如何一步步展开其政治意涵,值得深入分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
前引《国语》范蠡语已经显示出将刑德政治与天道阴阳相对应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早期黄老学文献《黄帝四经》中表现得更加明确,并获得了宇宙论的支持。《十大经·观》云:
黄帝曰:群群□□□□□□,为一囷。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刚柔相成,万物乃生,□□□□□□□[德虐之行],因以为常。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10]210。
“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的说法,显然是承前引范蠡语而来,德虐即所谓德刑。二者关键的不同在于,《黄帝四经》为范蠡语补充了宇宙论的背景。“道分为阴阳,离为四时”的说法,让阴阳的天道背景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而也就增强了刑德政治的合法性。事实上,将以阴阳学说为代表的道家宇宙论与现实的刑德政治相联系正是黄老学的重要特色。如果将前者所代表的自然秩序称为“自然法”,将后者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称为“实在法”,可以发现,《黄帝四经》为我们呈现出的,正是“自然法”与“实在法”彼此区分而又相互关联的图景[11]429-430。
以完备的宇宙论为背景,《黄帝四经》提出了更为系统的阴阳刑德理论。《经法·论约》云:
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10]166。
《十大经·观》亦云:
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得后刑以养生[10]217。
在《黄帝四经》中,刑德与阴阳在具体的四时中得到了落实。四季刑德的循环体现着阴阳的终始,或刑或德的政治施为都根源于天道阴阳的自然节奏。阴阳的原则贯穿在自然与人事的各个方面。《称》云:
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妇姓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10]394。
可见,阴阳刑德理论的实质,是以阴阳的尊卑消长为基础,重新定义政治秩序,并为生活于该秩序中的包括君臣、上下、男女、兄弟在内的所有不同角色的个体确立新的身份、属性与行为准则。这时的阴阳,已经不必再借助天文、天象来预示吉凶祸福,自身就成为了治国安邦的大法宏谟,“自然法”获得了“实在法”的实存。
《黄帝四经》中刑德与阴阳的四时对应,在《管子》中发展为“四时教令”的系统。《管子·四时》对于刑德、阴阳和四时的关系作了透彻的说明:
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12]838-858。
阴阳是天地的大道,四时是阴阳的表征,因此,刑德必须按照四时终始而运作。根据这个逻辑,人君在一年中每个特定的时间都有应做与不应做的行为,这些规定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四时教令的体系。《禁藏》篇云:
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糱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颉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12]1017-1018。
上述教令是对前引“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的具体化和丰富化。相较于《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之说,《管子》的四时教令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阴阳观念从抽象的治国原则发展为具体繁复的政教礼俗体系。如果说《黄帝四经》“春阳秋阴,夏阳冬阴”的立说重点是由具体事物逆溯其阴阳属性的话,那么,《管子》四时教令的思路则恰恰相反,乃是从阴阳四时的根本原则出发,建立起具体而普遍的秩序,实现对于万事万物的照料与安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禁藏》“(春)发五正”“夏赏五德”“秋行五刑”“冬收五藏”的说法已经具有了将刑德、四季和五行配对的意味。至此,阴阳与五行合流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只是五行的名目尚未提出。到《四时》中,金木水火土明确出现,阴阳与五行终于通过四时实现了更为明白的对应: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此谓星德。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此谓日德。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此谓岁德。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此谓辰德。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此谓月德[12]842-855。
四时各配木火金水,土遍辅四时。到此,阴阳、五行已经通过四时实现了合流,开始融于一体。
阴阳与五行在《四时》中的合流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文本上看,《四时》容纳了阴阳五行的基本要素,秦汉阴阳家言在此已初具雏形;另一方面,更重要地,从哲学上看,《四时》通过阴阳五行的结合实现了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合理安顿。
阴阳刑德理论以及由之发展而来的四时教令体系中始终存在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问题:四时教令整体是普遍性,特定的某一时及其教令是个别性。二者所代表的,其实是统一的政治秩序与该秩序下殊方异俗的民众的关系。然而,在《四时》之前,个别性本身的存在并未在哲学上得到论证。在阴阳刑德的话语中,由于阴阳相较于四时更为根本,特定的某一时及其教令不仅不能确立起自身的自足性,相反,在“春阳秋阴,夏阳冬阴”这样的叙述中,四时各自的个别性反而被化归于阴阳的普遍性之中。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异时殊方的民俗不能确立自己根本的独特性,据此制定的教令法度无法论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相应地,普遍秩序也就无法在理论上使民众与事物获得符合其自然的安顿。这样一种政治学说显然不够理想。
《四时》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引入德的概念而实现的。就个别性而言,德乃“物得以生”[12]770者,是万物之“自然”。四时各有其德,也就意味着每一种季节、气候乃至政令、民俗与秩序各是一“物”,有其区别于他者的内在的、固有的特质,不同的德或特质就划分出不同事物之间的边界。德既然是物得以生的特质,也就必然是自然且合理的,这实际上就为植根于自然秩序之上的各种不同的政令方式确立了自身的合理性。就普遍性而言,德又是“道之舍”[12]770,具体事物的特殊性在根本上只能来自于普遍性。这样,作为物得以生的特质的“德”,就与作为普遍性的“道”关联在了一起。“道”与“德”的关联具有鲜明的道家形上学意味。如果说《黄帝四经》中的“道”与“法”只涉及治理方法与其形上根据的联系,那么,以《四时》为代表的“道”与“德”则凸显出道家政治思想中更为根本的思考路径和价值取向:治理之“法”的制定,必须以成全作为事物之自然的“德”为前提,而全部个别性的“德”的充分实现就是普遍之“道”。《管子·四时》提出“德”的概念与“道”并举,无论是在概念形式还是政治意涵上,都是对此前阴阳刑德学说的重要改进。
需要说明的是,《四时》所见阴阳与五行的融合尚较为初步。这是因为,此时的德与五行之间尚未建立起根本性的联系。具体说来就是:四季所对应的五行实际上并非五行之德,而是不同时节所生的五种具体事物*这里,“土德实辅四时”的说法颇为可疑。从上下文看,木火金水皆不与德连言,而土独言之,作“土德实辅四时”,与下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重复。“土德实辅四时”的说法更像是涉下文而衍出之语。;相应地,《四时》中的不同时节之德,也还不是五行,而是日月星辰岁;此外,在四季之气的层面上,与阴阳并列的还有风与寒。简言之,阴阳与五行的对应,仍有待于德的中转。尽管如此,《四时》篇仍然开启了阴阳与五行融合的基本模式。相较于日月星辰岁这样渺远的天体,金木水火土五行天然地更易为人所感知,更适合被作为事物个别性的德的代表。因此,自邹衍和《吕氏春秋》以降,五德(四德)总是明确地与五行(四行)关联在一起*《吕氏春秋》以“盛德在木”“盛德在火”“盛德在金”“盛德在水”论述四季及其教令。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8、85、116、156页。,阴阳与五行的结合也就真正定型。应该说,这是《四时》阴阳五行说自然的逻辑结果。
(二)四时教令与五德终始
在《管子·四时》中,先秦的阴阳五行观念已经基本合流定型。然而,单就五行观念来说,其复杂意涵与政治应用至此并未全部展开。稷下学后期出现的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为先秦五行观念补充了重要内涵。
我们注意到,《四时》所表述的四时秩序,在政治上被应用于日常行政。不同时节、不同政令之间,是流转相生的关系。相应地,其所对应的五行次序——木火土金水——也是五行相生。如果将行政改为鼎革,五行相生改为五行相胜,那么,不同形态之间就变成了彼此相克的关系。这就是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3]2344。
按照邹衍的排法,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继周者得水德[14]284;各代之德象征的是其所独有的天命与统治秩序,后起者推翻前朝,如木克土、金克木,乃是天命所定。如前所述,五行相生与相胜的关系在春秋时已经出现,但两种关系的政治意涵在当时尚不明确。如果说以《四时》为代表的四时教令为五行相生关系提供了现实应用的话,那么,五行相胜则是通过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才显现出自身的政治意味。在这个意义上,五德终始之说可说是完成了五行学说自春秋至战国的发展逻辑。
五德终始与四时教令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五德终始所谓德,同样是指事物的独特性,与四时教令中的德相近。对于四时教令而言,不同时令的秩序各有其“德”,统一于君,君有统一的“道”;对于五德终始来说,不同朝代的秩序各有其“德”,统一于天,天又统一的“道”。看起来,两种学说的区别只在于观察的层次和角度不同:君主变革政事,正如天更革君主。然而,二者的基本精神却有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即在于究竟是承认人的主动性,还是将其委之于天。四时教令承认施政者能够且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来调整政令,以造成合理的政治秩序;但五德终始则认为,一种施政者有其天命所定、不可改变的施政方式与政治秩序,不同秩序间的转换只能依赖于天命的改换、五德的转移,不能也不应由施政者自主决定。因此,五德终始之说在逻辑上必然拒斥统治者按照四时教令随时因革其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学说根本处的张力。
四时教令与五德终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在《史记》的描述中,秦始皇遵从邹衍之说,“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方今水德之始”,应当“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3]237-238,秦遂以是灭亡。《史记》将秦代苛政完全归于始皇对五德之说的迷信,不免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但推究其根源,秦执苛法而不知变,也确与五德终始说的根本精神相合。在秦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四时教令对于政令典礼和君主行为的塑造,却再难发现五德终始之说真正持久地体现在一个王朝的施政当中。五德终始的思想几乎仅仅出现在改朝换代的谶纬符命里,而这大概正是邹衍最初发明此说的用意所在。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孙广德.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M]. 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
[3]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C]//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8]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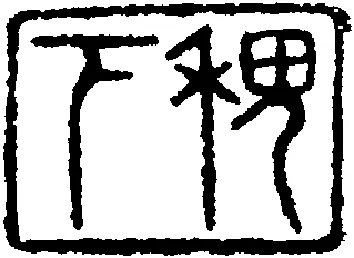
B227
A
1002-3828(2017)03-0042-07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3.07
2017-07-03
李震( 1989—),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
(责任编辑: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