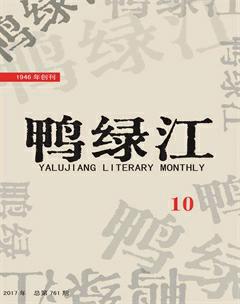杭州流水
钱红莉
去杭州的动车上,毗邻的女孩,一直在解题,她学的可能是理工科,那些稀奇古怪的字母、公式,我一点都看不懂。夕阳的余晖里,她笃定地演算着,浑身上下散发出纯洁的静气……
一
到杭州东站,排队打车,足足花去一小时。仅仅二十分钟到酒店,推开车门,泡桐花落到我脚上,自是异样……
于酒店附近绍兴小酒馆吃了两菜一汤以后,实在疲倦困顿,回酒店休歇一小时。出门三点多了,坐12路车,历经一个多小时,到达一公园,欲近黄昏。天上堆积着灰云,风越来越大,岸边有人拉胡琴,穿旗袍的老年女子唱越剧,滴血一样的凄厉,把西湖都吵死了。盛世一样的喧嚣,让人颓然地坐在水泥阶上,实在想哭。
叫师傅送去小孤山,价钱谈好,临了,他又改主意,说是要下班了;满觉陇更是去不成。他们个个精明而世俗,一齐杂七杂八点拨道:现在堵车厉害,送你去了,天就黑了。末了,又集体嘲笑道:那里是乡下哎,有什么好去的咧,不好玩的……
他们真是不懂。
前面不远处是雷峰塔。那么多的人,东方人,西方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热恋中的情侣,淡漠的中年人,一齐在湖边流连。我作为最不起眼的一个,形容疲倦地随着人流移动……好傻。
当你一路行来,原本心里面储备了很多东西的,却一次次地错过,不能与之共情,怎么不沮丧?
——当来到这个南宋的文化中心,当你心中布满苏东坡、范宽、夏圭、马远们,然后,眼巴巴看着他们流逝了。这个地方,可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山水格局,启启合合间,历经几个朝代的兴衰沉浮,依旧在这里。纵然人都不在了,他们的诗篇、画作依然永恒不灭,与山水同在。
去年秋天,夜里与几十人同游白堤。今年来,希望有时间走走苏堤,还是错过了。展开西湖平面图,苏堤距我的位置颇远。天快黑下来,走是走不到的。
怎么着也得去西湖上浪荡一圈呀。买了一张去瀛洲岛的票,不及十分钟,到了瀛洲岛。人山人海,反而衬得这座绿意丛生的岛更加荒冷,沿四周步行一圈,实在倦乏,静静坐在石阶上望水,望山——
这眼前山水,虽说是令人热爱,但,更多的是一份孤高峭薄,再往纵深处回溯,颇有那么一点精神上的自苦……不然,你来西湖作什么?早年,读贾平凹一本随笔集子,他劈脸来一句:西湖,不过是一摊水而已。那个时候,读到这样的句子,好吃惊。如今,西湖,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摊水了。我所热爱的子瞻兄,曾两次来这里做官,第一次:1071年到1074年,他做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第二次:1089至1091年,又是三年,这次做的是杭州知州,相当于市长的位置了吧。古代读书人牛就牛在这里,不仅诗文写得好,官也做得体面圆满,不比当今政客,胸无点墨,再看看王维、张九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们,哪一个不是心有格局之人。
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适逢西湖水患,他遣人梳理西湖,将挖出的淤泥和水草堆成了一个坝,便是被后人命名“苏堤”的那个坝,如今,人人踏上去,顿觉风雅。说白了,那是苏东坡的政绩,未承想成了后人吟风弄月之所在。苏堤比白堤短得多,那一段有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春天去走那一段,最是适宜抒怀。这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水一山,以及你心心恋慕的人,相互倒映,彼此托衬着,也算得到了一个圆满。
将这个堤坝围成以后,子瞻兄本人也是颇为满意的,诗云:
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
坐在瀛洲岛上四望,天色灰沉,特别契合了他这一句——老葑席卷苍云空。恰好,我坐在“三潭印月”之三座小石塔附近。它们在水里,我在岸上,如何够不着它?什么叫镜花水月?这就是。黄昏的风越来越大,吹得湖水起了涟漪。喉咙里被呛着一口口的冷风,一直冰到脚底。抱着膀子与眼前这三座小石塔对望良久。这三座小石头建筑,玲珑有致,怜俜可爱。倘若深夜点一盏灯,与星空辉映,然后,你在这星辉斑斓里放歌,何等辽阔无边。苏杭的意义,悉数包含在风月无边里。这三个小玩意儿,恰便是子瞻兄当年遣人打造的,也是为着泄洪排污之用。千年过去,一个暮春的黄昏,迎来成千上万游客在此驻足流连,小小的我,作为子瞻兄的知音,此刻,僅有的唯一的知音,恰好随着人流浪荡至此,原本意兴阑珊(因时间的关系,没去成满觉陇、小孤山,情绪一直低落),未承想,误打误撞,还是遭遇到了男神的遗迹——是的,子瞻兄一直是我的精神偶像,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他,特为将孩子取名“子瞻”,向他致敬——这个名字曾不止一次遭到同事耻笑,她说,你一个写文章的,取什么名字不好,偏要照搬苏东坡的,太没想象力了。
是的,在偶像面前,我们变得矮小,甚至自卑了,何来想象力可言?孩子很小的时候,坐在澡盆里唱《水调歌头》,音起高了,渐渐地,拔不上去,瘦瘦的脖颈上青筋暴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么多年以来,每天早晨,他一睁开眼睛,我们就把小录音机开着,以唐宋诗词喂养他,不晓得日后他能记得多少,只盼望,有光照到他的心上,有所陶冶与浸润,长大后不要成为一个满腹铜臭之人。我们不能给他留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套房产,只能引导他一条精神路径。这样的一条小径,也是可以通往无限的。
二
宋(无论北宋抑或南宋)在我眼里,恰似那日西湖的天空,也一直是灰沉沉的,但,西湖这样子的山水格局实在令人流连——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谁会想到,就是这样温软清逸的自然环境,成就了南宋文明的巅峰?无论绘画领域,还是科技、医学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超越了盛唐。
酒店书吧间,一眼瞥见蒋勋的书,拿起来随便一翻,就是南宋的那些画,他一点点地分解,字字入心。一直在储备,将来有机缘,希望可以写写范宽他们……蒋勋一直是我欣赏的那类作家,他的功力在于随时地点拨你一下,让你惊叹,哦,这样子啊,一下豁然。这个人堂廓广深。
于12路车上慢行,偶或看见欧米伽专卖店,细青砖勾白缝的外墙上,开了一面巨大橱窗。年轻时看朱天文小说,女孩子跟男友分手后,忽然有一天,想起什么,哭着走了好远的辛苦路,在基隆河边,把一块欧米伽咕咚一声丢进水里。曾想,女孩傻啊,典当掉也好,可以换回几季的裙子……endprint
现在,终于明白,应该丢掉。自糊涂到明白,中间得历经几十年的光阴岁月。而,生命里许多的事情,都是被我们的混沌不清费掉了的。
去一公园对面的丝绸店,一条长裤两千多,实在买不下手。但,也不失落。物质的东西,可无限拥有,也可无限放弃。人生并非吃饭穿衣,还要建立精神的广厦,一个小小的“我”,居在里面,方不为外物所动。这样你会强大一点儿,外物纵然夺人,但不足以击垮你。
晚餐,依旧去了中午那家绍兴酒馆,叫老板娘下一碗青菜面。小妹端来一大盆,足够三人吃。虽不合胃口,也勉强吃了一小碗。临走,她送我一小袋抗过敏的试用装,叫买一元钱的那种矿泉水稀释一下涂脸……走在路上,泡桐花还在路灯下开着,那些紫花与白天的两样,散发出夏天花露水的香味,让人想起童年,有微微的远意。酒店旁是枯树湾巷,安静极了,路灯把人影拉得好长。在影子里,慢慢地走,慢慢地走……
那么,杭州,这座南宋的文化中心,我也算是来过了?
三
翌日,起得早,餐罢,离出发时间尚早,自酒店出门来,右拐,去菜市转转。最喜欢去陌生的菜市,那里是生活的根部,让人踏实喜悦。这个世间,似乎没有几样东西可轻易把我带到快乐之境,不知是缺乏自我快乐的能力,还是心如死灰沉疴积厚?
有人在剥黄泥笋,润白润白的肉身,目测,大约来自天目山。我若在这里居下,会买五六棵黄泥笋,跟火腿同煨;再买一把西芹,两斤淡菜,养在洗菜盆里,滴几滴芝麻油,把泥沙滤掉,老蒜瓣拍拍好,爆炒之,偶或激点花雕酒,火光四射,俗世里最殷实的日子。搬只小木桌,放到门前泡桐树下,与孩子一点一点地剥淡菜吃,微微的腥气杂糅在泡桐花的芬芳里,阳光筛下大片浓荫,四月的风吹着你,快要睡过去了。
每日清晨,拎回几棵笋,坐在泡桐树下剥剥,紫花落了一地,两只脚都没处搁,全是花——在花香里剥笋,过自己的日子,平平凡凡,落落大方。银杏叶那么绿,在晨曦里微微晃动,小鸟嘀嘀咕咕,偶或风来,带回槐花的清香。
毗邻的绍兴酒馆里,正炖着黄鱼,西湖醋鱼也会做的吧。刚到的那日午餐,小妹推荐一盘回锅肉,因为不辣。回锅肉里点缀着红椒青蒜,好看得不得了,还有干子。杭州的干子蛮可口,我一人把两菜一汤吃掉大半,临了还吃下一盏饭。
去千岛湖,车过钱塘江、富春江,江水浣浣,船只三两,横斜江面,江岸满目郁葱。路过钱塘江,你会不自觉想起,子瞻兄的句子——我在钱塘拓湖渌。自信,而意气奋发,这个才华绝伦的人,踏实又能干。
富春江镜子一样,如此清澈,叫人看了又看。这些大地上的支脉,慢慢淌着淌着,最后都是要入海的。我现在的生命勉强算得上一条支流,浅,薄,弯,无可厚重——可是谁不曾做个天才的梦呢?天才就是抵达大海,我们一直走在去大海的路上。
沿途的山有层次感,有音乐的流动,简直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协,满目流动着的春天气息,山竹的泛黄旧气里,也埋伏着苍松的新。覆盆子开花了,洁白的小花开了一路。泡桐,苦楝,梦幻一样的紫花低垂,望之蕴藉。
沿途的那些山,不愧为流动的古典音乐,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地推进,是看不够的。黄公望令富春山不朽,富春江令黄公望圆满,二者相互成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在自我成全。
四
到得千岛湖,吃过中饭,稍微休息一阵,便去游湖。春天的湖,与秋天的湖自是两样。天气晴朗,视野愈发开阔,随便坐在哪一处,都得朗朗清气,是那种直见天地的辽阔,仿佛一直给你远景,不停地往空阔处推着镜头,湖水一如昨日,清澈无垠,有海的壮阔。我站在岸上,一次次看见了空无——远山、近水都退了去,眼界里空无一物。是把我自己都清空了的——你心里有什么,眼里就会见到什么——眼界是一直受着心灵制衡着的,以及你的心性和格局,皆受制于灵魂。泡桐花在湖边静静地开,静静地落。
人少,坐的是快艇,可抵达至不一样的幽深,穿过狭窄的镜子一样的湖面,孤岛一座座耸立,伸手可触。岛上临水处,全是花——覆盆子和山杜鹃,美得叫人尖叫。山杜鹃的红,有乡野之气,但,不伧俗,被湖水比衬着,特别雅致。那种红,没有语言可以精准地形容,比喻也不行,范宽、牧溪们怕也都调不出来的。这种红是一种险境的红,汉语对它无能为力。玫红,肉红,橘红,都不是,谁叫是天和水给它滋养为它调色呢?在这种山杜鹃的红面前,怕是连汉语都要丧失掉自信的。
还有覆盆子,这种鲁迅笔下出没的植物,原来并不都开在他家后院里。这次,是开在了一座座孤岛上,如此高洁无尘,仿佛一生中只愿开在水边,一蓬蓬地,素洁贞静地开,孤清,独自,近似于小津的电影气质。待小艇走远,再回头看它们,原来,也是有着热烈的,那种洁白无邪,仿佛是把整颗心都捧在手上送给你……你又总能辜负呢?日后,久居都市的你,会一直记得它的纯洁,彼此纵然不着一言,但,到底遇见过。
遇见,就是无言的美好。
天,地,人,自然,浑然一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四季的更迭中,默默生长,到了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子,简单,混沌,淳朴地轮回着,是湖水把我们连在了一起。一湖的翡翠被发动机变成了碎钻,飞溅在舷窗上,一路跟着我们,在斜阳的余晖里闪亮夺目——湖水倒映出的光,是天堂的光,摄人心魄,无法忘怀。
台湾人常常说的一个词是——惜缘。惜缘,莫非珍惜眼前?
会一直记住这晚春的覆盆子、山杜鹃以及湖水,它们都是为我开,为我清澈的。
这人世,何等复杂纷繁幽暗,每想起远方的山花、湖水,一颗也曾沐浴过光芒的心,会一点点地变得纯粹起来。
五
回到合肥,屡屡想起西湖的格局。西湖之上,哪一处不是匠心独运?只有退回到合肥,再去复习它的山水格局,一草一花一木……方凸出它的舒豁美好。随便站在瀛洲岛哪个位置上,皆可看见四枚明月。花木葱茏,尤其含笑,一直以为是灌木科,但在瀛洲岛,它们长成了树。满枝花朵,远望,月白一片,待近了看,却是米黄色系,甜香扑鼻;蔷薇正盛,临水处,三串两串……少不了鸢尾,繁缕,在路边等你,直至没了你的脚……
游人如织,打破了瀛洲岛的平衡。倘若深夜,划一叶小舟去,更能体味出别一种意境,孤清的,独自的。四面被渺茫的湖水围困,偶有禾花雀。西湖的麻雀比别地的消瘦些,毛色发亮,大约源于诗性的养育,山水不但令人有不同姿态样貌,甚至可以把鸟儿塑造得富于气质。一直喜欢瘦的东西,瘦是一种诗性的气质,弱态之美。
大华饭店那一带,如梦似幻。一架水泥廊檐,攀了木香,简直繁花弥天,开得何等迷醉——在这架辽阔的木香面前,我就是帝皇啊,除了拥紧江山以及众多美人,寡人我只能想起一句诗来——木香戚戚雨沉沉。
湖畔那些柳树,同样端肃而干净——西湖边的树木仿佛都有来历,与别地不同,底蕴深厚些。它们在漫漶的岁月里一点点地储备了许多东西,自是不同氣质,甚至青砖缝里长出来的草,跟别地自是两样;那些姿态横斜的石拱桥,一律天青色,修在什么位置上,你走上去,远望,一湖茫茫之水,萦绕的,流动的,处处清奇骨骼。多少代人,做文章一样,孜孜以求慢慢建立起来的一处所在,总是给你画面感,有景深、层次。那山,那水,以及整个的景观,酷似宋元以来的一幅幅画,有册页窄轴,更有写意泼墨。湖水空茫,仿佛大片留白。这留白似乎成了中国人的哲学观,空无一物,实则应有尽有。小荷渐渐浮上来,一公园那里虽极度喧嚣,但,看着湖里这点点荷叶,心会静下来。暗紫色系的新叶,在风里荡漾——四周被市声嘈杂围困,反而显得静气,分明一幅幅写意小品,好能压得住阵脚。
西湖整个的气质,让人说不好,就像忽然遇见一个人,往那儿一站,没有来由地,你便倾倒了,是家传的修养,富于内敛、含蓄之美,纵然未曾开口,却也能令人捕捉到一种独异的心性。
西湖是有格局的,适合久处,慢慢地,你原本晦暗的灵魂会被它照亮,也是彼此成全吧。
虽只在局部停留二三小时,但,永远忘不了,那种美会在日后一点点地被释放,让你心仪,不能放下,然后有了苦恼。不能拥有,所以苦恼。
不如放下,过眼前的日子。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