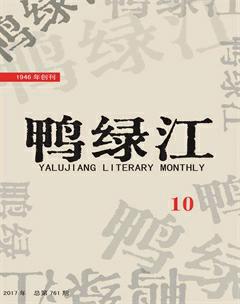缝缀碎片的情绪
高维生
都怪那个梦
我必须站起来,伸出手拽窗帘,它在移动中,把缙云山挡窗外。
午休不过半小时,被电钻的轰鸣声吵醒,尖锐的声响,带着锋利飞来,在空中高速旋动,一圈圈地荡开。这么厚的水泥墙,也未能阻挡它的侵害。我躺在床上,回味暂短梦中的情景。抓住每一个细节,分析梦的出现是为什么?
起床后,拉开窗帘,亮色涌进来。我到阳台上,读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命运》,“它那精神的眼睛都不能划出地平线的远方,在俄罗斯灵魂面前敞开着。在寻找真理,绝对的、神性的真理,希望拯救世界,让万物朝向新生命的复活的火焰中,俄罗斯灵魂正在燃烧着。”哲学家对任何事物的观察,不会是常人的感受,他提出的灵魂,不是小灵魂,而是一个民族复活的火焰,不是为了观赏,放的斑斓的焰火。火焰和焰火,一反一正,但品质上不同。它们在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结果大不相同。读到这时,身后云华路上的噪音背景,发起一轮轮的噪音攻击,583路的小公共汽车刚过去,585路的大公共汽车刹车声,摩托车吓人的轰鸣声,在身后交织污染。它们似乎过狂欢的噪声节,轮番比试看谁的声音大。它们犹如锃亮的钢刀,逼人的寒气切割寂静,一块块地抛向空中。
我发现书上落下一根白发,可能手拂时碰掉的,瞅着枯叶一般的白发,明天是中秋节,远离家乡和亲人,有说不清的滋味:
时间的皱纹
刻在记忆中
当我的头发渗出年轮的苔藓
银丝中染上等待
胃口变得迟钝
一点的食物
维持生命的存在
只有顽强的激情
仍然火焰一般地燃烧
取出一条焰
点起黄昏的回忆
照亮赴约的路
有一天
我们都会老去
一起去看黎明的日出
修整自己的情绪重新阅读,让俄罗斯的精神,缝缀碎片的情绪。
三点钟一过,我打开电脑,准备修改《触摸佛多妈妈》。电脑工作得正常,改稿较顺利,未遇什么难题。生活中的事情无法预料,突然发生的事件,弄得措手不及,不知怎么应对。光标有节奏地移动,咔一声响,电脑关闭黑屏。我瞅半天屏幕,触摸键盘的手指,似乎向它提出疑问,摁几下启动开关,没有一点反响。拔下电源连接线,再重新插上,电脑还是不见动静。我忙出一身汗,左拍右摸,无任何结果。
电脑是在游行示威,提出强烈的抗议,逼我做出圆满的答复。这台电脑是几年前,父亲送我的礼物,当时在笔记本电脑中,算是价格比较贵的品牌。它来到书房,并没有得到器重,因为我写作用台式电脑,就把它放在一边,偶尔使用360帮它消毒,使用一下。有一段时间,台式电脑坏了,我就用它写作,很长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后来又买台式电脑,它再次被冷落。这次来重庆,我只好携带它,看出它的特点。矛盾是一对冤家,不会轻易地化解。电脑记仇,几年积攒的怨气,无地方发泄,偷偷地做出复仇的准备。我来到不几天,它不正常工作,弄得我心绪大乱,而它又变得温顺听话。
今天电脑的脾气大发,进行强大的报复。我来到北碚,开始写缙云山笔记,写出的文字在文档中,一份没有复制。如果电脑真坏了,二十多天的工作全部白费,丢掉的情感,不是一句话收回的。我绝望地盯着电脑,很想攥起拳头,一下子砸去。电脑不知道,我是有思想的人,想尽办法处理它,打掉抬头称霸的念头。
每一个键都变成敌人,手指每天摁动它们,传达我的体温和情感。我怀疑是A键,它在英文字母中排第一,起领头的作用。它要掀翻我的统治,对下面的弟兄发出命令,它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机械体制中,个性是被淹没的,服从不能违背。我必须找出嫌疑犯,让它顺服人的命令。我的指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不容忍任何东西争权夺位。
坐在阳台上,一肚子窝囊气,无处发泄。我责怪自己粗心大意,不复制移动硬盘里,也怪午休时那个梦的出现,要不然这件事不会发生。
远处的缙云山,笼罩一天的浓雾,一点点地退去,露出狮子峰的原形。一股中药味飘来,不知谁家煎中药,味道十足,冲进鼻孔中。虫鸣一阵欢叫,很快被云华路上,跑过的汽车吞噬。
楼下有人说话,说的重庆话,我一句没有听懂。
高淳海从学校回来,看我的情绪不高,问发生什么事情。我把电脑罢工的事说出来。他拿起电线检查,所有的线都拔出,然后再接上。重启的电脑竟然屏幕亮起。我问到底什么原因,他说交流电源适配器和电脑接触不好。我看那家伙一眼,不是A键领头闹事,而是它在干坏事。
危险的袭击
绝不是一般的声响,巨大的炸裂声,撕裂潮湿的夜空,将房间的静摧毁,碎片在我的身边乱飞,甚至散落周围。我承受不了意外的刺激,从睡梦中惊醒,第一个反应向窗外望去。
一道闪电空中窜动,打开冰冷的寒光,随后又是一串炸响。闪电的大锤,在天空的铁砧上,锤炼黑色的灵魂。
我发现没有关的窗子,它是背叛的奸细。平常是我愿意待的地方,对它格外照顾,它的墙壁有半米厚,所以窗台变成工作台。电脑和小桌子,一些书及吃的药摆上面。我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楼前小区的草坪,“寄北酒店”的大楼,一座二十多层的米黄色居民楼,一排排间距相等的窗子,横越的云华路,一片江南风格的居民小区,再远处就是缙云山。层次分明的景物,随着天气的阴晴,早晚的光线不同,感觉不一样。它是我来北碚交下的第一个朋友,它了解我的心情,观察神情的变化。我料想不到,面对偷袭的雷声,它竟然不抵抗,拼命地阻击一下,发出狼烟似的危险信号,让我有时间做好充足的准备。
睡眠被彻底打破,我不知所措,如何面对突发事件。躺在床上,肾上腺素飙升,望着昔日的好友,点头哈腰地迎接气势汹汹的侵略者,不抵抗的政策,拱手把自己的土地送出去。天邊的雷声,一阵低声的咆哮,接着大发雷霆,一串串炸响,冲击波的碎片,洪水一样地从窗口涌进。面对这一切,我无法反抗,不容易有反击的机会。声浪呼啸地扑来,一层层填满房间,我被压在下面。一波强大的攻击后,是短暂的喘息,甩掉积压的声浪碎片,挣扎地坐起,调动耳朵、鼻子、意识,组成一支庞大的军团,迅速地围拢,收复失去的地方,解放痛苦的折磨。天上的雷声波浪般地滚动,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我不能再多想,必须先发制人,将它们扼杀在萌芽中。我翻身下床,抢在雷炸响之前,将窗子关上,筑起一道防线,顾不上谈过去的感情。窗子合拢的瞬间,雷又一次爆炸,轰鸣声带着啸音飞来,映得玻璃闪亮,接着一声炸开。手未离开窗子,一道怪光打在上面,我看清手背的老年斑。关好的窗子,把湿气隔在外面,无法阻挡残暴的雷声,任意地斩割,它们吞噬房间的静寂,光的马车,满载战利品离去。我无能力反抗,打击嚣张的气焰,想起童话中的魔瓶,只要打开瓶口,能将它们收复。雷声懂得心理战,它用吼声威吓,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征服我和房间。endprint
这是我的领地,不允许陌生的东西进来,一只苍蝇飞进来,我举起拍子四处追杀,直到消灭为止。狡猾的蚊子躲在暗中袭击,我采取科技手段,打开灭蚊灯,把它干净利落地灭掉。雷声送来一道闪电,它的能力强大,不是小动物相比的。它从窗子越进,横冲直撞,一点道理不讲,纯粹是欺负人。闪电有后台老板的支持,它知道我是五十多岁的人,已经不年轻,身体中的激情耗尽。窗台上的几个药瓶,里面装的药片,每天维持生命的运转。它知道我不能有多大的反击力,搅乱平静的生活。
我无声地抵抗,不拉上窗帘,看着它们能统治多久,总不能这样下去。一次次的雷声中,感受空气的震动,忍受声音的碎片落身上。连环的雷声,北方很少听到,几乎不是在天空爆炸,而是房间里。我搜索一辈子积存的经验,将印象中的雷雨天气排列,按等级分列,这次雷声应在红色预警之上,列为特一级。重新编排档案,起身点亮灯,在透明板夹上的A4纸,记录下时间、地点,不带一点形容词,口述午夜雷雨的情景。
雷声一阵折腾毁掉睡意,它安静下来。突然骤密的雨下来,雨声渗透水泥墙。
雨声与雷爆声不同,它是催眠的小曲,它的哼唱容易进入梦中。我重新躺在床上,恢复睡姿,身心放松,一场人与雷搏斗之后,感觉疲惫不堪。感谢雨的到来,驱赶霸道的雷声,雨声更民主一些,带有诗性的浪漫,人容易满足的。我瞅了一眼窗子,想修复被雷破坏的关系,只能道一声“夜安!”
毛竹菜墩
这件事情的发生,绝未想过的。菜墩子是每天使用的东西,第一次使它时,仔细地看一下,这是什么木做的。北方长大的人,印象中菜墩子都是木做的,只是凭生活的经验。看了半天,觉得比较顺手,没有过多地想什么。
按正常的时间,每天晚饭后,第一件事情出去散步,走回居住处,应是七点五十分左右。当电梯的门在身后关上,咣当一声响,并没有对声控灯起作用。楼道里的邻居,每次都是咳嗽,声控灯得到信息,我和他们不一样,而是拍手,这样有个人的性格。
今天走出电梯,楼道里黑暗一片,无一缕光亮,我和往常似的拍手,两手在黑暗中快速伸出,向中间聚拢,接触的瞬间,清脆的响声在空间荡开,音波被水泥墙吸引,脚步空洞的回音,反射到吸顶灯上,声控灯迅速燃亮。从电梯到住处门口,往前走三米多,必须向左拐一个角,正前方的门,就是现在的住所。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环境不熟悉,由于视力不好,一时适应不了。不管什么时间走出电梯,都是光线不足,如果不弄出响声,声控灯不会亮,给人一种压抑感。电梯的反应慢,要等几秒才合拢两扇门。身后电梯里投出的灯光,在黑暗中钻破一片亮,总觉得后面有人跟踪,造成心理压力。
散步以后,身上的汗未消干净,拐出那个角,拍了一下手,声控灯亮起来,看到住处灰色的铁门。
听到敲门声,高淳海打开,不是和往常闪开身子,让出一条路,使我快一點进屋。今天他有些奇怪,脸上有一丝得意的神情,半掩着门,不如往日似的说:“回来了。”他手中拿着一寸多长的竹块,问我这是什么,我脱口说出,这是竹块。高淳海嘿嘿一笑,卖关子地对我说:“出怪事了!”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他拒绝回答,只是一脸笑意。我被他神秘的举动,弄得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无法猜测。环视屋子里觉得没有变化,也不可能有亲人从山东来,搞突然袭击,给我们意外的惊喜。
手中的竹块和事件有关系,令我琢磨不透。高淳海让我去厨房,灶台上有十几块相等的竹块,高淳海神秘地说:“这是菜墩子。”我望着这些竹块,无法与菜墩子连在一起。我是写文字的,对于生活的观察,还是比较认真,绝不走马观花。我扫一遍厨房,根本发现不到疑点。他笑呵呵地说,这就是你每天使用的菜墩子,它变得没有了。这时我才注意,撂菜墩子的位置,现在空空的。垃圾筐中有一堆零乱的竹块,不是菜墩子那样排列得齐整,让人辨认不出来。我捡起几块,看着每块竹子不经修饰,还带着毛刺。菜墩子的原材料,竟然是竹片挤压成型,外面套一个铁圈,捆束住竹块,形成圆形的墩子。我分不清竹子的种类,高淳海说是楠竹,缙云山四处长竹林。
楠竹对于我是新名词,我翻阅资料解释说, “南竹”, 就是平常的“毛竹”,“南竹”不能写成“楠竹”。所以统称为毛竹,它是一种实用竹。南竹对生长的环境要求不高,它生长期快,材质用途广泛,经济价值大。南竹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调节小气候,净化清新空气,美化周围的环境。
夜晚又下一场雨,清晨终于停下。推开阳台的门,感受清凉的风从外面挤进。我看楼前装垃圾的蓝色大塑料桶,菜墩子变成散落的竹片,成为丢掉的废物。
小区安静,大多数人家在梦中,我决定倒掉竹块。我拎起塑料袋中的竹块,深感不仅是竹块的重量,是永远的告别,我们曾经每天在一起,昨天晚上在上面切菜。楼道里的光线黑暗,拎着竹块,两手不能相击,只好学邻居的样子,咳嗽一声。棚上的声控灯亮起来,投出一片光明。我孤独地站在电梯前,机器轰隆响起,看到红色的数字不断地变化。
电梯的门咣当打开,我和竹块走进去。
渴望阳光
2014年8月30日,是我来北碚的第九天,天天下雨,停一阵子算是晴天。想起赫塔·米勒每次出门,她母亲问她,你带手绢了吗?在北碚应改为,你带雨伞了么吗?阴湿的天气渗入身体中,我不得不去药房,买两盒“湿毒清片”,用药物帮助,排除体内积存的湿气。
今天早上,一推开阳台的门,心情格外好,是一个难得的晴爽的日子。缙云山还是湿雾缠绕,过不多长时间,阳光挥动手中的金鞭,甩出几个炸响,将一群群吃饱的雾羊赶走,让山露出真实的面貌,晒一会儿太阳,饱吸光的温暖。我来到阳台,注视缙云山,每一缕雾气,在空气中发生变化,相互依靠,形成水气坠入山谷,渗进坚硬的岩石里。湿雾化成水的过程,发出轻微的声响,一定是最美的声音。观察雾的变化,是一门学问,不是简单说得清的。风向、阳光、温度在不同的情况下,雾会改变形状,甚至躲藏起来,等待雨的降临,然后一窝蜂似的涌出,重新包围缙云山。endprint
上午十点多钟,阳光丰沛,眼睛适应阴灰的调子,遇到这么灿烂的光照,一时接受不了。我在阳台,向远处的缙云山望去,清晨的雾消失,山脱去雾的面具,露出真实的面容,它立在天空下,鸟儿的叫是召唤的声音,让我走出家门,去山中散步。
感谢阳光,我从内心发出的一声,表达对太陽的渴望。鲁北平原,一个夏季难得下几场雨,阴雨天在干燥的北方,是人们渴求的好日子。现在地理位置不同,正好相反,雨是这个地方的正常天气,太阳是人们盼望的亲人。我既喜欢阴雨天,也想念阳光丰富的日子。
来到北碚后,床上的被子,一直没有机会拿出去晒,让棉花的纤维接触阳光,除去湿气,免得身体受罪生病。被子搭在阳台的栏杆上,享受阳光。光吸走被子中的湿气,填满干燥。
我拿出一把椅子,坐在阳台上品味阳光,阅读戈登·汉普顿的书,他是一个声音生态学家,他随身带着音量计,测量声音在空气中的分贝。我学着他书中说的方法,倾听阳光在空气中的声音,寻觅原始的音调。无奈每分钟都在发生变化,云华路上奔跑的汽车声,附近装修的电钻轰鸣声,楼道前大人训斥小孩声,门被关上的撞击声。各种声音纷纷登场,组合成噪音交响乐队,演奏一支强暴的音乐剧。这种声音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打消平静的心态。我听了半天,无法捕捉到阳光在空气中,流动时发出的音响。
我决定实现自己对好天气的诺言,几天前,我在江边赶大集,买到一个宝塔形的鲜笋。我在北方吃过袋装的笋,在酒店中吃过笋菜,对于笋既有新鲜感,又喜欢笋的味道。鲜笋当时在农民的竹筐中,沾着缙云山的泥土,拿在手中闻到土的气息。我对笋的了解,局限于吃的记忆。买下这个鲜笋,回到住处存入冰箱中。今天心情好,想在孩子们面前表现一下,做一道竹笋炒肉。我在百度上搜寻,学习如何做笋,做出好吃的菜。
笋从冰箱中取出,按照百度说的做法,切丝入水焯两分钟,将肉切成丝,倒入料酒、味极鲜、淀粉勾兑。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打开天然气灶,倒入菜籽油。我做错的事情开始,笋对于我只是资料和感觉,并不真正了解它的脾性。炒好后的笋,尝了一条,差不多吐出来,笋不是鲜美,而是苦涩难咽。我的热情被苦味冲散,面对一盘失败的菜,不知该怎样处理。
我一肚子扫兴,关掉天然气灶,来到阳台上。阳光尽情地照耀,栏杆上的铁管,晒得热乎乎的。我让阳光映在掌心,感受多日不见的温暖。厨房炒菜的不快,一时抛脑后,只想和阳光交流,什么不做,也不去想。
缙云山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出它雄伟的美,山峰勾出的曲线,富有自然的韵律,附近传来一阵鸟叫声。我愿意放下手中的事情,穿好登山鞋,踏着阳光的节拍,走向进山的路。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