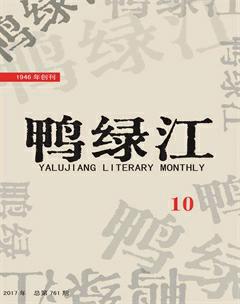玉希布早的春天
天野
1
玉希布早村美术馆新馆即将开馆,得到消息后,李桦提前订了返程的机票。他原本想取道莫斯科,再回国。作为京城知名画家的李桦,去欧洲举办个人画展后,又游历了北欧几个国家,前后有两个月了。
李桦是在去年夏天,筹备新建玉希布早村美术馆的。李桦第一次来这里写生时,觉得这个村名字的寓意很有趣,“三个牛娃子”,有意思不说,更鲜为人知的是,李桦的乳名叫牛娃子。当然母亲去世后,再没有人这么叫过他了。
先前的玉希布早村美术馆是利用该村小学旧校舍翻新而建的。李桦找的赞助资金。美术馆的画作是他邀请全国各地的画家,来村里写生创作的。当然他的作品最多。
李桦作为新馆筹建人,开馆仪式,一定要出席的。
玉希布早村的春天,整整比北京晚了两个多月。回到北京,到处是鲜花盛开,此时的玉希布早村,盘根交错的榆树刚刚发芽。杨树的叶子也才舒展开来,翠绿欲滴,像朝气蓬勃的少女,看了让人欢喜。也让李桦欢喜,他爱这里的山川溪流,花草树木,家畜飞禽,当然最重要的是爱这里的人。
迪娜大学毕业后,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到玉希布早村工作。乡村美术馆斜对面的那间房子,是她的宿舍。
会计专业毕业的迪娜儿时喜欢画画。乡村美术馆兼职讲解员的差事,落在她的身上,她一点也不意外。
村支书那扎尔说,迪娜年轻漂亮有知识,非她莫属。说着村支书递给迪娜一份打印的材料。迪娜拿着资料,笑眯眯地对村支书说,试试看。
打开玉希布早村美术馆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少女画作,少女面容白皙,身着红色衣裙,胯下一匹枣红色马,昂首挺胸,目视前方。背景是草原风光,远山,白云,绿野,青松,隐约的毡房,夕阳的光投射在少女脸上,柔和,温暖,妩媚。少女嘴角微微上翘着,侧着的那半边脸上,浅浅的有一个酒窝,似一汪山涧潭水,荡漾着一种撩人心扉的涟漪。
迪娜眼睛一亮,心里不觉惊诧道,这姑娘太像我了,或者说,我怎么跟这姑娘长得那么像。想着便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不由觉得,有种火辣辣的感觉,似乎这幅画,画的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少女的目光有种穿透人心的力量,瞬间就令人魂不守舍。
迪娜读大学时,也常去看画展,可从来没有一幅画作像这幅画这么打动她。迪娜将目光移到画作下方,那张巴掌大的说明卡上,作品名称:《姑娘阿莱》。作者:李桦。后面还有个括号,标注着:努尔。时间:1993年5月。
迪娜仔细地观看了整个美术馆的作品,在一百多幅画作中,一大半的题材是表现哈萨克族牧民生活生产场景的,妇女们清晨开始挤奶、擀毡,夜晚在毡房里刺绣。男人们在割草、宰牲。金雕、老人、孩子在无声地交谈。牛羊在草地上漫步,孩子与它们戏耍。姑娘要出嫁,小伙子扬鞭策马地在追。转场途中牧羊犬尽职地照看着羊群。高大的骆驼把毡房的全部家当背负在身上。当然还有北京天安门,雄伟的长城,上海外滩,疾驰而过的动车等作品。
整个美术馆恬静、优美、抒情,一下让迪娜焦躁的心静了下来。
迪娜关上美术馆门的那一刹那,心里升起一串疑问。这个叫李桦的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有一个哈萨克名字?为什么在这里建座美术馆?
带着疑问,迪娜找到了村支书那扎尔。村支书说,人家是北京的大画家,以前来这里写过生,说这里的景色好,不仅画了山,画了马,画了毡房,还给孩子和老人们画了呢!画出来的画,跟相片一样。
迪娜追问,他什么样子?说出这话时,她感觉自己声音有点大,母亲早对她说过,姑娘说话要轻声,不能那么大声,显得没教养。可她心里太想知道这个答案了。要知道,在山区,旅行的人多,徒步的人多,画家却不多,何况是北京的大画家。
村支书看迪娜一眼,并没有马上回答。
迪娜心里紧张,低垂眼睑,不敢看村支书的脸。她两手抱于胸前,心怦怦什么样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村支书说完,背着手出了村委会的办公室。
迪娜觉得村支书太幽默了,哪有这么形容人的。这跟没说有什么两样。她的意思是具体一点,比如说身高多少,圆脸还是方脸,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戴没戴眼镜这类的信息,至少让她从描述中,对这个神秘的人,有个大概的了解。
迪娜显然对村支书的答复是不满意的。她期待能从那些杂乱的资料里翻找到一张照片最好,可她把村办公室的柜子、抽屉,包括几个码放在文集柜上,落满灰尘的大纸箱子,都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
迪娜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灰头土脸,额头和鼻尖都微微有了细碎的汗珠。瞅着自己这副样子,感觉有点滑稽,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至于这么费劲吗?即便找到照片又能怎么样?知道他的模样又能如何?彼此任何关联都没有。即便这个人,现在出现在眼前,又能干什么?没看出来吗?他关注的是那个叫阿莱的姑娘,他画的是她。他把她画得那么白皙那么美。她果真有那么美吗?是不是被他美化了。此刻迪娜莫名有了一股醋意,似乎这个叫阿莱的女孩,不是画中的人,就在她对面,似乎两个人成了对手,有种一决高下的架势。
想到这里,迪娜忙用双手捂住了脸,太不好意思了。真幼稚,跟一个画中的人,计较起来了。
2
迪娜大学毕业前的那场就业招聘会上,有家企业与她签约,就业意向是该企业的财务部门。在其他同学来看,这家上市公司让许多同学都很羡慕。迪娜高兴得很,当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阿依丹。母亲激动得一个劲说,学没有白上,又说会托人带信告诉她阿勒泰的奶奶。奶奶已七十岁了,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她该有多开心。迪娜从小是跟奶奶长大的。
迪娜的母亲是护士,三班倒。迪娜刚一岁,就被母亲送到奶奶家了。不是奶奶耳朵背了,迪娜肯定会把消息先告诉奶奶的。
想起奶奶,迪娜就想起辽阔的草原,挺拔的松树,怒放的花朵,还有奶奶痴迷的花毯。迪娜的奶奶是草原上遠近闻名的哈萨克族刺绣能手,经她手绣出的花毡,那花朵比别人绣得格外灵动。endprint
小时候,奶奶绣花毡时,迪娜便拿着一根木棍,在地上,学着奶奶的样子画。奶奶绣好的花毡,迪娜反复用小手抚摸着,像奶奶抚摸她那样,动作轻柔而亲密。迪娜把稚嫩的脸旁贴在花毡上,闭着眼睛,那神情,像草原上盛开的花朵。奶奶笑着,喊迪娜的名字。我的宝贝迪娜,等你长大了,一定可以画出比花毡还漂亮的花来。
等迪娜读小学时,美术课一直没有老师。大概是三年级,来了一个又黑又瘦的男老师,可给迪娜和她的同学们上了不到两个月,准确地说是六次课,不知什么原因,课就中断了。
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迪娜遇到了美术老师。老师,我想跟您画画。迪娜小声地说。她声音太小了,只有她自己能听到。老师似乎没有听见,一脸严肃地冲迪娜说,快点回家,路上小心。说完便匆匆走了。
迪娜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想再重复一遍剛才的话,可声音在嗓子眼卡住了,像是一块干馕堵在那里,不上不下。
美术老师为什么走了。迪娜最初跟其他同学一样都充满疑问。直到快放假时,迪娜才从两个老师的闲谈中得知了真相。那天,阳光暖洋洋的。迪娜随手摘了校园草地上的一朵紫云英,看紫云英在指间轻盈旋转的姿态,欢喜地对紫云英微笑。两个老师坐在教室门前的两块大石头上闲聊着。是风把老师交谈的话送入迪娜耳朵里的。老师很随意的样子,没有注意到迪娜。
美术老师走了。
走了,嫌工资太少。
也难怪。
听说参加招工,被一家企业录取了,大概已经上班了。
山里交通不便,待遇不高,愿意来的美术老师更少。直到迪娜小学毕业,再没来过一位美术老师。
可迪娜一直喜欢画画,喜欢画画的人,梦想成为一个画画的人。
3
夜里,迪娜躺在宿舍的床上,憧憬就业的兴奋如夕阳落尽后,心底某个角落里又钻出一只小鹿来,让她不得入睡,在无边的夜里,陷入一种纠结之中。
下午,迪娜从微博里看到一则消息,说一位北京的知名画家将在一个叫玉希布早的村子,帮助新修一座乡村美术馆。乡村美术馆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都不多见,怎么会选在天山深处?这太难以想象了。仅就风光壮丽作为标准,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在绵延两千五百公里的天山,从任何一处进入,壮美的风光足以让每一个初访者惊叹。那么除此之外又会是什么呢?
这个消息撩拨起迪娜心中的一个希翼。她后悔当初没有选择美术专业,听从母亲的话,选择了会计学。
你也许会问,迪娜的母亲不是护士吗?理当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适时给予投入,把这个爱好培养成为孩子的特长,说不定会影响孩子的就业和一生。
这个浅显的道理,别说是迪娜的母亲懂得,就是山里的牧民也都是懂得的。问题是,迪娜的父亲奥斯肯因车祸,终日坐在轮椅上,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上美术班是要掏钱的,且比一般的培训班费用都高。母亲一个人,除了照顾父亲,还要抚养迪娜和弟弟布拉克拜。
当初迪娜被母亲送到奶奶家时,太小,并不知道,那时母亲已有了身孕。当弟弟进幼儿园的那年秋天,意外发生了。
父亲是卡车司机,长途贩运中途休息,几个人在饭馆吃饭。这时,驶来一辆长途班车,停在饭馆门前,呼啦啦下来了三四十人。去了厕所,有的坐在棚子下吸烟,有人则点了饭。有个小男孩手里的皮球滚落下来,另一个稍大的男孩,捡起皮球,随手扔了出去。小男孩随着皮球的方向跑去,皮球不偏不斜,飞向公路了。一辆车正疾驶而来。迪娜父亲知道那车的速度,小男孩不过五六岁,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迪娜的父亲在这次事故中成了残疾。那个捡皮球的小男孩获救了。他的名字叫亮亮。
迪娜得知这个消息后,只想快快考上大学,尽早工作,帮助母亲分一些家庭的负担。那个渴望画画的种子被埋在了心底深处。
如今大学毕业了,是在外地工作,还是回家乡去。玉希布早美术馆的消息却像个皮球一样,一直浮在深夜的脑海里。看或者不看,它都那么显眼。
4
迪娜回到了玉希布早村时,部落里的许多牧民都骑着马,从各家的毡房赶来看她。
作为第一个考上内地大学的哈萨克姑娘,迪娜成为整个村庄的荣耀,妇女们姑娘们与迪娜拥抱,贴面亲吻,有的人眼里噙着泪花,大家一起吃饭,唱歌跳舞,热烈的场面持续了一天,余温在太阳下山后彻底冷却下来。
迪娜无法入睡,从床头拿了披肩搭在身上,她想出去走一走。
出宿舍门,右转便是条山路,蜿蜒伸向大山深处。山路旁就是深浅宽窄不一的河。此时,正值春季,河水像吃饱肚子的马儿,一路欢腾狂奔,声音在山谷中传出很远。
迪娜户口本上出生地写着这个村,一直跟奶奶生活在阿勒泰草原的她对这里却是陌生的。
当然,居住在这里的牧民大多都是从阿勒泰迁来的,大概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村里的牧民许多亲戚都在阿勒泰,就跟迪娜家一样。
迪娜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只有近二百户牧民的村庄,二十年间,先后走出了四百多名大中专毕业生,“状元村”的美誉如百灵鸟的歌声一样,飘出了大山。
迪娜走进村支书家的毡房时,村支书坐在炕上喝奶茶,见她进来了,忙招呼迪娜坐下,倒了一碗奶茶给她。
那个叫努尔的人,在哪里?迪娜喝了一口奶茶,放下茶碗问。
哦,你是说帮着建起美术馆的李桦嘛。他在北京。美术馆让村里的孩子们知道了外面世界的样子。他的那些画,也让孩子们开了眼。
你是说,因为美术馆,村里才有那么多孩子考上学的吗?迪娜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村支书。
可不是吗?自从美术馆建成后,每年村里小学开学第一件事情,就是集体参观美术馆。孩子们知道了首都北京,大都市上海,知道了高铁,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地方。
给孩子骆驼大的财富,不如给孩子纽扣大的知识。让孩子好好学习,走出大山,走出草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草原上的孩子,不能只会放牧。村支书说。endprint
村支书还给迪娜讲述了那些从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有记者、医生、护士、干部、老师、畜牧师、演员、工程师、工人等。这些人都有故事,如果想听的话,以后慢慢讲。
当迪娜问及那个叫阿莱的姑娘时,村支书打着哈欠,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以后再说。
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月光照耀着整个山谷,从树叶间遗落的光影,斑斑驳驳,这些光斑如一面面小镜子,发出明亮的光,又如舞台演出时打出的那种炫目的光,容易让人头晕,甚至产生一种幻觉。这让迪娜有些恍惚了。这到底是在天山深处,还是在演出剧场。迪娜眼睛有点发酸发涩。用力眨巴了几下,症状没有缓解。她便用手背揉了揉。心想,这是怎么了,自己的视力正常,怎么会发花,真不可思议。
忽然一团光影闪烁着,一个人影从亮光中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发至肩头,两肢胳膊很长,垂在身体两侧时,接近膝盖。这让迪娜有點惊讶,这样的人太少见了。那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冲迪娜招了一下手,那意思,跟他走。
迪娜有点好奇,心想怎么会冒出一个人。迪娜是不信鬼神的人,此刻她一点也没有害怕或者恐惧的情绪,他会带自己去哪里?
那个人走在前面,迪娜跟在后面,彼此相距不过几米,那人像飘浮在空中的云一样,听不到脚步声,也听不到呼吸声。
迪娜想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对一个新认识的人,第一个想知道的信息就是名字,要不然怎么称呼?就这么没头没脑地说,既不礼貌,也显得没教养。
当转过一个山弯,那人向东走去时,迪娜立刻明白了,是带她去美术馆的。
世间有许多神奇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都感觉十分奇异,这样的事情迪娜就遇到了。比如说,当那人走到美术馆门口时,原本锁着的门自动就开了。迪娜感到太奇怪了。门上的钥匙除了村支书有,另一把就在她这里,当然是挂在宿舍的墙上的挂钩上。迪娜特意给钥匙拴了一个红色中国结,这是她跟同寝室的同学学着手工编织的。
那人如数家珍地给迪娜讲解每一幅画作的故事,作者创作意图表达的思想,以及与村庄的渊源。这让迪娜惊讶,原来村庄曾经发生过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但令迪娜疑惑的是,那人在《姑娘阿莱》的画作前,却没有停留。她想问一下,嘴还没有张开,一阵夜风从门里钻进来,那人就不见了。迪娜慌忙追出去,空荡荡的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四周安静得出奇,只听到自己胸腔里发出的喘息声,一阵紧过一阵。
迪娜转身时,一缕银光照射在《姑娘阿莱》上,柔和的光,让画中的姑娘更加柔美了,姑娘的目光依旧注视着远方。此时迪娜感觉阿莱不是画中的人,就在她面前的山坡上。
阿莱!迪娜喊出了声音。
半晌,没有人答应。迪娜愣愣地站在画作前。从身后投射的月光,把迪娜瞬间变成了一尊雕塑。
5
李桦到玉希布早村时,村委会门口已经围满了牧民,许多人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他,但还是像欢迎初到这里的客人一样那么隆重热烈。
新美术馆就坐落在村委会的旁边,是一座建筑面积四百多平米的木质建筑。迪娜熟悉这样的建筑风格,在阿勒泰的山里这样的房子很多,但多半都是用来接待游客的。这里用在美术馆却是意义不同。
新馆布置时,迪娜并不在现场。她作为家属陪着父亲去广州做手术了。那个曾经被父亲救过的亮亮,从广州医科大学毕业,留在了广州一所医院。当亮亮得知迪娜的父亲,因为股骨头坏死急需手术时,多方筹集资金,决定给迪娜的父亲更换股骨头。原本一筹莫展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母亲工作太忙,实在走不开,弟弟在上学。迪娜向村支书请了假,坐着火车,陪父亲去治病。这一去一来就是一个多月。
新馆开馆在即,作为美术馆的讲解员,怎么能少了迪娜?接到村支书的电话后,迪娜忙跟母亲商量,母亲说,她最快也得一周后才能去广州。亮亮得知情况后说,请迪娜放心,他会精心照顾好老人,何况自己的父母都已到广州了,也会来医院进行陪护。
迪娜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当白色面包车停稳后,从车里依次下来几个人,中间第三个人,忽然让迪娜眼前一亮,中等身材,头发到肩,他左手拎着挎包,右手自然地下垂,恰好到膝盖那里。这人似曾相识。对,不是那天夜里遇到的那个人吗?他就是美术馆的创建者李桦老师吗?想到这里。迪娜有些激动。她往前靠了一下,身体的血液像山里喷发出的火焰一样,顷刻间,让迪娜沸腾了。
迪娜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人,她希望他能看她一眼,哪怕一眼也好。她不认为他们是第一次相见,那天夜里他们就见过面的。可那人的目光只是扫视了一下欢迎的人群,并没有落在迪娜所在的位置,更没有注意到迪娜。迪娜挪动了一下脚步,将脚跟抬起,这样自己就高一点,也许他会发现。可迪娜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并没有回头,没有再看迪娜一眼。
整个仪式很简朴,第一项是介绍参加活动的领导及嘉宾。念到名字的人,都向前一步。当李桦的名字从麦克风里传出来时,他同样向前一步,右手放在胸前深深向面前的牧民们鞠了一躬。迪娜的眼里顿时涌出了泪花。她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这么多人面前,为这个人满含热泪。她怕人看到,赶紧用捏在手里的纸巾擦拭了一下。接着是乡里、市里领导和嘉宾们为美术馆剪彩。牧民们热烈地鼓掌。迪娜也使劲地鼓掌。
迪娜,迪娜。忽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迪娜慌乱地循着声音望去,原来是村支书。
哦,我讲解员,怎么忘了。迪娜忙从人群里走出来,快步走到村支书跟前。
村支书朝身旁的李桦说,这是村里来的大学生村官迪娜,同时兼美术馆讲解员。
迪娜连忙微笑点头,并问了一声:李桦老师好。
李桦双眼顿时闪出一种兴奋不寻常的光,他直勾勾地盯着迪娜,目光中有惊喜,有激动。他伸出手,主动握住了迪娜的手,并用力晃动着说,你好,迪娜,辛苦你了。可话说完了,手还没有松开。
迪娜被这双厚实有力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甚至隐隐感觉到了手骨节传递来的疼痛,但那手掌的温热,迅速就将疼痛化解了。这种温热传导给迪娜,像毡房里亮起了灯似的,心中是满满的温暖。但她还是感到有些紧张,心在心房里扑腾腾乱跳,让她有些慌乱,赶紧从李桦的手里抽回自己的手,悄悄地垂在胸前,不知所措地来回摩挲着,以掩饰自己的窘态。endprint
之前来布置展馆的小李转身对李桦说,大家一起看看新展馆吧。
李桦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刚刚的行为有点失礼,忙低头笑了笑,挽着村支书的手一起跟随宾客进了美术馆。
迪娜的整个讲解过程令李桦相当满意,他的目光不时落在迪娜身上。可他哪里知道,看似从容地讲解着的迪娜,心里跟春日的河水一样,汹涌澎湃。李桦每称赞一次,她的心就狂跳一次。手心早都渗出了汗珠。
当走到《姑娘阿莱》画作前,身后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迪娜多像画上的姑娘!
迪娜听了这话后,脸“腾”地红了。脸一红也凸显出脸上的酒窝。
一束目光传递着炽热的温度,迪娜侧脸时,李桦正看着她,迪娜猛地一惊,她发现他的眼眶隐约闪着泪花。她迅疾将目光移开,投向了画作,她却能感受到,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
晚上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牧民纷纷向李桦敬酒,表示感谢。能筹集百万资金为村里新建美术馆,给牧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村支书说,这几年,牧民们纷纷利用自己的院落开起了牧家乐,每逢节假日,来山里旅游度假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美术馆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亮点。一些美术学院的师生、画家都来村里写生,给美术馆赠送作品,使美术馆的作品数量增加了不少,更让外面的人知道了玉希布早村,等于给村里做了广告。
李桦从牧民的手中接过酒杯,仰着头,一饮而尽。他的脸不红,而是越来越白。迪娜站在旁边渐渐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情绪中。如果真喝醉了怎么办?他刚才说,他担任了一个全国画展的评委,时间很紧,不然他会多待几天,无奈订了明天中午的机票,若是饮酒过度,延误了飞机怎么办?
当又一个牧民来给李桦敬酒时,迪娜抢先一步,挡在李桦的面前说,李桦老师不能再喝了,身体健康第一,请理解一下。
话音刚落,大家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都射向了迪娜。那目光有疑惑,有不解,有嘲讽,总之似乎都在怀疑,她这样贸然打断饮酒,破坏了气氛。
你一个姑娘,不懂男人的心情,李桦老师这么远来了,我们总得热情款待,怎么能不喝酒呢?有人说。
迪娜顿时感到了一种紧张,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为一个男人辩护。当众人的目光汇集在她身上时,她的心跟敲鼓似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脸瞬间就有了烧灼感。
村支书站起来拍拍迪娜的肩膀说,傻姑娘,别担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但是,您也喝酒了呀!迪娜不好意思地说。
喝酒是男人们的事情,你就别管了。村支书说。
哑口无言的迪娜,目光黯淡地看着跳动的篝火,不好再说什么。
显然,李桦已经有些醉了,他歪歪斜斜地站起来,接过牧民的酒杯,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虽然我在全国乃至世界多个国家都举办过画展,也获得过许多大奖,但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这座美术馆,它就是我的孩子。说完,直接将酒杯中的酒倒进了嗓子里。用手抹了一把嘴角,又说,兄弟们的心意,我是不会拒绝的。
李桦的这种豪情,有点像天山上走下来的侠客。当年这个村里就接待过《七剑下天山》的剧组,明星大腕云集,好不热闹。大概他们在晚上也如此豪饮过,不然怎么拍出那么侠肝义胆的人物!迪娜这么想着。
曲终人散。李桦被村支书搀扶着送进毡房。
夜深了,迪娜毫无睡意,脑子里跟放电影似的,回放白天李桦的所有影像。她忽然有种重新学画画的冲动。要是自己懂画了,就能与他更深入地交流了。
迪娜走出宿舍,她想一个人走一走。天空有云,月亮时明时暗。出了院子,右拐,一路向前,不远处有一汪翠绿的潭水。这是被洪水冲击而成的。平日迪娜喜欢在潭边坐一会儿,或者与潭水对视,或者随手捡起一枚石子扔入潭中,看泛起层层涟漪的水面。
从狂喜到冷静,迪娜今天的心情如坐上了过山车一样,起伏巨大。她想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走出院子一百来米,迪娜隐约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声音忽高忽低,含糊不清。这么晚会是谁在说话呢?迪娜往前走,在路的左侧不远处便是一片榆树林,不算浓密,但单株榆树很粗,大多是三四个人都围拢不住的百年榆树。
距李桦所住的那顶白色毡房五六十米的地方,是一株呈Y字状的榆树,树的根部交错重叠的根系形成两级台阶。一个男人搂着一个的肩膀,另一个揽着对方的腰。俩人头挨着头。
声音是从这里发出的。迪娜忙躲在路边一株榆树后,屏息静听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们是兄弟,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我对你是又恨又爱。
咱哥俩,恨从何说起?
我恨你,太有才华,一来就把我们部落最美麗的阿莱姑娘给征服了。她当向导陪你们上山写生,给你们送饭,给你们洗衣服。再就是你住在她家养病的时候,那么心细,跟照顾自己亲人一样。你要给钱,她一分不要,凭什么?傻子都能看出来。你哪里知道,我喜欢阿莱好长时间了,你没来之前,她还跟我说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眼看到手的燕子,飞了,我能不恨你吗?
一晃这么多年,我又喜欢你,你画得好就算了,人也这么重情义。以前山里来过画家,可画完就走了,没给山里留下一幅画。瞧瞧你,给山画,给牛羊画,给老人画,给孩子画。画一年不算,坚持这么多年都来画,谁能做到?画了不行,建起这美术馆,牧民们或多或少都受益了。我不喜欢都不行!
那扎尔老哥,真对不住了,我真不知道你喜欢阿莱。阿莱从没有跟我说起这事。阿莱姑娘太美了,肌肤跟雪似的,比江南的女子都白净。我第一眼见到她,她就钻进了我的心里了。记住一个人,只需看一眼,而忘记一个人,一辈子都做不到啊!
酒后吐真言。
迪娜听清楚了,这是村支书与李桦在说话。
等迪娜醒来的时候,李桦一行已经下了山。她站在山路上,望着空荡荡的山路发呆。可她心里却翻江倒海,后悔昨晚趁着李桦老师清醒的时候,应该把地址和电话留下,以后好联系。endprint
李桦在开幕式和晚宴中不止一次地说,他还会回来的,这里就是他的家。可迪娜知道,这哪是容易的事情。据村支书说,上次李桦来这里写生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这几年,他在世界各地办展览,一切都是经纪公司策划好的,作为画家,他只能配合,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不像前些年,一两年就来一次,待上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人说,李桦就是头山羊,玉希布早村的山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此时,迪娜眼前浮现李桦的身影,他在向她招手。
6
第二天早上九点,迪娜习惯性地打开市里的广播,新闻里播放玉希布早新美术馆落成的消息。从新闻里获悉,李桦十多年前来这里写生时,遇到山中大雨,从山上下撤时,不慎摔入山谷,后来被牧民救出来,腿骨折了。在名为阿莱的姑娘家休养,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而阿莱家为了营救李桦,错过了抢救自己财物的最佳时机,羊圈被冲毁不说,还损失了十几头羊和三个牛娃子。洪水把羊圈旁的几棵百年老榆树连根拔起冲走,土木结构的老房子瞬間坍塌。只有毡房保留下来。
李桦为了感谢阿莱一家的救命之恩,答应帮助建起一座乡村美术馆。但等李桦第二年来到玉希布早村时,才得知阿莱刚刚因病去世,她的父亲悲痛欲绝,一病不起,被她远在青河的姐姐接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李桦内心十分愧疚,一夜没睡,画出了那幅《姑娘阿莱》,并在当年秋天开学时,玉希布早美术馆也开馆了,作为美术馆名誉馆长,他把这幅作品挂在最为醒目的位置。
父亲和母亲从广州回来了,这次父亲不用坐轮椅了,更换完股骨头后,亮亮给父亲装了假肢,重新站起来的父亲,决定回一趟玉希布早村,看看老朋友们。
迪娜说,她要陪着父亲和母亲看看美术馆。
刚进村办公室,村支书递给迪娜一份信。迪娜瞄了一眼邮戳,是来自北京的信。她急不可待地打开,是李桦寄来的。信是用小楷毛笔写的,这是迪娜没有想到的,如今谁还会用毛笔且是小楷写信呢!
李桦信上说,见到迪娜后,他过目难忘,回到北京的这些日子,神情恍惚,以为是阿莱复活了,他寝食难安。他必须告诉她,不然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股风从窗子里吹来,满屋子都是野蔷薇的花香,玉希布早村的春天来了,那风把桌子上的信封吹到了地上。迪娜拿着信,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责任编辑】 铁菁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