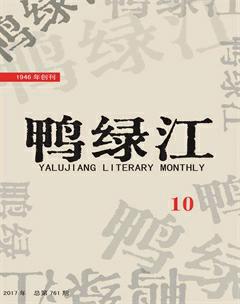哈瓦那往事
柏舟
温暖的黑暗,湿透了我的双眼。我不知道罪恶,这是令人升华的疾病。我以死相许的生的需求——被爱。
——萨拉·凯恩
大哥立在我的面前,嘴里横叼着雪茄,冷漠地盯着我。
大哥说:“你去死吧。”
“去死吧!”大哥的声音如滚滚长江之水,混浊而汹涌,“啥子?好凶?”现在我又梦见了大哥,他披了一件黑色的斗篷,带着一副宽边的黑墨镜冷冷地盯着我。每次死的时候,我都要朝四周张望,看看大哥在哪儿。我总能看到大哥。有的时候,大哥也不作声,嘴里叼着一根粗大褐色的雪茄,吸一大口,然后,那些浓重呛人的烟雾就喷到我脸上;有时候,我刚想说话,问问他,大哥就阴笑两声,拍着我的肩膀就消失了。我后来曾经回忆,大哥与我都快有十五年未见面了。每次想到大哥,我便会摸着方脑壳连带他先人一起骂;想到大哥的诅咒,我就做噩梦。老是梦见我真就死了。大哥他,有时在我的身后,有时在我的头顶上,我乞怜、惶惶地望着他,大哥却木然地扫我一眼,眉毛微微耸一下。那张马脸毫无悲戚之色。
大哥仿佛魔鬼附体一般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想,总有那么一天,我要被这个可恶的撒旦给毁灭。
那段日子,我似乎生活在梦里。好像我这一生的梦都在这个阴冷、潮湿又寂寞的冬日做完了。我曾经发誓,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就是死也不会再回到这个让我毫无一丝留恋、绝望透顶的地方。
一定要离开它。我仿佛得到上帝神谕一般,我把自己的两扇黑色中带灰白的翅膀张开,张开它们的伟岸,“雄起!”我大喝一声,似给自己施了法术,“我是摩西,我是堂·吉诃德,飞,飞,飞。”我就飞了起来。后来,我看见有一条黑影带着呼啸朝我飞来,不妙,我尖利地大叫想躲开——胡哈儿说:“想幺妹了嗦?”妈的,原来是胡哈儿在扯老子的耳朵。
“卖钩子的。日你先人。”我翻翻白眼,把痰啐到碗里。
“呸,装疯迷窍,”胡哈儿说,“锤子,你个脚猪,晓得个铲铲嗦。”他点点那个宜兴紫砂壶的把儿,嘿嘿,哈哈,他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灌了几口水,笑道:“还要日人?你娃娃?格老子混江湖的时候,你娃儿在做抓子?”他猛然把肥大的手指戳向我的裤裆。
这个老二流痞子。我劈开他伸来的熊爪。
“随口掰儿嘛!”我抓抓头皮说。我说,胡哥你,我乜斜他一眼,指指过堂上端盘子的那个围着白兜兜扎辫儿的女人,眼睛眨巴两下。他问:“啥子事哦?”我说:“这个人是哪个,怎么认不到喃?从哪搞来的?当小老婆嗦?”我在心里犯嘀咕,老天啊老天,你就是不长眼,像他哈儿这种戳戳,凭啥子腰包有腰包女人有女人;那些女人真是墙头上跑马,卵蛋上摸虱子。“嘘!”他用茶缸遮挡住自己的脸,朝那个女子觑了一下,像是给我打预防针似的。
“莫乱说,莫乱说。”
我哈哈笑了起来,把欠着的身板挺直,回转头朝后面的厨房伸长了脖颈扯大嗓门喊:“二嫂,二嫂。”
胡哈儿给了我一个脑壳:“来碗担担面?吃了再接着耍?”
原来在哈儿这耍了两个通宵的麻将,唉,他一说到吃,肚子也真瘪了。咕噜咕噜叫了。我咂巴咂巴嘴,脑壳摇晃得厉害,眼皮子上下瞌巴。我连续打了几个哈欠。我的眼球充斥着血丝?或者是闪着绿莹莹的幽光?如果是在荒蕪的旷野、坟茔里行走,会遇见狐狸精吗?狐狸精会缠上我?白天有狐狸精吗?应该不会有吧。蒲松龄老先生不是在他的书里,都说了,狐狸精喜欢在午夜和书生缠绵、缱绻嘛,老子又不是书生,又没得票子,万一要是真的遇上了呢?我把四个兜儿翻了两回,给哈儿看,“没得票票了,免费吃?要不,再借一点儿钱嗦?”
“滚!”胡哈儿把手里的茶缸往桌上一掷。你可以想象,那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是何等绚丽。茶缸里的老茶溅了我满脸都是。“噫,狗日的,你看,你看,脖子都气歪儿了。可惜桌子了哦。”我用食指来回地在桌子上轻轻地划着圈圈。
“莫当真,莫当真,和你说着玩的。看你小气的哦。”
“喂!那个妹子,你过来,添酒,添酒。”我也像哈儿那样摆威风,拳头捏起擂桌子,嗓子震天响——老子请客。那个妹子回转身子,瞥了我一眼,犹豫地立在那儿。哈儿挥挥手,他狗日的意思是让那个妹子干活去。那个妹子抿着嘴,走开了。“真是好看。”我吹了一声口哨。小嘴,杏眼,淡淡的柳叶眉,脖颈雪白、颀长,辫子上用手绢绾着,这狗日的哈儿哪弄来的?我心里晓得很,胡二嫂这个时候是不会在店里的,二嫂日子过得巴适,瞌睡不到太阳升到三竿是不会起床的。要花钱打牌耍麻将只需莲藕般又白又嫩的手往胡哥面前晃晃。如果是从床上下来,哈儿一定是乖乖地贴着勾儿把钱递过去的。我想。哈儿的骨头酥得很。过了会儿,那个妹子很害羞地过来,低着头只是给我续了茶水。我心猿意马地看着这个新来的妹子。我脑壳里有好多影子在晃悠,乱糟糟的。也就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看见哈儿的母亲,街上的人都喊她哈儿婆婆,拄着根黑色的“老龙头”走了进来,婆婆踮起脖颈四下环顾,起先,我没听清婆婆嘴里咕噜着什么。婆婆走到哈儿的身边,也不说啥子话,好像眼乌子突然朝上,像一个死人醒过来一般很吓人,拐杖就劈了过去:“败门风个东西,你,要得死。”婆婆气咻咻的。好像一头快要赖下去的驴。那个时候,店里的大厅里还没有几个顾客,只有包厢里传出麻将的“哗哗”声。我悄悄地溜出了“哈瓦那”。看到胡婆婆,我就忽然想起幺爹来了。
那就来说说幺爹嗦?印象中,爹这辈子没羡慕过多少人,我不明白爹为啥子就特别羡慕幺爹?我听爹说过:幺爹在长江上打鱼放筏子的那些年头,有过一个相好,长得与胡二嫂一样好看,当时,爹问我,世界上哪个白最好看?我说,“雪莲白。”
“对头。”爹咽了口唾沫,望着远处正黯淡下来的峭壁下的长江,龙泉宝剑一般的白眉毛一闪一闪的,好像一个哲学家在思考人生。爹呼出一口长气:“那个,真是妈个好看哟。”爹说话的神态让我觉得真是好笑,看爹那个样子,好像是在说自己的婆娘(口水沫子在空气中乱飞,神情庄重)。那个时候,我从书上学来一些得意的句子,“闭月羞花,”我给爹说,“你应该用这个。”这个镇子上的人,有个坏毛病,喜欢鼓捣摆龙门阵的人。endprint
“找老婆,就要找幺爹相好那个样的。”
“哪个样?”
“屁屁儿,像水桶桶,胸嘛,要大,还要白,比雪梨花还要白。”爹掸了掸烟灰,用手比划着,就,就,就这么大。我的喉咙上下滚动了几下。
有一年,幺爹从上海来看我们。幺爹起先说的是上海话,听他说话硬是累得很。幺爹问我,读书识字了没有。我看看幺爹,摇摇头,不晓得他在说啥子事。真是怪得很,幺爹和爹是一个爹妈养的,啥子就说这种“软绵糖”样的话呢?后来,幺爹从干部包(是那种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里抓出来两把大白兔奶糖,说,切,切(我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过还有什么奶糖,总以为陶罐里的红糖是天下最馋人的东西,爹总是用一把黑色生锈的大铁锁把它锁在碗柜里)。幺爹说:“大白兔,香不香?”我说:“没我妈的奶香。”幺爹说:“让你爹给你再找个妈。”有两句话,幺爹像是卖关子,吐着白烟圈圈(他吸的是一棵老粗老粗的纸烟。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幺爹抽的是哈瓦那雪茄),拖着长调调,一字一顿,像领导作报告,倒是说得我能听清楚——幺爹说,富贵命中定,姻缘前世结——都是命啊。是不是嗦(那个晚上,也是我吃了我这一辈子中吃过的最多也是最后一次吃的大白兔奶糖)?爹给我灌了几口包谷酒,拍拍我的小屁股:“去睡觉。”这酒真是好喝得很,入口浓烈,却很香,绵厚,淳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我被他们的吵骂声惊醒,窗外那棵大樟树上,猫头鹰“咳咳”地叫着,像个生病的老头,声音特别骇人。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拉到我的床沿边。那只猫头鹰估计被他们的吵骂给惹毛了,扑棱着翅膀在屋檐外的浓黑的夜色里转圈儿。后来,我听见爹“呜呜”“呜呜”地骂起幺爹来了。人有的时候不仅犯贱,也怪异得很,那几年,我在攀西的监狱里“受教育”,没有一天不想到胡哈儿。每次我回想起幺爹来,总是会把他与胡哈儿联系起来。
快到中秋的时候,胡哈儿打电话来,说,爪子?好久没得见你,去哪个地方发财去喽?可以听出电话那头,他有些得意。他说,他又开了一家足浴店,让小姐给你小子按摩按摩?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正在梦里。大哥他又来赶我的梦场了。我依稀觉得大哥是从那个生锈的铁锈红的铁栅栏的间隙飞进来的。大哥冷漠、无声、冰冷的两手交叉怀抱于胸前,立在面前,与窗外那蓝色梦幻般的背景融为一体,像一堵高大黑色的墙。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困顿在围墙内的一条狗。这座黑色的墙随时会坍塌、下陷,将我掩埋覆盖。我不知道,上帝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不阻止这个可恶的魔鬼来取我的性命?我把胡哈儿的电话给摁了。没多久,电话再次响了,还是这个哈儿电话。他说,妈个X,让你小子来不来?我说,老子没得空。我是要杀杀这个哈儿的火焰。不要以为他天下老子第一。我想,你个胡哈儿牛个卵?当年在我大哥面前就是狗屎一堆。
有些事情,就如同缘分,相遇了,故事就开始了。晚上,我还是鬼差神使地去了那家足浴店。既然不能做梦,又无处可去。挂掉电话后,我从枕头下面翻出一本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你们一定会笑话我吧?一个连自己的饭碗都无法拿稳的人,也看《思想录》?脑壳进水了吧?不会看看《谁动了我的奶酪》?回到小镇后,我的枕头下面会藏着几本书,无聊的时光,那些书中的人物便与我一起审视这个世界。人生的本质是什么?是到处都充满了隐喻,讽刺?还是,原本就是无限的绝望和黑暗?“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个什么呢?对于无穷就是虚无”,那个思想者说,我想,那个思想者是多么智慧,他洞彻了这个世界。我对着爬满了蜘蛛的、黑斑点点的天花板发了一阵呆。窗外不远处的大叶榕树上的叶子“哗啦哗啦”摇曳起来,好像有一道光影闪烁,那只不知去了哪儿、消失了好些天的金鹰又开始“哇哇,哇哇”不停地聒噪着。
到了足浴店,天已经完全黑了。估计已经过了十点。胡哈儿却不在店里。那个新来的妹子也不在。走出门的时候,我回头朝店里的方向啐了口痰骂了一通胡哈儿,说狗日的哈儿,心想,龟儿子放我“空枪”啊。也就在我骂骂咧咧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我怔了怔,她说,是胡老板让她给打的,我说哪个?她说:“胡天龙。”“是胡哈儿?你是谁?”听声音好像有点耳熟,我问她。她说,你忘记了?她叫蓝书香。她说,他们在哈瓦那。去哈瓦那的路上,我的脑壳里,在搜寻蓝书香的有关记忆。
“小子你牛哈,脑壳翘得很?”胡哈儿从按摩床立起身子,打了个豁嗨,“真个搞不醒活。”
我瞪了他一眼说:“管老子嗦?”
我环顾了一下屋子。房间不大,那个红色的窗帘把外面的世界给隔离开来,让房间显得逼仄狭小。墙上挂了一幅油画,一個外国女人裸露着身体眺望着大海,好像有一阵海风从遥远的地中海吹来;灯光散发着颓废的、暗黄的朦胧色调。就在我张望的时候,蓝书香端着一只木桶低着头走了进来。我忽然脸红了。下面那个地方也鼓胀了起来。我又偷看了一眼蓝书香。她的脸好像涂抹了胭脂一般,比我还要红,像“玛格丽特王妃”。
房间静静的。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我脸上的汗水像山溪里的泉水汩汩地流着。她的身上有股柠檬的味道。胡哈儿悄悄地消失了。他像一个导演,更像一个阴谋家,让一个世界与另外一个世界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无法预知的、复杂而混沌的世界。微弱昏黄的灯火此刻显得尤为幽暗,仿佛将我们的不安和点燃的欲望掩盖和扑灭下去,如同风隐藏在黑色的夜空中一般。她的手力道好大。有那么片刻,当蓝书香的小手捏着我脚踝时,我一阵痉挛。就像自己的隐私被人给窥探,赤裸裸地暴露着。
“不舒服吗,还是病了?”她声音轻得像蚊蚋,“是第一次吧?”
我摇摇头,笑笑,却又莫名其妙地点点头。结巴子地说:“不,不是的。”
蓝书香咯咯地笑了,几颗小玉米牙真白。我曾经无数次地回想那日我怎么就这么个德性,我早不是什么处男,在读中学的时候,就与胡哈儿的妹妹胡盈盈整天鬼混。我突然笑了起来,因为也就是这时候,我看见一个蚊子叮在她的胸脯上,我哎哎哎地指着她说,好大一个。她窘态地低下头去。
不久我便陷入了不安。那个晚上,蓝书香告诉我说,足疗,对缓解疲劳、放松压力还是挺不错的。她一边给我按摩,一边对我说。她为啥子要与我说这些?我躺着那张按摩床上,闪过无数个镜头:一个大腹便便、肥胖的男人,一个秃头的、冒着油脂的老男人,一个嘴上毛茸茸、孩子气的男人——他们盯着她的奶子的眼睛发着绿光,嘴角上挂着淫荡的微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和她做爱,总是,当她呼吸局促,用指甲掐我肩膀,像夜鸟一般呢喃的时候,我会忽然从她的身上一跃而起,迷惑地、惶恐地看着她。endprint
我有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月光照在窗上,风把窗吹得呜呜响。胡哈儿像一条鱼样地从水底浮了上来。
“巴适哟,格老子的。”他捶了我一下。
“喝酒去。”胡哈儿不等我们开口,便拖我们上了他的那辆红色宝马,把我们带到了“戴高乐”。我们靠着吧台,胡哈儿要了一瓶酒;舞池里,一群男男女女扭着身子,在强劲的摇滚音乐中,像抽风似的,甩着头,仿佛他们体内有只潜伏已久的兽,逃命般地急于逃离魂魄。朗姆酒闪着琥珀色的光,仿若迷幻的天空背景。哈儿喝着朗姆酒,摇晃着酒杯扯巴子,说,这个“戴高乐”,过不了几天,就是“哈瓦那”的了。起先,我只是要了一瓶“雪花”,我想不起来,蓝书香喝的是什么;灯光扑朔迷离,那些跳舞的人仿若祭神的众生鼓捣着。哈儿的面庞轮廓冷硬,严酷,眼神里透着捉摸不定的表情。他嘴里叼着“哈瓦那”雪茄,样子像极了多年前大哥的神态。他不停地给我们灌酒。我感觉自己似乎并没喝多少,照理说,我的酒量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大概是因为后来,哈儿给我喝的那种龙舌兰,或是音响的噪音,使我的胃开始翻腾起来。我起身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蓝书香追了出来,我回过头看了一眼,与哈儿的眼神碰了个正着。哈儿朝我瞥来的目光带着一股冷冷的轻蔑。
我沿着江边的一条小路往回赶。蓝书香在我的身后跟着,像无法驱逐走的鬼魅。江水呜呜地流着,仿佛从我胸腔里蹿出来,我可以听到他们的恐惧,焦躁;同时,我觉得,他们若一头头怪兽把我紧紧地裹着,不断地蔓延,让我窒息。几只鹧鸪不时地从草丛里跳出来;蓝书香发出的尖利叫声,惊醒了那些山鸡、猫头鹰们的美梦。那是一种美妙的大合唱。水面上,远远近近的,有些灯火,它们闪闪烁烁,发着吊诡的光,是不安,悸动的魂灵在这世间,骚动与呐喊吗?这时,喉咙又有东西往上翻滚,我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单位倒闭后,我几乎天天酒不离身。我也没怎么多想,反正没老婆没娃儿。怎么混不是过日子?哭鼻子有啥子用呢?在县城里和一帮朋友混吃混喝了一年多。不是说,“唯有酒肉,才是爹妈”嗎?进单位的时候,领导说,“年轻人,要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我记住了理想,可是,我没法献身啊。有天晚上,我像一个疯子,躺在马路牙子上,对着天空,人群,两只手臂高高举起:“萨达姆,萨达姆。”夜空是如此清澈,那些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星星,真是可爱的孩子,它们围绕着我做着快乐的运动,我听见有两颗星星捂着嘴笑,说:“看看,这个宝气。”行人从我身边好奇地走过,那个开“手拉手”的女孩嘻哈地对男朋友说,要是哪天我们高兴了,也睡到马路上,好不?
妈个X,我心里骂着——真的不是乱豁你们——老子是在看,有哪个星星在流眼泪。我眯起眼,想,萨达姆他头顶上的星星在哪?那天下午,朋友早早地来找我,让我去喝酒。只要有酒喝就成。兄弟们喝酒喜欢纵酒论美色,指点河山。大家伙喝得高了,有个家伙搂着我的肩膀子说:
“为破产干杯。”
“倒闭万岁。”我把酒水像祭奠先人一样洒开来。庄严,神圣。店伙计为讨好我们,把电视打开,说助兴助兴。电视里正在播放萨达姆被逮捕的画面。我惊呆了。我的嘴张开得老大。我对朋友说,不喝了,不喝了。那个晚上,我仿佛看到:萨达姆凄楚、悲凉、不甘的目光里映照着我的影子。我想,萨达姆完蛋了,我不能完。第二天,我搭了一辆小三轮从县城来到了镇子上。我不清楚自己为啥要选择回到这里,难道只是因为爹在这留有一间可供我栖息的落脚点?
如果爹地下有灵,知道我这个没出息的娃儿,如今混得叫花子一般,他会像大哥诅咒我吗?我也没有想到还会回到这个镇子上来。古人有衣锦还乡——格老子的,老子这是落魄,晓得不?
那个晚上,天空中的空气好像凝固住了。屋子外一片死寂。那些鸟也没有了往日的聒噪。蓝书香裸着身子,嘤嘤地抽泣着。
“人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太要面子,是不是嗦?面子又当不得饭饭?”我的手在蓝书香的脸上身上来来回回轻抚摸。我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蓝书香安慰。可不要歪想哟,格老子再不是个东西,也晓得感情这个事儿,要慢慢培养,急不得的。
多少年来我曾经无数次闪回到那个“牛郎织女”的月夜:繁星,朗月,桂子的暗香。它们总是在我记忆的河流里缓缓地流淌。还有蓝书香身上柠檬似的气味。窗外的树影影绰绰,几只麻雀在枝叶间喧闹。从小窗口望出去,能看到屋檐上的枝条突兀地凌空着,像鸟的翅膀。有一阵子,看上去,又像一束黑色的火焰。天空蓝得透明,清澈。星星看多了,眼睛有些迷糊,蒙眬,可我耳朵灵光得很,能听见好多好多星星在瓦片上跳跃。这是真的喃。我晓得你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儿的。
蓝书香酒量好差劲。又没看见她怎么个喝(蓝书香告诉我,在老家的时候,她能喝一大碗包谷酒),她像一只喝了“敌敌畏”的狗似的,头往后仰着,拽着黑色的蝙蝠衫领口喊渴死了,渴死了。她的脸煞白得吓人,在床脚边蜷缩着身体,觳觫着。屋子燠热,像被小蒸笼裹着,她那只手,不停地动着,动着。每一次手一抻,领口就像张开的嘴巴,我的眼睛就会不停地闪,她的胸脯起伏着,雪白的奶子仿佛要跳将出来了。我鼻子不听使唤地翕动,像一条饿犬。
好像是刚过了立冬,有天半夜,我回到屋里,看见她坐在窗前的小桌上支着下巴儿出神,我问,“发啥子呆?”她斜了一下我,小嘴巴嘟嘟,不说话,眼里水汪汪的,像是蓄着一潭月光。她说,你来看看,哪颗是织女星。
“神经戳戳,”我说,“没得事情,不会睡觉?”
“哼。”
“还牵牛星呢。”
“他们躲哪儿去了呢?”她可怜巴巴地望着窗外叹息着,好像那是她一对走失的孩子让她焦灼,伤感。
她说:“你就会骗我,还说我是你的宝儿?”我苦笑。摇摇头说:“好,不耍你,耍星星。”我揽过她的肩膀,寂阒中,可以听见窗外屋墙下秋虫的呢喃。浓黑的秀发拂到我的脸上,痒痒的。真香。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我轻轻念着。她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你还会作诗啊?”endprint
“老子只会做娃娃!”我把嘴巴堵在她的嘴上。我没有告诉她,这是唐朝的一个老夫子写的。她问我,那个晚上,我到底有没有碰她?“哪个晚上?”我嬉皮地笑着去搔她的胳肢窝。“真坏,你个四川娃子。”我把她抱到床上,说不看织女牛郎,我要看妹妹哈哈……她使劲地蹬腿用小拳头捶我,像一个被猎手捕获的小野兔子嗷嗷地叫着,挣扎着。
她简直是一只小猫。每回做爱,她喜欢以一种得意的、舒缓的动作伸展开身子,如小猫一样地躺在我怀里。我就对她说,你是一只猫。她将双手做成要抓我的样子,“喵喵”地叫唤。她把脑壳贴着我的胸口,紧紧的。彼此间呼出的一团白雾,在我们的上空、身上聚合,缠绕。然后淡淡地散开。我好像有一种不妙的预感:这个冬季,两个畏寒的人,他们将把自己最后一点热量、青春消耗殆尽,就如同火焰它带着最初、最原始的生命力量,但它最终将在燃烧中自我熄灭。我也想过:人生不就是一次远行,赴一场生死之约吗?如果能爱一次,哪怕是化蝶成蛹,甚至成为灰烬,又有何惧?她抬起下颌,怯怯地,脸儿红红的,娇嗔,羞涩,说她真的很怕。“怕啥子事情?”我抚摸着她的脸蛋说,“放心,老子会好好地疼你一辈子的。”
“不骗我?”
“王八骗人。”
我们两个人傻兮兮地从被窝里起来,坐到了靠窗的桌子旁。她拽着我的手,好像我是牛郎星似的,也会忽然间消失在遥远的夜幕中,只能遥遥相望。我告诉她,“你看,现在我们的头顶上有许多星星,有的挨得很近,有的相距遥远,那两颗,你仔细看看,喏,看到没?就是很黯淡的那两个,它们有的时候会特别亮。”她歪着头似乎是思考着,然后点点头,问:
“那牛郎和织女在哪?”
“私奔了去喽。”
“瞎说。四川骗子。”她做出愠怒的样子。她也真是好看,小鼻子,小嘴,眉毛淡淡的,有些往鬓角延伸。眼珠很黑,施了蓝黑色的眼影,脸是那种狐狸脸。我听人说过,狐狸脸的女人会勾男人的心。
她说:“我不管,你给我把牛郎和织女找出来。”我说:“明天吧,明天一定把他们给你找出来。”我已经冻得开始哆嗦。我说,睡吧。我趿拉着鞋把她背到床上。她躺着我的怀里,说,睡不着。她说她有点怕。
“怕啥子事?老子不是在你边上?”
“讲个故事好吗?”
“讲故事?你又不是小娃娃。”
“就是,就是。讲一个嘛。”她把身子紧紧地抵着我,覆盖在我的身上,那个奶子温软,绵柔,滚烫。她简直是一条浅蓝的水母,把我裹在她的怀里。一种窒息的死亡。我日后想,是否所有的悲剧都来自这种连自己都无法知晓、也不能保障的爱?后来,她用鼻子尖抵着我的鼻子撒娇起来。“你要笑死我嗦?讲故事?当饭饭吃,还是当票票用?”
我想,这个夜晚,地球上会有多少宝气人躲在被窝里说故事呢?我说,要不给你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有那么一瞬间,我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还是给她讲一讲希腊神话故事,最次,也得像模像样地像给女娃娃儿那样讲“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人,有时候会自我膨胀地把自己想象得过于强大,或虚妄,在说故事前,我想象着,蓝书香听到希腊神话故事,一定会讶异地看着我(我给她讲故事时,我隐瞒了人物的真实身份,我不知道我出于何种动机。我把幺爹改头换面了)。故事讲完的时候,蓝书香愣怔着,仿若浸淫其中。我这个也是怪得很,与蓝书香做爱后,通常我会燃上烟,靠着窗口,心想,她与胡哈儿做过爱?也会在高潮的时候,像夜鸟那样喃喃地欢叫吗?有一回,我从后面进入她的身体,她欢快地,昂起头,转过头来,眼里带着火焰,像是要喷发似的让我再用力。
她一定充满了怨恨,我心想。也许,她猜到了我内心有鬼,一个男人,为啥子,总要求女人的身体是干净温柔的?我心里问自己。有时,我能看见,她的眸子里,是那种透亮的安静和坦然。有时,是悲悲戚戚的怨怼。前些日子,我买了一本《周渔的喊叫》。书才翻看了几页,我不知道,那个叫周渔的女人,做爱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鼓捣着尖叫?
我想起来,大哥有次请一帮弟兄喝酒,他斜叼着那支在我看来代表着得意、威严、地位的“哈瓦那”雪茄说,雪萍(也就是胡哈儿的前任女友)夜里尖叫的声音,简直太巴适了,刺激啊!
“尖叫?做啥子,夜里叫?”我问。
“安逸呗!你个瓜娃子。”大哥朝胡哈儿看看,“是不是嗦?”胡哈儿紧咬着嘴巴,眼里冒着火。
那段日子,大哥和胡哈儿他们两张面孔常常会重叠起来,断裂,错开,再重叠,我分不清,他们究竟谁是我的大哥;甚至,我会将蓝书香当作那个叫雪萍的女人,有时,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这个冬天,漫长而寒冷。蓝书香渐渐地沉默寡言起来。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薄薄的雾,即使是做爱,她也很少说话;只有难得的几天,还会像先前那样,战栗着身子轻轻地呻吟。却不再用那指甲掐我了。有时,半夜,我醒来,她正襟危坐,愣愣地,睁着那双黑葡萄眼睛定定地望着天花板。墙上除了蜘蛛、被烟熏黑黄的八卦图外有什么可看的呢?有一天,她趿拉着到走廊外的厕所小解,许久了也没回到房间,我支棱着耳朵,楼道里静静的,只有一只猫在叫着,像是在寻找丢失的情郎。
对于那个糟糕透顶的夜晚,多少年来我依然记忆犹新。我一直试图将那天的事情遗忘,可发生的事情,你根本无法忘却,它就像是一个身体上的瘤子,或是印在你脸上的疤痕。后来,我裸露着半身,披着那条味道难闻的潮湿的红毛毯子去了卫生间,她蹲在地上,身子哆嗦着,脸色苍白,小声抽噎着。
“怎么啦,肚子疼?”
“不用你管,走开,走开。”她哭泣起来。
我把她硬拉起来,抱回到床上。我问她究竟是怎么啦,她不理睬我,背对着我哽咽着。我恼火地扇了她一巴掌。后来,她爬到我的身上,说她怀孕了。“什么?怀孕?”我推开她,“谁的?”我指指自己说。我听到窗外开始起风了。大榕树的叶子在玻璃窗上哗哗摇动着。我听见有个声音从自己的肺腑里跑出来:杀了他,我要杀了那个死猪哈儿。
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蓝书香。胡哈儿呢,倒是来攀西监狱探视过我一次;我们聊了我幺爹,聊了我的大哥;我们好像是之前商量好了的,都未谈起那个叫蓝书香的女人。我们生命中难道不曾有过这个女人吗?还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了遗忘?胡哈儿告诉我,其实,他才是我真正的大哥。
前年,我在南方的某个城市一个大排档上喝酒,街上是熙熙攘攘的车流,霓虹灯闪烁着暧昧的光晕,老板娘的MP3架在凳子上,那个男歌手的声音嗄粗而又带着磁性。很悲伤的歌曲。放完了,我问老板娘,能不能再放一下。她说,这是陈楚生唱的,叫《有没有人告诉你》。我说,喜欢。我让老板娘再加两个菜。她盯着我看好老长时间。听着歌,我有些迷糊了,我觉得脸上黏糊糊的有东西流下来。我起身离开。当我拐进街道时,我回身望了大排档一眼,总觉得这个女人有些眼熟。是蓝书香吗?我心里想。我回头再看她时,发现她身边站了一个男人,竟然那么像我大哥。夜色如水草一般弥漫开来。我恍恍惚惚的,不知身在何处,那些灯光,行人,像隐匿于夜色中的怪兽睁着诡异的眼睛发出毛骨悚然的嗤笑。空气骤然降温,我打了个寒战,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稀稀落落的,像極了那年的星星。据说,这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下得最大的一场雪。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