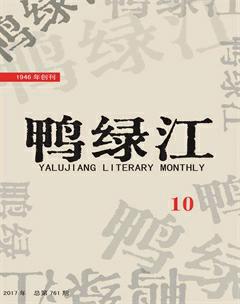男人夜话
柏亚利
海洋性气候的风,于仲夏的夜晚轻柔地吹向这座沿海城市。当风儿撞上那些高楼大厦后,被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和各种喧杂的声音揉碎了,变得悄无声息。倒是这座城市边缘处,风儿能够自由穿梭在—个视线没有被遮挡的豪华别墅区,穿梭在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穿梭在人工湖面浅吟低唱。
深圳夏季的夜晚,最是迷人。
这个精英汇聚的现代化都市里,一些中高产阶层特别是有一定“小资”情调的财富人士,愿意成为此处业主,不单因为它的优雅时尚,还在于它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别墅区:雍容华贵的会所里,除休闲、娱乐、健身项目外,还会在周末定期举办一些有品位的讲座,诸如国学、文学、哲学、艺术、音乐,还有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些讲座安排在会所一楼大堂往右、一间布置典雅的“业主沙龙”进行。商场上博弈久了,累了,这样一处家的氛围,不失为一个放松的好场所。
今晚周六,是“饮食养生”专场。一个小时的活动于夜晚九时结束。几十名听讲座的业主离去,却有三个相熟的五十多岁男人,意兴阑珊地留在“业主沙龙”里。
小区实行的是“二十四小时家居服务”,三个男人将续上意式咖啡、美式点心的服务生“谢了”出去,就开始他们三人之间的神侃。
“浩哥,我电话都催几回了,请你们全家去迪拜玩你不答应,昨儿约我们三家一起阳光酒店晚餐你也不答应。今晚把俩弟叫来喝个免费茶,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总得给个机会让我们表达谢意嘛!”
说这话的北方人大刘,膀大腰圆,头圆、脸圆、鼻头圆,尤其那两个耳垂圆成了肉珠子。他的两个眼睛不圆,两道缝,一笑更像是嵌在眉毛下的两条纹。作为一家民营电子公司的掌门人,他的主打产品远销海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大刘架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一脸虔诚地望着浩哥。
“是啊,浩哥,我跟大刘给你磕三个响头都不为过!要不是以前你拦住我们不进股市,要我们安心做实业,只怕如今我们赔得精光了!浩哥,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强弟说完开心地打哈哈,他是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年近五十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脸上老挂着顽皮的坏笑,额上有了三道不浅的抬头纹。他的资产不浅,经营着省内十余家大型连锁商场,大有滚雪球发展下去的态势。
浩哥笑说:“如果我拦不住你们,进去了也不会像他们那样豪赌吧?”
“难说,鲁迅早就说过:‘国人好赌。2015年上半年那场牛市,把多少人的赌性都勾出来,做融资杠杆。嘿嘿,幸亏我们没进去,听了大哥的话,不然赔惨了。”强弟笑嘻嘻说。
大刘亦感慨:“是啊,哥,你真是我们的头!”
“嗯,言归正传,”浩哥说,“咱们从今晚这讲座话题说开去。”
“哎,浩哥,要说这吃啊养生啊,当年给慈禧祝寿的‘百鸟朝凤不过就是鸡,给秦始皇吃的名菜‘斩鱼丸也不过就是鱼,哪像咱们吃到极致:天上除了飞机没吃过,地上除了人没吃过,你说咱还缺吃啥了,用得着叫俩弟来听这个?不如我给他们讲讲那年吃的十八万元一席豪宴!”大刘来了兴致。
强弟笑了,“吃那些沾了金粉的丸子有么子好讲的?不稀奇!稀奇的是我前些年回湖南去吃了那餐报纸上有争议的人乳宴。我如果开讲,告诉他们那些菜是怎么用人乳来调配的,准把他们眼珠子瞪圆了!哈哈!”
“这年头深圳来了新花样,雇个奶妈在家里,吃最新鲜的人乳,据说最养生,你何不如此呢?”大刘调侃他。
“嘿嘿,那我屋里的堂客还不闹得鸡飞狗跳满城风雨?”
“叫俩弟来,”浩哥打断他俩说,“是我们忙得一个多月沒见了,虽然住这么近。不答应你们去玩去吃,也是因为忙。吃就没必要这么奢侈,玩可以过年找地方三家一起去。”
浩哥身材魁梧,五十八岁的人了头发依旧密实,不像两个弟已经有些谢顶。俩兄弟尊崇浩哥,不单因为他的资产远超俩弟,还因为他博学多才。来深圳打拼多年的他,是一家大型民营地产集团的董事长。他做的项目从未失手。如今的金融形势下,他更是主张收紧银根现金为王,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买理财产品。
“嗨,我说啥事呢?又不是聊女人,用得着关这间屋里?还不如找一地喝个痛快!”大刘因脂肪肝已基本戒酒了,但只要三兄弟聚一起,他就要喝个尽兴,三兄弟只喝红酒。
他们三人相识于二十多年前深圳的“十元住宿店”。虽然各奔了前程,但凡有个难处,三人便会相聚,拿个主意,喝点小酒。也就是从那时起,三人中彰显老大浩哥的智慧和果敢,让两个弟佩服有加。也是浩哥提议,兄弟三人扎堆在此买房而居,方便彼此往来。此处建筑不是浩哥公司的手笔,浩哥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公司的落差,尽管他刚落成了一座五星级酒店,颇受业界赞誉。
大刘和强弟把不解的目光投向浩哥,却见他眉宇间锁成一个“川”字,正凝神望着对面墙上镜框里四个遒劲有力的行书字体:精神家园。
“大哥,你是要我俩来好好欣赏一下这幅书法吧?哪个名人的墨宝?”强弟不解地问,随即跑向对面墙的镜框下仔细端详,拿右手五个指尖在玻璃上滑动。
“谁写的不重要,你们看它的意思?”浩哥微笑着颌首示意。
“嗯,这和对面墙上的‘业主沙龙是一对儿,指‘业主沙龙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陶冶。”大刘坐在沙发上欠了一下身子眨巴小眯眼说,圆圆的身子把沙发填满了。
“我想,”浩哥不正面回答他俩的话,“借今天沙龙的题目,聊聊我们当知青那个年头的吃,一定很值得回味,我们过去海天海地,就没聊过这一段。”浩哥若有所思。
“好啊,我先讲。”强弟来了兴趣。
“那还是1976年吧,你们知道的,我下乡可是在湖南湘西的大山里!当地山民那个穷哦,不晓得你信不信,我亲眼看到有的人家只有一床棉絮,脏得黑乎乎一团,一家四口人挤一张床上。冬天太阳出来时,村里看到母亲在孩子的头上和衣服里抓虱子。我还看到有的孩子拿着糠饼吃,有回我饿也因为好奇要了半块来吃,那种难以下咽的味道呀,打死我也记得。好歹吃下去了,到了出口的时候也难,嘿嘿,过两天把我憋急了,用手抠出来!”endprint
“哈哈哈……”
强弟端起咖啡“咕嘟”一口,仿佛要把还在身体里的糠渣冲掉,接着又说:“第一次下队去‘双抢锻炼,又是抢割稻子又是抢插秧苗,头上烈日暴晒,脚下水田滚烫,我一个城里伢子哪吃过这种苦?拼命挨啊,尤其是饭吃不饱,到了夜里肠胃就奏起‘交响乐。好在我住的那户人家是两兄弟,仨人凑一起是个诸葛亮。他们没娘只有爹,爹爹不在家,做什么的留个悬念先不讲。那两兄弟一个叫腊狗,一个叫腊妹。你们莫笑,山里人缺文化,都是随便叫个小名。
“一个月光不太亮的夜里,我们三个人出去了。做什么?炸鱼,炸生产队水库里的鱼!
“腊狗走我前面,他瘦得真像只腊狗,其弟腊妹五大三粗,俩人不像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我夹在两兄弟中间走着,有些腿脚发软,心里打鼓:行不行啊?这可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
“不怕,甩炸药我是老手,当民兵练够了。腊妹像是看穿我的心思给我打气。
“到了,腊妹点燃瓶口上那截导火索,‘咝、咝、咝……火星直溅,他猛一甩手投向水库中间,‘轰的一声巨响,暗淡的月光下那水里犹如腾起一条白龙。
“我们仨人扑通扑通跳进水里,于混沌中一阵猛捞。得手后一路跑回去。
“到得家中,插好门,灶屋点上灯。把鱼开膛破肚,先煮来饱餐一顿!讲实话,这顿鱼的美味,打死我也记得,这辈子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鱼!那鱼汤像牛奶,比牛奶好吃!”强弟咂了咂嘴巴,好像那鲜味还在唇齿间留香。
大劉问:“那鱼炸了不查吗?那时候抓到可不得了!”
“查呀,怎么不查?”强弟眼里闪过一丝得意的光,伸出五指朝后摩挲着头发说,“我们就怕有人顺着鱼腥味来查!连夜把鱼内脏都埋进菜地里,十来斤鱼肉拿盐腌了藏在几个坛子里。其实担心是多余的,天一亮,听见队里人声嘈杂,嗬,大家都在喊捞鱼去,那就去呗。好家伙,但见水库中央白花花漂了一层鱼,足有二三百斤。全队老少都来了,会游水的下去捡了往岸上丢,家里孩子捡起往桶里装。我们也跟着抢,又是十来斤。”
“结果如何?”大刘憋不住又问。浩哥似乎预见到了结果,露出会心的笑。
“结果嘛,”强弟吧唧了一下嘴巴说,“公社里派了专案组进驻生产队来查,重点是清查‘黑五类分子,腊狗家成分硬,父亲在公社里算个不大不小的官,有这样的后台,当然没人怀疑。所以,末了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滑稽的是,招待专案组在队上那些日子吃的荤菜,就是我们炸上来的鱼,只不过是从各家摊派收缴来的。”
“怎么样?”强弟颇有几分得意,“我的光荣历史。”
“这事儿,我也有,”大刘也来了兴致,“不过你是炸鱼,我是偷跑到水库边钓鱼,我能通过鱼儿吐的泡来判断是什么鱼,比如说:鲫鱼、鳊鱼是单泡上冒;鲢鱼泡是黄豆大小密密麻麻一大片;鲤鱼泡是成串的,然后聚成团;草鱼吐的泡小,聚成拳头大的片。认识了鱼泡,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饵料。水库鱼好吃,鲜嫩,我每个月都能吃几次鱼。
“可惜,后来我调到北大荒密山农场,深山老林的,离水库太远,有鱼吃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刚去头几月还扛得住,再往后就馋得不行了,成天清汤寡水的,谁受得了?那时候谁要是回家一趟,捎点咸菜、咸鸭蛋,那得‘共产共食。那时,我被农场知青们称为‘菜包子,知道这外号的来历吗?就因为我办法多,总能找来吃的。偷点花生、地瓜之类,常事。还有,周围哪个生产队哪天要杀猪了我都能打听到,干什么?混进去,趁主人不注意就偷猪下水。有时候是一猪腰子,有时候是一猪尿泡,有次慌忙中,居然把一截还没清理好的猪大肠揣身上,粘了满身猪粪。”
“哈哈哈……”三个男人爽朗的笑声震得窗玻璃似乎都在震动。
大刘意犹未尽:“偷那玩意,得有招。棉上衣没扣子,一根草绳扎腰间,逮着目标一眨眼就进棉衣里了,有草绳兜着呢。”
浩哥逗乐:“你当时想过没,要给发现了怎么收场?”
大刘不急不忙地说:“我就跟他们求饶作揖,大爷,我们离爹娘太远,饿得慌,求您开开恩吧!
“有时实在弄不到吃的,我还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一个犒劳自己的好办法,就是想象自己坐在一个豪华饭店里,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美食,有大鱼、大肉,有冒着热气的馒头。我把它们一口一口送进嘴巴里,有节奏地嚼。饭菜的香气源源不断地飘出来,香透了整个身体。不过这之后有个后遗症,就是更饿了。”
三人又一起大笑起来。
大刘缩了一下鼻子,感叹道:“看来‘民以食为天是个硬道理,受过苦日子的人特别有感受。”
浩哥用手抚着浅浅胡楂的下巴:“我和你们有些大同小异,只不过作战人数的规模比你们大,也讲究策略。”浩哥笑了笑,接着说:“我下放在江苏海安的一个知青点。那年头,正赶上长身体,又能吃,一天劳动强度那么大,肚子里没油水闹得慌。特别是修水库的艰苦日子里,工地上的伙食那叫一个差呀,今天说来牙齿都发冷。人多,有白米粥就不错了,菜是那种黑乎乎的腌咸菜,都长蛆了。每人一大碗白米粥舀一勺黑咸菜盖上去,那蛆遇热后就拱出来,农民大哥们用筷子夹了丢掉,继续用咸菜下饭。他们说那蛆不脏,是菜蛆。”
“扑哧!”“哈哈!”强弟和大刘听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
浩哥接着说:“我们知青也只好这样做,好歹有个菜。从工地回来,人要饿疯了,就夜里出去找吃的。开始是知青结伙去偷社员家的鸡。当地养鸡不圈养,都是放养。到了晚上,鸡都蹲在院子里的树上睡觉。树不高,去捉的时候讲技巧,如果伸手抓翅膀它会大叫,用手轻轻伸进它肚子底下再托起来就不吭声,才能得手。偷了几只鸡后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妥,社员家穷啊。于是动脑筋要搞回大的——盯上了大队书记家的猪。在我们眼里,他家富裕。
“那时候猪可真是个宝。书记家的猪养得壮,是‘走地猪。社员家的猪只有一二头,都是圈养,书记家养了好几头,村里村外到处跑,那势头就好比说,我是书记家的猪,谁敢动!可我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青,硬是把书记家的一头猪搞到手了。我们当时采取的战术是这样:有的知青负责望风,有的负责赶猪,等到把这头猪赶到了我们知青点的屋里,一床被子蒙住它,一顿锄头就解决了。我们还敢作敢当,吃那头猪的肉时,我们准备了几瓶二锅头,把大队书记也请来吃,刚开始我们说是镇上买来的。香喷喷的红烧肉,书记直夸好吃。这时候,书记老婆来找他,说你还在这里喝酒,家里一头猪丢了。书记喷着酒气说:不用找,迷了点路,赶明就回了。我们连忙拿了几斤猪肉送给书记老婆,说是镇上买的,她拿着谢过走了。endprint
“酒足饭饱,我们向书记摊牌了:书记,猪,别找了,是我们杀的,今晚这菜就是,算我们欠你的。书记听了半晌没说话,随后脸色变了,酒也醒了,走时只丢下一句话:‘我算领教你们这帮知青了!”
大刘、强弟就一起问:他不报复你们吗?!
浩哥若有所思:“没有,也许因为大队中小学都是我们知青在代课,知识上用我们的还多呢。”
接着浩哥叹了口气:“那年头的我们,怎么那么浑呢?”
“刚来深圳的时候,我们也还是浑的。”大刘接着说。
“对,”浩哥说,“我们仨刚来深圳闯荡住十元店的日子,也有一个吃的故事,你们还记得?”
大刘眨巴了一下小眯眼,“啊哈,想起来了,那晚我们仨在福田区一家大排档吃晚饭……”
强弟插话:“那家便宜。”
大刘:“对,味道也不错。我们去了一看没位子要走,老板招呼我们说在门外支张桌,我们看了一下天,说这沉沉的要下雨咋办?老板说今晚绝对不会有雨。”
“是啊”,强弟接说,“浩哥还问了句,万一真下了怎么办?老板把脖子一梗牛皮哄哄:真下了,这顿饭不要你们钱,我请客!”
浩哥道:“天公作美,我们吃到一半时,一阵急雨偏就下来了!”
大刘笑接,“就听浩哥一声喊:‘还等什么?跑啊!我们三人立马就跑,跑过那条街,在一家电器行的屋檐下躲雨。”
浩哥说:“这回是强弟一声喊,‘哥们儿,我们回十元店接着吃!看吧,我手里拎着一瓶啤酒,大刘手里捧着半条红烧鱼,强弟手里抓着几块猪排骨……”
“哈哈哈……”这回不只窗玻璃震动,连屋顶似乎都要被掀翻了。男人大笑比女人笑出眼泪、揉着肚子要放肆得多,与这高档尊荣的会所似有几分不协调,惊得服务生推门探头望了一下又很快缩回去。
等三人在沙发上重又坐稳时,浩哥笑问:“我们为什么会那样?”
大刘:“人穷志短呗!”
强弟:“民以食为天!”
浩哥说:“符合马斯洛夫说的人生五项需求之首,不过我们有违常规。”
沉吟片刻,浩哥又说:“今天叫俩弟来有个原因,我最近外出考察一个项目,顺便到了当年下乡的地方。看到乡亲们还不宽裕,想想当年有愧于他们的地方,我心里痛啊,我給他们捐款盖学校、敬老院。想想我们这些年赚钱后的挥霍,特别那十八万元一桌的酒席真不该,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呢?所以我提议俩弟,不如各回一次你们刚才故事的发祥地,看看你们能为那里的乡亲们做点什么。”
“好啊,其实忙忙碌碌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藏有这个结,期待有一天解开它。”大刘说。
“我也同感,大哥,你真不愧是我们大哥!”强弟双手拍了一响。
“哥啊,你是想转型做农业吧?农业,它今后将是最令人振奋的领域,不仅在中国,在全球也是如此。还鼓动人们赶紧去弄个农场。大哥,你叫我们往乡下跑,是不是让我们也动这心思啊?”大刘顿悟。
“不一定。如果有好项目好品种,可以去做,带动乡亲们致富。”浩哥说。
大刘说:“我知道,我们有着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了,但其实还缺少一种什么。”
“追求的快乐!”强弟接道。
大刘感慨:“对!我知道钱这东西看似越多越好,其实多了也就是个数字。以前是挖空心思去赚去比较,甚至会想我哪天超过李嘉诚就好了,可是看看这世道又变了,人家巴菲特、比尔·盖茨都把财产捐出来,我就想干吗还累死累活赚钱呀,不是有些个富豪都累病累死了吗?那钱留下来有啥用?我现在有点找不着北了。”
大刘指着刚才服务生缩回去未关严的门外,有个四十来岁的清洁工在拖大理石地面,“看见没?我们的快乐也许还不如他多,一个生日蛋糕、一顿丰盛的晚餐也许就能使他满足,公司发个过节的红包,也许就能让他乐上好几天……”
强弟打断大刘:“他的快乐是没有保障的,比如家人突然重病或一场灾祸。没有经济支撑,沉重的债务立马就会把这种平民快乐击个粉碎。”
大刘反驳他:“我指现在的时空状态下。我和你还有浩哥,我们谁不担忧商场上的竞争对手?我们出门谁不担心自身安全?怕自己、怕妻子儿女遭到绑架,现在有人仇富心理那么重。你说一个清洁工他每天有这样的烦恼吗?”
三人一时无语。
还是浩哥先打破沉默:“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索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常常迷惘:有了钱的这些年,吃、穿、玩都尽兴了,我们想换的也都换遍了:车子、房子、妻子……我们到底还要什么?除了钱还是钱吗?”浩哥的声音变得有点沉缓,“我不是说教,我们前面大半生其实是有意义的,磨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然后用精神力量打拼出财富,获得财富后,我们精神的那部分棱角就慢慢磨平了。”浩哥的眼神又定定地望着对面墙上的镜框,“看这几个字,能勾起我的回忆和一份沉思。”
这回,是强弟打破沉默:“我知道了,精神的东西永远要摆在第一位。我看过报道:国外发达国家,人们基本上每年读五十本书。就是说,每星期应该读一本书。看看当下周围,我们有吗?”
“每天都学点东西才不落伍,才不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浩哥说。
“惭愧,我可是多年没有好好读一本书了。我会把今天这感受说给我公司里的员工。其实每个人都要固守一个精神家园,有这方面的追求,不然,就是一个躯壳,像我,就只是个赚钱机器。其实,我常常觉得自己精神空虚,走不下去了。”大刘颇有感悟。
“这个精神方面有得研究了,要和以后的事业挂钩。”强弟兴致勃勃。
“拿红酒来,服务生!”浩哥大声招呼,“看来我们要好好喝几杯,接着往深里聊!”
“叮当”,脆生生的碰杯声中,酒杯映红了三张不再年轻的脸。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