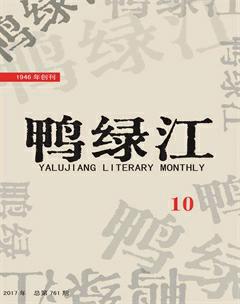粉红衫儿青丝帕
王选
粉红衫儿青丝帕,妹唱歌儿为了啥?
唱得渴了唱饿哩,唱我心上的难过哩。
想唱歌儿给郎听,高山挡住不传音。
菜油倒到瓷碗里,唱着叫你心软哩。
我总是搞不清父亲为什么把海明叫海明娃。按理说,他们是一辈的。但这么一叫,感觉海明就成小一辈的人了。再说,他已经三十好几的人了。
我们跟着父亲把海明也叫海明娃。从来不会叫海明叔。一是这么叫好玩。另一个因为他是光棍,我们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他。反正父亲这么叫,我们学来的。当我们伸着脖子喊海明娃时,他总是举着一双鞋垫佯装追赶而来,要打我们。末了他还会说,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但海明娃总算还是秦源村里的厉害人物。他会绣鞋垫。村里会绣鞋垫的男人,就他一个。
绣鞋垫,先要有鞋垫。他从村里关系好的女人们跟前要一些旧衣服、破布头,堆在炕角。然后把玉米面馓成糨糊,我们叫“面然”。旧衣服,拆了线,剪成布块。铺一层布,刷一层糨糊。再铺一层布,再刷一层糨糊。跟配套练习一样。糊了二十来层,最后糊白洋布,就行了。再糊一个。这样就是一双。压席底下,热炕烘。三四天就干了,印着细密的席子纹。硬邦邦的,像一面干牛皮。从旧课本里翻出鞋底的样子,用针线固定在鞋底上。一把快剪刀,沿着样子小心翼翼剪掉多余的部分,鞋底就成型了。
然后是绣。花线是从走村窜乡的货郎担那里买来的。货郎担挑着挑子,吆喝着“头发换针换线来——”经过他门口。他一个男人,没剪下的长发。只好用粜粮食的现钱,买了十来样花色的线。有酒红、水红、粉红、大红、大黄、明黄、橘黄、屁黄、鹅黄、草绿、墨绿、粉绿、浅绿、深蓝、冰蓝、天蓝等,一个颜色一小股。
绣鞋垫,是腊月里农闲时间的活儿。大雪落了两天,封了山野。男人们凑一堆,暖着热炕,喝酒、划拳、游胡。女人們凑一堆,干点手工活儿,拉呱点鸡毛蒜皮。海明娃不爱跟抽烟喝酒、吵吵嚷嚷的死男人坐一起,就喜欢钻进女人堆里。人家做鞋子、打毛衣,他绣鞋垫。他绣得最好的是荷花。趴在炕上,先用铅笔在鞋垫的白洋布上轻轻画上轮廓,没画好的地方,细细擦掉,再画。成形了,就用圆珠笔描一遍。然后开始绣。绣鞋垫是个慢活,得一针一针来。鞋垫厚,用顶针使劲推,才能钻透。不小心,还会打了针尖。
半个月,在一坨热炕和一堆唾沫里打发掉了。
雪落了一场又一场。不觉间,一双鞋底拉好了。粉红的瓣儿,明黄的蕊,墨绿的秆儿,草绿的叶。一朵荷花开得艳,还有几个花骨朵。两只蝴蝶,一只蓝、一只黄,扇着翅膀,往返流连。他还会绣一种格子的,方块状,看着就很复杂。但他得心应手,映着窗外的雪,飞针走线。女人们时不时瞅瞅海明娃的鞋垫,满眼羡慕,嘴里啧啧不已,恨老天把自己生得心笨手粗。
海明娃的女人缘好,大家都爱跟他在一起,有说有笑,还能听他打山歌。打山歌是他除绣鞋垫之外的另一项本事了。如果说绣鞋垫是硬工夫,那打山歌就是软实力。这个满村的男人不会,女人们,也没人会。
干一阵手工,指头就酸麻了,得歇歇。有人提议,海明娃,给我们唱一个。海明娃还推辞。唱一个呗,时间长没听了。唱一个。忸怩了半天,禁不住怂恿。他边剪着鞋垫背面的线头,边说,那唱一个。
天空的云彩黑下了,地上的雨点儿下大了。
睡到半夜哭开了,记起你说下的话了。
天发白雨天变黑,我成了草上的露水。
连来了三趟着没见上你,一辈子留下的后悔。
山不远着隔河远,河水响着叫不喘。
我有心和你见个面,没有桥着不能见。
烟雾收起雨来了,尕妹妹寻着我来了。
天发白雨着哩,我把花儿领进庙哩。
你搂哩吗我抱哩?把佛爷吓得张口哩。
佛爷本是泥菩萨,咱二人坐下白不咋(不会怎么样)。
女人们红着腮帮子,不知是炕太热,还是心里热。嘴上嚷嚷道,唱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想哩想哩实想哩,想得眼泪大淌哩。
想哩想哩不想了,浑身称不下一两了。
一把拉住绵绵手,心里有话难开口。
女人们稀里哗啦笑了,脸更红了。
打山歌,是海明娃从小在他母亲那里学来的。母亲一直想要个姑娘。但没有,就把海明娃当姑娘带。六岁前,穿花布鞋,穿裙子,穿碎花衬衫,头上扎“刷刷”。在厨房做饭,他烧锅,母亲擀面。母亲就给他教,一句一句。母亲怎么会的?母亲是舅婆教的。舅婆怎么会的?得问舅婆的舅婆了。海明娃记性好。教六七遍,就记得差不多了。
五月里,胡麻花儿开。蓝格盈盈的花,像一面海,映照着蓝格盈盈的天。风吹来,胡麻花儿微波荡漾,溅起了几只黄蝴蝶、紫蝴蝶。
海明娃蹲在地埂上给猪挑菜。他前年腊月里看的老母猪,快要下崽了,最近口刁,胡麻衣子用开水烫了,撒上玉米面,不好好吃。成天哼来哼去,就爱吃青菜。这家伙,跟人一样,一怀胎,就嘴馋。好在洋芋地的草锄了,玉米苗匀了,割麦子尚早,是个空当,还能挑趟菜。
菜挑满了,压得很瓷实。海明娃坐在草坡上,歇缓一阵。眼前是成片的胡麻花,蓝得发紫,蓝得晃眼,蓝得让人想起隔山的妹妹,被河坝里的溪水打湿了花衬衫。想起隔山的妹妹,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委屈。
那一年腊月,他去镇子上赶集。在猪羊市场来来回回半上午,硬是花了二百元看了头猪娃。就是现在养的母猪。卖猪的一手提起猪娃后腿,塞进了化肥袋。猪娃在袋子里拧来扭去,吱哩哇啦叫个不停。付了钱,海明娃揪起袋子,扛在背上,就走了。快出集市时,肚子有点饿,才想起早上走得急,没吃。便挤到一家小吃摊子上,坐在长条凳上,要了一碗面皮,猪娃放在一边。面皮刚端到手,一根还没咽下去。袋子口没系紧,猪娃一挣扎,从袋子里钻出来,跑了。他赶忙丢下碗,撵猪娃去了。
集市上人多,你拥我挤,猪娃在人缝里钻来跑去,海明娃拨开人,追赶着。但人实在太多,流水一般,拨不及。眼看着,猪尾巴在人们腿缝里一晃,不见了。他心急如焚,满头冒汗,像蒸包子的汽。在人群里找来找去,依旧没有猪影子。他想着要么跑丢了,要么被别人捉走了。这么大的集,这么多的人,就是丢个背篓都找不见了,何况还是一只会动弹的猪。他有点丧魂落魄,心里咒骂着该死的猪,放慢了脚步,无精打采地东瞅西看。正当他准备放弃寻找时,突然看见不远处一个女的站在台阶上,手里倒提着一头猪。正是他的猪,他认识,肚子上有一大块黑斑。猪还在挣扎着,吼叫着,腰弓着,腿踢腾着。endprint
海明娃和那女的就是在集市上这么认识的。
那女的就叫妹妹。他们总是在集市上能见到面,说话也投机。时间久了,海明娃就有了追求妹妹的想法。村里人都说海明娃不正常,会绣鞋垫,会打山歌,爱钻女人堆,是个“二意子”人,对女人没兴趣。但人们都错了。海明娃也会喜欢女人。只是以前没有遇上合适的。
他问妹妹,我想和你好,你觉着咱们能不能在一搭?妹妹脸一红,没点头,也没摇头。那就算是同意了。他在集上给妹妹买了一件新衬衣。那时候,已经不时兴扯布缝衣服了。妹妹抱着衬衣,脸红得啊,像抱着个煤炉子。临走时,海明娃还塞给她一双绣花鞋垫。这一次,不是荷花,不是五瓣梅,是一对凫水的俊鸳鸯。鲜红的嘴,鹅黄的脚,白色的眉纹,紫蓝的胸,蓝绿相间的羽冠,在雪白的布面上,游动着,游进了妹妹的心窝里。
海明娃的心意是明摆着的。妹妹也是满心欢喜的。
海明娃说,我给你唱个山歌吧。妹妹点点头。
你是谁家的女子娃?两肩吊着长头发。
红板立柜双抽匣,想死不能到一搭。
不许胡唱,你过几天到我们家来一趟,知道吗?妹妹扑闪着黑眼珠,说完就走了。
海明娃提着两瓶酒,请上媒人赵桂喜去说亲事了。但结果让人失望。女方家父母一个是嫌海明娃年龄大,另一个嫌没有父母,孩子嫁过去,要受罪。能说会道的赵桂喜,说了半辈子媒,基本一说一个准,但这一次,他费尽口舌,还是没有说服人家的父母。
这事就这么一直拖着,也没有眉目。海明娃再没找,也没托人介绍。妹妹赶集少了,也不知道啥情况。
海明娃揪了一把屁股边的草,看着胡麻花,自然勾起了伤心事。他心里一直放不下妹妹,总是梦见他们在地里割韭菜。但人家父母态度坚决,好话说尽,人家不听,也是枉然。妹妹毕竟是个乖姑娘,长了二十来岁,啥事,都是父母做主。父母不同意,她也只能偷着哭几场,不敢说半个不字。他已经三四个月没见着妹妹了。这满眼的蓝,让他想起了妹妹。那股惆怅,像五月的风,在他心尖上刮来刮去。他不由得唱了起来。
月亮上来锅盖圆,把你缠了整两年。
心里话儿千千万,多咋能给你说完?
双轮磨儿转圆了,把你缠了两年了。
年时个(去年)缠你到今年,看不上人吗没因缘?
黄杨木的香筒子,想死不得两口子。
黄杨木的立柜儿,想死不得一对儿。
爱你爱到心里了,想你想到命里了。
假若和你见一面,今晚死了也心甘。
今生今世不见面,黄泉路上等百年。
七月里,麦子进场。
八月里,麦子晾干,就要碾场了。碾场是个吃力活,大都是村里对路的人互相帮工。你给我家碾,我给你家碾。从胡麻花儿落了,结上豆大的小铃铛开始,海明娃就没消停的时间了。他人缘好,每天都有人叫着去帮工。海明娃爱去,一来凑个热闹,二来混一顿饭。反正他光棍一条嘴一张,也懒得做饭,能凑合一顿算一顿。加之时间一长,没见着妹妹,心里老是隔着一疙瘩东西,不舒坦,就更没心思做饭了。
前天晚上,赵耕田捉着一根旱烟锅,吧嗒吧嗒吸着,来请他,帮着明天碾场。海明娃应了。
碾场,第二天,主人家起大早,把早已被拖拉机碾轧得光溜溜的麦场再扫一遍。然后站在梁上,朝村子里大声吆喝:摊场了——摊场了——听到吆喝声,帮工的人扛上木叉或者铁叉,到场里来了。有人上麦垛子,从顶上把成捆的麦子丢下来,几个人用叉推到场中间。海明娃一叉扎进麦捆,感觉软绵绵的,提起麦捆一抖,四五只没长毛的老鼠儿子掉了下来,红兮兮的身上,透着暗蓝色的血管,在地上蜷成一堆,蠕动着,发出了吱吱声。海明娃用铁锨铲起来,丢在了麦场下面的荒地里。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恶心和不安。
在麦场中间的人,把麦腰拆开,麦穗朝上,一圈圈均匀地摊开。最后像波纹,一环套着一环,摊满了麦场。
摊完场,大概十点,拖拉机就进场了。秦源村人少,没人开拖拉机。碾场,得请其他村子的拖拉机,完了给人家掏点油钱和人工费。差不多二百元。碾第一遍,拖拉机不挂铁辘轳,因为麦子没轧平,挂上辘轳,会被颠翻。拖拉机从外向里,一圈一圈,织布一样,细密均匀地碾着。突突突的叫声混合着蓝色的柴油烟,在村子边上,没有休止地缠绕着,缠绕着,伴随着那些扬起的灰尘,挂满了村庄的每一根树枝。
帮工的人到了赵耕田家,吃晌午饭。油饼用大铁盆装着,放在地上。谁要吃,随手抓。汤是鸡蛋汤,鸡蛋打得多,搅得匀,白是白,黄是黄。地桌上摆着白菜炒粉条、凉拌胡萝卜丝、炒洋芋丝和咸菜。人们围成一堆,蹲在地上,稀里呼噜喝着汤,开着玩笑。两碗汤,三个油饼,几筷子菜下肚,就饱了。
海明娃不爱和男人们在一起。和几个帮工的女人在院子里,围着一个小板凳吃。
吃毕晌午。大家又到场里,开始抖场。拖拉机歇了,颤抖着身躯,哈着粗气,停在场边。司机回去喝汤了。人们在外面,站成一圈,用叉把碾过的麦秆挑起来,抖动一阵,将碾出的麦子抖落在地上。再将麦秆翻到外面。人们从外向里,有规律地依次转着圈,像指针一般。第一遍抖完了。拖拉机进场,接着转圈碾。人们躲在没有碾的麦垛子,藏在阴凉里。主人家的西瓜来了。大家在灰尘里一人端一牙西瓜,哼哧哼哧啃了起来。
海明娃和一帮女人坐在一堆没有搭起的麦草里,闲聊着猪的事。聊了一会儿,有人问起妹妹的消息。海明娃叹了一口气,说,没那个缘分,我也不指望了。女人们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有人后来说,不行就算了,说不准后面还有更好的等你呢。海明娃苦笑著,说,像我这情况,要人,人长得也不攒劲,要钱,手头没几个子儿,要房,几间塌房烂院,要父母,两个早早就死了,你说人家看上我的啥?我还是把光棍打好就成了。别说这丧气的话了,我们大家都给你留意着,有合适的再介绍,来,给咱们唱一个吧。
高山的烟雾缠山嘴,我照妹妹在担水。
照着山上着不着人,照不见妹妹急坏了人。endprint
再往高处走一走,瞅着妹妹去的地方瞅。
照着窗子照着院,狠心的妹妹不闪面。
盘盘路来路盘盘,哥在门前打转转。
哥在门前打一转,妹在屋里点灯盏。
灯盏点着你没来,把你坏了良心的。
花儿担水扁担响,不由我的眼泪淌。
豌豆开花吊着呢,看见花儿笑着哩。
人有几个十七八,花儿能开几次花?
第二轮抖场,是从里向外,还是一圈圈,逐渐扩大。麦子经过反复碾轧,麦粒脱了,混在麦衣里。麦秆也被轧扁了。人们用破毛巾捂着嘴,带着草帽,只留一对眼睛。麦子的灰尘扬起来,雾腾腾一片。眼睫毛上,像落了厚厚的霜。
第二遍抖结束。拖拉机挂上辘轳,接着满场转圈碾了。
帮工的人,到赵耕田家吃午饭了。人们在瓷脸盆里,洗手、洗脸,洗得脸盆里的水黑乎乎,脏兮兮,快成泥了。有人蹲在大门口,捏着鼻子,哼哧哼哧擤鼻涕,一串串灰尘又黑又黏,在鼻孔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擤出来。有人用毛巾掏耳朵,一掏一疙瘩土。有人脱了鞋子,往外倒着麦子,饱满的麦子顶得脚趾头发红。
午饭是黄瓜凉面。凉面油泼得多,油光光,滑溜溜,浇上黄花臊子,撒上黄瓜丝。人们蹲在廊檐下,狼吞虎咽。一个男人,三四碗。最后,提来了三扎啤酒,放开喝。男人们端着瓶,仰着头,咕咚咕咚灌,喉结上粘着麦衣,上下滚动。女人们用碗喝,可能是渴了,也可能是乏了。女人们酒量也分外好,一碗接着一碗,直喝得两颊杏红,两眼冒花。海明娃也喝了五碗。他酒量很差劲,两碗就晕,三碗脚底下就拌蒜了。五碗眼皮子直接就搭在了一起。
吃完午饭。再回场里,抖最后一轮场。这次一抖,麦穗上碾轧掉的麦粒就全脱落在地上了。
拖拉机吼叫着,跑着最后几圈。人们分成几堆,围坐在场边,有的抽烟,有的瞎聊,有的提着酒瓶,还在喝。
女人们和海明娃在一起。或许是酒喝多的缘故,她们眼珠子发红,嘴皮子耷拉,咧开笑着的嘴,忘了收回去。她们显得异常吵闹,异常兴奋,时不时冒出一句黄话。有人提议海明娃打一个山歌,要那个点的。海明娃眯缝着眼,假装不懂。问,啥样的?
就那样的,你看,这样的。有女人伸着大拇指,碰了碰食指。
其他女人一看,立马哗啦啦笑倒在了麦草堆里,被灰尘呛得差点咳断了气。
海明娃故作难为情,说,我可唱不了那样的。
你把啥不会,来唱,再不唱,我们就教你了。有人凑上前,在海明娃肩膀上使劲掐着,打着,笑着。
行吧,我唱,我唱,给各位妃子们打一个山歌听。
女人们又是一阵哗笑。
八月里来八月八,我和阿哥拔胡麻。
阿哥一把我一把,阿哥我并肩拔。
一拔拔到地埂下,阿哥给我梳头发。
日头下山牛进圈,我俩回家吃黑饭。
吃着吃着心变了,窗户关上门闩了。
丝绒裤带扯断了,花鞋后跟蹬烂了。
手扒肩膀脚蹬墙,耳环子摇得铛啷啷。
叫声哥哥你算了,三魂六魄都散了。
这一次女人们彻底笑翻了,大家一个个倒在麦草里,捂着肚子,蹬着腿子,张着嘴巴,笑声压住了拖拉机的突突声。笑到最后,有人咳嗽着,快把心脏咳出来了。有人眼泪扑簌簌落在腮帮子上,哈喇子在下巴上扯了一尺长。有人又是拍打着大腿,又是捶胸顿足,笑得差点晕厥过去。
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有人说,海明娃, 你太坏了。有人说,来把海明娃闪了(抬起来,丢到空中,再接住,如此反复)。大家一哄而上,把海明娃压在下面,他使劲挣扎,也无济于事。光那些丰硕的奶子就把他压展了,更不要说那些长年累月干活的胳膊大腿了。有人抓着海明娃的手腕脚腕,有人揪住他的衬衣,有人扯住他的裤腿,更多的人抓在他的裤带和裆里,他仰面朝天。有人喊,起。海明娃被高高抛起来,他看到了蓝格盈盈的天,像极了蓝格盈盈的胡麻,那胡麻,让他想起了妹妹。他心里一阵怅然。但紧接着,他又坠落、坠落,背后被抓住,又抛起,又坠落……妹妹在胡麻花里朝他挥手,又消失,又挥手,又消失……
最后,女人们听见了怪异的破碎的声音。
海明娃落下来,像一摊泥,女人们没抓住,落在了地上。扑通一声,溅起了白花花的灰尘。
海明娃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他像一只虾,腰弓了几下,就绷直不动了。女人们吓傻了。拖拉机碾完了最后一圈,停在场边,熄了火。世界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寂静,像抽空了一般。
接下来,就是起场,把麦秆抖成堆,三四人一组,抬到场边,码成草垛子。最后就是扬场了。
扬场,要等风来。但没有风,人们等来的是女人们的惊愕和尖叫。
海明娃死了。
有人说,海明娃是被女人们不小心捏破了蛋,疼死的。男人们说,海明娃,终究还是死在了女人手里。
三天后,妹妹和她舅舅來了。据说是家里人拗不过妹妹,只要一反对,她就睡炕上,两天不吃不喝,父母怕出个三长两短,只好同意了,先让亲戚带着去见见面,谈谈结婚的事,等腊月里,如果有日子,就把这婚事办了。
但妹妹再也没有见上会拉鞋垫、会打山歌的海明娃。
【责任编辑】 宁珍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