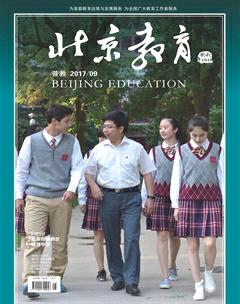教育新思维:地方教育与地方感
[摘要]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说明“地方”概念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探讨“地方”概念的意义;第三部分说明以“地方”为出发点,如何形成新的教育观点、思维与探索教育实践的可能。
[关键词] 地方 地方教育学 地方感 地方性
为何以“地方”为起点
为何以“地方”为重新思考和检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基础呢?“地方”不就是个平凡无奇的日常用语吗?正如许多研究者(Casey,1998,2001;Greenwood,2003,2010;Hung&Stables,2011;Malpas, 1999;Relph,1976;Smith&Sobel,2010)所说,“地方”是个貌似平凡实则涵义丰富的语词,因为人不是生存在空洞的宇宙之中,而是存在于某种地理因素、环境元素、空间架构之中,因此,从多元的语用脉络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环境的“地方”。
“地方”概念之探讨
在此,我们检视几位重要思想家关于“地方”的定义。加拿大学者David Greenwood(2003)将“地方”分为五向度:知觉、社会学、意识形态、政治、生态。人们对于“地方”的理解包括上述五个相互影响的面向,“知觉”面向偏向于个体与地方的关系,个人感受某个地方,通过身体各种感官如眼、耳、鼻、舌、身与地方互动、理解,并建构该地的意义;而其他四个面向则倾向于从群体角度看待人与地方的关系,包括某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习俗、宗教、传统等因素。这些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成为在特定地方的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地方”的意义涵摄复杂多元因素与复杂面向,也揭示出人与地方相互建构、相互依赖的关系。Greenwood提及的第五个生态面向更具特殊意义,但是这一面向最常被忽略。地方的生态面向意味着,理解“地方”应纳入自然生态因素,并将非人类的存在纳入考虑,包括生存在同一地方的动植物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因素。
美国哲学家Edward Casey(2001,684)曾指出:“没有地方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也没有地方”,这个洞见相当重要。“自我”的探索一向是教育学者、人文学者与哲学家的重要课题,但是探讨“自我”通常集中在文化、道德、伦理或艺术向度,忽略了空间或环境因素。我们通常认为,“自我”只跟“人”有关,即与其他人的互动影响“自我”的内涵,但是生活的环境或空间,则可能与“自我”无关。Casey指出,前述观点是有缺失的,环境、空间或地方是自我生存不可或缺的向度,每个个体都必定生存在某个场域之中,这个场域的空间或地理因素会在无意之间渗透、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进而影响个人的自我建构与认同。“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我在哪里”(Hung&Stables,2011)。Casey(2001)认为,“自我”其实是“地理我”(geographical self)。人与环境的长期互动产生“惯性”(habitus),而“惯性”是“自我”与“地方”交会互动的中介,具体是指生活于特定地方的人们经过长期实践产生的一种行动倾向与习惯,居民“内化了地方上的特性”而产生惯性。Casey通过Bourdieu的“惯性”概念来说明,“地方”是人们自我的一部分,当人们的自我在时空中不断更新改进,也不断与地方互动之时,会将地方环境的各种因素融入自我。
加拿大人文地理学者Edward Relph(1976)则提出一个相当具有意义的概念——“地方感”(sense of place),当人们与地方有真实、深刻、长久的互动,人们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对地方产生出深沉丰厚的情感与思想,包括认同与归属,那么,这个地方对于人们而言就是一个具有深度真诚(authentic)“地方性”(placefulness)之处。
综合各种观点,笔者认为,所谓“地方”并不是任意的场地或空间,而是对个体具有独特意义的所在。某个地方对于某人具有特殊意义,是因为个体与这个地方有深刻的、真实的互动。对于个体而言,当一处地方让个体产生归属感、安全感、依附感、参与交融等情感,这个地方对个体而言就具有了“地方性”(sense of place,placefulness)。这样的地方才叫做“地方”,并对于个体而言具有丰富的“属真性”(authenticity)。总结来说,本文所说的“地方”意指“有地方感的地方”(a placeful place)(洪如玉,2016,86)。
正如上文所述,“地方”不是泛指一般的地方、场所,也不是Lefebvre(1991)说的抽象空间,而是指对于个人“具有独特意义的所在”,如家、学校、童年游憩的绿地、某个公园、某个湖泊或山脉等。这栋建筑、这片绿地之所以能被称为“地方”,是因为此地对于个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特别的意义在于个人的“重要生命经验”(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就发生在这个场域。
基于“地方”之新教育学思考
清楚了“地方”的基本意涵,接下来进一步思考的就是“地方教育学”的意义。“地方”包括人为或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如上述Greenwood将地方分为五个向度,涵摄了个体的知觉,群体的社会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脉络,还有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通过人与地方的多面向互动,人的自我认同在此过程中逐渐建构发展,而人们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影响、改变、改造地方或对地方进行保存、保育。在此,笔者想探讨两种环境的地方教育学的实践,一是人造环境,二是自然环境。
人一般生活在人为环境之中,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接触真正大自然的机会少之又少。如果我们同意Casey(2001)所言,地方会影响甚至形塑人的自我,那么,人为环境也会在无形中形塑了人的自我。Relph(1976)曾经指出,现代建筑景观所产生的“乏地性”的地方,包括下列五种特色:1.“导向他方的地方”(other-directed places)。受旅游文化影响、为迎合观光客需求的建筑物或区域规划,这些建筑与当地的自然生态或人文环境全然脱节,只是一味追逐时尚流行;2.“迪斯尼化”(disneyfication)。一种让人们脫离现实的人造、奇幻、想象的乐园化空间,如迪斯尼乐园等;3.“博物馆化”(museumisation)。一种刻意仿古的历史性建筑规划;4.“未来化”(futurisation)。地方的未来化可说是迪斯尼化的一种,与上述博物馆化恰好相反,博物馆化关注过去,未来化则充满各种对未来的想象、对科技发展或太空探险的美好愿景;5.“郊托邦”(subtopia)。“郊托邦”是指现代都市郊区地区的空间,它混合了他方导向、商业化与迪斯尼化的特征。Relph之所以提出“郊托邦”,是因为在北美地区,大多数中产白领阶级居住的高级社区建在都市的郊区,形成一个不同于都市中心的区域。当然,这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洪如玉,2013)。这些受到现代科技影响所构筑出的新型地景,可能有趣,但是却缺乏生命力。人们可能会想去一探究竟满足好奇心,但却很难对其产生认同或归属感。换言之,这种地方不会被当作“家”。endprint
我们把焦点转向自然环境的“地方”。现代人可以在都市中的公园或保留地、郊区、乡间的溪流、农田与林地等处,接触到自然的“地方”,动植物等非人类生命的孕育与成长,代表着地方的自然因子,与其互动也能培养出居民对于自然地方的地方感与认同感。然而我们面临的事实是,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而且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仍抱有消极的、事不关己的态度。如南美洲雨林被大量砍伐,北极冰层融化、乡间麻雀与溪流中鱼虾的大量减少等,人们对于身处周遭地方中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视而不见。然而,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切,应源自对周遭地方的敏锐感受与真诚关怀,这正是培养“地方感”,也是地方教育学的基本目标。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三点地方教育学的具体建议:
1.关于人格培养与自我认同。基于前述可知,“地方”是人格与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地方特有的语言、文化、习俗、传统、记忆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个人成长经验,因此“地方”也可說是某种潜在课程。有时,潜在课程对于人格与自我认同培养的影响力甚至大于显性课程。如人格教育或道德教育非常重视某些重要的普遍价值或德目,如大方、尊重、公平、孝道、勇敢、慈善、正义等美德,但“地方”才是落实并促成价值或德性内化于人格的真实脉络,如果学生在教科书里学到诸多价值或德行,与真实生活情境的经验不相符,学生学到的价值或德行就可能沦为口号,无法产生真实的教育意义。再如教师期待培养学生尊重大自然的素养,但是学生的地方经验却是充斥污染或废弃物、山林滥砍而无人闻问的环境,“尊重大自然”的价值教育对于学生就无法产生深刻作用。因此,如何建构一个让价值或德性得以落实的地方,在人格教育上意义重大。
2.关于课程规划。课程编制与编纂教科书也应注意“地方”蕴含的各种文史民俗与生态自然元素,不同区域、环境的课程除传授共同的基本知识之外,还应具有特殊性。教科书编定主要是部定课纲,适用于全国学生,缺乏对地方的各种元素的具体描述。在部定课程的架构下,融入地方的特殊文化特色与自然生态议题,将课程编制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材料,这不但符合学生的具体生活经验,也更有助于地方文化传承与培养学生关怀周遭自然生态的态度。
3.关于学校具体环境规划与建设。地方教育学主张,学校规划的具体实践可与户外教育、服务学习、社区教育、环境教育连结。学校并非孤立于社会的单位,而是社区的一部分,因此应与地方、社区结合。所以,学校教育不应该仅仅限于教室与校舍里,学校建筑以外从校园到社区都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学生到社区进行户外教育、服务学习,或到学校外的自然野地进行环境教育,都可视为地方教育学的实践。在建筑与环境规划上,学校应摆脱围墙的局限。学校与地方是一体的,围墙将学校与地方分割开来,以往学校在规划过程中常为了安全因素而筑起高墙,事实上,这反而可能造成学校教育与社会的隔离,忽略学生具体真实经验的缺陷。
最后,当人们能够理解并感受自身与身处的自然环境(包括一般环境中的自然元素)之间的关系,人通过与周遭的互动,也会深刻地融入自我并形塑自身的未来以及后代子孙的未来,人们对周遭环境就会更重视、更在意、更有感触,也更能激发出守护与保育身处环境的热诚与期待。如,我们一般最为在意的地方应该是自己的家园、家乡,“家”通常是最具“真诚地方性”之处。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守护家园的情感、知识与行动,并将此种感受与理解转移或扩大到其他地方,“地方”不仅止于自己的原生家园,也可能将新地方建构为家园。因此,无论是人为环境或自然环境,倘若该处对我们而言具有真诚地方感,我们对其有认同与归属,不同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家”。将街道、都会、公园、乡野、山林、海港视为家,就可能促使人们将爱家、护家、持家的感受与实践施展于不同地方。Greenwood(2010)曾指出,守候地方就包括重视与保护地方上的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与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换言之,地方教育学的目标是重新深度检视自己身处之处,重新理解自己与地方的关系与意义,了解地方特色,尊重地方文化与自然生态,在此基础上可建构具有人文生态关怀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编辑 李刚刚
参考文献:
[1]洪如玉.“地方”概念之探究及其在教育之启示[J].台湾:人文社会学报,2013,9(4):257-279.
[2]洪如玉.从地方教育学观点探讨跨议题融入之课程与教学[J].台湾:课程与教学,2016,19(2):83-102.
[3]Casey, E.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4]Casey, E. Between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in the place-world[J] 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1,91(4):68-693.
[5]Greenwood, D. A. Foundations of place: a multi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place-conscious education[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03,40(3):619-654.
[6]Greenwood, D. Place-based education: Ground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n geographical diversity[M]. // Smith, G. A. & Sobel, D. (Eds.), Place- and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in schools, New York, NY: Routledge,2010:137-154.
[7]Hung, R. & Stables, A.Lost in space, located in place? Geo-phenomen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school[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1,43(2):193-203.
[8]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Blackwell: Oxford,1991.
[9]Malpas, J.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0]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UK: Pion,1976.
[11]Seamon, D. Lived bodies, place, and phenomenology: Implicaitons for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J].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2013,4(2):143-166.
[12]Smith, G. A. & Sobel, D.Place- and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in schools[M]. New York, NY: Routledge,2010.endprint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