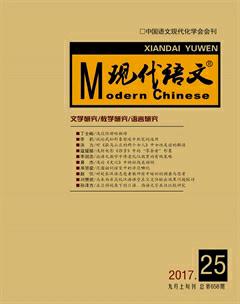毛姆《面纱》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解读
摘 要:小说《面纱》是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毛姆的代表作品之一。文章试图通过运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相关理论,来解读《面纱》中女主人公凯蒂的曲折经历及从一个被社会塑造的女性向一个“独立主体”的命运转变过程。通过采用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内在性”和“他者”,来分析凯蒂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她的精神是如何游走于平庸与反抗之间,并最终走向主体意识觉醒历程的。
关键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内在性 他者 主体意识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形成于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并发展成为女权运动的重要流派,它的显著话语诸如:“内在性”“他者”“超越性”,为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流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把波伏娃的《第二性》作为重要的理论支撑,且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深挖女性“内在性”和“他者”身份的塑造。这门女性哲学从性别身份的差异来反思我们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建构中的不足,并提出了女性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行性路径和方法。无疑,毛姆小说《面纱》中女主人公凯蒂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和身份意识觉醒历程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希望通过对凯蒂的解读,会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使得女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努力摆脱传统男权制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一、凯蒂“内在性”的束缚和“他者”身份的被塑造
波伏娃用“内在性”来描述女性的性别特征。“‘内在性描述的是一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对历史不会产生影响的工作处境,在这种处境中女性处于封闭、被动而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其外在表现最直观的就是女性在经济上、文化上对男性的依赖。”[1]从凯蒂的成长历程看,她的“内在性”的形成和她的家庭密切相关,凯蒂从小就是一个美人,且活泼又可爱,而这先天的资本在她那虚荣又势利的母亲——贾斯汀夫人那里都成了可被利用的资源,她在凯蒂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为了使女儿和绅士们相识,她频频给女儿谋得参加舞会的机会,并经常在一旁敏锐地打量着一切,为女儿洞察形势。她野心勃勃,要为女儿寻找的不是一个好丈夫,而是一个杰出的丈夫。[2]为了给女儿撑排场,几乎把她爸爸赚的钱全都花光了。而这时凯蒂已经到了二十五岁,还是单身,她更是怒火冲天,经常给凯蒂甩脸子。作为一个母亲,她教导女儿的不是努力工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来实现人格上的自由,而是引导她把幸福生活寄托于男人,一个杰出的丈夫。另外,对于男人的依赖,还体现在凯蒂母女们对丈夫、父亲的态度上,她们始终把丈夫、父亲当作赚钱的工具,供她们吃喝玩乐,而父亲挣钱少了,她们母女则表现出冷漠和蔑视。而在和唐生撕破脸皮后又回到被自己羞辱的瓦尔良的身边,无疑经济上对男人的依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经济原因,还有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在以往的历史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男性的手里,衡量、评价女性的一切标准都是男性参与制定的,女性大多被要求优雅、贤惠、顺从……就像凯蒂对瓦尔特所说的:“我就是这样被教养大的,我身边所有的女孩都是如此……你不能强求我不具备的东西……我有的仅仅是可爱漂亮,天性活泼。”[3]凯蒂的言语中透露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中男权思维模式在法律和伦理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凯蒂及她身边的女孩子都把对男性的依赖作为自己的内在准则和观念指导。女性正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男性的主体意识,并心甘情愿地处在“他者”身份下。
波伏娃从存在主义的视域出发,从大量的神话和文学作品中悉心捕捉男性意识的蛛丝马迹,对人类文明做了深刻的梳理,她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4]并阐述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5]贾斯汀夫人虽然是一个野心勃勃且支配欲极强的女人,但是在社会中女性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极小,所以她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丈夫所在的父权制社会中,而女儿们正是母亲的缩影,也希望通过找一个条件优渥的丈夫来实现自己的经济依赖。貌美虚荣的凯蒂为了不再看母亲的脸色,为了避免在妹妹的婚礼上显得难堪,一气之下嫁给了老实本分的医生瓦尔特,在婚后难掩内心的欲望,蠢蠢欲动,直到遇到唐生,奋不顾身地跃入唐生编织的爱的陷阱之中,坠入男人的权力牢笼之中,唐生亲切地称呼凯蒂为“小东西”“小鬼头”,足以显示在男权话语中,女性并非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他者”。
二、坎坷境遇中主体意识的觉醒
凯蒂原本坚定地认为深爱着的唐生会给自己爱和归属,可以成为自己毕生的依靠,孰知唐生自私自利,善于钻营,根本不会为了凯蒂牺牲自己的大好前程。绝望、悔恨还有苟且的生存欲望迫使她重新回到瓦尔特身边,心灰意冷地踏上霍乱瘟疫盛行的湄潭府的路程,而这也开始了她的精神救赎之旅。初来这座被瘟疫笼罩下奄奄一息的中国南方小城,凯蒂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修道院,却恰遇一个修道院的姐妹不幸去世。在与修道院长交谈之中,凯蒂得知这些姐妹们单纯又善良,她们带着博爱和对宗教虔诚的信仰背井离乡来到这片苦难之地,来拯救这里的难民。这些深深地触发了凯蒂内心深处的同理心,她向院长自告奋勇,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说过去的凯蒂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会选择平庸,她逃避母亲的脸色,逃避不喜欢的婚姻,逃避情人的背叛,逃避跟随丈夫到异国湄潭府的艰苦,那么现在她生命里的责任与爱被召唤起来,她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去反抗苦难,反抗过去那个庸俗逃避的自我。她每天辛勤工作,悉心照顾孩子们的衣食起居,他感觉精神焕然一新,浑身充满了力量,工作的充实也使得她渐渐淡忘了唐生。在与修道院的姐妹们和韦丁顿的攀谈中,在自己的审视下,唐生和瓦尔特的面纱渐渐被解开。唐生的愚蠢虚荣和自私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小人,而表面上木讷腼腆的瓦尔特却隐藏着一颗厚道和善的心。
说到底真正唤起凯蒂主体意识觉醒的还是在修道院的所见所闻,修道院的姐妹们带着圣母一样的光环,她们离开热爱着的祖国法兰西,在充斥着疾病和困苦的异国他乡来照料呵护那些受苦受难的儿童,最终收获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这里让凯蒂觉得与自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修道院长,她是一个朴素且谦逊的女人,但骨子里却透露着威严,她来自法国的名门,却缄口不言自己的家世,她优雅温和,将关爱给予每一个孩子,却从未有任何抱怨。她意识到在这里,自己是多么无足轻重的人,自己以往的琐事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些为了男人而歇斯底里的岁月是多么荒唐可笑。她甚至对自己瘦弱寡言的丈夫产生了友好与敬重之情。“安宁,在工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不在欢乐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或这所修道院中,它仅仅存在于人的灵魂里”[6],修道院长的话恰似一道灵光将她的精神引向光明。丈夫瓦尔特的死对她来说是一个解脱,因为在她的内心深處,她并不爱他,甚至是厌烦。但是当她窥见自己内心的龌龊想法时,愧疚感油然而生。这种变化是由一个被社会塑造的女人向独立主体的转变,减弱父权统治下对第二性欲望的控制而倾向于更多地考虑人性的理智与信仰。endprint
再回到英国的凯蒂,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了避开母亲的嘲讽而着急嫁人的无意识的洋娃娃,在经历唐生的背叛、异国瘟疫、瓦尔特之死、修道院长指引、怀有身孕、母亲病逝后,凯蒂心中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一面逐渐觉醒。[7]怀有身孕的凯蒂最终选择和父亲一起生活,是她主体意识选择的结果,并非要依附于父亲的男权地位,而是为了弥补这么多年缺失的爱和责任。在结尾处,凯蒂对腹中的孩子寄语到:“我要把女儿养大,让她成为一个自由的自立的人。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爱她,养育她,不是为了让她将来和哪个男人睡觉,从此把这辈子依附于他。”[8]凯蒂在坎坷遭遇中逐渐摆脱了“内在性”和“他者”对自己的束缚,不再依附于男人,而是努力迈向个体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进而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在“内在性”中寻求超越。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夏区教育厅“产学研聯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DT201606]。)
注释:
[1]刘慧敏:《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的自由与解放——浅析波伏娃的<第二性>》,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3期。
[2]阮景林译,W.S.毛姆著:《面纱》,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3]阮景林译,W.S.毛姆著:《面纱》,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4]陶铁柱译,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5]陶铁柱译,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6]阮景林译,W.S.毛姆著:《面纱》,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7]刘露:《从恶魔、天使到理想女性——论<面纱>中主人公凯蒂女性意识的觉醒》,名作欣赏,2016年,第35期,第114-116页。
[8]阮景林译,W.S.毛姆著:《面纱》,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参考文献:
[1]刘慧敏.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的自由与解放——浅析波伏娃的《第二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
[2]阮景林译,W.S.毛姆著.面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陶铁柱译,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刘露.从恶魔/天使到理想女性——论《面纱》中主人公凯蒂女性意识的觉醒[J].名作欣赏,2016,(35):114-116.
(景莉莉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 7500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