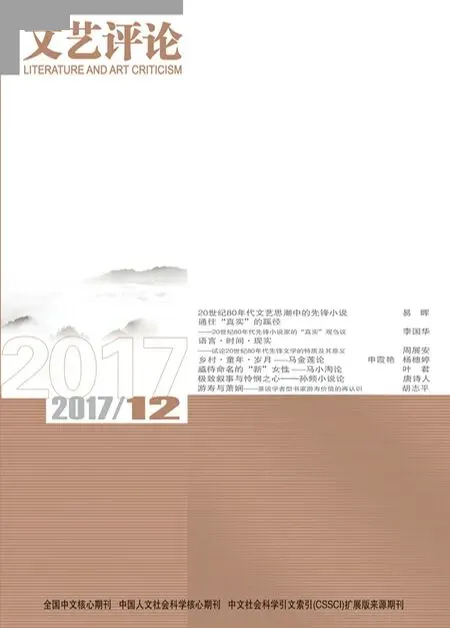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文艺思潮中的先锋小说
○易 晖
20世纪80年代文艺思潮中的先锋小说
○易 晖
1987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推出了一期“实验文学专号”,进入这期专号的,有后来成为“先锋小说”代表人物的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和孙甘露,但他们当时还只是一些“身份不明的无名小辈”,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此之前已发表过先锋作品,但像这样冠以“实验文学”的名号集体亮相,在文坛尚属首次,而这也标志着作为一种流派或思潮性的“先锋小说”正式登场。就像当年“朦胧诗”的兴起一样,“先锋小说”的这种“实验”在当时也招致了怀疑和不满。多年以后,余华回忆这期专号时写道,“其他文学杂志的编辑私底下说《收获》是在胡闹,这个胡闹的意思既指叙述形式也指政治风险”,“当时文学界盛行这样一个观念: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①。“胡闹”“不是小说”“玩文学”,这样的批评言辞也显示出“先锋小说”背离当时的文学主流是多么遥远。
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一个思潮纷呈、流派迭起的年代,文坛盛行着突破与创新之风,每种思潮、每个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尔后即被继起者挤到一边。从新时期文学发轫的“伤痕”“反思”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无不以否定前朝,别立新宗而名世。但是相比前期的那些思潮、流派,“先锋小说”的创新(或者说背离)无疑是一种全方位的质变,是从文学观念、作家主体意识到叙述风格、语言的根本性变化,用批评家陈晓明的话说,是“无边的挑战”②。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小说,尽管是对当代文学前三十年“革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两结合”文学的否定和批判,但同时也是对“揭批文革”和“拨乱反正”的国家话语的响应与表达,是对前三十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颠倒的承续;其后的“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小说”,尽管从不同的面向对“伤痕”“反思”文学与国家政治话语的高度同构保持警惕与疏离——前者返身传统文化,试图以现代意识激活传统,以传统匡扶现代;后者则既拒绝伤痕反思式的政治批判,也不愿勉力充当为国家把脉、为民族寻根的文化英雄,他们是现代化的敏感者和践行者,又是“后文革”(或“后革命”)时代反抗压抑、捍卫自我的个人主义者,文学在他们那里成为生存观念变革的载体。
而“先锋派”比他们走得都更远,其变革与创新不仅是内容上的,更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是以形式——集中体现在叙述观念、策略和语言上——的实验创新达到对内容乃至文学整体的变革。
“先锋小说”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现实主义把文学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反映,强调文学描写现实的客观性和典型性,这种文学观建立在一种相信人类能够真实准确地把握和再现世界与人生的认识论基础上。而这样一种文学认识论到了“先锋派”那里就成为问题。“先锋派”的文学观深受西方现代、后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已变得岌岌可危。弗洛伊德认为,所谓的人的本体不过是一个只知道满足眼前快乐的昏昧的本能;继起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哲学则是要把人从“自然界的统治者”和“意义的唯一合法的指定者”的宝座上拉下来,③并进一步追问和颠覆弗洛伊德曾经试图树立为“我”之本体的“无意识”,得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具有语言的结构”,“主体最终只有承认,他的存在只是想象的产物,这个产物使他什么都无法肯定”④。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宣告具备某种认识论和观念形态的“人之死亡”:“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想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相反,对所有那些使全部认识依赖于人本身之真理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若不想人类学化就不想形式化的人们、若不非神秘化就不想神话学化、若不直接想到正是人在思维就不想思考的人们,对所有这些有偏见和扭曲的反思形式,我们只能付诸哲学的一笑……”⑤
中国的先锋派作家在西方现代、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学与哲学观念的浸润下,既不相信人能够真实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也无意去描写所谓的客观现实,甚至根本上就取消了文学中的“真实”概念。先锋小说家当然要描写和展示叙事者所观察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现代派”的反叛性的自我表达中抽身出来,转向客体世界,在先锋派那里,借助文学来传达/表达某种文化价值、某种“真实的”生存状态的使命感业已消失,写作是从对社会关怀意识与本体论自我意识的双重怀疑与否定中展开。
在先锋作家中,马原堪为玩用消泯真实/虚构界限的叙事游戏的前驱和高手,当其他人还在默默地探索和转变时,他就写出了一系列手法纯熟的先锋小说。马原曾经把自己的创作方法归纳为“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⑥,他的小说一般都有非常结实的故事,人物、情节、细节、环境等等都清晰可睹(即所谓的“偶尔逻辑局部逻辑”),似乎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的传统规范,但同时通过技术上的跳跃、拼接,通过对人物无内心、无主体状态的刻画,通过对文本的有序性、内在统一性的破坏(即所谓“大势不逻辑”),来拆解现实主义建构的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隐喻、象征关系。马原的一部中篇小说就直接冠名为《虚构》。“虚构”之名者,似乎预示着作者要写作一部纯想象性的小说,以“元小说”的方式拆解作品的写实性。作者开篇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这是一次虚构,一次杜撰,一次为获得耸人听闻的故事效果而进行的天马行空的编排。与此同时,作品又将现实作者、文本叙述者与主人公形象这三重身份通过文本中“写小说的汉人马原”而扭结在一起,似乎又是在做一篇自传性的写实小说。因此,阅读这个文本就变成了一次在文学阅读契约的两难困境中的“冒险”:读者既难以按写实/纪实性作品的阅读契约把它理解为作者的自叙传(或拟自叙传),又难以按虚构作品的阅读契约把这个三者合一的“马原”理解为具有象征、隐喻意义的文学形象。叙述者看似平实、写实地讲述自己独闯麻风病村的离奇经历,细致地描写对麻风病人的生活内容、习性、人性的观察,乃至于与麻风女人包括性的交往经历,但由于这种观察和描写始终严格摈弃心理和情感的介入,会让人产生一种全然的陌生感,因为这个麻风病村根本就是一个虚无之境,而闯入虚无之境的主人公也就成为虚无中的虚无。读者阅读中隐隐产生的对人物形象在人性、人情意义上的理解和判断,最终被这种虚无感所瓦解,由此会意识到,文本开篇的那些关于“虚构”“杜撰”“天马行空”的交代和声明,不仅是在叙述技巧意义上的提示,同时也是在文本主题上瓦解人性内涵的暗示。通过对“虚构”和虚无之境的描写,马原的小说进行着从意义的建构、传达、解释到故事的讲述,再到意义的颠覆的转换,世界和人生在马原那里就像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说的那样,“既没有意义,也不荒谬,它存在着,如此而已”⑦。
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重建文学主体性的过程。所谓的“文学主体性”,对外是文学要摆脱政治的依附和工具地位,“回到文学本身”;在文学内部,意味着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文学形象,都要从外在的社会身份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本身”。新时期前期的“伤痕”“反思”小说,文学主体性主要表现为通过批判极“左”路线束缚,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达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社会权利与价值的确认。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和文化不断开放与转型的背景下,这一文学主体性运动发展到“现代派”(诸如刘索拉、徐星、刘毅然以及早期的王朔)那里,则进一步内化为个体的独立人格、生命感觉和生存价值,“现代派”写作孜孜以求的目标,便是要创造出区格于他者——尤其是表征着压抑的社会规范或“父法”——的主体形象,表达一种觉醒、差异和反抗的自我意识。
然而这一目标在先锋派那里则被弃之不顾,在先锋派看来,那种青春式地把文学当作宣泄苦闷、表达欲望或确立自我的工具的做法是幼稚而虚妄的,既然现代主义赖以立身的“非理性”“无意识”都是“他者的话语”“想象的产物”,又如何能通过文学确证和呈现话语之外的本体自我?!实际上,“先锋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导致知识分子身份错位、变迁的产物,在“后革命”或“后人道主义”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先锋派一方面和大众一道分享社会文化转型、意识形态解魅带来的自由,同时又面临着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大众意识、情感、意愿分离的处境,而先锋派更通过自己的写作促成、张裂了这种分离:他们似乎牢记艾略特“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⑧的忠告,既放弃自我呈现,放弃那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性化、本体论的“自我意识”,又拒绝那种站在时代精神中心的“关怀叙事”,而只是在经历、相像、幻觉甚至迷失状态下钩沉文本化的“临界感觉”。
在解构自我意识神话方面,格非1988年发表的《褐色鸟群》堪称先锋小说的典型文本。这篇小说运用博尔赫斯式自我悖反的迷宫结构来追问存在之迷,展开的却是一次反存在主义的书写,通过解构自我在时间之流中建立起来的记忆、意识、经历、身份……最终解构自我本身。和马原的《虚构》类似,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参与故事,有一种阅读作家自叙传的效果,讲述“我”——一位蛰居水边的作家——与少女棋的两次相遇和交谈,又引出“我”对以往混合着梦境与幻觉的经历的记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点中国古典记梦、仿梦小说的影子——如六朝的《枕中记》《南柯太守记》。在传统小说中,梦的内容尽管荒诞离奇,但它被严格锁定在梦境中,与现实是清晰可分的,它或者传达出古人乃至人类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永恒追求,或者表达对沧海桑田、一切皆空的悲寂。而《褐色鸟群》表达的却是后现代的时空观、存在观,作品刻意泯灭了主人公在梦境或迷幻中才有的超验感觉与物理世界、现实经验之间的清晰界限。或许主人公在故事里的单个经历是可读、可解的,但整合在一起则不可思议,捉摸不定,作品在一种互相反悖、互相颠覆的记忆叙述中层层展开,它不像《虚构》那样,从非逻辑(即虚构)入手进入逻辑内部(即具体的故事讲述),最后又回到整体的非逻辑,而是逻辑与非逻辑同时并行,在回忆与讲述的展开与怀疑中,使叙事始终在真实与幻觉的两端来回游移,最终消解叙事、故事与现实的关联,同时也消解自我的真实性,达到庄子式的“蝴蝶是周,周是蝴蝶?”的奇妙效果。“存在还是不存在”,人类这一亘古之问被“我”的时间游戏和语言游戏的迷宫感受凸显出来。
如果说《褐色鸟群》通过追问存在而展开反存在主义的书写,那么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则是一部借助“伤痕”素材创作的“反伤痕小说”,并在历史的复现与遮蔽的悖反中揭示人的自我意识、主体身份连带历史记忆如何丧失的悲剧命运。作品讲述一名研究中国古代刑罚史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初年被造反派抓走后失踪,20年后,即1986年,他成为一个疯子,回到当年生活的小镇,并当众在自己的身体上一件件表演古代惨不忍睹的刑罚。作品截取当代中国变化最剧烈、最富有历史感的一段历史的两头——“文革”初年和结束后的第十个年头。对前一个时间点,作品描写主人公在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一种本能化的恐惧,以及恐惧中的下意识幻觉,它既来自“文革”中的恐怖见闻,更来自浸淫在主人公脑海中早已被知识化、文本化的残酷历史,两者在历史教师的实际处境中高度叠合,因此,历史——作为被习得的文本化历史和亲在的现实化历史——导致了他的疯狂,这是一种走不出过去,永远停留在历史当中的状态。而作品重在展示历史的另一头,让一个疯子来承担复现“历史记忆”的重任,这是一种戏弄,更是一种悖论式、悲剧式的隐喻。我们知道,疯子一般是没有时间感的,更谈不上历史感,甚至连身体感觉也异乎常人,而疯狂作为一种极端变形的自我丧失症状,同时又积聚起强大的精神病理学动力,使得主人公能够顺利地、触目惊心地释放关于历史的本能的、深刻的记忆——古代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同时又暗示性地把它们与“文革”的残酷相联系。当他在自己的肉体上桩桩件件地施刑的时候,自我被彻底客体化、表象化了,在他歇斯底里的臆想中,他变成一个施刑者、复仇者,将他从文化、历史,也许还有个人经历中获得或遭遇的种种罪恶、仇恨、残忍、邪恶都无比畅快地释放出来。在这里,余华魔鬼般残酷的想象力,不仅表现在他细腻地、毫无遗漏地描写疯子(历史教师)施刑/受刑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施刑的满足、受刑的惨状,更在于他精细地过滤掉任何人性、人情的蛛丝马迹,让观看与阅读反应仅仅停留在一种纯生理的恐怖和窒息状态。但这样一种历史复现方式,其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那些惨不忍睹的施刑/受刑场面,始终在小镇上人们(包括主人公的妻子和女儿)毫无所知的模式和依然故我的日常生活的对照中推进,后者的历史记忆始终没有被激活,历史就是在“疯狂”、“刑罚文本”、“施刑/受刑表演”这样一些历史能指的无限滑动中抽身离去,永远伫留于人们的视域之外。正是在这里,我们读出作品“反伤痕文学”和“反启蒙”的内涵。
放弃了摹仿和反映现实,也放弃了呈现“自我主体性”,文学在“先锋派”那里“回到了自身”,其中一个关键表征是“先锋派”对文学语言异乎寻常的关注。固然,任何时期的文学、任何作家都不会不关注语言,但“先锋派”对语言的关注是如文学理论家彼得·比格尔所说,建基于“艺术自律”之上,“是以艺术作为一个与生活实践分离的领域而完成其进化为前提的”⑨。传统现实主义把语言当做透明的媒介,与现实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认为语言一方面来自人的观念、意识和情感,产生于并服从于现实,同时又能准确而完整地表达人的观念、意识和情感。而先锋派认为,语言不是一条走向意义、走向自我的直通道,它本身就包裹着意义,建构着意义,也扭曲或分解着意义,不是人(主体)的意识(意义)在生产自己的语言,而是人类在社会现实、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一整套表意系统、话语方式决定着意义生产,人不过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⑩。因此,语言在“先锋派”那里被确立为文学乃至存在之本体,所谓“自我”——如果存在的话——也正是在对陈词滥调的旧语言的拒用、对蕴涵着新的社会、文化和美学观念的新语言的寻找与接纳中产生,写作对于“先锋派”来说,正是一件语言破坏与语言开拓的工作,是罗兰·巴特所谓让“马拉美说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说的‘改变世界’同时出现”的“语言乌托邦”⑪。
这种语言乌托邦追求在孙甘露这位被陈晓明指认为“当代小说写作最极端的挑战者”⑫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读过他的《信使之函》的人不会忘记里面五十多个“信是……”的判断句,你可以把它们读成隽永的诗、富于洞见的哲言,或者华丽的废话、貌似惊醒的呓语,唯一能确定的是它们不曾对信这一事象做出过任何功效和逻辑意义上的判断。在《请女人猜谜》这个文本里,颠覆的对象从事象转移到人物,主人公“士”一会儿是个具有启世和谕世功能的作家,一会儿是个偷食医院标本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摇身变成钢琴师或球童、工于心计的谋士或心力交瘁的臆想者、忠诚的爱人或虚伪的偷情者……这种极端化的身份分裂表明人物与故事、情节、细节一样,纯粹出于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生成于一种不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的“语言游戏”中,文学语言便从传统上的思维、表达或实践的工具颠倒为主宰——“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兰波),文学形象的真实性、一致性被毫无顾忌地取消了。通过这种“语言游戏”,孙甘露也殊途同归地与马原、格非、余华等走在瓦解同一、本真的自我和人性的道路上。
①余华《1987年:〈收获〉第 5期》[N],《北京青年报》,2014年3月21日。
②⑫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 138页,第138页。
③[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A],转引自杜声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M],台北:远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④[法]拉康《拉康选集》[C],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9页。
⑤[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6~447页。
⑥马原《方法》[M],《中篇小说选刊》,1987年第1期。
⑦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A],柳鸣九主编《新小说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⑧[美]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C],王恩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页。
⑨[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2页。
⑩[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⑪[法]罗兰·巴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A],见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