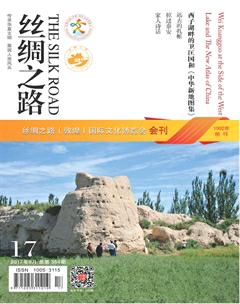远去的扎帐
徐永盛
春分降春雨,雨润大凉州。2016年,河西走廊上的第一场雨雪来得比往年早一些,雨和雪绕着河西的山川、平原、沙漠,在不同的生态区里奏着交响曲。不管是淅沥的春雨,还是曼舞的飞雪,都在这片一度以干涸而出名的土地上营造着朦胧的、诗意的美丽。
就在雨亦飘飘、雪亦飘飘的日子里,因着扶贫任务,我再次驱车前往远方的扎帐村。
一
扎帐,是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东坪乡的一个行政村。
每一个地名,就是一个地方的史志丰碑。东坪,藏语称“东本措哇”,取藏族部落名“东本”和“坪山”首字而得名。“措哇”,是藏族社会最普遍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可见,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东本和坪山两大部落的人们在这里安家生活。今天,这里有大麦花、扎帐、坪山和先锋四个行政村。没有走进东坪乡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那里有平坦的山峰吗?那里有野性的大麦花吗?谁曾在那里扎帐安营?谁又是那片土地上的先锋?
东坪乡,位于天祝县最南端,当地人称之为“飞地”。这里东与兰州永登县河桥镇相连,西南与青海乐都县芦花乡相邻,北靠天祝赛拉隆乡。偎依着大通河,“鸡鸣三县”成为这道岭上、这个村落里一道永恒的风景。
从有着“天马故乡”“葡萄酒城”之称的武威出发,向着华锐高原天祝县出发,有近140公里的路程。从天祝县城到东坪乡,又有着110公里的路程。为了赶时间,我们在拂晓6时的夜色中踏上了前往扎帐的路。
“昔我来兮,杨柳依依。今我去兮,雨雪霏霏。”没有了穿越古浪峡、翻越乌鞘岭的惊险与豪爽,在接连穿越乌鞘岭五个隧道后,天祝县城华藏寺已经遥遥在望。由此继续前往东坪乡,需要取道永登县和青海乐都的部分地方。从手机上打开卫星地图定位识途,从永登县城开始,一路经过永登县通远乡、连城、河桥镇,在河桥镇分岔,一路直达海石湾,便直通向东坪乡。沙沟、墩岭、牛站……这些沿途的村名与七曲八弯的山路,无不显示着这是一个隐于大山深处的村落。
资料上记载,明朝初年,大元宗室脱欢率部投诚,被安置于连城。他的儿子巩卜世杰于明朝永乐元年(1403)奉旨进京,被升任庄浪卫百户。后来,脱欢的孙子因为立有军功,又升任土司都指挥使,并赐以鲁姓,由此在这里形成了有名的鲁土司。从明朝初期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鲁氏土司家族一直统治着连城一带,他们的辖区包括今天永登县的连城、河桥、民乐、通远大部乡镇和兰州的红古、西固,以及天祝县的赛什斯、赛拉隆、东坪等乡镇,还有青海民和、乐都、互助等地区的一部分地方。近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鲁土司家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无疑,东坪乡扎帐村,同样属于鲁土司的领地。
山路陡峭,迂回盘旋。前望,重山云隐疑无路;回首,逶迤悠长如银练。行行重行行,时将午时,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东坪乡扎帐村。
二
朝辞凉州午扎帐,日月两扇门虚掩。
村妇笑问何处来,谷水堂里一野人。
扎帐村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山岭,当地的人们俗称“西坪山”。西坪山上住着东坪乡的村民,东与西的概念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意义。
走进扎帐村,真正在现实世界里还原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情景,记忆里所有与山有关的古诗词在这里一一得到复活。雨雪笼罩中的扎帐村一片静谧,除却贫穷等与苦难有关的话题外,那苍老的枯树、危檐的屋舍、飘逸的炊烟、风雨浊蚀的残垣,乃至悠闲的毛驴、羊只,都在古朴苍凉中呈现着曼妙的意象。
村子里,一个个如用久了的火柴盒般的院子横七竖八地卧在各个山窝里,参差错落,有棱无角。门上的对联和门神尚留着还未散去的新春气息。留着长须的老者,全然不顾雨雪的飘洒,站立在大门口,抽着烟,望着我们。村妇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顶着头巾,领着孩子去串个门子聊个天。几个赶学的孩子,拿着雨伞,三五成群地走在雨幕里。
今天,他们在此扎帐,是这片土地的主人。那么,在更遥远的过去,是谁,在这里扎帐建下了自己的家园呢?
2014年金秋时节,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脑海里就一直徘徊着这样的思考。同行的天祝县广播电视台台长李旭春告诉我,这里有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利用午休的短暂时间,我在东坪乡干部马伟鹏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那处马家窑文化遗存。
扎帐村有八个组,当地的人们称之为社。每个社既可以称呼为规范的几社,也可以用当地村民的俗称。扎帐村六社,就是所谓的罗家湾,就有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在一片阳山坡东西约400米、南北约500米的坪地上,当地村民发现了石斧、石锛和单耳、双耳的各种彩陶罐、壶、瓶、杯等器物。经专家考证,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当地文物工作者还从村民那里收集到了一件形体较大、既无耳又无柄的锥状尖底瓶,这在马厂类型中实属罕见。无耳无柄,底端尖锐,既无法提水,又不能盛物,究竟为何用,尚待考究。或許,它只是祭祀的器皿,或者墓茔的葬品。
秋日正午的阳光和煦地抚摸着罗家湾这方平台,山风习习,天高云淡。轻轻走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恐扰了远古的先民。不经意间,一次次触及到半裸露在地面的残陶片瓦,数千年前锅碗瓢盆的生命之音便哄然作响。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定西发现了距今5700多年的马家窑文化。它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30多年后,考古专家通过调查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认定它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是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继承和发展。据出土于马家窑的人骨鉴定,创造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居民与中原仰韶文化创造者同属一个种族,他们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武威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得华认为,羌实际上是游牧民族,戎是农耕民族,羌戎是个历史概念。它在天祝县这一带活动的历史很悠久,一直到隋唐时期。这些研究成果说明,扎帐村的土著民族,应该是羌戎。他们在迁徙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创造了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彩霞。endprint
还有另外一处马家窑文化遗址,在东坪乡坪山西北的小沟村。这里暴露的文化层厚40~60厘米不等,现在已经被当地的农民辟为耕地。当地群众在耕作时发掘出了石斧、石凿、羊型石锤等许多石器和罐、壶、杯、纺轮等陶器,还有一些石质坚硬的刮、削、砍、砸器。彩陶钵罐造型粗糙,大部分为砂石岩磨制而成。有的施以黑色、红色的彩绘纹饰,纹饰以网纹与三角纹为主,夹杂菱形方格纹及平行线条纹等。这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的特征基本吻合。由于时间匆匆,第一次前往东坪乡的时候,我无缘得以参观。后来,马伟鹏发来微信说,下次相逢的时候,一定带我去看看这个比罗家湾遗址更大的场景。可惜,这次相逢又因为时间和雨雪天气的原因而不能成行。
扎帐四社的社长叫马兆瑞,今年已经60岁。他们的祖上是从临夏迁来的。马社长说,前些年,外地人盗掘文物成风。他们趁着黑夜,偷偷钻进坪山村,用一种细而长的类似探测器的东西来寻找、挖掘文物。当地人在土地上耕种,有时候一夜过后,地里的作物都不见了,全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洞坑。我问老人,为什么当地的村民不去挖掘文物?马社长说,村民们都很本分老实,他们相信地上的麦子,种一年就有一年的收成。
扎帐,这个大山深处的普通村落,承载着天祝藏族自治县历史长河里最重要的两处信物,已经不再平凡。而在当地的一些宣传资料上还提到,相传文成公主当年就是从这里进藏的,扎帐村的名称据说就是因为公主在这里安营而来。我查阅了文成公主进藏的大体路线,从大唐王朝的国都长安出发,到今日的西藏拉萨,大唐公主走在今天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四省区约3000公里的和亲大道上。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省的界山——陇山后,先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然后溯渭水继续西上,越过鸟鼠山到达甘肃临洮,最后从临洮西北而去,经过河州渡黄河而进入青海境内,先后到达青海民和柴沟北的古城和昔日被称为鄯州的青海乐都。今日的东坪乡扎帐村临近乐都,但是否由此经过,史料没有详细的记载,亦不知官方缘引了哪里的资料。
在与马兆瑞社长和80岁的党迎禧老人交谈中,问及这里有没有与文成公主相关的传说或民间故事。他们说没有听说过,也觉得这样的宣传有些牵强。村民们倒是告诉我,他们的祖祖辈辈,确实与迁徙有说不清的关系。这里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大麦花村,一个叫小麦花村。这其实是青海一个大部落的两个姑娘嫁到了这里之后发展起来的。藏语中把女婿叫作“木华”,时日久了,大木华和小木华所在的村子就音变成了大麦花村和小麦花村。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运动,是事物的本真;迁徙,是村落的宿命。扎帐,在美好的期盼与祝愿中,亦然无法改变万物固有的规律。从远古时期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人,历经强汉盛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扎帐的,是新人;远去的,是故人。而山未变,岭依旧。
三
结缘扎帐,扎帐便扎根于心田。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关注着、搜索着与扎帐有关的信息。
天祝籍学者李占忠曾写过一篇文章《天祝是土族的故乡》。他在文中写道,天祝是甘肃土族的主要分布区,也是土族的故乡。据《凉州志考·德集·平番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鲁土司辖民“有土民三千二百四十五户,二万一千六百八十六人”,共分十旗,即上四旗、中二旗、下四旗。大通河流域的朱岔、天堂、炭山岭、赛什斯原本就是土族的发祥地,经历了由吐谷浑先民融合当地民族向土族演化的全过程。作者还写道,东坪乡是著名藏族学者乔高才让的家乡。这位学者小时候经常看到村子里和永登县牛站坡一带有一部分藏族和汉族,在每年农历三月初的一天,集中在一个僻静的山弯里煨桑烧纸,翻穿皮袄、头戴毡帽,跳一种类似于安召的舞蹈,跳完后在野外吃肉喝酒。乔高才让认为,这些人的祖辈原是土族,后因种种原因融入藏族或汉族。但为不忘祖先,他们定期举行追忆仪式。从而说明天祝县的东坪乡及相邻地区在古代就是土族聚居的地方。
省迎春一家六口人,却包含了汉族、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四种民族。在和当地村民的交谈中,他们不觉得这里有集中的土族,但对牛站坡却有着一定的崇敬之情。走向扎帐,必须路过牛站村。这个村子位于连城镇最南端,明初称为“丰乐堡”,明末清初至今称为“牛站”。史料记载,这里有一个牛站大坡,是旧时通往青海的门户要塞。顾名思义,牛站坡者,应该是前行的牛群在此歇息后继续爬坡的地方。那牛,想必定是有着“高原之舟”之称的牦牛。在昔日古道上,成群结队驮着各类物资负重前行的牦牛队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牛站坡每年农历三月初七的庙会远近闻名,节日里的社火高跷和秦腔表演也很有特色。扎帐的村民们说,以前村子里没有保佑他们的神灵,他们从牛站菩萨处请了一批手红,带回了村子。
扎帐村没有多少特殊的民俗。在几千年的迁徙与交流中,他们一次次在彼此的适应中经历着嬗变的阵痛,实现着融合。今天,村子里最隆重的风俗就是农历三月初七的庙会。从这一习俗来看,这里确实和牛站有着割不断的聯系,与学者乔高才让记忆中三月初的仪式有着一定的脉络关联。
马兆瑞社长给我讲述了村里的庙和庙会的故事。多少年来,当地一直传承着“选苗官”的习俗。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也是土地爷出门上地的神日。这一日,村子里的青苗委员会会组织神圣的“选苗官”活动。青苗委员会的负责人,当地的村民称他们为“头人”。这样的称呼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土司或部落的影子。头人选派几位壮丁,抬着安放有九天圣母娘娘塑像的神轿,走出寺庙,在村子里寻找当年值日的“苗官”。他们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寻找,如果无意间轿子在哪个男性面前停了下来,或者冲了一下,那个男子就是当年值日的“苗官”。如果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会抬着轿子走进村落去串巷子,随意挨家挨户地走过。如果走到哪一家门口停了下来,说明当年的“苗官”就在这个人家。人们说,这不是轿夫的意思,这是冥冥之中神的旨意。这样“选苗官”,让人不禁想起藏传佛教中寻找转世灵童的仪式。也许,这是当地的一种民约,但其中不乏从宗教仪式中受到的启发或影响。endprint
有意思的是,被选中的“苗官”都是男性。选中了的“苗官”从二月初二这一天起,就要走进村庙里开始当年的值守,每天负责进香、焚裱、敲锣、祷告。遇到天旱,负责求雨;遇到涝灾,负责息神;遇到别人家里有个不吉祥、不太平的事儿,就去打卦攘解。从种青苗到收青苗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不得回家,不得吃荤,不做人事。青苗委员会给“苗官”600元的工资,另外提取香客在功德箱里捐献的香钱的20%作为补助。
对于这样的一种民俗,我甚为好奇。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我踏着泥泞的山间道路,伴着细如牛毛的密雨,走进村民们所说的寺庙。寺庙无名,门前有一株苍天青松,寺庙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原来寺庙前有两株青松,一株已遭雷击,村民们放倒了大树,供奉在庙门旁边。活着的这株青松苍翠挺拔,需要两三个成年人才能抱得拢。寺庙负责人说,这株松树有400多年的寿命了。这里还收藏有一块匾牌,是清朝光绪年间敬献的。在一间储物室,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乡亲们虔诚地揭去覆在上面的红色被面,让我们观看。匾牌上写“慈荫永覆”四个字,右侧写有“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姑洗谷旦立”,左侧写有“庆阳府儒学正堂信官杜钧薰沐敬书”。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姑洗月是阴历的三月。通过这处牌匾,我们知道,一位叫杜钧的庆阳府儒学正堂信官,相当于现在某中学校长这样的一位官员,在距今120多年前的阳春三月的美好日子里走进了寺庙,敬献上了敬请慈悲之心永远关爱荫及这方热土和生灵的祈祷之音。
扎帐村的寺庙没有辉煌的建筑,亦缺岁月的沧桑。这里供奉的神灵没有被凝固在屋内的上龛。他们的座骑是一顶顶小巧而灵动的轿子,前面有遮帘的名之为暗轿,没有遮帘的名之为明轿,暗轿在中,两顶明轿在侧。他们坐在轿子里敬受乡亲的朝拜和供奉。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又被乡亲们请上轿子抬到离村子再远一些的山顶上的一座庙里。这样的宗教仪式,又让人想起了游动着的游牧民族的特性。一顶帐篷就是一个家,在哪里扎帐,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而他们心中的神灵,也将随同他们一道走遍天涯。
在寺庙的门口,见到了寺庙管委会贴的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今年“庙官”的联系电话。在那张纸上,分明写着“庙官”二字,而非我所听到、理解到的“苗官”。这样的书写,难免令人多一份缺憾。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成了“苗官”,那将更加富有诗意。就像作家朋友曾经写过的“末代紧皮手”一样,那是来自对农耕文明、对山乡大地、对万物生灵的敬畏和热爱。而“庙官”的书写,却让清静之地多了一点现实和俗气。
四
人类的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永远不会安宁的运动史。如果说,人类的血液注定了流浪,那真正决定人们流浪的,其实是血液滋养着的向往和平与幸福的那颗驿动的心。
地处青藏、黄土两大高原结合地带的东坪乡,海拔2100~2450米。这里年均气温4℃,平均降水量只有350毫米,相对无霜期達到140天,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农牧区。这里山大沟深,干旱少雨,水源奇缺,虽然居于大通河畔,唯闻河水淙淙流,难见河水富桑梓。村民们只从一条自青海乐都马营乡流来的大淌子沟里汲水饮用,以旱灾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资源匮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这是一个边远而贫困的山乡。人们对于这个乡村的了解,缘于餐桌上离不开的农作物洋芋蛋。因为这里气候和土层的原因,种植洋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前些年,当地党委政府提出了打造“武威洋芋第一乡”的规划,下大力气在这里建设优质种薯和商品薯基地。人们对于这个乡村的知晓,还缘于《北京青年报》曾刊载的一条题为《卖血村见闻》的新闻。这里穷急了的村民们被迫走上了以卖血为生的路子,听来令人心酸不已。
岁月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贫穷的影子一直未曾离开过扎帐这样的小山村。80岁的党迎禧现在是扎帐村上的孤寡老人,老伴已经去世。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入赘青海乐都,当了倒插门女婿;小儿子30多岁,却出外失联已有两年多的光景。还有许多的村民30多岁却娶不上媳妇,有些人家通过各种方式娶回了媳妇,但媳妇生下孩子后就悄然消失了,家里只有爷孙相守。
一切的一切,缘于一个字:穷。
沿着盘山的路途行行走走,眼前出现数年来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守望和别离。也许,昨天的人们为了避免一场场战争,走进了大山,在这里落脚避难。也许,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好,丛林秀美,匆匆行走的部落一族或者游牧大通河畔的牧民一族相中了这块地方,在这里扎帐,却迟了起步的行程。也许,哪支王朝的军队经过疲惫的跋涉后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此屯兵守候……于是,这里有了人的繁衍生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扎帐不是舞台的中心,但却是梦一般温暖的港湾。吐谷浑、吐蕃、凉州六谷部的铁骑也许匆匆经过这里,强权的长鞭也许直指这里,但历史只在这里留下了行过的影子,它是过客般的际遇。
“在路上”永远是生存的天道法则。今天,扎帐的村民们将开始新一轮的起程。这里的扎帐,亦将成为历史的回忆。昔日松山古战场,今变移民新家园。在距离天祝县城30多公里的松山镇南阳片区移民点,当地党委政府实施着“下山入川”工程。几年时间里,扎帐村的许多村民相继来到了这里,过上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70岁的扎帐村老人杨得福含泪挥别故土,笑赴新家园,撰联“户纳绿水金凤池,门对青山龙虎地”,迎接在川区的第一个新春。马兆瑞告诉我,山区扎帐村的西头,原来有着茂密的原始丛林。因为贫穷,人们打柴为生,破坏了生态。这些年,村里的年青人觉得打柴不如打工,都相继走向外面的世界,这里的生态一年年好了起来,许多野生动物都相继出现,在这里安营扎帐。
越走越远的是道路,越来越近的是希望。
3岁的小亚楠出生在扎帐,而今天将落户扎根在新的家园。在她幼小的记忆里,也许没有太多关于大山的回忆。有的,只是爷爷用松树枝做的小风车。在人们的眼里,它很别扭,甚至有些悲情。奔跑在松山滩和煦的春风里,小亚楠拿着它尽情玩耍。她说,那是爷爷造下的“风车战神”。
离开属于扎帐村民的新移民点,想起远方的远方,还有一个将要只属于地名而必将远去的山区扎帐。我和小亚楠相约,春风再起,我拿漂亮的小风车去换她的“风车战神”!endprint
——以天祝藏族自治县扶贫实践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