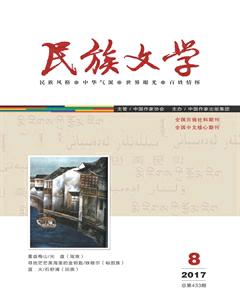寻找茫茫黑海里的金钥匙
在马马耶夫山冈那边……
“河谷里的笨蛋们,让我去马马耶夫山冈吧……”
不知是源自一个梦,还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或是一部二战电影中有人在这样喊。“马马耶夫”这个名字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当然那一年我去俄罗斯并不是因为马马耶夫这个名字才去的。
马马耶夫这个俄罗斯化的名字,其实来源于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拔都汗的后裔马麦汗。马麦是金帐汗国的贵族。从他的时代开始,金帐汗国日益式微。马马耶夫山冈在蒙古语中叫做“马麦汗·套勒海”,意为马麦汗的山冈。这个名字体现了不同族群的语词交汇融合。2011年秋,我们从莫斯科到了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格勒曾一度被叫做察里津和斯大林格勒。汽车驶出伏尔加格勒后,卡尔梅克蒙古学者热尼亚带我们到了伏尔加河畔的马马耶夫山冈。对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高山大河中成长的我来说,俄罗斯的马马耶夫山冈只是一个在东欧平原上常见的普普通通的低矮山冈,是我的族人叫做“皋圖勒”的那种地形。这个小山冈据说是古代蒙古-突厥人的坟墓形成,我觉得形成时间也许更早。就因为成吉思汗后裔马麦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山冈有了大名,使它象征着最坚强最勇敢的战斗。而对于内亚游牧族群的后裔如我辈的眼中,南俄罗斯草原、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山冈只是亚欧大草原的西端而已,是草原游牧人的旧地,是我们的祖辈自由自在放牧的家园。
平缓的马马耶夫山冈上85米高的“祖国母亲在呼唤”雕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非宗教或神话雕像。苍天在垂泪,母亲在挥剑呐喊。
热尼亚和我并肩走在山冈上,他指着母亲雕像对我说:“eikinotohktodana.”他用伏尔加河畔的蒙古语方言说的这句话,可以译为“祖国母亲在呼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生死攸关的惨烈战役的纪念。马马耶夫山冈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主战场,因为控制了这里就可以控制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运输线。1942年夏天到1943年冬天,在这里的一系列战役中双方死难估计约两百万人。我们在马马耶夫山冈下的红军纪念碑广场徘徊,在风中瞭望斯大林格勒市和伏尔加河。
“eikinotohktodana.”
在俄军中服过兵役,在欧洲和亚洲几个国度游历的卡尔梅克蒙古学者,见多识广老辣之极。听着卡尔梅克朋友们俄语和蒙古语的交谈声,我在想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悲剧可汗马麦,还是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地球上,另一个类型的战争自有了人类以后从来就没有停止,那就是——语词的战争。
我和ANUU站在石头上,把白色的哈达扔在水面上,献给了伏尔加河。我们乘坐的汽车一直向南奔驰在秋天的原野上,这里是伏尔加河以西,黑海以东,高加索以北的原野。进入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后,从车窗里看着卡尔梅克蒙古人的房子、畜圈、牛羊。平坦、辽阔一如蒙古高原。
在卡尔梅克人孟克和瓦丽亚夫妇家,在巴兹尔和维拉等朋友家中,除了奶茶和羊肉外,都是俄式西餐。伏特加、威士忌,还有各种红酒。在卡尔梅克的许多次宴会和交往中,亚欧大草原的话题,熟悉的语词和伏尔加河的风一起灌入耳膜,令人遐想。
伏尔加河口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列宁的祖母便是这里的卡尔梅克人。当年土尔扈特蒙古的和鄂尔勒克汗带骑兵围攻这个里海北岸的城市,围了几个月没有攻下来。因为当时城中的火器太猛烈。关于卡尔梅克蒙古人的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书籍不少,我没有必要在此赘言。
瞧,阿特拉斯罕古城中的公园里,表演俄罗斯古风的俄罗斯人围成一圈在唱歌。唱歌的姑娘们,鲜艳的服装,拉手风琴的男人,精致的马车。我还在阿斯特拉罕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一个木制的奶桶,这是塔塔尔或巴什基尔牧人的用具,这个奶桶和我母亲用过的打酥油的奶桶一模一样……
最让我们久久回味的是埃利斯塔市郊外的一个巨大的黑色雕塑,那是纪念卡尔梅克蒙古人流放西伯利亚的历史。黑色熔岩般的巨型雕塑,悲鸣的马、火车、森林、寒冷、饥饿和死难……多难而伟大的人民,这个“人民”已经不仅仅是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蒙古人,而是20世纪地球上所有苦难的人民。这个雕塑上刻着20世纪惨烈苦难的全部特征。伟大、阴郁、受难,为了在痛苦的大地上实现理想而受难……
卡尔梅克女学者达尔玛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多次去印度朝圣,聆听喇嘛的讲经。她给我们讲述了1943年12月的卡尔梅克,苏德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年轻人大多都在各个战场上的红军部队中战斗,他们的父母们却被定为“有罪的民族”“法西斯的走狗”,流放在西伯利亚。被流放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牛羊在哀叫/孤儿寡母和年迈的爷爷在哭泣/火车在伏尔加河边飞驰/人们被押送往西伯利亚……(斯·马祖尔克维奇《1943年12月28日》)
卡尔梅克人被押上列车后,他们的狗在后面追赶着列车,一直追着,直到累死在铁轨上。卡尔梅克老人、妇女和儿童们挤在寒冷肮脏的货运车厢里。每天,都有母亲们在已经死亡的婴儿旁边哭泣,到处是冻僵的尸体。他们成群地死于寒冷、饥饿或疾病。他们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最寒冷的地区整整十三年,他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尔泰边疆区,鄂木斯克,雅库特,萨哈林……没有食物,炊具和房屋,有的人被押着关进牲畜棚,他们用偷偷藏在身上的首饰等值钱的东西换点食物和炊具,但是仍然饿死冻死病死许多人。父母死了,姐妹兄弟死了,因冰冻的地面根本没有办法挖开,他们就把亲人的尸体匆匆埋进积雪里,春天雪化时尸体又露出在地面上,春汛泛滥时,河水把尸体又冲了上来,还有那些女孩的尸体,长长的头发还是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漆黑柔软。活着的人又牵着牲畜驮着那些尸体去埋进土里。那个泰加森林至今仍然叫“卡尔梅克森林”,因为有太多的卡尔梅克蒙古人死在这里。
1944年1月到2月,在前线和德国人浴血奋战的卡尔梅克红军战士和军官,纷纷被召回,被押送到了乌拉尔的建筑工地,当战士们得知自己的家属也被当作“法西斯的走狗”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时,绝望和悲伤使“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也垂下了头”。有些战士从建筑工地幸运地逃脱后又返回了正在激战的前线,去战斗去牺牲,好一个草原民族的血性。更多的红军战士在各地的建筑工地或古拉格被折磨死去,在科雷马,在西伯利亚,在北冰洋沿岸无数的古拉格集中营像牲畜一样死去。卡尔梅克诗人卡良桑吉就曾在科雷马集中营服刑,也就是著名的集中营作家瓦尔兰·沙拉莫夫服刑的地方。
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被流放的卡尔梅克等族群被平反,幸存的人们陆续返回了支离破碎的家园。自治共和国也陆续恢复。但那些被折磨死去的人们呢?那一个个被摧残被蹂躏的灵魂呢?那一个个被丢弃在无名荒原上的骸骨呢?
就是从那个时代起,卡尔梅克蒙古人开始大规模使用俄语名字和俄文。达尔玛说,如果说卡尔梅克蒙古文化是珍宝的话,那么西部蒙古地区通用的托忒蒙古文就是金钥匙,而如今这把金钥匙被扔进了茫茫的黑海里,因为周围多是使用俄语的人,卡尔梅克蒙古语词汇渐渐显得贫乏。她说现在急需编纂一部高水平《卡尔梅克蒙古-喀尔喀蒙古-俄罗斯语大词典》,他们正在编纂卡尔梅克文献的辞典,就是要让民众去用文献中那些丰富的语词。人类有多少文明就这样失落了,像那个被扔进黑海里的金钥匙。
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大多数学者用俄语发言,其次是英语,用卡尔梅克蒙古语发言的很少,卡尔梅克蒙古语只限于会议祝辞等仪式。在卡尔梅克小学里,年迈的卡尔梅克老奶奶在认真教孩子们本族语言和习俗,举止大方气度非凡的孩子们在学习和表演中,也是极为投入而认真的。在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专家的后裔家中,穿着蓝色卡尔梅克蒙古袍的老奶奶用温厚的手拉我过去看她的舅舅奥其尔先生——已故的史诗《江格尔》专家,他曾在斯大林时期多次被捕入狱,最后是在她和她妈妈的照顾下去世。在她家佛龛前,她拿出珍藏的旗帜苏鲁锭放在我们几个人的头顶上举行了仪式,并念诵着卡尔梅克蒙古语的祈祷语词祝福了我们。
伏尔加河畔使用蒙古语的族群——卡尔梅克蒙古人对自己语言文化怀有深沉的感情,他们在欧洲强大族群中顽强挣扎。他们在1943年的大规模流放和逮捕中,在东欧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在创造奇迹,这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语词的战争和语词的融合。语词间的战争和融合往往是不同的文明或冲突或融合的最主要部分。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工作和学习的卡尔梅克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喀尔喀蒙古人,还是在那里的哈萨克人、塔塔尔人、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还有高加索诸族以及其他许多的族群,我能感觉到他们都有自己强大的灵魂和坚强的自信。
在俄语的海洋中。几十万人使用的卡尔梅克蒙古语在战斗在融合在高歌在欢笑,卡尔梅克人珍视自己的古代的风物。
呵!久违了的关键词
在埃利斯塔市,ANUU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从中国新疆迁居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蒙古人,乌兰巴雅尔和乌图娜生夫妇,那木吉勒和孟根夫妇等人。我们去埃利斯塔郊外的原野上,到英年早逝的新疆伊犁籍蒙古学者绰罗斯·额尔敦巴雅尔的坟墓拜访。木制的墓碑已经被南俄罗斯草原夏天的烈日晒成了咖啡色,我们在他的墓碑上拴了一条蓝色的哈达,祭洒了伏特加,愿他的灵魂在这长满羽毛草的广阔原野上安息。
在宴席上,卡尔梅克人长长的颂词开始了,接着开始喝伏特加和各种红酒果酒。卡尔梅克人比我们尧熬尔人更多地记住了自己的诗歌。在卡尔梅克共和国国立大学,ANUU用蒙古语介绍了尧熬尔,西喇尧熬尔,远在青藏高原边缘的祁连山等。对许多卡尔梅克人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游牧的尧熬尔人。
“这位是尧熬尔……”
接着是惊讶、善意和好奇的目光,好像是似曾相识在千年以前。古代的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神圣的鄂尔浑河于都斤山……
还是不必追溯太远。就是自匈奴时代,自从冒顿单于的五色骑兵集团军以后,自铁猴年(840)的大雪后,我们曾轮回了多少次。我们积淀了多少歌哭,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多少次死里逃生……
我们的那些基于血液的浪漫华丽的语言,那些驾驭着人们全部心灵和感情的语词,这一切不仅变成了俚俗方言,而且语词渐渐贫瘠和浅薄。
有谁还记得那些关键词呢?如“尧熬尔”,如“博格达汗”“金格斯汗”如“兀鲁斯”“汗腾格里”“于都斤额客”“额客瑙套格”……
对于这些我在祁连山下的原野上,在那座烟熏雨淋的黑帐篷里喊哑了嗓子的关键词,远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人是熟悉的,中亚细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熟悉的。祖辈留给我们的语词,告诉了我生活在亚欧大草原上的人们内在联系的奥秘。
另一部分语词却在膨胀和扩展,成千上万种语词被吞噬。
在卡尔梅克,以各个部落固有名称自称的四卫拉特蒙古人在三百年前迁居伏尔加河时并不自称“卡尔梅克”,就像半个世纪前尧熬尔人并不自称裕固。
无论是小小的游牧族群尧熬尔人还是卡尔梅克蒙古人,他们都是在内亚草原游牧的阿尔泰语系的族群,他们都生活在欧亚大草原的最前沿,一个在东欧伏尔加河畔草原上,一个在亚洲中部的青藏高原边缘山中。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生存环境是天地之別,历史经历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语词的战争中有一点是相似的。
语词的战争和融合在人类有了灵魂、舌头和耳朵后就开始了。我从生下来就置身在语词的战争中。
在马马耶夫山冈那边,在多瑙河,从飞着白色海鸥的伏尔加河到秃鹫展翅的祁连山,在西伯利亚,在各个大洋大洲……语词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
如今的卡尔梅克草原就是公元前的萨尔马提草原,是匈奴王阿提拉的战场,是术赤的后裔金帐汗国马麦汗的战场,是十六世纪卫拉特蒙古人的草原,是二十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历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卡尔梅克的夜深沉无比,我在梦中呼喊着天上的星星,我的梦呓略加删节和修饰就像一首摇滚歌谣:
玛勒奇奥登——牧人之星。/道伦布尔汗——七神。/阿勒腾嘎达斯——金钉。/浩日软玛日勒——三只母鹿。/星星上有乌托邦吗?/星星能为地球上的众生伸张正义吗?/星星能救人类吗?/星星就是仁爱和平吗?…………
人的语词神的语词魔鬼的语词都在我的头顶呼啸,不停地穿越这个世界。语词从嘶哑哽咽的喉咙发出,从地球的五脏六腑发出,深入人的内心深处,直达死亡。
呵!语词
夏日塔拉的深秋,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逃亡者手记》已经杀青,在写名称索引拉丁字母转写时,我找到语言专家巴图格日乐和精通尧熬尔语的卓玛核对。
如今把这些语词,这些寓意已经弱化了的神圣的语词找回来,放在从前的语境里,凸显出了特殊的意义。那些和远古的祖先精神上的关联,还有他们的记忆都随之复活了。
仍然需要一个人面对这语词的战争和风暴。我在自己的书稿中呼喊:那个古老的族群之箍和生命符号〓〓。我在梦中常常用自己的母语喃喃低语……
每当这个符号在人们耳旁响起时,人们面前轰然打开的是那个遥远的英雄时代的精神结构和思想。有多少意义是在对这个符号的回忆中创造的呢?不管怎样,都要从人性的基本态度出发去了解。这一个词的运用,意味着重新继承了这一个古老族群和他们的历史姓氏。意味这个族群有人在努力靠近自己的本质或内核。喇嘛们常说:“语词就是神,写错或亵渎一个神圣的语词是要受到惩罚或报应的。”
语词的英雄时代在向我召唤。
然而,有多少感情和语词也一同变成了化石。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早已南辕北辙的东西,这一切不会与先辈们发生任何联系,古代完美的精神和灵魂教养早已是明日黄花。我的眼前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因长期缺少盐而病入膏肓的虚弱肌体,一个个心灵受到重创的人们。边缘小族群就是一个个大时代的化石。
新时代以一个个语词,一句句的话语,铺天盖地的常用语,无孔不入的句型代替了那些原有的语词而潜入人们的肉体和血液。语词比子弹更具杀伤力。语词也有獠牙、尖利的爪子和血盆大口。“语词就是微小剂量的砷……”这是德国的犹太语专家维克多·克莱普勒的话。“语词就是微小剂量的砷,你吞食了它后,过一段时间才会显露出它的毒性。”语词带着或是善良或是凶恶的种种感情。
有些语词被丢弃了,有些语词被膨胀了,有些词在被滥用。语词的风暴将我们覆没,席卷一切。
久久的沉寂后,从高山大河、原始森林、冻土带、沙漠戈壁和大海上又冒出无数美的语词,像子弹一样穿越时空,像晚霞像彩虹像群星……
无论是我使用汉字写作还是用尧熬尔语或蒙古语说话时,我一直想在语词和文字中都保持中性,不带任何色彩。我一直努力想拥有一个冷静如外星人般的眼光。但仍然被环境的大海染上色彩,而且总是被大山遮住我的眼光。
被雷电击死的牦牛
一个星期后,勤奋的卡尔梅克语言学者萨沙和他儿子腾吉斯走了。我和ANUU,还有欧琴三个人去冬窝子拾蘑菇,巴图恰安看守小屋。春季虽然有好几次暴风雪,但立夏后一连许多天没有下雨,所以草地上没有蘑菇。三个人一无所获地返回小镇。
立秋后,雨水又多起来了。山上的蘑菇在疯长,邻近的农业地区和城镇的人聚集在草原上拾蘑菇,很多铁丝围栏被踩得歪歪斜斜,草丛中随处可见他们扔下的饮料瓶和小吃的包装盒,以及啤酒瓶和其他垃圾。
夜里下起了大雨,雷鸣不已。秋雨声宛若钢琴、冬不拉和马头琴声,我时睡时醒。早茶后,我和ANUU在院子里散步,看看扎在院子里的黑帐篷和蒙古包,回想宛若昨日的牧人生涯。每当在这样的时候,往日的岁月和消失语词就会接踵而至,令我应接不暇。
8月28日晚又是暴风雨,电闪雷鸣,我和ANUU关了院门。一夜听着刷刷的雨声和雷电的轰鸣入睡。今晨接到在夏营地放牧的大姐才岑卓玛电话,她说昨晚雷电击死了三头牦牛,有两头是牛群中最大的种公牛,还有一头是乳牛。大姐让我找个车去夏营地把死了的牦牛肉拉到小镇卖了。我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找车,然后又给杜曼氏族的书记和安江氏族的村长汇报了雷电击死牦牛的事。大姐又来电话说连续几天的雨,西嶂的夏营地泥泞不堪,汽车上不去。大姐找到在夏营地的邻居马龙,马龙是我舅爷的儿子,让他帮忙又找了几个邻居剥了牛皮,把牛抬上马龙那辆四驱越野汽车,然后由马龙帮忙送下来。
午后,马龙开着车到了,还有他的小儿子昂丹和我们的牛倌小董。三头牦牛放在车箱里。一头大角黑色种公牛,卷曲的毛发,黑色的大角优雅明亮而又充满了力量,这是一头威风凛凛的牦牛,可惜死了。另一头是棕色种公牛,是我们家标志性的棕色牛。另一头是银灰色的乳牛。
大姐在电话里说,昨晚的暴雨非常猛,电闪雷鸣时,她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空落下,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声音。我觉得那是暴风雨中的球状闪电。大姐说她当时有点害怕,就蒙着头睡下了。早晨天亮后她去查看牛群,四周仍然是浓雾茫茫,她在沼泽地和高山柳林边看见倒着三头牦牛,知道是被雷电击死了。走近细看,地上还有几道像是刀痕般的痕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她看见整个牦牛群在沼泽地浓雾中奔跑着,惊恐万状。牛群可能被昨晚的雷电和暴风雨吓坏了。直到下午,大姐收拢牛群时,受到惊吓的牛群还是很难收拢。大姐说,早在几天前,就在雷电击死牦牛的地方,常出来几只惨白色的旱獭,自从雷電击死那几头牦牛后,那几只旱獭也不见了。大姐还说,天晴后,她看见我们家那匹黑褐色马走到牦牛被雷电击死的地方,久久地低着头看着,状若沉思。
这次被雷电击死了三头牦牛后,母亲说可能是我们夏营地的山神生气了。几年前镇上领导和九条岭煤炭经销公司的人,带南方老板来我们的夏营地开矿,挖掘长着高山柳的山崖,挖出不少深洞。从那一年后,夏营地的沼泽地出现了塌陷的坑和深深的洞,突发的山洪把矿区的泥沙冲下来,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铁丝围栏或被淹没或被冲掉,洪水冲过的小河谷里出现了断崖和坑。从那几年后,牦牛也不断死于意外事故。这说明山神不高兴了,不高兴人类那么放肆随便地挖山,弄脏那里的雪水河、沼泽地、高山柳和哈日嘎纳灌木。那个地方数千万年里从来没有人搞脏过。可是自从开矿后,工人们把简易厕所建在雪水河旁边的沼泽地上,就在神圣的雪水河旁边的山坡上。
那些长着柏树的山崖塌陷了下去,那些柏树大多都死了。挖矿山的人走了有三年了吧,但那里的柏树再也没有活过来,裸露的断崖没有长出草或灌木来,一下雨那里的泥土总是被冲下来。还有很多垃圾,空心砖、水泥块、旧衣服、塑料制品……大姐她们花了几天时间集中烧毁了一部分,但是还有许多。被雪水河冲下去的垃圾也是捡不完的。
那几个煤矿虽然不是我们挖的,但当时也是我父亲同意后他们挖的,后来虽然我们拒绝了他们继续挖煤的要求,但他们还是偷着勘察过那个山,因为那里新堆着许多圆形石头,还有一些深洞。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夏营地给山神煨桑。一如既往,煨桑就是对苍天大地对世间万物表示感恩、敬畏、忏悔和歉意。
翌日上午背了一点昨天被雷电击死的牛肉去楼上,给父亲和母亲煮了牛肉。母亲说雷电击死的牛留在山上,让秃鹫吃了也挺好,秃鹫会高兴的。
一个凌晨,我和ANUU,还有欧琴和巴图恰安出发。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巴彦哈喇山巅的鄂博旁边。从高高的巴彦哈喇嘛山巅可以远眺我们夏营地的三座青山。从这个山巅可以俯视夏日塔拉群山草原的整个东半部地区。
我们准备了干枯的柏树叶、蒲公英、紫莞、马先蒿等,还有煨桑的布袋子里早已准备好的炒面,以及糖果和牛奶等食物,另备一瓶酒。先点燃了枯柏叶和花草,因为立秋后雨水多,枯柏叶和花草都有点潮,好不容易才点燃,烧起的火燃着了干牛粪和柴,在火上放了煨桑的食物,围着桑台顺时针方向转了三圈祭洒了酒,念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嗡啊哞……”磕头,呼叫着我们的祖辈自鄂尔浑河畔时就呼喊的“呼雷……呼雷……”遥望祁连山的神峰阿米岗克尔,心里想那三千大千世界感恩苍天大地宇宙……
几年前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在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埃利斯塔近郊,来自美国的迪瓦活佛在卡尔梅克的布尔汗巴格西阿勒坦寺院(释迦牟尼金顶寺)用英语讲解佛经,有俄语翻译。我和ANUU给他献了蓝色哈达,迪瓦活佛和蔼而威严。他强调人们不要总是想着自己,不要总是“我我我”……
火红的太阳在卡尔梅克的原野上渐渐西沉,成群的乌鸦从黄昏的原野上飞过。晚饭在毡房内举行,卡尔梅克的毡房多是从蒙古国或中国新疆的伊犁草原带去的。卡尔梅克蒙古人的毡房大多在强制执行集体农庄式的劳动和定居放牧时,渐渐消失。宴席上,年轻的蒙古国僧人学者亚丹加布唱了民歌。還有一次在郊外草原上的几座毡房前,卡尔梅克蒙古人表演了唱歌,除了卡尔梅克歌谣外还有蒙古国和中国蒙古的歌谣。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在表演歌舞时,骑在黑枣骝马上的卡尔梅克男子亲切地和我问候。
阳光明媚的大地上歌声在不断地回荡。
夏日塔拉,9月1日。大姐电话中说,一只丢失了四五天的小牛犊找到了,但是它已经死了。大姐在灌木丛里、小河谷里和高山柳丛中找了几天,终于看到这只小牛犊的尸体,这只小牛犊是在一个塌陷的沼泽地深洞里,深深陷在泥泞中,只看见尾巴,根本取不出来。大姐说,这只小牛犊不是自己跳进去的就是被其他大牛撞下去的。前几年,煤矿老板们在夏营地挖煤,现在虽然不挖了,但是夏营地上不断出现了塌陷的坑或洞,有的深有的浅,还有的地方出现了滑坡的迹象。有些地方被雷雨过后的山洪裹挟的泥土淹没了。
都市的夜里,听着不远处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听着秋雨打在窗外那两棵梧桐树上的声音,总是想起故乡的一幕幕。牲畜跌价,房子涨价,人们在忙碌中在挣钱的路上死去,来不及去看病,来不及抬头看看星星,来不及凝望月下的阿米冈克尔神山。在繁忙嘈杂的土地上,我们忘记了那些事关我们灵魂的关键词。
“尧熬尔是谁?……”
几千年来,我们在语词的风暴中逃亡……
每日每夜,无论是暴风雪还是蓝天丽日,无论是在大陆另一头的一座城市还是在我那座用牦牛毛织的黑帐篷里,我都和纷纭而来的语词短兵相接,我想喊出自己的语词,那是和平仁爱的语词,我将随着这些语词和众生一起重新诞生。
责编手记:
自由与真实是铁穆尔钟情于散文的重要理由。相较于一些精致优雅的美文,铁穆尔的散文粗粝沉重,比之精巧的构思与编排,作者更注重笔下的精神承担,文章如奔涌的江河,裹挟着人生的复杂况味呼啸而来。散文模糊的边界、开放的形式、对真实性的遵循为作者澎湃的激情、执着的坚守提供了倾泻的出口。
《寻找茫茫黑海里的金钥匙》是一篇具有浓郁作者个人风格的散文作品,行文自由不羁,情感灼热深邃,延续了铁穆尔长久以来对人类精神苦难史的关注,对人性尊严的召唤,对自由精神的捍卫。文章从词语的此消彼长写起,探讨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通过对俄罗斯卡尔梅克人遭遇的探讨,思索大时代小族群的命运。对时代苦难的敏锐感受,对精神救赎的艰苦跋涉,使铁穆尔的文章冲荡苍茫,这独属于作者的精神气脉将文章的思想碎片连缀起来,抵达更辽阔的远方。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