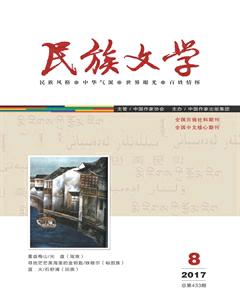母语与汉语
阿来
在我自己的文学经验中,我觉得翻译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翻译才可能使得不同语言中的不同经验、不同感受产生交流。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每一种经验和表达不可能都靠一种语言来创造。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别的语言当中借用一些东西,或者从别的语言中获得表达和命名事物的启发,使自己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同时,我们也通过翻译将自己语言当中特别好的修辞和经验传递到别的语言当中。
语言的交流对所有的语言对所有人都是不断成长不断丰富的过程。汉语诗歌当中就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比如元代诗人萨都剌,他是少数族裔,不是汉族,他的诗歌《上京即事》中有四句诗:“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过去写西域写草原大漠的边塞诗,大都是内地诗人写的,多是思乡悲苦的主题,并不是真正的欣赏。而萨都剌这里的马酒祭天,从沙漠上吹来的风都送来了远处的草香,是游牧民族才有的感觉。这首诗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当地游牧民族的生活,和边塞诗大体一致,但是里面所包含的客人与主人的经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每一种语言当中都包含着自己獨特的经验,甚至是独特的价值观。这种经验和价值观,即便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也不会丢失。有人说只要用汉语写作,就是对汉语的简单的归化。我不这样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参与汉语书写,既扩张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又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新的感受。这种感受,这种异质的审美,改造和丰富了汉语的面貌。
我个人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实现的。翻译有两种层面,一种是从一个文本翻译到另外一个文本;另外一种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生的。比如我写作时使用汉语,但是只是借用汉语来表达,可是用它来表达藏区的藏族人特殊的感受、特殊的价值观、特殊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够用的。当出现用汉语表达特别不通特别不够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想一想,用我自己的语言来想一想,当出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说法有时可能比汉语当中的说法要好。比如说“爱情”,汉语当中有很多表达,被反复使用已经没有了新意,我想到了我们民族中有种表达“骨头变轻了”,就有异质色彩。
有人跟我说,你的语言很好,可是和孙犁的语言之好又有不一样的东西。这不一样的东西从哪里来?从母语来。母语中包含独特的经验、看法和历程。有时我们把两种语言的区分有些绝对化,其实它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一种互相沟通、互相丰富、互相补充的关系,最后的结果是两种语言都会成长。不管是从事翻译工作,还是用汉语写作或是用母语写作,都是对民族文学经验世界的建构过程。
我自己早年从事文学创造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是语言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是要有故事,要有思想,但是文学最基础的是从语言开始,从修辞开始。
(根据作者在2017《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的讲座整理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