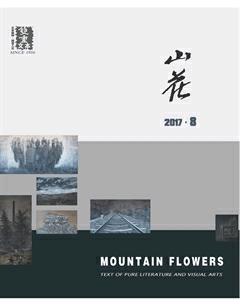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民族性和语言问题
柏桦
实际上很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汉诗的过程中都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西方近百年的整个文学或者诗歌在我们这里仅用了极短的时间很快地学习了一遍。我们几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流派学了过来,以期迅猛地跟上世界的步伐。不仅是中国文学,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按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就是“以极端短暂凝缩的形式”把西方百年来的诗艺用短暂的十年或者二十几年的时间集中重新学习了一遍。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共同看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说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十年一变。他说中西文化一旦接触起来,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在这之前我们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自以为具有绝对霸主的地位。结果“1842年以后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不断的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他说有许多现代史家为了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就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这牵涉到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即我们是被迫卷入到现代性的潮流之中去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晚清以来的历次惨败从此开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从1894到1895的甲午之战,这是很多历史学家注意到的一个历史关节点,这一战太重要了,因为好像以前觉得输给西洋人还说得过去,但无论如何不能输给日本,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彻底输了。甲午之战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包括文学史。因为在那个时候,即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彻底地被迫卷入了现代性的潮流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被卷进去,我们还自以为是天下的中心,那我们今天可能仍是用古文在书写。现在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孙中山当年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儿所谈的世界潮流,其实就是现代性这个潮流。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了西方化。所以说唐德刚认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这个西化为许多学者不满,认为失了面子,这样我们的主体性就丧失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一种本位主义,或保持主体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讨论不休的问题。在此,暂不作深究。
现代性在中国发生之后,它的路线图大概一般学者公认为经历了三次标志性的转变。第一阶段从晚清以来到五四时期,在那个时间段里,我们对西方的心态比较复杂。既羡慕西方,又狂热地恨自己;既想融入,又要追赶。一时间有很多争论,到底是西学为体还是中学为体等等。当时大致出现了两派,有很极端的,也有保守的,譬如学衡、甲寅和新文学之争。新文学那边的傅斯年也好,胡适之也好,还有鲁迅也好,都说过很多极端的话。鲁迅甚至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当时新文学诸家几乎众口一辞:唯有灭掉汉字中国才可以兴盛,包括汉字拉丁化,包括后来的大众文学运动,包括中国的文字是最野蛮文字等等。不过那时的焦灼激愤之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要赶上所谓的世界潮流,反映在中西文化上,一部分人就必然要救亡要启蒙要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这些都是从日本输入进来的概念。另外一部分人讲求改良,保持中国本位,出现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晚清另外一派的文学,这一派是被压抑下去了,后来有人(王德威)说这是被压抑下去的现代性。还有人认为从鸳鸯蝴蝶派到张爱玲是另一条现代性线索。这个线索被后来的左翼文学压下去了。这一切后来又发生了逆转,毛泽东文体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后面还将论及),国外汉学非常重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公认他开辟了或者说创造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叙述方式,是对现代性有所贡献的一个人。在他的文体引导下出现了新的文学风貌,包括诗歌风貌都有所改变。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中国现代性的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又和前面两个阶段不一样了。这时我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变,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论述下,对西方开始了全面开放,这一次我们是彻底地认输了,即除了羡慕之外我们也心悦诚服地认为应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推进我们的整个现代化进程。
前面讲了现代性在中国发生的这么一个大致情况。但有些人却非常霸道,比如杰姆逊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就是欧美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没有什么印度现代性或日本现代性,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越南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现代性都必须在欧美这种模型来执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或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研究中国的方法)模式下,中国便只能是在西方的现代性猛攻中回应西方的挑战。这种说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比如王岳川,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必须具有自身的文化指纹和身份,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身份,这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仅仅是后殖民的进程而已。王岳川就曾对杰姆逊这一说法作过如下义正严辞的表态:“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王岳川这话说得不错,但是在面对西方文化强攻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现代性的三个进程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这一段是俯首称臣的,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规划来实践我们的现代化的。所以出现了曹顺庆先生讲的“失语”,所谓失语也就是不会说话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西方文论来指导我们,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写文章了。说到这一点,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北师大教授郑敏年轻的时候非常西化,她在西南联大学习西方哲学,到美国后也学的西方哲学,写诗必师法西方,她自己也承认她年轻时是完全西方化的。到了晚年,她突然对此(对她年轻时的写作)持否定态度,完全否定。1993年3月,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此文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她写那篇文章不仅是反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诗,更涵括了现代汉语”(奚密),其目的是完全否定新文学,否定新诗,认为现代汉诗是彻底失败的。当然也有人批驳她的观点,美国汉学家奚密就看出她的论述方式和观点是西方汉学家所习见的,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种说法在西方汉学界长期存在,从第一批治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如捷克的普实克到后来的兼乐(William Jenner),到最近的宇文所安,观点完全相同。我认识的汉学家都是这样,他们只崇拜和推崇中国古典文学,认为是瑰宝,是可以和西方文学并驾齐驱的伟大文学,他们说了很多赞美的话(甚至包括庞德,雷克思罗斯等),而且发自内心非常推崇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包括现代诗歌在内,他们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普实克最早就说过,中国乃至日本及整个东亚的现代文学根本就不是这些民族的文学,完全是西方文学的翻版。这样的话非常多,就不一一提及了。现在回到郑敏,像郑敏这样的人,她在晚年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段话非常令人震撼:“今天,经过了八十多年的检验之后,历史已经开始在惩罚我们了,我们一代一代的工作都放在毁灭自己的传统上,到今天,可以说,这种毁灭已经几乎完成了……今天我们已经切断了去继承遗产这条线,我们没有了后备。我们每天都在等待西方提供给我们明天的去向,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几乎自觉地沦为文化殖民地。”(郑敏:《遮蔽与差异》)我刚才说过,早年的郑敏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后来却完全变了。这也有点像王岳川,他早年也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后来也变成一个很保守很传统很“士”的一个人。这个题目也算一个研究课题,这种转变很有意思,包括刘小枫等许多人早年都很西化,后来全部都回来读中国经典。老年的郑敏在《新诗评论》的访谈中有一节,说当年她自己看到朦胧诗很亲切,一点都不隔,很像四十年代袁可嘉,穆旦,以及她自己当时写的诗。其实和传统的断裂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就完成了,传统是在他们手上结束的,在《九叶集》中结束的。她自己就承认当时他们是非常西化的,完全没有中国传统。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提醒我们注意那个时间点),中国现代汉诗就停止了向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停止了这个冲动,再也不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了。
中国现代汉诗从胡适之开始,胡适写尝试集的时候,他也有很大的焦虑。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概我们这一辈子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纯粹国语文学的人;新文学的创造者,应该出在我们儿女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国语(白话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的缺点了。”(引自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4页)。由于“我们这一辈”写的不是纯粹的白话文或白话新诗,这个所谓的“缺点”,成为胡适的一个焦虑。胡适之也好,刘半农也好,他们这一代人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然后去西方留学,他们本身是中西合璧的。但是从胡适之这段话感觉得到他想把中国古典的这一面完全切割掉不要,而要纯白话的文与诗。他的这个焦虑其实是杞人忧天,没有必要。他写的白话诗到了闻一多等新月派那里就出现了一次纠偏,新月诗人开始走中西合璧的路了,并不是扬西方而压中国。闻一多的名言是希望中国的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到了卞之琳就明确提倡化欧化古,化欧化古到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但胡适也很复杂,他一方面提倡纯白话诗,一方面又提倡整理国故,国学在胡适的提倡下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问(有关论述,可参见我另文《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现在我回到现代汉诗这个问题上来,在我的好几次访谈中,我说过这样的话:“现代汉诗应从文言文、白话文(包括日常口语)、翻译文体(包括外来词汇)这三方面获取不同的营养资源。文言文经典,白话文,翻译文体,三者不可或缺,这三种东西要揉为一种。”既然现代性已经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回到古典了,我们也不可能用古文来书写了,我们只能用白话文来书写。这一点没有办法,当年的很多实验有些被压抑下去了,有些被开发出来了。被压抑下去的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而成为我们传统的是1949年之后的东西,毛泽东思想也好,毛泽东文体也好,或者新华社文体也好,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形成了一种并非永恒的传统。改革开放,西方文艺的涌入是伴随着翻译文体的进入,这些实际上都成为我们临时的可启动的写作资源,这种资源也不可能完全放弃。我们说的白话文,除白话书面语外,还牵涉到日常口语,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日常口语是写作中最有生机活力的部分,但在中国诗歌写作当中,又是最困难的,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呢,我们的文字不是西方文字,西方文字跟着声音在走,话同音;我们是跟着文字走,书同文。现在有人提倡口语诗,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语诗,好的口语诗应该是方言诗。这一点,以前的学者诗人做过努力,包括新月派。新月派诗人是非常资产阶级化的,非常布尔乔亚的,都是留洋的,都是教授,他们写过很多口语诗,方言诗。
如果口语诗不是方言写成的,我认为是伪口语诗。打个比喻,每个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会发出默默的声音,他用什么话在说,是用四川话在说吗?闽南话在说吗?还是广东话在说?还是吴语(苏州话)在说?这一点对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普通话说“谁”,即“哪一个”,广东话却说“宾果”。一个人写诗也好写小说也好,如果你叙述一个人物描写一个人物,你不是跟着声音在走,你就不敢写“宾果”,你一定会不自觉地把它翻译成普通话,那么实际上你笔下的人物就丧失了一种在场的感觉,一种可触摸的在场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说得严重一点,你作为写作的主体也已经丧失了,因为当你将你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时候你就隔了一层。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我写东西,塑造一个人物,我写完以后,有些地方我感觉很精彩,但有些地方我马上感觉不统一,和人物形象完全不吻合,后来我发现了原因,原来是有些地方我会不自禁地冒出四川话,这反而是对的,但许多地方又是普通话,这样一来语感就完全乱了,所写人物也不是那个人物了。还有些时候,新华字典里没有这个四川话发音的字,我不敢用,怎么办,实际上,我马上很快在内心里把他翻译成为普通话,翻译成普通话之后一下就别扭了,感觉这个人物就不对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口语诗我不是不提倡,我十分提倡,可是实际上口语诗是最困难的,名堂也是很多的,非常困难。真正要写口语,我个人认为首先得用方言来写。满足口语诗的第一条件是方言,没有方言何来口语,而颠覆大一统的普通话写作更何从说起。我现在看到的所有学术文章没有谈这个问题。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完全可以按照我的思路写一篇学术文章。我不反对白话文写作,白话文写作中有白话书面语,就是普通话,以新华字典上的字为主。那么,纯粹的口语,方言写作则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为方言立法,各方言区编出自己的字典。
很多人研究新诗,却忽略了新月派的诗人居然作过这种方言诗(即口语诗)实验,我吃了一惊(颜同林博士作过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比如在徐志摩诗歌中,他就曾大量运用过他的家乡话(海宁硖石方言)来写作。他的这类诗大致可以看懂,比如说在这首《一条金色的光痕》中开篇写道:“得罪那,问声点看”“得罪那”还听得懂,“问声点看”,就勉强知道是问一问的意思。再说一个叫蹇先艾的贵州诗人,他用贵州遵义方言写诗,贵州遵义方言其实就是四川话。这些人都是当年真正的大学者,却用了很多纯正的方言来写作,实验出了一批可观的口语诗,再比如说蹇先艾的诗歌《回去》,“哥哥:走,收拾铺盖赶紧回去”这是第一行,“乱糟糟的年生做人太难”,“年生”四川人才懂,上海人也好,广东人也好,看不懂的,什么是“年生”?他们不知道。第三句“想计设方跑起来搞些啥子”我就有过这种情况,当我写“搞些啥子”时,我就会自动地翻译成“搞些什么”。所以说这个里面的问题(指方言转换成普通话的问题)很大。接下来一句:“哥哥,你麻利点”,“麻利点”这个人家也不懂得,包括后面的“这一扒拉整得来多惨道”“这一扒拉”必然使其它方言区的人困惑,“男人们精打光的呲牙瓣齿”。这个在理解上还好点。还有《飞毛腿》,闻一多用北京土话写的。从以上总总,可见当时高雅的新月诗人们的确不简单,各自用方言做过很多实验。如今我仅发现一个北京大学的博士(现已留校),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胡续东,四川人,他写了很多四川方言诗,写得非常棒,极有意思。而现在很多诗人根本不敢用方言写诗,头上总潜在地悬着一把“普通话”的剑,虽然他们口头上反普通話写作,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的普通话写作,因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普通话写作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语境中,(他们)认为普通话写作是正宗……至于它好在哪里,有没有弊病,则很少深加思索”(颜同林),他们其实内心怀有一种方言的自卑情结,而绝非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一切伟大的诗歌与文学都是方言所写。
另外,文言文作为一种资源,把它放弃是非常可惜的。清一色的白话我们会觉得太贫乏太顺溜了。文言中有一些遒劲紧凑以及硬语盘空的感觉,这在白话文中不是特别明显的。而翻译体就没有办法了。翻译体是一个大工程,它不是晚清才开始进入的,从佛教征服我们时就开始了。中国文字经历过两次大的震荡,第一次是佛教,佛教进来,我们翻译佛教经典引进了很多词汇,而这些词汇后来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如“刹那”,“宇宙”等都是来源于佛教,不一一例举了。会有专门的学者来做这个事,当作大工程来做,当作学术专著来做。到了晚清和“五四”以来也发生了很多改变。“五四”时候对传统的舍弃首先意味着对文言的舍弃,认为文言是死文字,这个文字已经死去了,要灭掉汉字等等等等。从新月派开始到卞之琳到张爱玲到胡兰成,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也不存在胡适当年的焦虑,他们统统都把这一切化解了。对文言文也好,对翻译体也好,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刚才讲过,灭掉文言就是灭掉一个可贵的资源。它的灵活多变的词语组合和可观的词汇量以及硬语盘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尤其是词汇量,白话文的词汇量本来就少,因此必向文言中求得。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向文言的学习都不成功?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艾略特曾说过,传统根本就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继承的。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让人百读不厌,至今仍属于源头性的文章。他认为传统是一定要通过很辛苦的劳动才可以得到的。传统一直很难被打开,它偶尔被打开了,但这几个孤单的人被另一种大叙事压抑下去了,没有形成一个就近的传统来引领我们。比如这个传统,曾向孤单的卞之琳敞开过,向张爱玲敞开过,向胡兰成敞开过,包括向丰之恺敞开过,等等。当然还有些人,可惜这些人没有成为我们文学的主流。当然后面也有些人在做这个工作,但都是孤单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翻译体,因为翻译体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講到佛教征服时期所带来的震荡,那么五四前后或晚清末年却是第二次震荡,这次震荡远超前者,这一时期的翻译体对中国语文的改造可谓天翻地覆。所以说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很多学者也这样讲,如果我们拒绝用外来词和翻译体说话,或者说是作文,那么我们就不能作文了,不能开口说话了,当然也更加不能写诗了,工作都要瘫痪。包括我们的语言、用词、语言的结构,这些都是西方的(如on one side……on the other side)。包括“刹那”“宇宙”,我刚才讲过,宇宙这个概念最初是从佛学进来的,但是后来从日本重新引进之后,变成了西方人对宇宙、对时空的一个看法,成为了另外的一个科学概念,一个天文学的概念,就不是佛学意义上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翻译体本身的无处不在,不是我们要去学那个翻译体,翻译体已经强行进入了,就看怎么学。包括翻译体怎么改变了我们古典的生活方式,我看过一个书,鸳鸯蝴蝶派的一个重要作家包天笑的作品,包天笑老年的时候在香港写过一本回忆录,叫《钏影楼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包天笑讲述了一个有关张之洞的故事,在二百一十二页,他说:在晚清的时候,当时的外来词“如同洪流的泛滥到了中国,最普及的莫过于日本名词,自从我们初译日文开始,以迄于今,五十年来,写一篇文字,那种日本名词,摇笔即来,而且它的力量,还能改变固有之名词。譬如‘经济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由日文中引来,已作别解。”在这里我也想起这么一个事情来,比如我们说的民主,民主自由的民主,中国古代就有民主,但是和现在的意思完全不同,古代民主的意思是民的主人,现在和古代刚刚相反,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自由,谈论的是人人平等,是人权,完全与古代不一样。所以包天笑说对了,经济一词在古代就有,但是从日本进来之后,就有一些另外的意思了。再譬如“社会”两个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这个释义也是从日文而来。诸如此类甚多。包天笑还说了一个笑话:“张之洞有个属员,也是什么日本留学生,教他拟一个稿,满纸都是日本名词。张之洞骂他道:‘我最讨厌那种日本名词,你们都是胡乱引用。那个属员倒是倔强,他说:‘回大师!名词两字,也是日本名词呀。张之洞竟无言以答。”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词汇的进入是势不可挡的,翻译体这个资源我们是不能舍弃的了,作为现代汉诗,是必须要保留,古典汉语和文言文也应该有部分的保留的,只是一个取舍问题。还有就是白话文,白话文是现代性的大势所趋,必须是白话文,不可能回到用古汉语写的时代了。那么怎么写出一种好的语言,不管诗、散文、小说、论文,怎么写出好的语言是一直困惑我们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被很多中国人忽视,反而一个外国人正视起来了。他就是顾彬,前段时间炒得很热闹,他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顾彬谈论的一直是语言问题,他觉得中国的作家也好外国的作家也好,都不太磨练自己的语言,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要回答究竟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书写一篇文章,一篇散文,或者一篇诗歌,这个里面大有讲究。也就是说,传统要靠大家一代一代地来积淀。但是现在现代性已经发生了,已经回不去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来回头梳理一下。比如说,我们在现代性的第一个发生时期,也就是晚清末年和五四前后,那个时候也出现这么一个人,现在提及这个人的也比较多了,在当时是批评居多,这个人就是李金发。李金发这个人是个怪才,他几乎不受五四影响,跟五四无关。他在法国,启蒙他的是法国象征主义,是波德莱尔这些人,但是现在去看他的诗歌,里面文言词汇居多,整个语言节奏还是有中国本位,有中国主体,还不完全是西洋,所以他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形成旋风。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我问过现在的很多老人(当时还是中学生),如已去世的方敬先生,他们年轻时都非常喜欢李金发,疯狂地喜欢着。可以说,李金发身上最早出现了中西合璧的东西,包括文言文,他的文言文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后来有的人说李金发中文也不好,西文也不好,写得不文不白,其实,个中问题大可深究,并非那么简单。我个人认为从李金发到新月派再到卞之琳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尤其是在卞之琳那里,可谓结了一个很大的硕果,又可惜的是卞之琳的这一脉传统没有得到继续,他的传统被后继者破掉了,如果沿着卞之琳的这个传统再继续,现代汉诗的前景可能会非常好。因为卞之琳是化欧化古的高手,既有现代性也有古典性,他那近乎完美的诗篇我就不在此一一展开了。
回到民族性上来讲,我有个问题,提到民族性,民族的面向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民族的文学风貌是非常多姿多彩的,它不是单面性的。比如说我们有屈原的传统,有道德、有良心、有担当、有责任、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学传统,有左翼文学,启蒙文学,革命文学,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还有其他的文学面向,我们好像已经把它忘掉很长的时间了。比如说文学当中的“逸乐”观,逸乐作为一种文学观、美学观和价值观,还有颓废等等,颓废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现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国古代的颓废,如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他就在研究现代性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代性。逸乐作为一种文学观、美学观和价值观,实际上被我们忽略了,这一条线索可以从古到今进行梳理,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并不亚于所谓的启蒙、救国救亡、道德良心、担当责任等等,这几者是并驾齐驱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文学应该有多翅膀和多面性,要知道一个鸟儿一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比如我们只提倡文学的伦理学,但是还有文学的美学,要两个翅膀飞起来才是完整的。我举个例子来谈逸乐,你们就会很清楚了,逸乐作为一个中国文学非常核心的价值观、美学观自古有之,它可以追溯到孔子的“食不厌精”。比如说白居易,我们从小到大对白居易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我们对白居易的印象可能只是停留在中学时期学过的《卖炭翁》,就是那种类型的,现实批判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可能我们已经习惯用这样的话语去规范他了,其实白居易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么白居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白居易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实际上是被断送了的,其实白居易的文学传统是一个了不得的文学传统,白居易真正的文学品味和整个文学资源在日本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平安朝出现了一些惊人的文学名著,比如说《枕草子》,这是我非常推崇的女作家清少纳言的作品,还比如说最伟大的小说《源氏物语》,这两部著作都得力于白居易,日本乃至世界都承认“没有白居易,就没有日本平安朝的文学”,这两部书真正非常的精美、颓废,它们的标准就是唯美,没有别的标准。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白居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个人,那么白居易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白居易这个传统是在宋代才发扬光大的,宋孝宗、宋徽宗都非常崇拜他,天天都要写他的诗,后来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头号闲人,头号“快活人”,是一個非常逸乐的人,比如他任官杭州时,几乎无事可做,仅行他那日以继夜的诗酒文会,难怪他要说:“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他在杭州和苏州做官时,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杭州三年,苏州二年,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他当官时的日课就是天天玩乐,喝酒写诗,看风景,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我马上要出版的书《日日新——我的唐诗生活与阅读》里面有提到,白居易怎么买房子,他要和自己的诗歌兄弟元宗简买在一起,买了房子怎么装修、庭院怎么布置、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喝酒、喝什么酒都有写进去。白居易是一个生活专家,一个享乐专家。话说回来,把这些东西抽象一下,白居易的任务就是书写惋惜时光这样的文学,白居易深懂“人,终归一死”,因此他要“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我也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人不死就没有文学了,因为人终归一死,所以才有了文学。说到这里,又想到了日本人,日本人就特别喜欢惋惜时光,日本人每到看樱花的时候,几乎都是举国出动,花开花谢,一期一会,确是“良辰美景奈何天”。日本人对事物细节的完美追求,对风景的感怀,对光阴流逝的轻叹,很多都是从白居易那里学来的。白居易在欧美受到的推崇也是一样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只想说白居易的文学传统被近现代的革命文学压抑下去了,这个传统在宋朝曾被发扬光大,元明清也发扬光大,后来“赶英超美”的呼声遮蔽了白居易的歌声,因为我们要启蒙、要救亡,当前的任务仍然是要改造我们的国民,要废弃古文和古书,要灭掉汉字,在这样的传统下白居易只能消失。我们不理解白居易,但并不能说我们的古人不理解。那么按照白居易的诗歌线索往下推,就连宋徽宗(也是大艺术家、大画家)也无不叹服白居易的生活与艺术情调,他曾以他的“瘦金体”书法,手书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可以说他几乎是按照白居易的人格来锻炼自己。南宋孝宗也曾在亲笔抄录了白居易的《饱食闲坐》后发出感慨:“白生虽生不逢时,孰知三百余年后,一遇圣明发挥其语,光荣多矣。”再往下排,后世也有很多白居易的崇拜者,晚明那就更不得了,到了现代,大家都知道,林语堂是传承了白居易的传统的,但是他是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当然也得到了某些嘉许。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有很多面向,就刚刚提到的“逸乐”而言,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性特征,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性压抑下去呢?再比如说,《红楼梦》这部小说,现代有些学者就敢这么说了,李欧梵就曾经说过:“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最伟大的颓废小说”,从这个面向也可以研究,颓废就是过度精致,过分沉湎和耽溺,沉醉于某片风景,沉醉于某个细节或一朵花,这个就是颓废。颓废是一个中性词,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后来现代性在中国的进程变得比较单一了,被另外一个东西取代了,这就是下面要讲到的现代性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文体的出现,毛泽东文体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比如李陀就研究过,李陀的文章《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和《丁玲不简单》,发表在《今天》上,都谈到了毛文体。谈到现代汉诗就不能不谈到这第二个阶段,因为现代汉诗在这个框架中呈现出来的已是另一幅画面了,它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呈现出来。那么这里就可以稍微地说一下毛泽东文体,也不能完全展开来谈。毛泽东早期著作是文言和半文言,后期都全是白话了。毛泽东有几篇文章非常重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都是不得了的文章,当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括我们的行文方式,谈话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姿态、风姿,都被这几篇文章深刻的影响着。福柯晚年也受着影响,垮掉派的金斯堡每天要看的都是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37年到1945年,毛泽东文体进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对中国文学,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超强影响力,《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可以算是现代汉语的里程碑,当然,功过是非可以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影响力是不容置喙的。毛泽东的文章为我们统一了一个社会的口径,约定了我们说话的口气和思考表达的方式,从此新一代的人用起来就很方便。我们的报纸,包括新华社文体,我们的电影和恋爱几乎都采用这样的一个语法和修辞,换句话说,毛泽东通过自己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学习制度。在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剧烈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何其芳,何其芳是一个非常唯美、古典的诗人,既西化又传统,有些评论家如江弱水认为何其芳是“雌雄同体”的诗人,一个每天都做梦的人,一个生活在晚唐的人,那么纤细的一个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毛泽东文体改变了,这从何其芳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包括卞之琳也被改变了,多多少少都受着毛泽东文体的影响。李陀在《丁玲不简单》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为什么毛文体那么厉害,可以把已经被塑造定型的人一夜之间改过来,“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所以说不仅中国人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西方也受着影响。连胡适后来也对唐德刚说过,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见唐德刚:《胡适杂忆》)。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成长的,我认识一个学音乐学的朋友付显舟,现在是音乐学博士,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现在都还记得,也就是谈论了毛文体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他说:“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就是毛文体,是规定了的那套话语”。无可厚非,这跟他的成长有关。瓦雷里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写作的人,只要他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一本决定性的书,就能改变他的命运。”我的朋友曾经说过,他最初是想尝试用一种经过现代汉语翻译的西方现代散文语言来写作,或者五四时期的语言,但是语境已经不相同了,场景已经变了,已经写不出来了,用那些语言经常词不达意。而明显的是,用毛泽东的文体就得心应手,这个当然跟他早年熟读毛泽东著作有关,而毛的著作可是在他决定性的年龄读到的呀。我还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后现代主义专家,一个女学者写的,书的名字我忘记了,她是专门研究话语权力的,她认为毛泽东是话语权力的首创者,后现代的源头要追踪到毛泽东那里。她舉例说明了,毛泽东在1942年写作的《反对党八股》中为话语权力作了最准确的解释,“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党八股》是阐释话语权力的经典著作。从延安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毛泽东的文体在全国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局面。这点我们都知道,很多诗人和文学家都是前仆后继地感受到了毛泽东文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的魔力。这种中国现代性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也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中国国门的全面打开,西方思潮的全面进入,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番景象,朦胧诗出现了。朦胧诗的出现也是很有意思的,朦胧诗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他们要从毛泽东文体,从新华社文体,从大字报文体当中脱颖而出。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交战和对抗,它要出来就必须启动另外的资源,不然还是在这个资源当中,那就不行,就不能成功。那么怎么从这个资源出来,就像两军对垒一样,启动什么部队和另外一个部队作战,他们自己都有现身说法。在许多访谈和采访中,北岛说过,其实我们当时靠翻译体起家的,没有翻译体出不来。翻译体像是一个应急系统一样,这个在当时很重要。这个资源是个临时性的资源,但非常管用的资源,可以立竿见影,拿来就用,所以北岛他们通过翻译文体对毛泽东文体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了一次正面的发难,所以他们可以脱颖而出。这个不需要过于的展开,从这点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当时他们读了很多翻译书(这方面目前有很多资料很多文献可以供你们去查阅了解),基本上都是翻译诗歌、小说、散文、哲学著作,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开始的。又回到前面所说的,比如说北岛早期的那些诗,从对抗美学这个意义上讲非常有意思,但是它进入国际资本流通的时候,即被翻译后,就受到有一些汉学家的挑剔,比如宇文所安在一篇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里就谈论了北岛的一本英文诗集,其中谈到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而且就直接认为北岛的诗歌是缺乏民族性的。这篇文章在1991年发表在《新共和》上面,发表之后引起很大波动,论战也很多,有持相同意见的,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专门批评了北岛的一些诗,比如《雨夜》,他说像《雨夜》这首诗是写作者应该学会避免写出的诗。因为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歌的病症,这首诗歌出现在政治性诗歌当中显得很幼稚,应该避免。《雨夜》这首诗歌大家都知道,其中有如下几行:“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叫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 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也绝不会交出你”等。这正是我想谈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也是老生常谈,杰姆逊也谈过第三世界文学有个特点,第三世界文学是一个民族寓言,政治和艺术不分,公和私不分。举个例子,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一个西方读者来读的话,他只会读成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内心独白,但在中国文学的语境里当然应读成是吃人,鲁迅在此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一种彻底批判,“吃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这样一个象征意义并成为了一个民族寓言。那么《雨夜》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寓言,它虽说是写爱情,但不单单是在写爱情,这个爱情牵涉到了某种政治对抗某种英雄形象,血淋淋的太阳要我们交出青春 ,自由和笔,而我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也绝不会交出你,这里如按照杰姆逊的读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一般人总是这样来谈论朦胧诗,好像他们的诗比较政治化,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沾上政治的诗就不是好的艺术。真是这样吗?如再按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学是艺术和政治不分,那这一点正是它与众不同的力量之所在,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从古代来讲,其实也是这样的。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主要特征是个什么样子,我刚才讲过了有很多特征,有颓废的特征,逸乐的特征,兼济天下的特征,还有现代性的特征。有的西方人甚至认为,第一次以“零度写作”姿态写诗的人是王维,后现代第一个作家是王维。这是很多西方学者的共识,的确如前所述,中国文学有很丰富的容貌,不是简单的一个面孔。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呢?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政治性特征,我认为它是一个深远的传统,这点我前不久也正好在一个日本汉文学家吉川幸次郎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他说:“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在以诗歌为中心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国民谣及朝廷举行仪式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这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就成为中国诗的传统一直被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二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和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被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他这席话很有意思,当然可以辩难,可以讨论,不过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不能以一个政治性就把今天派、朦胧诗给否定了,好像政治性强的文学就是一个很差的文学。这可不一定,政治性当中有非常优秀的文学,吉川幸次郎那段话中所说的那些大诗人便是明证。政治性中也有很好的书写,比如萨特的行动哲学,它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其文学性也是一流的。
至此,我将结束这篇长文了。在结束之前,请允许我对这一题目作一个回顾(因古人说“温故而知新”):我对于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之诸问题的思考和言说,始于2002年,可见该年5月受凌越访谈(《书城》)之文章;2004年在接受马铃薯兄弟为《中国诗人》所作的访谈中,我又进一步探讨了此问题;但此问题正式登场是2006年3月初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次演讲,后来在众多访谈中亦涉及此问题,其中最为令我难忘的一次乃是泉子对我所作的那次访谈,此访谈后发于《西湖》。接下来,我在2009年四川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一个更为全面细心的程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至今仍在路上,但愿此文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来更多的高手参与其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各自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