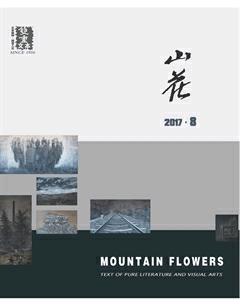秘密
冯积岐
两个人擦肩而过。这简直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舞台下或集市上,人头攒动,神色慌乱,步履匆忙。在他下意识地回过去头的同时,她也回过来了身子,四目相对,两张面孔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都没有开口,都用目光在探询对方:你?他的记忆力在迅速地旋转,唤醒他的不是她的那双好看的杏核眼,不是她性感而红润的嘴唇,不是她爽朗得有点放肆的笑声,而是那种只有他能嗅到的气味,如同祥云一般朝他飞来了——他的嗅觉变得十分灵敏。他吸了吸鼻子。他说,我闻见了。她说,你闻见了啥?他说,我闻见了你身上的味道。她说,啥味道?他说,狗臭味。她伸出指头修长的右手在他身上拧:你真瞎(坏)。他把她紧紧地揽住:我不瞎,你不爱。两个人都一丝不挂。他们搂抱在一起,他又吸了吸鼻子,他说,你就是走到天尽头,我也会认出你的,你身上有一股味儿,甜味咸味酸味,各种味儿混合在一起的味儿。我一吸鼻子,就知道是你,娟子。她说,别的女人身上有没有?他说,是人,都有。你的味儿很特别,只有我能嗅到。她说,咋特别?他哧地笑了,把手伸向她的福地:这里的特别,你能说清吗?她说,你就是瞎。他说,我就是不瞎,也说不清的。他把她压在了身底下,灯光下,他看见,她用牙咬住嘴唇,脸庞上、双目中流露的巨大的愉悦是用看似痛苦的表情来表述的。他带着她的味儿离开了她。人在一年一年地变老了,味儿如同亘古不变的蓝天白云一样依旧清晰可辨。他向她跟前走了一步,她身上的味儿淡了许多,可是,质地没有变,还是那么的特别,那么的醒目,他略为惊讶地叫了一声:娟子!她抬起了眼,上下打量他,——好像是,又不是。是他吗?她是平静的,平静而忧郁的脸庞上闪上一丝微笑,又很快消失了。他说,娟子,我是李正开,你不认识了?她苦涩地一笑:老了。他说,三十年了,能不老吗?走,找个地方去坐坐。她急忙说,不,不去了,我还忙着。他说,你咋到这儿来了?谁住院还是……他欲言又止了。她说,女儿住院了,在肾病院。你呢?他说去看望一个朋友。她说,你忙吧。她拧身就走。他伫立在那儿,眼看着她淹没在人的洪流中。我咋没有问一问,她的女儿在几病室,几号床位。
李正开本来是来看望和他一同在古都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的老师的。他没有上楼去看望那位老师,而是从大厅里的人群中挤出来,下到地下室的车库,开上车,径直回到了学校。
刚走进办公室,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他还没有开口说事就被他打断了:我有点不舒服,有什么事明天说吧。这位年轻的系主任用蹊跷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出去了。校长答应他,下半年一定叫他退下来。并不是因为他要退下来而敷衍系主任,他确实没有情绪和任何人谈工作。三十年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西京医院——这个全国人都慕名而来看病的地方邂逅娟子。是娟子不愿意面对你,还是她女儿的病不允许她有一时半刻的怠慢?为什么你在三十年后才见到她?一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么多“后”,为什么不去看她一眼?薄情?无情?还是……不论是什么原因,他都不能原谅自己。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不再见面比见面好。他说,结婚后,你就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想我,咱们都把对方牢牢记在心中。我不会再来干扰你的,也不再见你。她啜泣。她蜷缩在他的怀里。她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不再见你,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你不会离婚的。他用手捂住她的嘴,不叫她再说。
结婚前的前两天晚上,当乡政府沉入梦乡之后,她来到了他的房间。那一夜,两个人都一眼未合。他们不停地相互诉说,诉说未毕又做爱,做完爱又诉说,一直到黎明时分,她才回到了她的房间。她说,我遗憾的是,没有怀上你的娃娃,我多么想要你的一个娃娃呀,只要怀上你的娃娃,我就是这一辈子不结婚,把娃娃生下来,养活大,叫他上大学。等他成人后,我会给他说,他的爸爸是谁。二十岁的女孩儿,想法多么甜蜜、浪漫呀。他说,你后天就要结婚了,你结婚后,自然会怀上他的娃娃的,你的娃娃也就是我的娃娃。她说,你把我的心摘走了,我和人家能过好日子吗?他沉默不语。她的这句话,唤起了他的罪恶感——是的,她爱他爱得太深了,至关重要的是,他是她的初恋。初恋对一个小姑娘来说,意味着把常青树的种子种在了心里,它一旦发了芽,出了土,即使一万年,也不会老的。他不只是把她的心摘了,他把她的魂也占有了。她这一辈子,和谁结婚,也不会很幸福的,当他意识到爱情的果实是这样的时候,他真后悔当初的冲动。
李正开垂下了眼,扑入他眼帘的是亡妻的那张照片——妻子因肺癌去世才一年多。照片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结婚前,他想把他和娟子的事给妻说明白,又怕妻不理解,因此而失去了她。他没有担当的勇气。结婚后,几次想说,也没说。妻弥留之际,他本应忏悔,本应把心中的秘密坦露了,又怕刺激妻。心中的这个秘密就这样被他掩埋了。偶遇娟子,他才觉得,亏欠着两个女人。
作为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一项工作归他分管——给乡政府挑选一个打字员。来报名的女孩儿有八个,年龄都是十七八,都是初中毕业,长相都有亮点。他偏偏选中了松陵村的这个叫做苏娟子的十八岁的女孩儿。他用挑剔的目光端详、打量着她,他距离她只有几十公分。使他对她产生好感的不只是端正的五官——八个女孩儿都能用“漂亮”来形容,他明晰地嗅到了她的味儿——不是劣质雪花膏的味道;不是香水的味道——农村女孩儿,谁还用得起香水?是一种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香气袭人——他不由得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袭人。在他看来,袭人并不是一个坏女孩,即使她和宝玉关系暧昧也不是坏女孩儿。况且,这个苏娟子也不是袭人,只是有一身香气而已。娟子到乡政府来上班,他是她的直接上級。乡政府的所有下发的文件、材料都要他签字,都要她打印,他们之间的接触不免比其他人多了许多。
偶然。完全是一种偶然。他随同乡长检查乡村企业的生产情况,那天的晚饭,他们是在乡化工厂吃的,他喝多了。事后,他才知道是王乡长吩咐小娟来给他端水,打扫他呕吐在脚底的赃物的。半夜里,他醒来一看,娟子坐在他床头跟前的凳子上,双手托着腮,看着他。他的第一句话是:给我端些水喝。娟子从套间外面端进来了半杯开水,兑上了放在床头柜上的半杯凉开水,递给了他。他坐起来,一口气喝干了。他没有把杯子直接放在床头柜上,而是又递给她——就在他递水杯的那一瞬间,他把持不住自己了——他拉住了她的手腕。她并没有挣脱。她从容不迫地将手中的茶杯换到左手,放在床头柜上。她的右手的手腕依然在他的手中。她那双并无睡意的眼睛里饱含妩媚,脸上霎时间有了一层红晕。他拽住她的手腕将她向他跟前一拽,她的头倒在了他的怀里……事后,她哭了。她用手捂住嘴——生怕哭出了声,两行眼泪顺着脸颊向下流。他慌了手脚,害怕极了。她只有十八岁,而且是第一次。你卑鄙的用酒后乱性来替自己开脱:娟子,我喝酒了。我喝多了,你能原谅我吗?她只是默默的流泪,一句话也不说。你知道,你是清醒的,在那一刻,你十分清楚;你从见到她的第一面就爱上了她,这半年来,你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得到她,是你的蓄谋,是你的愿望,是你的需要。你该怎么办?你想到的是你,而不是她。一个十分清纯的、十八岁的农村女孩儿被你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苛刻地说是糟蹋了。假如她明天就后悔,就去派出所就去告诉她的父母,或者,到凤山县妇联去,给在县妇联当干事的你的妻子任莉莉说了,那时候,你的一切都完蛋了。刚才从她身体上获取的庞大的、从未得到过的愉悦转眼即逝,转换成了内心的恐惧。你无望地看着苏娟子,目光里的求助显而易见。苏娟子擦干了眼泪,扑哧笑了——女孩儿情绪的变化快得如闪电一般——你惊愕而慌乱,不知怎么应对。她扑上来,双手搂住了你的脖颈,把舌头伸进了你的嘴里。你狠劲地吸着、吮着。她呢喃着:正开,我还要。你说,我不敢了。她笑了:有啥不敢的,我爱你。你十分惊讶:真的?她说,不爱你,能叫你得到我?你说,是刚才爱上的?她说,不,从第一天看见你就爱上了你。你心中坚硬的冰块即刻融化了。你说,娟子,我爱你,我是爱你才和你那样的。你相信吗?她说,相信。是我愿意给你的。我就是你的,你想咋弄就咋弄。这一次,你不再紧张,你放松了。当身心和肉体融为一体的时候,你觉得,你消失了。随之,一阵绝望感袭来了——你把人世间最美好的已经得到了,你还能得到什么呢?
黎明时分,她恋恋不舍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走后,你睡不着。只有你自己明白,你确实爱着她,你的灵魂深处最丑陋的东西你掩藏不住——也许,你会欺骗她,可是,你骗不了你自己,——你爱的是她的漂亮、她的年轻,她的身体给你带来的巨大无比的欢悦——你爱的是和她做爱。你吩咐自己:一定要善待她,要对她好。她比莉莉单纯,比莉莉真诚。其实,他给妻子也挑不出多少性格上的缺陷和品质上的毛病,他就是讨厌她那很干部的表情很干部的腔调——只做了几年干部,她身上的所有细胞似乎被“干部”这两个字吞噬,连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也干部化了。他给莉莉说,咱俩在床上的时候,你不说普通话行不行?莉莉在他的身体下扭动着用普通话说了一句:好舒服呀!立时,他就没兴味了,一动也不动了。他觉得,“好舒服呀”这四个字就好像摆在柜台上的赝品,一眼就能看穿它是假货。同样,莉莉却接受不了他的语言的直捷,在那刻骨铭心处,他的粗俗出口了:××真好。莉莉高叫一声:流氓。一把将他推下了身。矛盾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他和莉莉同样是关中西府农村农民的儿女,为什么他当了几年干部了依旧很农村很农民——生活方式和父母亲一模一样,而莉莉的变化咋那么快?他想不通。当初,在西水市农业学校读书谈恋爱时,莉莉还是一副农村女孩儿的扮相,农村女孩儿的做派。
和娟子在一起的那三年里,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他床头上的那几部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简爱》,还有《红楼梦》,娟子拿去都读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读书的时代,娟子加入文学爱好者的行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那时候的他已经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四篇小说了——娟子对他的爱中难免有一种崇拜——读文学作品越多越崇拜他,越爱他。
两个人的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他们在彼此的宿舍里偷情——无论是晚上夜阑人静之时,还是午饭后乡机关的人在午睡之中——能逮住的时光,他们绝不放过。对此,他们已经不满足,他们在乡政府所在地的玉米地里、土塄上、水渠旁,在农民们目光不能及的地方撒遍了爱迹。她问他:你说我是安娜还是爱玛?他笑了:你谁也不是,你是苏娟子。她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安娜、爱玛或者简爱,或者德瑞那夫人。我在你身底下的时候就是她们,比她们更爱一个男人。我将来不是,我不卧轨,也不服毒。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么善良,肯定会有一个好丈夫好家庭的。她说,不,我不要丈夫,我就跟着你,给你生一大群胖娃娃。尽管,她说得很无心,但是,一提到娃娃,她还是担忧。
她已经为他流过一次产。
是他把她带到临近的一个县医院去流产的。做毕手术,她躺在床上休息了两个小时。他拉住她的手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他说,我不信。她说,为了你,疼也不疼。她的脸色有点发白。他看着她,一种怜惜之情萦绕在心头。他觉得,他很对不起她,而她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上回凤山县的客运车,她就呕吐了。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他被吓得不轻。那天,她只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她照常上班。他给她买了二斤红糖——和她相爱三年,他只给她买过二斤红糖和一双塑料红拖鞋。这使他一想起来就内疚。当然,不是钱的问题。
李正开以为他做得万无一失,他就没有察觉到,他的妻子任莉莉早已觉察到他有了外遇——一对相互在乎的夫妻就是彼此的晴雨表,谁也逃不出谁的感觉——尽管,你可以哄得天衣无缝,使一方捉不住任何事实的把柄,可是,感觉这东西却是无法掩饰无法掩埋的——有时候,确实有失误,但次数多了,量的积累就成了质的铁证,——任莉莉不止一次地从李正开的身体上感觉到了他有外遇,他把娟子的气味带进了家里,他和她在一起不是敷衍了事,就是力不从心。一次两次还可以,三五次也说得过去,经常这样,莉莉就无法承受了,她毕竟才二十四岁,处于欲望最旺的年龄阶段。任莉莉旁敲侧击的警告过李正开几次,而李正开总以为她没有证据,说了也是白说。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莉莉反而欲擒故纵,使李正开完全放松了警惕。当星期天午睡之时,莉莉用她偷配的钥匙打开李正开的宿舍门的时候,李正开和娟子半裸熟睡在床上。任莉莉没有哭,没有闹,她淡淡地给李正开说,起来,穿上衣服回县城。三天之后,他们办了离婚手续,二岁的女儿归任莉莉抚养。
就在那年年底,娟子仓促地和一个小学教师结了婚。第二年,李正开离开南堡乡政府走进省城里的时候,娟子的女孩已经快一岁了。他从此以后,没再和娟子相见,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踪迹。
娟子所说的患肾病的女儿是不是他离开凤山县前一年所生的那个女兒。如果是她,今年三十了。
三十年没有见娟子,在他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他觉得五十七岁还不算老年,为什么会在西京医院见到娟子。生命有时候会有暗示的。暗示什么?李正开一个晚上辗转反侧,没有睡好。他觉得他到了该偿还一份情债的时候了。这份债的内容不仅仅是十八岁的娟子和他上床的时候还是一个清纯的处女,不仅仅是娟子为他痛苦地流了一次产,不仅仅是她忠心耿耿地爱了他三年,这份债的数字是庞大的——他在她心中布下的阴影有三十年了,小半生时间,她在他的阴影下和另一个男人生活——他从她忧郁的脸庞上能看出来,她不幸福 ——何谈幸福?也许,十分压抑,十分艰难。她那模样就不是一个五十一二岁的农村中年妇女,而更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你现在什么都有了: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她呢?当你对你的学生们大谈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的时候,当你在各种学术活动中坐在主席台上人模人样的时候,你的学生你的同事和你自己,哪里会想到,你的身后曾经有这么一个农村女人深情地爱过你——这不是故事,这是生活。
第二天起来,他去学校里的工商银行办了一张二十万元的银行卡。他知道,肾病是要花一大笔钱的。他拿上银行卡,开上车,在西京医院隔壁的汉庭酒店要了一间标准间。他把车停在酒店,去肾病医院找娟子。
在医院的三楼三病区二十一床,他见到了娟子的女儿——一个叫做孙小芸的女人。这是一个四人室的病房。他进去的时候,孙小芸刚刚挂上了吊瓶。娟子一看是他,有点吃惊。三十年来,他第一次正视她的面孔,目光落在她那憔悴而有点慌乱的脸上。她看了他几眼,像犯了错误似的垂下了头。她接过他递过来的营养品,给躺在病床上的女儿说,小芸,这是你李伯伯。小芸试图坐起来,病床旁边那个男人——小芸的丈夫将她扶了扶,小芸坐起来了,她正眼看了看他,少气无力地说,李伯伯,我好像见过你。娟子说,这女子,叫病害得胡说哩,你咋会见过?李正开看了几眼孙小芸,她的脸色浮肿,颜色发黄。她说,叫女儿快躺下。他给娟子说,你跟我下去一下,我有几句话给你说。娟子稍微一迟疑,给女婿说,你照看着小芸,我一会儿就上来。
李正开领着娟子到了汉庭酒店。他不想问她的女儿是怎么得的病,也不问她花了多少钱,他也没问娟子这三十年来是怎么过來的,娟子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他能感觉得出,娟子的生活状况。至于说肾病是什么样的病,他清楚。他知道,最终要换肾。他很内行地问娟子,有配对成功的没有?娟子说:没有,我和我丈夫,还有小芸的弟弟都没配成功。等肾源已等了两个月,天天靠透析维持着。医生说,短时间等不到配型成功的肾源,恐怕……娟子欲言又止,泪水潸然而下。
他没有再说什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银行卡说,这是二十万元,在工行取,存的是你的名字,密码是你的生日650826。娟子愣怔地看着他:我的生日你还记着?他说,记着,1965年8月26日。她没有接银行卡,扑过来,抱住李正开,放声大哭了。她浑身抖动着,好像在发冷。她好像不是用口腔哭,而是用整个身体哭,全身的每一处都在哭。他抱住了她。你哭吧,娟子,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你的厄运是和我的不负责任分不开的。我知道,你难过了三十年。这全是我的错。你放开声哭,哭,哭。他的脸紧贴在娟子的脸上。两个人的脸庞都是湿的,已经分不清是谁的泪水湿了谁。
临分手时,李正开说,如果卡上的钱不够用,你给我说。娟子说,小芸在凤山高中教书,可以报销一部分的。现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肾源,真急人。李正开说,你不必过于焦虑,你说女儿很优秀,上苍会眷顾的,肯定有合适的肾源在等着她,你别急。
三天以后,李正开再次来到西京医院。他没有去孙小芸的病房,没有见娟子,他找到了他的一个学生——西京医院院办主任马东。他把他的想法给马东说了,并要马东给他保密。当天,李正开做了需要做的三项检查,结果使李正开大吃一惊,孙小芸所需要换的肾和他的正好配上对。他把化验单装在身上犹豫了几天,他咨询了几家医院的医生,在这几家医院都有他的学生。回答结果是一样的:一个肾完全可以延续生命,但是,人身上的所有器官没有多余的,两个肾才是合理的。怎么办?假如,他把肾献出去,他患了肾病怎么办?假如,小娟的女儿在短时间内没有肾源,危在旦夕又怎么办?没有假如,只有现实。是捐还是不捐。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他:为什么他们的亲人的肾都配不上对,偏偏他的肾就配上了对?这些问题,他越想越烦恼。
一个星期以后,他给学校的校长请了假,并且欺骗自己的女儿,说他去医院疗养一个星期。他找到娟子,给娟子说,他的肾能和小芸配上对。他要给小芸捐出一颗肾。小娟一听,坚决不同意。小娟说,哪怕小芸等不到肾,哪怕……娟子说着,眼泪下来了,她说得很坚决:你走人,不要,不要你的肾。你的命值钱,还是小芸的命值钱?你真是太糊涂了。他苦笑一声:都重要。我已经叫院办通知主治医生,明天上午就安排手术。就在那一天,李正开偷偷捡了两根孙小芸掉落的头发,吩咐马东将头发送到了DNA检验室。
手术很成功。
本来,李正开休息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在他准备出院的前一天,马东给他送来了孙小芸和他自己的DNA化验结果:孙小芸是他的女儿。他将化验单拿在手中,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这对小娟和他们一家人来说,又是一个秘密。他从干部病房出来,急急忙忙赶到了肾病院。
走进病房,走到病室门口,李正开站定了。他突然变得很清醒。透过门上一拃宽的玻璃,他向里看,孙小芸躺在病床上,旁边站着小娟和她的丈夫。小芸是有父亲的。既然这个秘密在他心中装了三十年,他就继续装着吧。只要孙小芸康复了,他的罪恶感就减轻了许多。李正开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