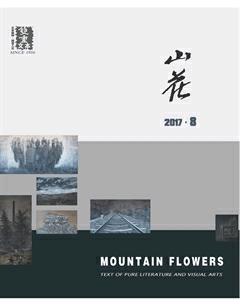关于孟煌远方系列的哲学思考
沃尔夫-于尔根·格拉姆+贾枝平
哲学试图澄清人在自我认知和世界认知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概念,特别是要把隐含的东西(前提、涵意、关联)揭示出来。在这方面,哲学也是语言批判,探求意义及有意义地表述条件和界限。依笔者理解,其理想是不偏不倚、开诚布公、冷静、准确地论述和遵守使用概念的规则。
而艺术,如果其表述成功,其表达的则是无法用语言对等表述的内容。对艺术进行诠释当然可能,而且也有意义,毕竟艺术使用的是可以破解的符号。但是,艺术总有可示而不可言说之处。
理解意味着划分、归类,找出共性,而艺术的生命力往往又恰恰在于某些不被理解、某些无法令人满意地终结理解努力的因素,在于艺术表达所唤起的情感,在于被唤起的回忆,深层的觉受、意境。
如果要从哲学角度观察孟煌的远方系列,就必须着眼于可解读的符号,着眼于其表达和象征的可言说之处。
关于远方系列
考虑到孟煌对个人经历的一些讲述,这位艺术家的远方系列所要表述的看起来是远与近、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安全、探险的兴趣或冒险精神与对安逸或安全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这些概念的两极之间存在张力,就意味着,单独化解其中的一极并不能完全而令人满意地化解张力。
对孟煌而言,空间是自由的象征。空间,可以从字面理解,就是地形学意义上的空间;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比喻,就是行为与思维的可能性空间。或许他的空间兼具两层含义。无论如何,画面中描述的地形空间看起来也象征着可能性空间,这样,在空间得到描述的物就可以代表某些可能性。
自由是一个有多层涵意的概念,其中有选择自由(或称意志的自由)与行为自由的重要区别。一个人的行为自由可以受到限制,而其选择自由则不受限制。即使我的行为自由因为外来的强制而丧失,我依然还有认可或否认这种外力强制的选择自由。
自由这个概念中另一个重要区别方式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即免于某些东西(如强制)的自由和行事的自由。就消极自由而言,若无人强制我行我所不欲,即我有自由。就积极自由而言,如果拥有可以扩展我的行动空间的手段或可能性,能够充分发掘我的潜力(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受教育带来的可能性),我就拥有自由或者拥有更大的自由。我们可以用规则为例来说明。一种道德或国家性质的规则可以限制我行为的可能性,但在无规则限制我的行为空间时,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扩大我的行为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规则不是限制我的思维,而是规则才使我的思维成为可能。游戏规则一方面带来限制,另一方面又為我带来了参与游戏的可能性。
免受强制的自由远不能说明我该做什么、什么正确,而是可能性的一个条件,而在选择的可能性的意义上的自由则是尊严与自重的条件。
空白的空间其实不能象征选择或行为自由。自由必须具有某种前提,某种可选择性,某种结构。孟煌的画作中含有风景和楼房或技术设备,尤其是铁路路轨。铁轨给定道路,(远方系列中有些画作中可以看到的)道岔口则象征着可选择性,因而代表着自由。不过,铁轨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成为选择自由或者合适行为自由的象征符号,因为自由要复杂得多。但是,轨道可以象征某种方向、某种预定的道路,象征某种追求或者渴望。孟煌的远方系列中并没有可见的目标,如果有目标,那也是在地平线之外,在远方。但是我们知道,铁轨终究要通向什么地方。这就让人想起孩提时代对远方的渴望,以为铁轨必然通向更有意思、更美好的地方,我们仅仅需要跟着轨道走就可以了。这样的画面或许在暗示,为到达地平线后更遥远、更美好、更自由(在积极自由意义上)的地方,屈服于轨道的强制——就是自愿放弃消极自由(比如意味着放弃对个人幸福或富裕的追求)——就是必要的。
这里的“积极”和“消极”不能作评判意义上的理解,不是指“坏的”或“好的”的自由。
画作中的黑白(或者淡褐色/淡黄色与白色)色调的黯淡一方面可能暗示,其他一切地方都好于此地,另一方面又可能暗示,一切好于当下的彼岸设想都是虚妄。有些画面的地平线上其实并没有光亮,充其量是我们希望有光亮,而另外一些画面中又可以看出那里有光亮。有时,黏稠的一团会从上方流入、滴落到画面中来——一种抑制自由空间、击溃对地平线充满希望与渴望的视线的现实?
但是,这种色调也并不是表达——至少不仅仅是表达——一种黯淡的氛围或者悲观的基本态度,而是(也)象征着严谨、冷静、简洁或者明晰,是对形与结构的专注。
远方系列的画作中没有生命。这或许是暗示:人性不在当下,但也可以是说,主体(这或许与画家或者画作观赏者的视角吻合)与其他客体之间的距离太大,使后者根本无法在最直接的环境中显现出来。
类如本文的哲学评论不能也无意提供明确的或终极的诠释,提供这样的诠释或许本就不符合艺术家之意。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画作的力量应该产生于生活经历而生成的智识悲观主义和一种对更美好、更自由的环境不可磨灭的、更多的是直觉式的希望的混合。这种充满力度的混合不可能真正地用语言描述,而是在孟煌的远方系列中展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