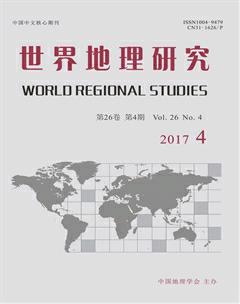从恢复力到社会—生态系统:国外研究对我国地理学的启示
摘 要:目前恢复力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正在取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本研究总结了恢复力理论的发展历史,结合恢复力研究已进入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阶段并占据了复杂科学的一席之地的现状,从思考社会—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出发,将不确定的问题总结为干扰和讶异两类,探讨由此带来的系统相对稳定和不稳定状态、边界和临界问题,总结现有研究对这些连续和不连续状态和演变过程的研究模型——适应性循环和扰沌结构,关注系统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的遗产效应和创新、保守的产生以及时滞问题。针对这些分析,本文认为国外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对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地理学有三点启示:①可持续发展不是人地系统的现阶段和最高形式,人地系统面临的问题是不确定的,天人合一可能更适合描述人地系统的状态和演变过程;②以时间维度为核心的社会—生态研究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状态、演变和遗产效应的研究路线梳理可以启发人地关系研究中时间维度的拓展;③作为擅长综合研究的中国地理学在将人地系统作为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方向上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一向关注天人合一的中国地理学是有方向可循的。
关键词: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中国地理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K90-0 文献标识码:A
可持续发展理论自提出以来,已成为很多学科的研究主流。尽管人们在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利益平衡间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实际上取得的经济收益与付出的环境代价非常不平衡,这些事实在工业化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已经得到了不断的验证,以人为本的人本中心思想让人类在面对环境和经济的时候,让步的始终是环境。不仅自然环境系统的不良变化不可逆,人类社会系统也如此。众多学者开始反思这一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只是我们对未来的野心[1],是对人类社会能否持续而担忧的表现,属于预期性的战略目标问题[2],不仅实践上不能解决问题,理论上也出现了“破缺”[3],相关研究显示可持续发展理论除了概念的滥用,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我国地理学研究长期坚持人地系统这一核心,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关系的现阶段形式或最高形式[2]。然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自哈佛大学于1986年取消地理系,全美大部分高校跟随撤并地理系以来,地理学经历了衰退后又在其他学科或学院重生的过程,除了地理信息系统异军突起外,地理学仍旧无法恢复曾经的辉煌。在中国,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地理学虽紧跟西方地理学理论但却没有走向消亡和衰落,反而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国民经济社会各方面承担了众多任务而得到长足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面临的困境也表明近年来人地系统理论的停滞不前。
走在污染最前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上不断被证伪的过程后,目前已经步入了反思和修补的阶段,并认为反思和修补没有办法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这些灾难有可能就是系统的累积效应,使得类似灾难管理、风险控制和脆弱性研究等预设性研究和生态管理实践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其中以恢复力(Resilience)理論最为流行。实践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区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致力于区域恢复力的建设,使得恢复理论有取代可持续发展的趋势[4]。目前,以恢复力作为分析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的重要框架[5],从复杂系统动力学角度研究系统对抗干扰的恢复和适应,已经成为探索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的主流[6-8]。从内涵上来说,社会—生态系统与人地系统非常相似,本文在总结国外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综述社会—生态系统在结构、状态、演变、遗产效果等方面的国外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地理学及人地系统研究有所启示。
1 恢复力理论的演变
自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家Holling提出恢复力概念[9]以来,恢复力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工程恢复力、生态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工程恢复力(Engineering Resilience)是恢复力的最早解释,强调系统的某个稳定状态并以恢复到同样状态所需要的时间[10]速度[7]来衡量。生态恢复力(Ecological Resilience)是对工程恢复力的修订,假设系统存在多个稳定状态,以系统在跨越这些状态时吸收的干扰量[10,11]而非时间和速度来表达恢复力。两者都属于传统恢复力,即认为多空间的复杂系统行为将围绕吸引场进入稳定域,如果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域,原系统的恢复力将丢失[12,13]。近年来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14]研究则开始聚焦于系统的演变过程,与适应和进化越来越近[13,15,16]。一般来说,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包括:系统在保持结构和功能时能忍受的变量;经受干扰后系统重组的程度;系统学习和适应的程度[17]。“恢复力联盟”也从3个方面理解系统的恢复力:系统保持同样状态前提下能吸收的干扰总量;系统自组织的能力;系统能够建立并增加适应外界干扰的能力[18,19]。这个层次上的恢复力和进化论有共通之处,不再强调稳定状态、多稳态的生态平衡或社会生态平衡,而是关注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在应对压力和张力时的变化、适应以及至关重要的转换能力[20]。对均衡的摒弃、对内在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的强调以及对持续性、适应性和可变化性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的深刻认识,为理解复杂的社会和生态相关性如何运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21]。而且关注演变过程通过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引领生态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复杂系统或复杂科学,即将工程恢复力对系统单一稳定状态以及恢复时间的关注、生态恢复力对系统多稳定状态和吸收干扰的量的判断转移到对复杂系统演变过程上来。
2 社会—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
社会—生态系统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融合研究,从概念上来看与中国地理学的核心——人地系统[22]非常相似,但在系统背景和系统环境问题上的考虑着有着基本的不同。如前所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基于恢复力理论的框架,在系统面临着什么以及系统的未来这些问题上,预设性的答案和人地系统理论有本质的不同。从环境决定论到可持续发展理论[23],人地关系理论注重人地的矛盾关系并最终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高形式或最终形式[24],属于美好且理想的目标问题,社会—生态系统则关注环境中的干扰因素,认为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应该通过灾难预防和生态管理等方法从干扰和讶异中恢复到稳定。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将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所考虑的系统面临的问题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干扰,一类是讶异。
2.1 干扰
干扰(Perturbation或Disturbance)被认为是社会—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原因,或是系统自身或外在的必须面对的挑战,就目前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来说,系统从一个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变通常由两种方式触动,要么是积累到一定阈值的缓慢的驱动,要么是不连续的冲击[25],因而干扰不仅可以理解为急性的,也可以理解为长期的、缓慢的;干扰也可以分为系统内和系统外,内因是地方的、小尺度的、主要形式为内在的,外因是区域或全国甚至全球、大尺度、外在的[17]。干扰是好是坏?或者干扰后的新系统与原系统相比如何?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生态学家认为干扰促使生态系统按照一套相互加强的结构和过程重新组织[26];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对原住民的干扰,增加冲突、暴力、不平等和贫穷[2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干扰也是新事物产生的、革新或发展的潜在机会,特别是在多样的系统中,甚至小的干扰也会产生戏剧性的社会结果[28]。在社会—生态系统案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系统的状态和什么样的干扰,即什么样的恢复力和对什么的恢复[29],所以干擾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干扰与地理学研究中的驱动有一定的相关,相对来说,地理学驱动(或压力)——状态——响应范式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对应为干扰——恢复——稳定。
2.2 讶异
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迄今为止都难以被理解,讶异(Surprise)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30]。所谓讶异就是意料之外的,如果按社会—生态系统的干扰和恢复力思路,一方面讶异属于干扰,系统要面对,要学习和适应。但另一方面讶异又是比干扰更不可能被观测到和预计到的,或者说已经发生的属于干扰,没有发生的又是意料之外的属于讶异。Holling认为,生态系统的变化性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可预测,但在其他方面总是有诸多意外,这一讶异概念建立在不连续概念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上面[10]。讶异和干扰的这种前后矛盾、内外矛盾无处不在,表现在一些旨在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稳定性或是减少干扰的政策通常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破坏稳定性的结果。例如在Liu的案例研究中[30],为了改变四川武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高质量的熊猫栖息地不断减少的困境,政府严禁当地居民收集竹林作为燃料以保证保护区的竹林资源,并按家庭户给予补偿,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为领到更多的补贴许多家庭就此拆分,当地的社会系统结构又产生了变化并进一步影响熊猫栖息地。因此,一些人为生态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态系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大部分的人类干涉会被系统排除[30],而人类干预导致不可预测的讶异对恢复力和人类社会健康都非常有害。
3 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非常重视过程,近十多年来地理学也相应形成了地理—生态的尺度—格局—过程研究范式[31],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关注系统状态连续和不连续性,并强调相对的稳定和不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系统边界问题,秉承了生态学中生态平衡的研究传统。
3.1 稳定景观吸引盆假设
恢复力联盟将状态(State)定义为构成系统的变量,即状态就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种与环境交互作用产生了功能与结构的一组属性,形成了状态空间(States Space)[18],用于直观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8]。由于状态是不稳定且时刻变化的,稳定只是相对的,Walker提出了“吸引盆地”[32]的假设来描述系统在一系列阈值范围内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组合而成的稳定景观,并且使用体制(Regime)来定义描述这一系列状态有着同样本质的结构和功能的系统配置[32]。
Walker用稳定景观吸引盆[18,19,32]解释系统体制的转移(图1):a、b两个盆地中的小球代表社会—生态系统的阶段状态,这个系统的三维空间体制就是景观盆。虚线分别对应的两个体制的边界状态(即阈值和临界)。小球从图a到b的移动表明系统经历了体制的更替,即系统过程和功能的变化。稳定景观吸引盆底部是系统的平衡状态,小球代表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景观盆中运动,如果系统演变趋于平衡,则小球就不断向底部运动,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这个趋势将一直存在。但是,动力系统的非平衡和平衡是不断交替的,就像小球不会一直在盆底一样,在景观盆的模型中,小球的移动路径受恢复力影响,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状态,在体制下这些状态的系统仍然可以保持原有的结构和功能。当系统超越了移动的界限(红线),驱动整个系统的反馈效应就会发生变化,小球突破现有景观盆限制,恢复力崩溃,系统将会向下一个平衡状态发展,进入另一个盆体,新盆体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
3.2 多稳态
Folke等认为景观吸引盆的假设过于复杂,比较赞同May[33]和Holling[9]采用多稳态(Multiple Stable States)来表征生态动力系统在相同的参数条件下存在不同稳态解的现象[14],即直接关注稳定状态的多样性,省却了体制这一系统配置的环节。多稳态的转换或者跃迁现象如图2所示,以类似吸引盆的剖面作为系统的稳态,当改变剖面的形状,即类似于改变系统的外部条件时,小球表示的社会—生态系统可能会在不同的稳态之间转换[34,35]。同时,系统的稳态转换不仅在于外界条件的改变,还在于外界的随机干扰,外界条件固定时,在随机干扰下小球会发生稳态转换(a随机干扰);另一种情况是当外界条件(系统参数)发生变化时,小球会发生稳态转换(b条件变化)[35]。
3.3 阈值和断裂点
如果社会—生态系统可以有多种稳定状态存在,那当某个系统变化过多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跨越某个范围或边界并呈现不同的行为方式。Folke等人将阈值(Threshold)定义为恢复力作用的范围,如果系统超越恢复力约束或遇到足以改变其结构和功能的条件失去鲁棒性,将导致新的状态的产生[14]。
断裂点(Tipping Point)也是临界的意思,是与阈值对应的、相关的存在,或是稳定系统破坏或进入不稳定的临界状态。直接测量社会经济系统的边界非常困难,唯一确定的方法就只有通过复杂系统的临界状态[20],因而断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在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时候所应具备的条件。
4 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
虽然目前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研究还处于理论阶段,无法实践,但很多思考对人地系统的过程有很好的借鉴。目前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研究主要借鉴复杂系统特别是Holland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36,37]的一些思路。适应的系统非常关注系统和环境的相互反应过程,这种系统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等一系列特点,最重要的是适应性造就了复杂性,恢复力的变化贯穿在整个系统演变过程中。
4.1 适应性循环
适应性循环是早期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变理论,是扰沌模型的基础。本文根据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发展总结了早期版本、简单双环[18,19]和目前的二维和三维适应性循环[12]四类。社会—生态系统在适应环境变化下所产生的变化呈现出双环、有向的、开放的循环,循环阶段主要分为四个:快速发展r、稳定守恒K、释放Ω和重组α。在早期版本中社会—生态系统的属性是资本(Capital)和连续性,目前是二维的潜力(Potential)和连续性以及三维的恢复力、潜力和连续性。
在适应性循环的双环中,r—K的动力演变反映了可预见的、相对较慢的前向回路(Front Loop),Ω—α的动力演变代表了一种混乱且快速的后向回路(Back Loop),这个后向回路对下一个前向回路本质有着强烈影响[14]。这个模型强调适应性循环不是一个绝对和固定的周期,仍然存在很多变异和讶异,系统或组织的管理者们如果能够擅于利用以上现象控制局势的发展,防止系统在稳定守恒后期发生崩溃,也就是通过系统较低尺度上进行释放和重组来避免系统在重要尺度上释放,可以防止保护阶段后期在该尺度上形成[38]。
4.2 扰沌
扰沌是适应性循环的多尺度和跨尺度效应——没有任何系统是处于单一尺度的,多尺度状态和受尺度约束从而产生不同的功能效应是系统非线性动力的来源。考虑多尺度和跨尺度问题,继承生态学的尺度等级性[39],以嵌套结构(Nested)来表达适应性循环在不同尺度上的系统演变过程,Gunderson和Holling给这种嵌套结构的适应性循环一个新的名字——扰沌(Panarchy)[12],如圖3所示。
扰沌的嵌套与传统的层级区别在于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如前所述的在更新的α阶段是每个层次上多样性的引擎和新事物的生产者;第二就是层级之间的连接性,即低层次的相互作用在一定时候会产生高层次的适应性循环。Gunderson和Holling将这些在不同层次之间可能会存在的各种联系归纳为比较关键的是两类:一类是记忆(Remember),另一类是背叛(Revolt),两者方向不同,目标也不一致[12]。
扰沌很快被一些生态学家接受,在扰沌的状态下,系统既高度联系又能自由实验,可以同时实现高效与创新。扰沌模型支撑着演变角度的恢复力,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恢复力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是“已经存在”,而是“正在发生”。并且,恢复力只在系统遭遇干扰时才体现出来,这意味着社会—生态系统会因逆境因子而变得更富有恢复力,而不是去逃离和回避。同样,扰沌模型将恢复力研究带入了一个演变进化的阶段,丰富了工程学和生态学对恢复力的理解,融入了持续性、多样性特别是适应性和转换性在不同时空尺度框架内的动态相互作用[14,32],并将社会系统中的制度、机构、领导、社会记忆、社会资本和社会学习的作用纳入其范畴,为理解社会理论和管理问题、社会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同视角[40]。
5 社会—生态系统的遗产效应
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研究关注系统在面对干扰或讶异前后的状态、过程及可能产生的新旧系统的交替,认为任何系统都存在积累,这种积累就是时间和历史,重视系统的积累和相应的遗产效应研究,了解创新和保守的来源以及历史和时间带来的时滞问题,可以使系统分析更加透彻。因此,在系统积累基础上的遗产效应研究实质就是对社会—生态系统状态、演变过程的总结,是时间维度的延长和空间尺度的进一步扩大。
5.1 系统的积累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秉承生态学对生物遗产的重视,认为系统存在遗产效应(Legacy Effect),就是系统的历史积累而产生的效果或反映,或者可以说是新系统对旧系统的继承。在扰沌结构的四个阶段循环中,从r到k阶段利用上个循环残留遗产作为系统连续性增长的来源和养分,从Ω释放阶段到α重组阶段则是为下个循环不断积累系统遗产,在小尺度到大尺度的不同等级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如此循环累积,即遗产效应。因此遗产效应不一定只是上一系统的残留,而是整个历史的反映;也是上一系统的残留,因为上一系统也是秉承至上系统的遗产。另外,系统的历史累积是生产多样性和新奇性的土壤,也是系统刚性破灭后连续性降低和脆弱性的来源,或者说既是系统生也是系统死的条件,为系统运行带来很多挑战和意想不到的讶异,使得系统每个层次上的结构和进程都有可能被重组,从而可能导致新的系统配置、合并新事物的机会、甚至是新的进入者,而这些都是早期阶段就已经累积潜在的。
遗产效应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系统的现在和未来。在遗产效应和恢复力的关系上,Adger等认为灾难过后前系统的残留变成新系统的生长点,依据假设的方法可以依次推导恢复力[41],除了这种灾难的假设方法,还重视社会—生态系统中长期累积过程,即重视遗产效应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使得恢复力理论不仅适用于短期灾难,也适合长期现象[42]。
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新进入者就是新的物种或等待条件成为新物种的物种;对于经济系统来说,就是新的发明、创造性的理念以及创新型人才。适应性循环在这一点上也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突变、入侵、发明和创新这些是能够积累的。也即是遗产效应其实不仅仅在于过去的历史累积,还有基于这些累积而产生的现阶段看得到的机会,如何利用,则是创新和保守的问题。
5.2 创新与保守
在具有遗产效应的扰沌结构中,适应性循环既是创新的,可以不断适应变化,也是保守的,保存了自身,即低层次上的适应性循环(小和快)可看作是高层次(大而慢)的某种试验[12],在这种实验中,创新和保守不断博弈。系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主要来源于创新,需要对创新加以重视。系统的创新和保守则无处不在,作为系统刚性的残留,保守一方面阻碍创新,一方面也促进创新。就生态系统来说,上一阶段残留的养分或物质有可能促进某种物种生长,也会抑制其他物种生长;就社会系统来说,经验和记忆是好事,也是坏事;对于制度来说,可操作的规则、集体选择规则以及组织规则三个层次都存在保守和创新;对于经济系统来说,个人选择、市场和社会制度无不在新旧之间博弈和循环;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基础设施以及治理、分配机制、规范等也如此。
扰沌中有三类创新:1)背景创新(Background)产生于边缘地带,不同层次的适应性环之间。显然扰沌并不是完全包含型的等级,所以高等级并非完全由低等级组成,即系统开放性的一个反映。2)增量创新(Incremental)发生在r和k阶段,即前向回路阶段,随着系统的成长而逐渐增加复杂性,也有可能会增加新层次的适应性循环。3)间断创新(Punctuated)发生在适应性环的Ω释放阶段,即创造性毁灭[7,12]。
5.3 时滞
干扰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冲击并不能马上体现和被观测,也不能被预测,这是因为时滞(Time Lags)问题存在,时滞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生态社会结果的外显[30]。时滞问题同样也比较复杂,产生时滞的一个原因可能会表现为多种指示因子,例如价格因素会影响来年农民会选择种植或不种植何种农作物,且该种和不种的经济效果也不能马上显现。反之,一个指示因子也会因为时滞的不同时间段而表现出不同的原因。例如在Liu的四川武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居民用电的价格变化会影响当地人使用竹林作为薪材收集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熊猫的栖息地,产生快速的时滞问题。但居民家庭出生人口作对当地人的薪材收集行为的影响却很缓慢,产生缓慢的时滞问题[30]。由于时滞问题的存在,加剧了尺度的时空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叠加在一起,在具体研究的时候根本分不清具体的尺度问题所在。
6 对地理学的启示
与所有复杂系统一样,人地关系是一个整体、开放的系统,可持续发展是融合了人类价值的美好目标追求,并不是人类本能为之不安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是人地系统所要面临的问题,更不是人地矛盾中所能体现的研究目标。基于系统存在恢复力的假设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对我国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系统这一复杂系统在应对压力和张力时的变化、适应以及如何实现至关重要的转换能力[20]、探索如何保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条件下管理能忍受的变量和经受干扰并学习[18]、从而提高系统自组织的能力和建立并增加适应干扰的能力等方面都有一些启示。
6.1 对人地系统研究的启示
在一些新型人地关系理论中,协调或协调共生,危机冲突与错误异化[24]代表了地理学家在统一和对立两个方向的思考。另外,地理学长期以来有对人地关系脆弱性和矛盾性的研究传统,表明人地关系研究中也重视逆境因子和环境压力、张力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评价就是考虑环境的顺境因子,恢复力则是逆境因子,干扰和讶异两类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和不确定性未来本身就是中性的概念,可能包括顺境因子和逆境因子,也有系统内和系统外、现在和未来等各种要素。目前人地关系研究中压力—状态—响应的范式有與社会—生态系统类似的研究思路,但仍需继续深入和细化,并关注恢复力在系统状态变化时的重要指示作用,借鉴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强调学习管理变化的必要性[43],将对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设想转变为诸如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主要政治变革和动乱的所谓干扰和讶异事件,关注在这些事件中系统可能经历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并进入后反馈或新系统阶段,这是更具多样性、挑战性和无结构的环境[44],据此实施应对,使系统恢复稳定。
在人地系统状态方面,地理学在借鉴生态学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相关研究后虽然形成了格局—过程的研究范式,但对人地系统状态的关注还较为片面,特别是状态的连续性、变化性、关键状态和状态变化的范围和边界等问题还不够深入。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稳定状态是系统在相对条件下的稳定,动力学意义上这种系统的稳态也被称为吸引子(Attractor)[45],吸引子目前是混沌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和假设,吸引子和排斥子也被归纳为源和汇的问题,排斥则为源、吸引子为汇[46]。数学家和跨界的生态学家[33]通过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证实了系统存在多个的吸引子,生态系统的多种稳定状态以及多稳态的更替和对于系统的不同结构和功能使得生态服务的价值各不相同[34],吸引着生态学家们朝着这一方面转向,对复杂系统的关注和系统思考使得生态学在近十年来不知不觉在综合研究方面逐渐超越了地理学,而擅长综合研究的地理学如果一直处于时空尺度断面下的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对微观社会空间的追逐,最终将惊叹生态学的进步并只能跟随。
在人地系统的尺度、结构和演变方面,地理学较为缺乏对人地系统结构和演变过程的模型化和哲学思考,对地域差异性形成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异质性的关注和片面、破碎化的研究使得尺度演绎一直是一个难题。尺度在扰沌模型中随着适应性循环的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得到了充分体现,Ostrom也认为,为什么一些社会—生态系统是可持续的而另一些是崩溃的,需要重视的是不同时空尺度问题,以及尺度问题下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47],因此尺度也是变量。人地系统也是如此,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交通网络基础上的物联网发展,地理空间在人地系统中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地理学尺度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
最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遗产效应以及相应系统循环和积累过程导致的系统中创新和保守和时滞等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是人地系统研究较为缺乏的,在人地关系系统中重视人地关系循环的规律发现和历史积累的剖析,认识时间对尺度—格局—过程研究范式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演变过程的理解,也在于遗产效应及相关的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和统一、时滞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表现等问题。
6.2 中国地理学的优势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实质就是相对的稳定和不稳定以及与两种状态转变相关的系统边界或临界问题,由此形成的系统结构、演变和尺度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历史积累,实际上人地关系研究中除了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个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存在并被认为是人地关系的最高形式[23-24]。“天人合一”一方面是人和地的时空耦合[3],这种耦合可理解为与相对稳定状态差不多的概念,地理学相关的研究较为多见,可以结合相对不稳定状态以及系统边界和临界问题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人地系统的状态持续问题。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地系统和周易的暗合[48],一些地理学家也在此领域有一些探索[2,49],这是更高层次的哲学思考,易经用卦的象、数、理、变、通所展示的天地人三才演變规律对目前陷入困境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型例如扰沌在解决思路上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
人地系统中要探索结构和演变,还有赖于对关系的研究,这也是地理学的优良基因。人地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人地之间两者,还有人地系统中的人的社会关系、地的自然关系、人地复合系统之间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第一层次是一维的人—人、地—地、人—地关系。尺度问题贯穿其中,系统异常复杂,三者关系也并非简单两两关系,还有三者共同作用的关系,即第二层次是二维的三者的两两关系,第三层次是三维的三者关系即三体问题,三体问题是至今为止科学还没有解决。当然,当前地理学的核心还是要解决第一层次的一维人地关系,还没有能力去拓展二维和三维,但上述所说一、二、三维对人地关系的影响则无处不在,大量的非线性是开放系统的特征。这种复杂的关系相互作用,使得整体不再是简单地全部等于部分之和,而可能出现不同于线性叠加的增益或亏损。扰沌的模型已然也承认大量非线性的存在,人地关系也应如此。目前的大数据研究力图以海量数据为基础、计算机统计和推演为手段,但计算机本身也存在设计和规则上的缺陷,可以解决一部分非线性问题,解决不了三维时空的大部分非线性问题。相对来说,传统的易学和中国古代地理学考虑则要多得多,向传统地理堪舆文化学习,理解易经中的八卦和道德经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时空维度变化规律,学习先秦及其以前智慧,是否也是当代地理学应该开始的转向。
6.3 复杂科学的一席之地
社会—生态系统和人地系统都是复杂系统,复杂系统这一概念常常和适应性联系起来,恢复力并非简单的恢复,也不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反的崩溃论,社会—生态系统也不是局限在整体和局部关系的系统研究,大量的对系统的相对稳定和不稳定状态的关注、非线性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过程等研究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已进入复杂科学阶段。
在钱学森指导下创立的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地理学是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地理科学共同构成了客体世界,使得地理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其综合性[50],即意味着地理学是最应该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更是应该在复杂科学大潮中取得一席之地,且更应是重要席位或领头羊的科学。一些秉承钱学森思想的重量级地理学者已经明确指出目前地理学危机和机遇并存的现实情况[50-51],并着手开始思考和进行顶层设计[51],他们是西方地理学危机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地理学危机的化解人,更是现代地理科学发展的前瞻者和先行者,在他们近期的著作中[51-52]不难看出对《易经》和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作用,而人地关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无疑是对人地关系的最佳研究切入点。
7 总结和展望
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人地系统还是任何一种复杂系统,所面临的都是不确定性的问题。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干扰和讶异,并以干扰带来的系统变化为核心,从相对稳定到不稳定、系统的边界和范围以及系统临界状态等问题出发,在时间这一维度上从小尺度到大尺度、短时间到长时间来研究系统的变化,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演变——遗产效应的逻辑思路,得到了相关研究成果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从这个方面来说似乎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具备了一种未来主义的维度,这也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自组织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14]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对地理学研究人地系统——这个地球上最高的系统[50]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原因。综前所述,本文总结如下:
1)参考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可见,可持续发展不是人地系统的现阶段和最高形式,人地系统面临的问题是不确定的,天人合一可能更适合描述人地系统的状态和演变过程。
2)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现了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和因此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演变—遗产效应的逻辑思路,对人地关系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有借鉴意义。
3)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对于复杂科学的贡献使得地理学面临的压力不小,作为擅长综合研究、以桥梁科学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地理学,在将人地系统作为复杂系统研究上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国外“已经有成为新流行语趋势危险”[14]的恢复力概念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在中国没有得到像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样的拥簇,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这也表明恢复力这种预计式的研究很难被证实,使得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关大部分研究均主要为假设或理论构建,目前全球的复杂系统研究也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奋起直追是可以的。并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开启,不确定问题的量化和使用更复杂的预测技术将会使得复杂系统的行为可能有93%被预测,但也表明迄今为止不确定问题还是现代科学始终无法解决的,要突破局面和引领复杂科学,中国易经、道德经和传统地理文化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Solow R M.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A]. //Robert N 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C]. 5th Ed.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2005:170-187.
[2] 周晓芳. 基于易经阴阳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模型[J]. 地理研究,2015,34(2):225-233.
[3] 牛文元. 理论地理学的内涵认知[J]. 地理研究,1988,7(1):8-9.
[4] Folke C, Carpenter S, Elmqvist T, et al.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adaptive capacity in a World of transformations[J]. AMBIO,2002,31(5):437-440.
[5] Lin B B. Resilience, regime shifts, and guided transi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Examin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managing continually changing systems[J]. Ecology & Society,2013,18(1):103-111.
[6] 葛怡,史培軍,徐伟,等. 恢复力研究的新进展与评述[J]. 灾害学,2010,25(3):119-129.
[7] Fol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16(3):253-267.
[8] 孙晶,王俊,杨新军.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综述[J]. 生态学报,2007(12):5371-5381.
[9]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4):1-23.
[10] Holling C S. Engineering resilience versus ecological resilience[M]// GundersonL H, AllenC R, and HollingC S.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resilienc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06:51-66.
[11] Holling C S, Meffe G K.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J].Conservation Biology,1996,10(2):328-337.
[12]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02.
[13] Holling C S. The Resilienc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M]// Clark C, Munn 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osphe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92-317.
[14] Folke C, Carpenter S R, and Walker B,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J]. Ecology & Society,2010,15(4):299-305.
[15] Adger W N.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24):347-364.
[16] 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 Cambridge Journal of the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10,3(1):27-43.
[17] Gumming G S, Barnes G, Perz S, et al. 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resilience: Surrogates for resilie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systems,2005,8(8):975-987.
[18] The Resilience Alliance. Research o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 basis for sustainability [EB/OL]. http://www.resilience.org,2005-10-2.
[19] The Resilience Alliance. Key concepts [EB/OL]. http://www.resalliance.org,2012-11-6.
[20] Carpenter S R, Westley F, Turner M G. Surrogates for Resilie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J]. Ecosystems,2005,8(8):941-944.
[21] 西亞姆巴巴拉·伯纳德·曼耶纳,张益章, 刘海龙.韧性概念的重新审视[J]. 国际城市规划,2015,30(2):13-21.
[22] 陆大道,郭来喜. 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 地理学报,1998,53(2):97-105.
[23] 王爱民,缪磊磊. 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评述[J]. 地球科学进展,2000,15(4):415-420.
[24] 方创琳. 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与展望[J]. 地理学报,2004,59(S):21-32.
[25] Bennett E M, Cumming G S, Peterson G D. A Systems model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resilience surrogates for case studies[J]. Ecosystems,2005,8(8):945-957.
[26] Scheffer M, Carpenter S , Foley J A, et al. Catastrophic shifts in ecosystems[J]. Nature,2001,413(6856):591-596.
[27] Peterson G. Political ecology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 integration of human and ecological dynamic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0,35(3):323-336.
[28] Adger W N. Vulnerabil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16(3):268-281.
[29] Carpenter S R, Walker B, Anderies J M, et al. From metaphor to measurement: Resilience of what to what?[J]. Ecosystems,2001,4(8):765-781.
[30] Liu J G, Dietz T, Carpenter S R, et al. Complexity of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J]. Science, 2007,317(5844):1513-1516.
[31] 傅伯杰,赵文武,陈利顶.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地理学报,2006,61(11):1123-1131.
[32] Walker B H,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 Society,2004,9(2):3438-3447.
[33] May R M. Thresholds and breakpoints in ecosystems with a multiplicity of stable states[J]. Nature,1977,269:471-477.
[34] Scheffer M, Carpenter S R. Catastrophic regime shifts in ecosystems: linking theory to observation[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2003,18(12):648-656.
[35] Beisner B E, Haydon D T, Cuddington K. Alternative stable states in Ecology[J]. Frontiers in Ecology & the Environment,2003,1(7):376-382.
[36] Holland J H. 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M]. New York: Perseus Books Group,1999.
[37] Holland J H.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M]. New York: Perseus Books Group,1995.
[38] Walker B, Salt D.Resilience Thinking: sustaining ecosystems and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M]. CSIRO, Australian,2006.
[39] 邬建国.景观生态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0] Westley F. The devil in the dynamics: adaptive management on the front lines[M]//Gunderson LH, 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2002:333-360.
[41] Adger W N, Rockstrm J.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coastal disasters[J]. Science, 2005, 309(5737):1036-1039.
[42] Rose A. Economic resilience to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Multidisciplinary origins and contextual dimensions[J]. Environmental Hazards,2007,7(4):383-398.
[43] Robert W K, William C C. Environmental surprise: Expecting the unexpected?[J]. Environment Science &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6,38(2):6-34.
[44] Moore M L, Westley F. Surmountable chasms: Networks and social innovation for resilient systems [J]. Ecology & Society,2011,16(1):365-366.
[45] Ives A R, Carpenter S R. Stability and diversity of ecosystems[J]. Science,2007,317(5834):58-62.
[46] 赵庆建, 温作民. 社会生态系统及其恢复力研究——基于复杂性理论的视角[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3(04):82-89.
[47]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2009, 325(5939):419-422.
[48] 孙峰华.基于易学与堪舆学的人地关系和谐论思辨[J]. 地理學报,2012,67(2):266-282.
[49] 马蔼乃.理论地理科学与哲学——复杂性科学理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0] 陆大道. 地理科学的价值与地理学者的情怀[J]. 地理学报,2015,70(10):1539-1551.
[51] 蔡运龙,陈彦光,阙为民,等. 地理学: 科学地位与社会功能[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52] 唐晓峰. 从混沌到秩序[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Abstract: Recently, Resilience has become a popular concept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has been replacing the topic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theory and its research step into the complex socio-ecosystem stage which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complex science. Then considers the problems faced by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re as perturbation and astonishment,discusses the relative stable and unstable states, boundary or tipping point problems and so on, describes the modeling of these continuous and discontinuous states and evolution processes, ie, Adaptive Cycle and the Pnarchy structure, pays attention to the system in the time dimension of the heritage effect corresponding innovation and conservative generation, as well as Time Lags.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silience an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tudies have three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geography: 1) The problem faced by the system is uncertain,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more suitable to describe the state and evolution of man-land system. 2)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state, evolution and heritage effect formed by the social ecological research with the time dimension as the core can inspire the expansion of time dimension in the stud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3) as a good 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geography in the man-land system as a complex system to study the direction of the road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ut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o Chinese geography is somewhere in the direction to follow.
Key words: resilience;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geography in China; rev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