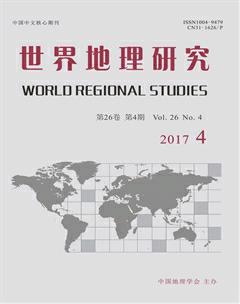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王疆 江娟
摘 要: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美国;母国集聚;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自21世纪初我国施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总额有了较大的提升,并且,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也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也日益关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1-6]。一方面,我国进一步扩大了对新兴国家的投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我国也开始尝试着将对外投资的目光慢慢转向美国等发达国家。《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额又一次实现了跳跃式的增长,高达1231.2亿美元,且在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中,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投资目的地。由此可见,研究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集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余珮等[7]以2007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在华投资的欧洲和美国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Lee和Hwang[8]则对韩国1771个FDI制造业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集聚效应(包括水平集聚和垂直集聚)对韩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Du和Lu等运用McFadden(麦克法登)的条件logit模型对1993年~2001年间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在中国进行投资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集聚效应对各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集聚之所以会对FDI区位选择有影响是因为:第一,FDI的集聚会产生知识和技术外溢作用[9],这种知识和技术的外溢通常会给周边企業带来裨益;第二,FDI的集聚区往往聚集着该领域的高质量人才,并逐渐形成了该区域所特有的稳定的人才市场,从而能够吸引后续更多FDI的流入[10]。第三,FDI的集聚区通常有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企业能够通过整合上下游供应链来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收益[11],这对外来投资者而言,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马歇尔用“地方性工业”来描述产业集聚,他指出,产业集聚主要来源于自然禀赋和宫廷的奖励[10]。韦伯则认为,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降低带来的生产活动的廉价,而集聚区的形成不仅可以节省生产成本,还会降低相应的交易与运输成本[12]。前人对集聚与FDI区位选择的研究大多是立足于产业集聚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不过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母国集聚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13-15]。来自同一国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的外溢与后进企业期望获取的知识与信息具有较高的匹配程度,这使得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更倾向于跟随母国的成功企业。
前人对于中国的类似研究大多集中于集聚效应对外商在中国进行投资决策的影响[16-22],很少有学者研究集聚效应对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的影响[23],本文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产业集聚效应和母国集聚效应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这将在一国内部区域层次上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2001年~2014年中国783起在美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探究。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除了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研发强度等一系列重要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和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产业集聚效应与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Li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跨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本土知识有着很强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者更是如此[24,25]。通常情况下,企业要想获得本土化知识,可以选择在东道国的产业集聚区进行投资,并与当地企业进行互动和进行水平与垂直学习[26-28]。由此可见,来自东道国本土的产业集聚区对外来投资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作用。当地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往往有着越明显的知识外溢作用,同时,当地产业的集聚还会吸引大量高质量的人才,人才的流动进一步加强了知识在当地的溢出效应[29]。此外,产业集聚水平比较高的区域还会进一步吸引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的集聚[19],一方面,这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外溢,完善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另一方面,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似的需求也使得规模效应成为可能,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30,31]。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在东道国的产业集聚区进行投资来直接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模式,与此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充分利用集聚区的劳动力资源与基础设施等来提高生产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当地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美国某特定州某行业的集聚程度越大,中国该行业选择在该州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1.2 母国集聚效应与OFDI区位选择
企业在跨国投资时,由于地理距离以及对东道国的商业环境不熟悉等因素,往往受困于外来者劣势,知识的直接获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32],而通过学习和积累海外投资经验却能大大提高成功投资的概率[33]。然而,依靠跨国公司亲身经历去获得经验知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况且,以前在国内积累的国际化经验往往很难在新的环境下照搬和移植[34],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参照以往成功企业的投资案例,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知识是一个好的选择[23]。地理的邻近能够产生积极的知识技术外溢效应[35],因而,企业在目标国进行相应的投资时,可以选择邻近其他企业进行投资,这样便于观察和学习其他企业的经验,进行替代性学习[36]。
先前进入的本国企业是很好的学习对象。来自相同国家的企业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特性、种族联系和相似的社会网络[14],相近的成长环境使得来自同一国家的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相似性。先前进入东道国的本国企业对当地的商业环境会比较熟悉,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后进企业通过学习母国企业的成功投资经验能够大大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37],更加快速地融入新的市场。并且,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跟随本国企业进入相同的投资区,可以加大企业投资的合法性[33],从而提高企业成功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母国所有企业集聚的影响,上一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会正向影响后续企业对该州进行相应投资的可能性。
并且,企业在选择跟随哪些母国企业进行投资时,行业类型的差异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相似的行业所需获取的信息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比较关注同类行业的行为[6]。竞争反应理论表明,由于国际的相互投资会对投资国和整个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环境产生不可避免的影響,企业会倾向于留意同行业企业的行为决策,并且为了减小竞争压力,确保市场竞争地位,企业倾向于追随先进入企业的投资选择[38]。由此可见,相比较于母国其他行业企业,来自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的后续投资行为有着更强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受到母国同行业企业集聚的影响,上一年中国某行业企业对美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会正向影响该行业后续企业对该州进行相应投资的可能性。
假设3b: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受母国其他行业企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上一年中国其他行业企业对美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会正向影响后续企业对该州进行相应投资的可能性。
假设3c:母国同行业企业已有投资行为对后续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区位决策的影响要大于母国其他行业企业已有投资行为的影响。
2 研究区数据来源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了2001年到2014年间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总共包含了2001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783起中国企业在美国51个州的相关投资事件。2001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只有21起,而2014年达到161起,增加了近七倍。图1展示了2001年~2014年间中国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事件的增长趋势,可见近年来,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而这些投资在美国各州各行业的分布亦有所不同。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较少,相应地,能吸引中国投资的州也屈指可数,中国仅在美国的7个州有少量投资,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投资事件相对较多(图2a)。
2014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遍布美国的27个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投资事件相对较多(图2b)。由2001年~2014年的投资区位可以看出,最初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的投资大多比较分散,主要集中于西部、南部、东部等沿海城市,随后,东部的投资企业逐年增多。并且,投资趋势展现由沿海到内陆的扩张趋势。
在投资行业方面,如图3所示,中国近些年来投资热点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与酒店行业,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行业,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行业,以及能源行业。
2.2 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是每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特定州的投资次数,数据来源是Rhodium Group的中国投资观察(China Investment Monitor)数据库。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母国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同时本文进一步将母国集聚效应分为所有企业集聚、同行业集聚和其他行业集聚。本文用某州前一年中国所有企业对美国投资次数来衡量母国所有企业的集聚效应。投资次数愈多,表明母国企业的集聚程度愈高;用某州前一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某特定行业的投资次数来衡量母国同行业集聚效应。投资次数愈多,表明母国同行业集聚程度愈高。用某州前一年其他行业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次数来衡量母国其他行业集聚效应。投资次数愈多,表明母国其他行业集聚程度愈高。母国集聚变量的数据同样采自于中国投资观察数据库。
本文用东道国各州某行业的区位熵来表示该州行业的集聚水平。具体而言,就是美国一州某特定行业的总产值占该州所有行业总产值的比例除以美国该行业总产值占全国所有行业总产值的比例。数值大于1,就表示该行业的集聚水平相对较高;数值小于1,就表示集聚水平相对较低。数据由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整理而得。
此外,文章根据已有文献对中国在美国区位决策的研究,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市场吸引力:用GDP增长率来衡量,数据采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劳动力市场状况:用失业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劳动力质量:用本科生在劳动力中的占比来衡量,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研发强度:用GDP中研究开发费用支出的占比来表示,数据采自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人均税负:用每年各州税收收入除以人口数量来衡量,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由于企业进入一个新市场进行投资决策主要是受到该市场前期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时间的延滞,本文对所有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采取滞后一期值。
2.3 模型方法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特定行业企业在美国某特定州的投资起数,根据研究样本为非负整数的特点,本文选择了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以往此类数据的研究常使用泊松回归和负二项这两大类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但泊松回归的一大假设便是计数变量的方差和均值是相等的。因而,如果出现了方差和均值不相等,且方差明显大于均值时,就会出现过度分散的情况。而负二项回归作为广义的泊松回归,允许过度分散的存在,因而该模型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更加适宜。
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负二项回归结果
表1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由相关性系数表可知,母国所有企业的集聚与母国其他企业的集聚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3,因此下文中,我们将母国所有企业和母国其他企业两大变量分开做回归研究,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给出了负二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假设1指出中国企业对美国进行相应投资的区位决策受到东道国产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模型1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东道国某特定州特定行业的集聚程度越大,中国该行业对该州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设1成立。假设2指出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会受到母国所有企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模型2检验了这一假设,实证表明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受到母国所有企业集聚的影响,上一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某一特定州的投资次数愈多,后续企业对该州进行相应投资的可能也就相应地愈大。因此,假设2成立。假设3a指出上一年中国某行业对东道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会正向影响后续同类行业对该州进行投资的可能性。模型3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显示往年母国同行业的投资次数越多,后续该行业继续在该州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设3a成立。假设3b指出中国企业对美国某特定行业投资的区位决策受到母国其他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模型4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上一年中国其他行业对东道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越多,后续该行业对该州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设3b成立。假设3c指出来自母国同行业的集聚与来自母国其他行业集聚相比,前者对后续FDI区位决策的作用更大,模型5将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同时纳入回归分析中,证明了母国集聚对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再次验证了假设3a和假设3b,同时Wald 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母国同行业集聚的影响要大于母国其他行业集聚。因此,假设3c成立。模型6将母国集聚效应与当地产业集聚效应这两大变量同时纳入回归分析中,验证了两类集聚对中国在美国FDI区位选择的积极影响作用。
3.2 稳健性检验
产业集聚是研究的核心变量,使用区位熵进行表征。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除了采用行业总产值来之外,还采用了就业人口来计算区位熵。如表4所示,主要变量的结果都与表3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3 结果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母国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都是决定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首先,产业集聚效应是促使中国企业在美国某特定州进行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行业集聚带来的知识外溢使得投资国能更直接、更高效地学习发达国家相应产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总而言之,地理的邻近为新进企业学习经验知识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其次,母国集聚是吸引中国企业后续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往往倾向于母国有投资经验的地区,这样可以降低搜索市场信息的成本,减少外者劣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风险,使得企业对新进市场的适应能力大大加强。无论是来自母国同行业的投资经验还是来自母国其他行业的投资经验,都对中国企业进入新市场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4 结论
本文以2001年~2014年中国783起在美投资的区位选择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母国集聚和东道国产业集聚的影响,得出了如下结论:(1)中國企业对美投资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产业集聚的影响,美国某特定州某行业的投资越多,中国该行业对该州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的行业集聚区往往有着很大的技术外溢效应,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2)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受母国所有企业集聚的影响,上一年中国对东道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越多,后续企业对该州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也就相应的越大。这说明前人的投资行为对后续中国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进入本国以往投资的区域进行投资会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也是企业在异国他乡获得合法性的便捷渠道。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对美国进行投资时仍然受限于不确定性和合法性较低的困扰,美国的市场还未真正打开,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同时,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母国先前投资区域的行为说明,中国目前的投资阶段主要是处于学习模仿阶段。(3)中国企业对美国某特定行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受母国同行业集聚的影响,上一年中国某行业对东道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越多,后续同类行业对该州进行相应投资的可能性也就相应的越大。一方面是行业的相似性使得新进入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前人成功投资的经验会吸引更多类似行业的进入。数据统计发现,中国近些年来在美国投资的热门行业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与酒店行业,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行业,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行业以及能源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是近些年来发展态势较好的行业,有些更是新兴产业,在目前这些成功投资事件的吸引下,上述产业在未来的投资中很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4)中国企业对美国某特定行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受母国其他行业集聚的影响,上一年中国其他行业对东道国某特定州的投资次数越多,后续该行业对该州进行相应投资的可能性也相应越大。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从行业的角度研究了母国同行业集聚、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东道国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其次,本文关注于中国企业在一国内部投资的区位决策,在更细致的层面上研究了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问题。
除此之外,本文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的产业集聚区进行投资,同时也倾向于在母国企业的集聚地进行投资。这既反映了中国企业投资中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也指示着中国企业应该好好利用由成功投资企业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向母国企业和东道国同行业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打好基础。同时,我们可以根据近些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各行业的情况来把握中国某类行业在美国投资的发展趋势,很显然,房地产与酒店行业、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行业、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行业,以及能源行业仍将是未来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主要部分。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中国企业真正打开美国市场带来了福音,中国需要尽快走出模仿学习的初步投资阶段,中国企业应当提高创新能力,更多地投资一些新兴产业,这既是趋势,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參考文献:
[1] Shao Y, Shang Y. Decisions of OFDI engagement and location for heterogeneous multinational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6,112:178-187.
[2] Lu J, Liu X, Wright M, et a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me country government support and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45(4):428-449.
[3] 贺灿飞,郭琪,邹沛思.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 世界地理研究,2013(04):1-12.
[4] Duanmu J-L.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64-72.
[5] Lin 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fi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rporate ownership, strategic motives and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5,34:274-292.
[6] 王疆. 组织间模仿、环境不确定性与区位选择:以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为例[J]. 管理学报,2014,(12):1775-1781.
[7] 余珮,孙永平. 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01):71-82.
[8] LEE K, HWANG 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FDI in Korea via agglomeration and linkag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14,19(3):464-487.
[9] Nachum 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location of MNEs: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FDI to the U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0,31(3):367-385.
[10]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London:Macmillan,1920.
[11] 郭建万,陶锋. 集聚经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2009(04):29-37.
[12] Friedrich C J. Alfred Weber's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
[13] Tan D, Meyer K E. Country-of-origin and industry FDI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an emerging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1,42(4):504-520.
[14] HE C. Loc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rs in China: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country of origin effect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3,82(3):351-372.
[15] Nunnenkamp P, Mukim M. The clustering of FDI in India: The importance of peer effects[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11,19(8):749-753.
[16] 梁琦.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J]. 世界经济,2003(09):29-37.
[17] BATHELT H, LI P. Global cluster networks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from Canada to China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4,14(1):45-71.
[18] Tokunaga S, Jin S. Market potential, agglomeration and location of Japanese manufacturers in China[J]. Letters in Spatial and Resource Sciences,2011,4(1):9-19.
[19] Du J, Lu Y, Tao Z. FDI location choice: Agglomeration vs institu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2008,13(1):92-107.
[20] 张会清,王剑. 企业规模、市场能力与FDI地区聚集—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1(01):82-91.
[21] 王宏. 集聚效应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2(03):115-124.
[22] 颜银根. FDI区位选择: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J]. 财贸经济,2014,(09):103-113.
[23] 潘镇.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和选址决策[J]. 改革,2015,(01):140-150.
[24] Meyer K E, Wright M, Pruthi S. Managing knowledge in foreign entry strategies: A resource-based analysi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5):557-574.
[25] Anand J, Delios A. Absolute and relative resources as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2):119-134.
[26] LI P. Horizontal versus vertical learning: Divergenc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ead firms in the Hangji toothbrush Ccluster, China[J]. Regional Studies,2014,48(7):1227-1241.
[27] Bathelt H. Buzz-and-pipeline dynamics: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multiplier model of clusters[J]. Geography Compass,2007,1(6):1282-1298.
[28] Malmberg A, Maskell P. Localized learning revisited[J]. Growth and Change,2006,37(1):1-18.
[29] Stone T. Business networks in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view)[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3,92(2):438-440.
[30]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9(3):483-499.
[31]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6): 77-90.
[32] 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2):341-363.
[33] 王疆,何强,陈俊甫. 种群密度与跨国公司区位选择:行为惯性的调节作用[J]. 国际贸易问题,2015,(12):122-132.
[34] Barkema H G, Shenkar O, Vermeulen F, et al. Working abroad, working with others: How firms learn to operate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40(2):426-442.
[35] Audretsch D B, Feldman M P. 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3):630-640.
[36] Baum J A C, Li S X, Usher J M. Making the next move: How experiential and vicarious learning shape the locations of chains' acquisitio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4):766-801.
[37] 王疆, 陳俊甫. 移民网络、组织间模仿与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当代财经,2014,(11):69-78.
[38] Gimeno J, Hoskisson R E, Beal B D, et al. Explaining the clustering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moves: A critical test in the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2):297-319.
Abstract: Employing the micro data on China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1 to 2014,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ountry-of-origin agglomeration and loc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of-origin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the same industr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inas previous investments of the industry in a particular state. Also,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arger the local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a specific state,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that Chinas enterprises invest in that state.
Key words: FDI; the U.S; country-of-origin agglomeration; loc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