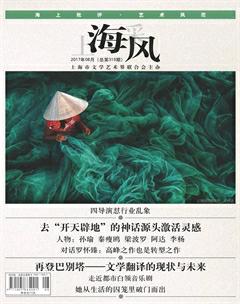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陆寿钧
谢晋的经典影片之一《舞台姐妹》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经典台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这部影片剧本的执笔者王林谷,是我们上影的一位老同志,1946年,他27岁时就进入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任制片主任、艺委会秘书,参与了经典影片《乌鸦与麻雀》剧本的创作。建国后,历任上海市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天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副厂长等职。我却很少听到人家叫他“主任”(厂长),大多数人都亲热地叫他“老王”,他也乐意大家叫他“老王”。
虽然我于1963年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但我与老王在“文革”前与“文革”中的十余年中从未有过接触。“文革”前,我们不仅在两个不同的部门工作,而且在辈分、资历、职务上,都有很大差距,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也从未想到要去接近他。“文革”中,他被打翻在地,一直关在“牛棚”,我也经历了“烙饼”般的翻来覆去,更没有机会和必要接触。与老王相识是在“文革”后,他出任了上影文学部的副主任,我刚被正式调入文学部当编辑,由于多种原因,难被任何人善待,更难说看好,纯属“小三子”,日子很不好过。一次,老王要去四川开拓稿源,需带两个助手,一个选中了巴金先生的女婿祝鸿生,那是理所当然的,巴老是四川人,祝鸿生去会有好多关系可以便于开展工作。另一个,老王却选了我,那是让我至今都不能理解的。以后熟了,我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此行,让上影在四川的组稿中打开了局面,以后几年,祝鸿生和我,在四川为上影组成了不少好剧本,扶植成了不少中青年作者。我心中十分明白,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功在老王,而且他还有恩于我。在我做出成绩后,他却没有在任何场合标榜过自己曾是我的“伯乐”。以后,老王升任文学部主任、文学副厂长,当上了局级干部(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属局级事业单位),但在我的心目中,他还是原来的那个老王。有一次我去三角街老民居他的住处讨论剧本,不巧撞见他正在痰盂上大解,彼此都很尴尬。此时我才知道,他家至此都还未有卫生设备,与当时的上海底层市民过着一样的生活。
老王离休前,再次入川,带我去重庆开拓稿源。在此行中我才知道,他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贫困人家,11岁起就到上海工厂、商行当学徒、练习生。抗战爆发后,他随商行西迁重庆,开始业余创作,发表了不少鼓励抗日斗志的散文和小说,加入了中国艺术剧社,开始从艺。他在重庆度过了八年,这段时间奠定了他的人生之路,是他一生所难忘的。我们在重庆组稿的间隙中,他带我去看他当时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常会呆视良久。我们住在党校的招待所里,傍晚散步时,他常会向我谈些上影老人们的事,说到曾两度主演过他所编剧本《乌鸦与麻雀》和《舞台姐妹》的上官云珠的一生时,感叹万分。我提议他退下来后可为上官云珠写部传记,他却愿意为我提供素材,让我来写。结果达成了一起合作、由我执笔的约定,于是就有了《上官云珠生死录》这本书,也算我协助他完成了一个心愿。
他离休后,我常去看他。后来,我当了文学部的领导,仍常去看他,没少吃过师母汪老师烧的可口的上海家常菜。在老王的心目中,我还仍然是以前的“大陆”。我们一起谈人生、谈创作,无话不说,我消除了他的一丝寂寞,也从他那儿得到了不少教益。我感到,老王的内心深处还是想自己搞剧本创作的,可他解放后一直从事的是创作上的行政工作,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除了《舞台姐妹》外,只写过《神龛记》《一条河的故事》《有一家旅馆》《时代的声音》等几个剧本,我不知是否有始有終地都成了电影?1981年,他根据于伶的原著改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七月流火》,总算拍成了电影。在一次我们文学部的聚餐会上,老王的老友谢晋,三杯酒一下肚,话开始多了起来。他指着老王说:你真可惜了!假如你不当官的话,完全可以再多写几个好剧本的……让老王很尴尬,好像他就想当官似的。幸好老局长张骏祥出来说了句公正话:谢晋你胡说什么?!林谷同志做行政工作,是服从组织的安排!这工作总要有懂行的人去做的嘛!老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一笑了之。但他心中明白:谢晋是在为他这个老友可惜,并无他意。老局长是感同身受,有感而发,他自己不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
老朋友还是老朋友,老王离休后,谢晋立即邀请他合作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的创作,拍成电视剧后,却至今都未能公映,可见,谢晋也不是万能的。其间,我根据于本正厂长的指示,曾邀他写过周璇的传记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由他来写是有不少优势的,然而,他仍然十分认真,不但采访了不少人,而且还在于厂长的帮助下,通过北京的电影资料馆,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刊上登载的有关周璇的文章全部复印了一份,足足有四百多篇。他写出的《周璇悲歌》上下集电影剧本,是我所看到的有关周璇的作品中把周璇写得最真实的一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拍成。对此,老王显得格外的平静,他干了几十年剧本工作,太理解其中的原委了。后来,当我得知老王得了癌症后,曾想协助他整理成一集后争取投拍。我想了三条理由去与领导陈说:一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拍这样一部三四十年代著名影星的传记影片正合时宜;二是我们正在营建电影景点基地,好多戏可集中在我们的景点中拍摄,不会花太多的钱;三是也算为老王做一件好事。领导很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去同老王商量。老王听后欣然一笑,说自己的身体怕再也握不起笔来,他委托我全权处理。最后,他告诉我,据他所知,中央电视台正在筹拍周璇的电视连续剧,根据影视的关系,拍了电视,就很难再拍电影了。我听后百感交集,老王在工作上一直是十分认真的,上影出品的不少好影片的剧本,都渗透着他的心血。由于他手中有权,所以处世也特别认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而据我的观察,他对自己更认真。就在他生命走向尽头时,仍然对自己、对别人、对厂里是那样的认真。我虽然安慰了他,显得信心百倍,但最终还是应了老王的预料。以后见到老王或与他通话时,我真怕他问起此事,可他却始终只字不提。我曾在谢晋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协助他组织剧本,二是宣传谢晋,有可能为他写个传记。此时老王虽已离休,却仍然全力支持我去做好此项工作。我们相约,有可能的话,一起为谢晋写个传记。老王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其中有件事特别让我感动:“文革”开始时的一个星期天,谢晋约了老王一起躲在市郊七宝镇的一家羊肉馆里小酌,他告诉老王,据他得到的消息,次日他将被隔离审查了,他两个弱智儿子自他被揪出后,在里弄里常被顽童们当作小牛鬼蛇神欺侮,甚至被塞进垃圾箱,以后可怎么办呢?老王明白谢晋是在“托孤”。他忙答应谢晋,只要他仍有一份自由,他会尽力去协助照顾的。这天,谢晋找了一个公园,与两个弱智儿子尽心地在草地上踢了一阵足球……谢晋生前,不愿意写自传,也不乐意别人去写他的传记。我也感到很难写好他的传记。所以,我与老王的这个约定也未能实现……
1995年春节前的一天,上午10时光景,我正整理行装准备回老家去陪年迈的父母过春节时,突然接到老王的一个电话,话筒中传来他颤颤抖抖的声音:“我是老王,我知道你要回乡下过节的,先向你拜个早年吧……”我一听,来不及有任何思索,立即抢过话头说道:“不,不,应该我向您拜年,我来,我马上来看您!”放下话筒,丢下没有整理好的行装,我一下冲出了门外……
那天,我来到了老王家,见他正依在床头看电视。人已骨瘦如柴,说话也十分吃力,却还为他夫人给我泡茶慢了而发火。师母告诉我,他不能进食,脾气越来越倔。我鼻子一酸,我知道老王是为了无力对我这个老下级热情而发急。师母又向我“告状”:老王听说厂里经济困难,不肯进大医院,不肯用贵重的药……我忍着泪水。老王又发火了:“你胡说什么?我不明白我的病情吗?大医院进了也白进,贵重药用了也白用,为国家省着点不好吗?”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哗哗直淌……我忙给他捧上带去的一束鲜花,有他喜欢的白丁香和红玫瑰。我说:“老王,真不好意思,让您先打电话来了……来不及备什么礼物,给您送上些您喜欢的花吧!”他高兴地笑了:“我喜欢你早已做出了牌子,逢年过节从不给领导送礼拜年,只回老家陪父母。今天你能来,还送我喜欢的花,我……”我有意说:“不喜欢我了?”我俩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我早明白老王将不久于人世,我在回家乡的路上,一直在想要给他写篇文章,赶在他走前给他一点安慰,可由于种种顾忌,虽冲动地在大年初一就动了笔,最终还只是开了个头。但我仍然认为:人走了,送再大的花圈,说再多的好话,已无多大意思,真有情,就赶在前。那天,我在老王家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认真的人在老而无权无力时的孤独。为此,我更敬重认真的人,并将终生告诫自己,要雪中送炭,而无须锦上添花。
春节回沪后,我给老王打过一个电话,他说他的病情有了些好转,能吃点流汁了。我高兴了一阵,却想不到没过几天,他就病危被送入了医院。他仍然不肯进局级离休干部的定点大医院,只愿住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地段医院中,我明白他的意思:一是不愿再去多花国家的钱;二是不忍让家人多花精力和时间在路上来回。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与文学部的两位老同事去的,老王鼻中插着输氧管,手臂上扎着输液管,我们相对无言。另一次,听说他不行了,是陪两位老厂长去的,老王挣扎着说出来三句话,一是问:“夏公走了?”他指的是夏衍的逝世。夏公病重,上影代表赴京去看望时,夏公也曾问起过老王。老王明白这回他将随夏公而去了。二是问起上影的现任领导。三是“谢谢老领导的关心”。老厂长徐桑楚听至此,眼圈一红地说道:“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此话当时我听过算了,现在想来,老王逝世于1995年,50年前是1945年,可能当时他们都是听从党的指示回上海工作的)。两位老战友的生离死别之情,让我非常感动。临别时,我挨在老王耳边说了声“保重!”他吐词不清地说道:“我没有完成任务……”这是我听到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只有我能听懂,那是指写周璇剧本和谢晋传记的事。他到了生病的最后时刻,还如此自责,让我更为感动。
老王临终前问起上影现任领导,其实问的是吴贻弓,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又不便让我转告。此事,多年来我一直不敢向外提及,主要是怕有损老王的形象,似乎到了这地步还在乎现任领导来不来看他。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在一次文联委员在外地学习期间,一天早上正好与吴贻弓一起吃早餐,就对他说了此事。吴贻弓听后久久没有说话,似乎深深地触动了什么,但他还是坦率地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他在执导影片《姐姐》时,是以受尽艰难的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风沙中继续勇敢地前进作为结尾的,寓意非常清楚:虽然受尽磨难,前途未卜,但她们仍然不失理想,坚持前进……在送审时,时任副厂长的老王认为“光明面”还表现不够,一定要打着红旗前进。虽然吴贻弓认为这种表现太直露、公式化,但他也只能作此改动。影片公映后,确实有不少观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让吴贻弓难以说清……我听后,恍然大悟,心灵顿时为此一震,老王啊,他在临走前,可能就为此事想对吴贻弓说点什么……
人與人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重点之一。我与老王的关系,并非如有些人想的那么“俗”,我从未去巴结过他,只在他临行前送来过他一束他喜欢的鲜花。更非如有些人想的那么“深”。人与人的关系除了带有道德和政治层面的色彩之外,更多的关系是建立在想认认真真地为社会做些事上的。但人与人的关系又难避免受道德和政治层面的影响,经历丰富和复杂的老王,势必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舞台姐妹》中写下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的经典台词,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但这恰恰是老王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