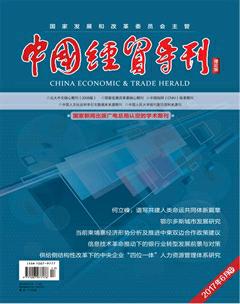文化资本、工具理性与公共文化服务
摘 要:公共文化服务为公民提供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提升公民的文化资本,创造有精神价值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和工具理性理论,本文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文化资本积累的最大化,之二是超越工具理性,培育人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价值,要抵制粗俗文化,平衡流行文化;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加快国家和人民文化资本的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要形成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
关键词:文化资本 工具理性 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兼具公共性和文化性双重特征。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它具有物质依托,依托诸如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文化馆等文化实体。二是它具有公共属性,有凝聚社会认同感、凝聚核心价值等社会资本塑造功能。三是它具有文化資本属性,作为国家文化资本积累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同样具有这三项内涵和功能。从价值意义上讲,公共文化服务为公民提供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共享精神价值,构建公共理性,进而抵御个人主义的消极倾向,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提升公民的文化资本,创造有精神价值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从文化资本积累和超越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价值之一——文化资本积累的最大化
文化资本是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胡塞尔“生活世界”观念影响下提出的理论概念。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积累,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经济资本,作为实际财富的积累,直接表现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和金钱,它以私人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二是文化资本,体现为知识、教育和文化生活形式的积累,它以教育资质的形式被制度化。三是社会资本,体现为社会义务和社会联系,它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1]。三种资本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但是三种资本形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1]。例如经济资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资本越多,文化资本也会越多,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需要长期的培育和积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这三种形式的资本,而不仅仅是经济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和生成围绕着文化资源展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文化资本持有者通过文化实践增加自身文化资本的过程,积累文化资本,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1]。
反观文化资本理论,不仅是个人,国家和社会同样需要文化资本积累。国家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是通过公民个人的文化资本积累来实现的。国家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来提升全体人民的文化资本积累水平,反过来,公民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也将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资本水平。国家文化资本积累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2]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与否取决于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取决于文化资本的积累。国家文化资本积累对于经济资本积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当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指标的文化资本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国家文化资本积累也会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国家文化资本积累可以为社会创造出更具信任感的社会氛围,从而提升社会凝聚力和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进而提升国家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会极大地提升社会的人文精神,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人民群众的文化资本积累除了靠个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外,需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价值和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率,这既是国家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途经,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3]。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价值之二——超越工具理性,培育人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
理性的观念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人提出逻各斯的概念,提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一个唯一的逻各斯,逻各斯是一而不是多,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赫拉克利特称:“要听从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才是智慧的。”[4]也就是说人的活动要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核心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而灵魂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4]认识你自己必须通过理性,理性是神圣的,灵魂只能在理性中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是认识自己的外表和身体,而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认识自己的灵魂是认识灵魂的理性部分[4]。通过理性,人能得到确定不移的绝对知识[4]。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又有所发展。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概念的不同方面,使得理性发生了分裂,后来的思想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继续探索,到康德最终将理性的分裂固定下来,从而预示了工具理性理论的出现。
思想发展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主体性原则,树立了理性的标杆地位,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确立了理性至上的原则,直至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的本质是在祛魅前提下用一种技术化的精于计算的方式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与工具理性不同,它强调的是某种目的或行动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结果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出发点、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义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简明地说,工具理性,是行动者纯粹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的,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价值理性,是行动者从动机和出发点的正义、正确与否的角度考虑的,而在一定程度上不管行动的结果如何[5]。工具理性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导致了集体非理性,最终也必然导致个人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本质是非理性。
综上所述,理性是人类追求知识和智慧的方式,可是一旦沦为工具理性就丧失了理性最初的本质,一味地任由工具理性膨胀,就会造成很多困境和危机:在公民个人层面,出现精神生活物化带来的内心焦虑,个人价值感失落、幸福感的缺失等;在人际关系层面,出现信任危机,戾气沉重、道德滑坡等现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造成环境污染;在人与历史层面,出现漠视历史遗迹和历史记忆,为追求城市发展盲目拆迁历史建筑和老城区的现象等。社会在追求GDP的同时,对人的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关注不够,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对人内心、道德乃至幸福生活的塑造重视不够,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对社会人文精神产生大量负外部性。这些都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的结果。
为回应这样的失衡,必须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是全社会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建设,目的和价值是超越工具理性,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最终培育人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文化资本的最大化积累。
三、公共文化服务两大核心价值的实现方式
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两大核心价值——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超越工具理性,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公共文化服务要抵制粗俗文化,平衡流行文化,培养公民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
当前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面临着粗俗化的风险。精神追求以物质为基础却高于物质,当人们的生活被物质追求和金钱的逻辑所支配,当人们的思想和内心被功利性目的所占据时,文化娱乐生活粗俗化甚至低俗化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生,介于高雅文化和粗俗文化之间的流行文化也很容易向下滑坡。究其原因,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从外因看,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经济利益主体利用各种现代化传播手段,尤其是互联网手段向人民输出粗俗文化产品;流行文化格调不高,以刺激人们的文化消费,赢得粉丝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倾向明显,最终也难免落入粗俗的泥潭;从内因看,当前国人的文化资本积累不足,文化素质、思想深度和文化需求质量不高,为文化粗俗化提供了空间。粗俗文化产品所传播的理念和价值大都没有脱离人的自然欲望、感官刺激和功利性存在的一面,长期浸淫其中,会给人以这就是文化生活全部的假象,限制了人们对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思考以及人们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保障和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要抵制粗俗文化,平衡流行文化,重建人们崇尚精神价值的文化追求。具体措施上应该从两个方向着手,一是调控文化市场,限制粗俗文化产品的流行与传播;二是致力于提升人的文化资本,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使人们在文化娱乐活动中自觉追求真善美,建立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加快国家和人民群众文化资本的形成[3]
为多元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有效供给,从而加快国家和人民群众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应尽快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对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资金投入不足,人民群众参与度不够等问题的积极回应[3]。未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多元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坚持政府主导有利于社会在政府的引导下,保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与公益性特征,从而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权益;坚持社会多元参与有利于充分利用多种社会资源,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3]。
(三)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要形成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各级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要尊重群众个人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把公众需求作为根本。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权与自主权,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来进行供给与获取方式的选择。公共文化服务只有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为其自身实践所接受,进而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水平。此外,还要兼顾各层次、各服务对象的文化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利用率。通过建立群众的反馈机制来加强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与群众的交流、互动,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度。此外,还要进行民主管理与决策,重视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以及有关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各级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话语权,保证群众真正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3]。
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各级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各级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在办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还要管好文化公共服务,实现对公共文化服务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结合。要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制定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进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群众满意度[3]。
最后,要积极审慎的制定文化发展政策。文化政策蕴含了非制度化的价值规范,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便是其内在价值理念传播的过程。政策无小事,文化政策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人们的文化需求及文化资本水平反过来也影响着文化政策,文化政策的制定是对公民文化需求表达及文化资本水平的回应。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包亚明译.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R].2013.
[3]黄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J].研究论文,2017.
[4]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修订本)[M].人民出版社,2013—4.
[5]王伟.冲破工具理性的“牢笼”[D].吉林大學,2015.
(黄威,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