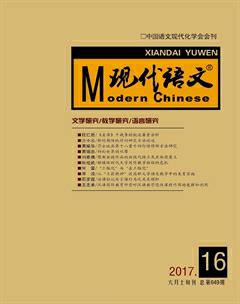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女巫》中两种女性形象的塑造
摘 要:罗尔德·达尔作为一名杰出的童话故事作家有着多部深受大人与儿童喜爱的作品。在欣赏《女巫》这部作品时,除了精彩绝伦的奇幻冒险历程外,深入分析则发现故事中存在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女性形象,由此折射出作者对于女性的态度。本文将结合文本与作者创作时所处的女权主义盛行的历史背景,试论罗尔德·达尔的男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女性形象 女性观 等级女权主义
罗尔德·达尔是挪威籍的英国杰出儿童作家,凭借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出多部魅力无穷的儿童作品,广受大人与儿童的喜爱。尽管童话故事多被认为是写给儿童作为娱乐、消遣并起到辅助教育作用的特殊文本,但不可忽视的是每一个童话故事其背后隐藏的大都是作为成人的创作者,并且现实生活中讲述故事的大多也是作为父母的成年人,由此及来得到的则是童话故事的受众中成人读者远远大于儿童的事实。因此笔者在以成人的角度欣赏《女巫》这部童话作品时,所看到故事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主人公奇幻的冒险经历,更深层次的则是通过罗尔德·达尔这位男性作家对于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他对于20世紀女性的看法及观念。二战结束后,文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妇女作家的崛起,她们的创作不仅有从女性角度表现当代妇女在男权社会所受的压抑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一面,还有回避女性自我意识,以非性别化的作家身份去观察世界、表现生活的一面。从世纪初争取男女平等的妇女到60年代以后“解放了的”妇女,都一直处于追求、痛苦、幻灭之中,女作家们反映了妇女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所经历的感情上的磨难,以及在一个仍为男性所主宰的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困境。[1]因此罗尔德·达尔于1983年发表的《女巫》在基于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直面书写并塑造出两种具有强烈对比的女性形象,展现出作者本人对于女性的态度。
一、社会规约下的贤妻良母
19世纪英国妇女尤其是初期的妇女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们生活在狭小的“三世界”中,即:教堂、烹调、孩子。[2]因此,正如芭芭拉·韦尔特所说的19世纪的美国妇女一样,社会所要求的真正女性需具备“虔诚、贞洁、温顺、持家”[3],这两种相似的规约实质上是把女性放在妻子与母亲的社会职能之内,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存在的意义。尽管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但男权主导下的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女性的错误界定并因此未有所改变。生于20世纪初的罗尔德·达尔深受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女巫》中塑造了适应大背景下的两名贤妻良母的童话角色,即符合男性规约标准下的姥姥和顺从的主妇詹金斯太太。
贯穿整部故事出现的主要人物之一即为姥姥这个角色,首先她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是慈爱、温和、拥有母性的,在故事中充当母亲这一角色。小主人公在与姥姥一起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依赖感,就像文中最后的部分主人公问姥姥可以活多少年,表示不想比姥姥活得久,因为“别人照顾我,我可受不了”,并想象“到那时我将是只很老的老鼠,你是一位很老的姥姥。再过不多久,我们就一起死掉”[4],这种感觉来源于恋母情结。但是这种恋母情结主要不在于他对“母亲”的热恋,而在于他热切的希望获得成年男子地位应该赋予他的那种权力[5],因此对于姥姥的依赖实则是对姥姥——这位年长女性的占有欲。同时,尤其是仍处在孩童阶段的小主人公,与姥姥相依为命的岁月里将姥姥视为母亲,在男性的意识下希望能与姥姥一同死亡,暗含有夫妻之间同生共死的意味,体现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6]。而作者笔下姥姥对小主人公无微不至的照料,除了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呵护外,女性照顾男性包含了社会地位的区分,使得小主人公充分展现了作为男性这个“第一性”所拥有的稳固社会地位——即使童话中的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其次,姥姥的角色在文中展现出对男性绝对的顺从性。这部童话故事的主导者前半部分是姥姥,而后的部分从真正遇到女巫开始,主导者转变为“我”。姥姥虽然拥有话语权,但是并没有主导行动的权力,在故事的第一阶段作为讲故事的人,仅仅叙述自己见过女巫的经历以及女巫的辨别方法,将“我”引入一个充满女巫的真实世界,而真正故事的高潮出现在第二阶段,“我”与女巫们斗智斗勇的历程。可以发现在第二阶段中,姥姥对于外孙的“我”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性,从“我”变成老鼠后溜到姥姥的房间告诉她看到女巫的事实,并对姥姥姥说“我”想出对抗女巫的妙招,到“我”提出在厨房里将变鼠药加给女巫们,姥姥无一拒绝并强烈赞成,且不断称赞道“了不起!”“你是个勇敢的小家伙”“我真爱你”,显示了女性不断契合男权的决定并且将自己渺小化以衬托男性形象的伟大与决策的睿智。
作为柔弱主妇形象的詹金斯太太,集19世纪英国妇女的所有优秀品德于一身,在整部故事中拥有的话语权并不多,主要通过其所处的环境及动作展现人物特点。当姥姥带着“我”和一同变为老鼠的布鲁诺第一次去找詹金斯夫妇俩时,詹金斯太太正依偎在丈夫身旁编织,并且在赶姥姥走时,对丈夫说“快叫经理,亲爱的”,由此展现出詹金斯太太对男性的依赖性,而在第二次遇见詹金斯夫妇时则是在餐厅,所以两次詹金斯太太的露面均没有摆脱社会限于她的活动范围,即家务与家庭。因此詹金斯太太被认为是作者笔下符合社会规约的贤妻良母,生性柔弱的她理所应当依附于自己的丈夫生存。“女人在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我们必须把女人的性格看成是一种自然缺陷”[7],作者以性格、生理上的缺陷加之主观色彩的判定,把詹金斯太太刻画为男性的附属品。因此对于童话中两位顺从女性的肯定性描写奠定了罗尔德·达尔的女性观;相反另一类女性则被他视为邪恶、不遵守妇德的一类,那就是女巫。
二、离经叛道的邪恶女性
东西方父权文化在寻找男人优于女人的根据时,首先从生理现象入手,大肆宣扬“男强女弱”的天然法则,而后对女性形象进行丑态化,因此罗尔德·达尔除了对上文中女性身心“弱化”的处理外,还将女性的丑态化体现在女巫身上。一方面是女性身体的丑化,姥姥讲述的辨别女巫的办法是通过观察他们的外貌,“她们吐的口水是蓝色的”“她们戴手套是因为没有指甲,只有薄薄的弯爪子”“戴假发因为真正的女巫都是秃子”“女巫的鼻孔比平常人大”等,并且在后文中将女性丑化到极致“这张脸正在发臭、发脓、腐烂,可以看出皮肤都溃疡和蛀蚀了”这些都是作者借故事人物之口对妇女进行妖魔化,“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利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8]故事中出现的戴着手套、礼帽、穿着高跟鞋、举止优雅的“名媛太太们”转而变成可怖的女巫,作者以抨击女性外貌达到彻底毁灭女性美感赢得父权绝对统治的目的。中外父权社会的统治者大都认为女性天性深处就存有邪恶成分,如不严加管束则会酿成灾难,法国作家萨德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女人是一个可怜的生物,总是不如男人,不如男人漂亮,不如男人聪明,不如男人富有创造力,只是愉悦男人的对象……她们是虚伪、丑恶、危险的。”[9]另一方面是对女性心理、行为的丑化,在“我”误入女巫集会大厅时,观察到“所有女性拼命抓后颈的头发、挖鼻孔、抓屁股”,大会开始后女巫们声嘶力竭喊道的要把肮脏的臭小孩都干掉,“每一个孩子都要消灭掉,都要压扁,都要压烂,都要烧死!”印证了从官方到民间流传着的“最毒莫过妇人心”这句警训。
父权社会卫道者中头脑较为清楚的人认识到,对女性一味的采取谩骂丑化的态度是不够的,应当从理论上对女性的劣等性道出所以然来,他们从父权文化对“人”的基本判断出发,认定女人缺乏做“人”的资格是因为女性缺少理性。[10]因此罗尔德·达尔为了证明女性是劣于男性的生物,还从女巫的智力方面描写了其残次性。暂且不说故事的小主人公与女巫们斗智斗勇,最终消灭了女巫,赢得了胜利。故事中作者甚至借女巫之口直言“一个笨女巫竟敢回嘴”“一个傻女巫没有头脑”“像你这样的白痴女巫,必须放在烤肉架上像烤猪”,以体现女性自身承认智力上不足的事实。智力程度越高的人才能在社会体系中处于高层地位,带领社会进步发展,男性不遗余力地指出女人先天缺乏理性,以此稳固男性社会地位中的绝对支配权。
三、隐藏在童话故事背后的成人
尽管罗尔德·达尔创造了许多受人欢迎的童话故事,他以成人的姿态努力向儿童思维靠拢,但是《女巫》这部童话难免带有作者本人强烈的性别意识。“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全程作为行动策划的总指挥,在姥姥的辅助下成功战胜了强大而又邪恶的女巫们,甚至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世界儿童的安全,再加之故事中多处展现出“我”对于不同女性细节方面细致的刻画描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作为未成年人能注意到的细微末节,因此总体来说作者只是隐藏在作为叙述者“我”背后的一位成人,叙述者“我”仅仅是成人的一副伪装面具。尽管这种异想天开的故事被广大儿童所追捧,在阅读童话故事时所关注到的仅仅是作为小主人公的“我”的机智勇敢,封闭性的结尾使儿童从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与真善美的永恒性,但是作为成人的我们在读童话故事时毕竟看到了其背后隐藏的真实作者——成人,那是他无论再接近儿童的思维和语调也无法排除掉的,多年来收获的社会经验和思想观念,因此笔者在分析了以上有关作者对于女性负面的描写和文中塑造的符合作者思想中女性的理想形象后,可以判定作者是持有男权主义思想观念的。罗尔德·达尔假借孩童视角与女性中的男权代言者姥姥,共同塑造了男性注视视角下的女巫。女巫的形象在文中可以理解为20世纪摆脱家庭束缚、取得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掀起的妇女工作热潮正与女权运动的兴起相对应,直到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妇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比例[11],可以认为具体来说独立的女巫形象是当时社会参加劳动、工作的妇女形象。这也与文中作者借孩童之口向大家诉说的相对应“真正的女巫穿平常的衣服……做平常的工作”“她甚至可能是这会儿在读这些话给你听的老师”,可见女权运动带给女性的解放是显著的,同样带给那些男权主义的捍卫者们的威胁也是巨大的,既然女性有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并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家庭的功能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往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变为个人独立的经济体,这使男性在维护自己绝对父权地位上略显被动,因此在《女巫》这部童话故事中罗尔德·达尔——一个父权文化的坚实捍卫者说了女性很多坏话,为了就是:让女性老老实实的承担牺牲者的角色。在文中一方面作者大肆攻击那些不肯牺牲的“出格”女性,另一方面为那些甘愿牺牲而又服从的女性大吹大擂,其目的就是规劝女性放弃个人意愿,服从男权社会的规约。
《女巫》这部童话故事对儿童来说是一部充满幻想和冒险色彩的优秀儿童读物,当作为成人阅读时难免被读者用复杂的目光审视其意义。之所以造成这部童话故事复杂性的原因有多种,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大环境的总体变迁与传统观念压制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分析这部童话故事中的两种女性人物形象,延伸出作者对女性的看法,大致确立了罗尔德·达尔在创作时持有的男权主义思想观念,这也与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盛行所带来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强化了作者的性别意识观,使童话故事背后的成人逐渐显露出水面。
注释:
[1]王佐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2]范景兰:《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繁荣之成因解读》,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43页。
[3]巴巴拉·韦尔特:《真正女性的崇拜》,《妇德:19世紀妇女》,哥伦布: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1页。
[4]罗尔德·达尔:《女巫》,济南:明天出版社,2009年版。
[5]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6]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60页。
[7]姚鹏:《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1页。
[8]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9]海斯:《危险的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
[10]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5页。
[11]钱乘旦:《20世纪英国的妇女与家庭问题》,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
(王婧娴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