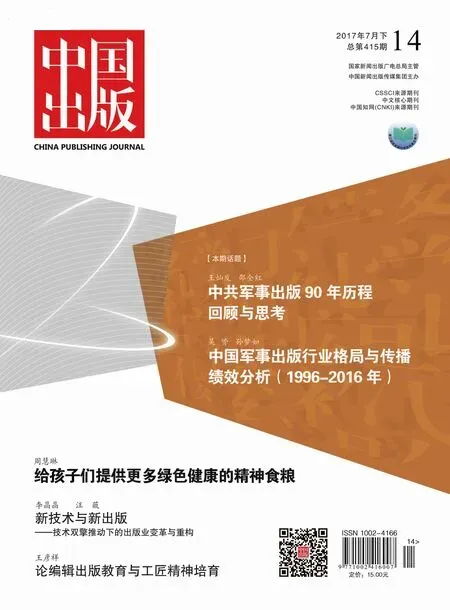论编辑出版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
□文│王彦祥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治国富民的文件中,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工匠精神”的精髓,那就是对待本职工作满腔热情、认真负责;工作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敢为人先;经过不断实践、成长和磨炼使自己技艺精湛,卓尔不群;为了国家和事业的发展心胸宽广、志存高远、爱岗敬业、勇于创新。
一、编辑出版历史和实践彰显了工匠精神
考察我们的编辑出版历史和编辑出版实践不难发现,人类自从有了编辑出版活动,编辑出版人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技艺型工匠,也始终践行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中国是出版物载体形式最为丰富的国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在竹简和木牍上刻写文字。那时的古人将竹片称作“简”,木片称作“牍”,多根竹简编联在一起称作“策”(册);连缀竹简的草绳或者牛皮绳被称作“编”,按照内容将若干竹简依次编联在一起就称作“辑”;专门做这项工作的劳动者由此便成为古代的“编辑出版人”。古时的竹简一般宽0.5厘米,长约30厘米,可抄写一行汉字,大约在20字左右,以此推算要将一部书稿连缀起来,往往需要编辑几卷甚至几十卷竹简。因竹简较为笨重,古代的编辑出版工作实为一件费时费力的体力活,古代编辑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体力劳动者,将其称之为有文化有专长的“匠人”,可谓实至名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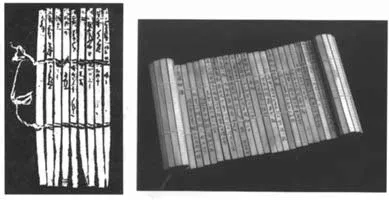
图1 造就古代编辑匠人的简策
竹简主要是用小刀或毛笔将文字刻写上去,力道需精准,书写要工整,虽“入木三分”,但不可有失。如果出错则需将错别字刮削下去重新刻写,连续出错则整支竹简就要报废,代价不可谓不高。故此,才有了孔子老而好易,删订《易经》时“韦编三绝”的典故,其用功之深,用力之细不难想象,这实际上也成就了《易经》的广泛传播。
古人用简牍来书写记录、著作出版是盛行于东周到魏晋的事情,掐指一算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中已流行了1000多年。西汉时我国劳动人民发明了纸,隋唐时期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由此进入典籍的印刷时代。雕版刻书对于编辑出版“匠人”的要求更高更严格,因编辑的疏忽,刻工的失误,都会造成整块印版的报废。如果编辑校勘不认真,错谬典籍散布于世,其影响不仅仅是编辑刻印质量不佳的问题,而是社会浮躁和文化缺失的问题。幸甚幸甚,我们的先人非常执著、专注和认真,流传下来的古籍绝大多数都成为了精品、善本,由此也产生了数不胜数的优秀编辑出版家和技艺精湛的刻工,这自然要归结为中国古代的工匠精神。
为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使生产出来的书籍成为后世典范,历史上才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以及翟金生总结撰写出《泥版试印初编》;才有了王祯发明木活字转轮贮字架并撰写刻印《造活字印书法》,以及金简受命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总结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才有了华氏会通馆和安氏桂坡馆的铜活字印刷精品,以及康熙和雍正皇帝接力推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铜活字印本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才有了从涂版、套版到饾版、拱花的多色彩印古籍以及木版水印的传世精品《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谱》;才有了乾隆皇帝举全国之力编纂世上首屈一指的《四库全书》,并特建南三阁北四阁分别庋藏;也才有了近代商务印书馆异军突起成为民族出版的翘楚,并创造出“日刊一书”的奇迹且质量堪称民国第一。
这一漫长的中华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也是优秀编辑出版“匠人”不断涌现的过程。比如,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历经数年整理皇家藏书,编订《别录》和《七略》;班固倾心编纂《艺文志》,成为书籍记录的范式;五代十国时期冯道奏请和主持刊印《九经》,使儒家经典广泛流行于世;宋代郑樵学问贯通古今,编出政书集大成之作《通志·校雠略》;岳飞九世孙岳浚刻书精湛,将工艺流程归纳为《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刻书无数,还专门造楼阁善待校书之学者;明末清初是编书刻书大师辈出的年代,代表性人物顾千里与黄丕烈精诚合作,佳作频出,开创了世人称道的“顾黄”时代;前清康雍乾盛世时的武英殿内异常活跃,纪晓岚率领几百名书作匠人和校工、刻工奋勇争先,创造了皇皇巨著《四库全书》的编辑出版伟业;民国书业更是人才济济,夏瑞芳、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叶圣陶、沈雁冰、胡愈之等编辑巨匠,引领民国出版不断推陈出新,并树立起潜心编辑、崇尚精品的新典范。
回顾自古至今的编辑出版匠人及其生动事迹,他们的勤劳严谨、专注执著贯穿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他们技艺精湛、敢为人先的努力过程也彰显无遗。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实实在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而也铸就了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国编辑出版历史。可以说,中国的编辑出版历史和实践,不仅体现出工匠精神的精髓,还诠释了中国编辑出版匠人的胸怀,给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栋般的优秀文化典籍。
二、现代编辑出版实践映射出工匠精神实质
回顾历史也要关照现实。现当代编辑出版工作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编辑效率更高,出版物产出量更大,对于编辑出版人的要求也就更加多样和严格。但贯穿始终的是初心未改,秉持着工匠精神,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大众奉献精神食粮。
编辑工作在整个出版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出版物的质量水平和荣辱成败,为此制订和实施编辑业务规章制度是必然之举。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领域陆续有了三审制、责任编辑制度,三校一读、责任校对制度等制度。这些制度强调的是调动编辑出版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在编辑出版业务中依照规范,严谨认真,消灭文稿的各种差错,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出版物。考察现代编辑出版制度和流程,其实质就是以专注执著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业绩,来践行现代工匠精神。
以编辑流程和质量管理来分析。现代编辑工作流程一般归纳为信息采集—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整理—物态设计—审定发稿—校样处理—样品检查—出版物宣传—信息反馈—重印与再版等12个步骤。整个流程牵涉面广,参与人员多,隐含的要求也较多较细,编辑出版人肩负的责任也大。
现代编辑出版工作还引入了管理学、统计计量学等理论和技术,以保证出版物质量。出版物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个方面,目前设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其中,内容质量以《出版管理条例》第25、26条的相关规定作为判定依据;编校质量以差错率是否超过万分之一为依据;设计质量以整体设计和封面、扉页、插图等设计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作为判定依据;印制质量则以国家《印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CY/T2-1999)为依据。在具体管理上,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方面均达到合格水平,出版物才能算作合格产品;若四项中有一项不合格,成品出版物质量就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若以工匠精神的标准来考量,以上质量标准只能算是低标准,而不是出精品创品牌的严要求,还需要编辑出版人和管理者一起努力,将精品工程落到实处才能使我国的出版物达到更高水准。
以三审制和责任编辑制度来分析。三审制即出版单位对稿件进行初审、复审、终审。在执行三审制过程中,包括对稿件内容质量和形式质量的评价,编辑要认真严格地审读稿件,不可有丝毫马虎。编辑在审稿时须坚持国家和出版单位制订的取舍标准,进行专业性、规范化的操作,通过比较、分析、综合等方法,给出科学客观的评价。
接下来的编辑加工整理等工序则是审稿的延续,这些环节就落在了责任编辑身上。责编制度要求责任编辑一般负责稿件的初审,并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付印样通读,同时还要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环节进行质量监督,以保证出版质量。责任编辑对稿件负有很大的责任,要通过专业化劳动使稿件内容完善、体例严谨、逻辑严密、材料准确、语言文字通顺,并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原则性错误。[1]
编辑加工整理等工作也是责任编辑发挥创造性、能动性的舞台。在进行具体工作时责任编辑必须凝神聚力,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地进行编辑加工整理。责任编辑还要耐得住寂寞,埋头苦干,从稿件正文到辅文,从内容布局到表现形式,从消灭差错到润饰提高,从核查校订到规范统一,从协调作者和各个部门关系到实现齐清定的审定发稿目标,这些过程复杂,环节多多,但都离不开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和真情付出。所以说,没有一颗为“为别人作嫁衣”的奉献之心,没有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责任编辑。
以校对工作和校对制度来分析。校对是文稿编辑后、印刷前的最后一道质量把关工序,要将各种差错消灭在出版物印制之前,从而保证出版物质量。校对是实现出版物价值的重要保证,其把关地位十分突出。通俗地说,前面的任何编辑工序出错都可以谅解,若校对环节把关不严,仍然遗留差错,将导致书稿错谬随出版物流出,产生不合格出版物,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2]
校对工作是具有文字性、学识性的创造性劳动,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因此,国家制订并实施了《校对符号及其用法》国家标准,并逐渐形成初校、二校、三校、通读、誊样、核红、文字技术整理、对片等八大校对基本工序。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保证出版物质量。[3]但是,机械式的工作还不行,在校对环节必须发扬工匠精神,并予以具体贯彻执行,才能达到预期的校对效果。
我国现阶段施行责任校对和“三校一读”的校对工作基本制度,这是任何出版物校对都必须坚持的制度。其中,每出版一种图书,都要指定一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为责任校对,负责文字技术整理,监督检查各校次质量,并负责付印样的通读工作。出版物校样必须经过初校、二校、三校和通读检查后才能付印;一般图书的校对不低于三个校次,重点图书、工具书等还应增加校次;终校必须由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这些做法和指标要求,体现了校对工作的特点和价值,也折射出校对工作中的工匠精神实质。[4]
一言以蔽之,现代编辑出版工作从各个方面都在指向一个目标,即在保证出版物基本质量的前提下,多出传世精品,多传播正能量。而在这些制度、流程、要求、指标、规范的背后,只有把握工匠精神的精髓,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不管是编辑出版业务重点的审稿和编辑加工整理,还是贯穿出版物生产的各个编辑出版环节,都存在很多细致和繁复的工作,这就需要编辑出版人克服浮躁的心态,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的思想,认真做好编辑出版业务的每一件事,圆满完成编辑出版的每一天工作。
现代编辑出版的工匠精神内涵经过近现代的继续丰富,以及当代的补充完善,笔者认为可用四句话来概括:胸怀理想、爱岗敬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注重细节、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奉献精品。
三、编辑出版教育要注重培育现代工匠精神
以上从中国古代技艺型的编书刻书“匠人”,论述到现当代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快速编书的新型编辑出版人。但不论古今,编辑出版人都属于有技能有文化的工匠,是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的辛勤劳动者。在教育界,老师谦称自己是“教书匠”;那么在编辑出版界,我们也可以将编辑出版人称作“编辑匠”。“教书匠”要用专业思想和教学实践,培养出合格的“编辑匠”,以恪守和弘扬工匠精神。
1.出版质量下滑影响到编辑出版教育
毋庸置疑,我国现阶段的出版物质量下滑严重,这与工匠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究其原因,社会节奏加快,人们心态浮躁,对待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现象比比皆是。目前在编辑出版界流传甚广的是“无错不成书”“编辑出版无学”等负能量的论调,但有显示度的、体现正能量的标志性词语一直没有树立起来,也没有体现在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之中。
编辑出版界也有负面实例值得警醒。如2010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某期刊主编写的一本书《嫁衣余香录——编辑文化学研究》,出版后被指概念不清、体系凌乱,语言文字基本功差、字词语句错误多,学术水平低下等。于是,老编辑黄占宝等人又做一书名曰《千疮百孔的嫁衣》,于2011年5月在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25万字的篇幅,以学术指误文章为体,对那本书进行了阅评、勘误,指出错谬之处,提出修改意见。这一事件就如黄占宝先生总结的那样,该书作者缺乏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对编辑文化学研究缺乏深入思考和认真梳理,致使错漏百出……我们不能容忍粗制滥造者将千疮百孔的“麻袋片”当做“嫁衣”,不能容忍如此粗劣的作品误导后辈编辑。[5]
再回看我们的编辑出版教育,个别专业教师在课堂讲授编辑出版相关课程时,课件内容不严谨,格式错误百出,内容缺乏新意,形式照本宣科。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受手机和网络文化影响,一些学生上交的作业、完成的考卷也是从内容到格式缺乏规范,更不符合编辑校对、版式设计的要求。浮躁、应付和所谓“宽松”的环境,令我们的专业老师也不去细究学生的错误,不去指导他们的专业素养,而是你好我好、得过且过,社会不良做法渗透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没有贯彻,专业声誉却有所下降。
2.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遍缺少现代工匠意识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如一些人过度追逐金钱名利,心态越来越浮躁。编辑出版人所属的出版产业是典型的微利产业,要想快速赚大钱是不可能的。同时,编辑出版人所从事的工作又属于文化事业,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大,需要通过出版物传播正能量,实现宣传、教化、引导等功能。
但这些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并没有吸引力。在独生子女、追求物质的环境下,受刷屏文化、手机快餐等影响,大学生比较看重的是哪个专业赚钱快,哪些工作轻松省事。编辑出版专业需要的一丝不苟、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奉献精品的工匠精神,目前在学生圈里普遍缺失。我们也没有看到哪所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教学中,特意开展过编辑出版工匠精神教育。
试举一例,实际编校工作中有一个著名指标,即差错率小于万分之一的属于“合格出版物”,差错率小于十万分之一的属于“优秀出版物”。可是,我们目前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并没有将行业规范贯彻到专业教学之中,甚至连校对课程和校对作业都不执行这一著名指标。如果动真格的,检查国内任何一个班的编辑出版专业完成的课程作业、毕业论文的编校质量,肯定没有一个班的差错率能够达标,即小于十万分之一。这说明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还没有与行业标准对接,也没有教育学生贴近行业,执行行业规则或标准,致使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明显缺乏现代工匠意识,以为专业工作就这么简单,通过标准就这么容易。
3.编辑出版理论教学中必须强化工匠精神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6]这些话其实也很好地诠释了编辑出版的工匠精神。
面对浮躁的社会环境,编辑出版教育要抓住工匠精神中爱岗敬业、专注执著的精神内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观点,在学生刚入学时的“出版专业教育”课程中,就旗帜鲜明提出:本专业不仅要学习通识性课程,还要系统掌握编辑出版专业理论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未来进入出版业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只有具备了现代工匠精神的学生,今后才能做好编辑出版人,才能胜任编辑出版工作。这是今后从事出版工作和专业研究的必备条件,也是编辑出版职业道德的核心价值体现。
在接下来的编辑出版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各任课教师都要以身作则,用自己一丝不苟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来演绎工匠精神,来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同时,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应以我国出版业的诸多工作规范和行业标准来要求学生,使其感受到做好专业工作必须严谨认真。更要让专业学生知晓,通过多道工序、多个环节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版物,都必须精细和达标,而绝不是读读书、考考试、上上网就能完成的,不仅要勤思考,还要多动手。
4.通过专业实践课程磨炼学生的工匠精神
编辑出版专业是一门实学,在校大学生应通过出版实践来掌握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从中感悟和磨炼出编辑出版工匠精神。事实上,我国高校的各编辑出版专业近年来都建设了条件不错的专业实验室、校内和校外实习基地,专业实习和行业实践活动也有所加强,这对于培养复合型的出版人才,磨炼工匠其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目前的编辑出版实践课程有一些流于形式,教学要求与行业要求相差甚远。不少的编辑出版实践课程,指导教师给分宽松,学生学的也较为轻松,大多数以提交书面作业的形式来结课,甚至也鲜有不及格的成绩。这样的做法不是在培养专业学生的正确认识,而是误导了他们的专业思想,更无法形成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面对新环境和新技术,编辑出版实践教学应摒弃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得过且过的教学思维,在教学流程、实践要求、考查形式等方面力争与出版行业的具体环节看齐,要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和成就感,应鼓励学生在实践课程的学习中发挥创造力,以做到既能仰望天空,也能脚踏实地。通过逐渐严格起来的专业实践课程,应该使学生感到专业实践的难度和压力,要全身心投入,不可有半点马虎,在编辑出版实践的考查中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而不能以合格、通过、差不多、过得去……这些低标准为目标。通过一系列专业实践课程的学习和磨炼,让学生们真正领会工匠精神的精神内涵,使其按照业务规范一字一句、字斟句酌地进行实践,在实践中感受精致工作和精品出版物的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高远目标: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7]
5.校企联动塑造专业化的大工匠精神
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了正规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以来,教育教学脱离实际、脱离行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也致使高校培养出的专业学生很多不被出版单位认可,毕业生的求职就业也出现了诸多困境。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仍然没有很好地对接,在专业人才培养的认识上产生了差异。出版业最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勤奋肯干,且胸有大志,能够很快胜任专业工作的“工匠型”人才。而学界更多地把重心和资源用在了学者型的、读书派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上,致使修完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并不了解专业工作的实质,不领会编辑出版工匠精神的精髓,体现出来的往往是眼高手低、轻视体力劳动,但经过实践打拼才能承担的选题策划、业务管理等工作,毕业生又很难马上胜任。
其实,现在出版领域有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事例,都应该在大学课堂好好讲述给学生,以使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职业观,立志成为编辑出版行业的“大工匠”。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等图书,几乎查不出任何编校和出版方面的错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色经典,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证明,达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的完美境界。毛主席作为一国领袖,在百忙之中还亲自校订过《毛泽东选集》,成为一时的编辑出版佳话。
世事变迁,编辑出版教育的物质条件已大大改善,编辑出版业务工作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在这样的前提下,高校和出版单位应该联合起来,双方都要拿出诚意和信心,在培养新的专业人才和进行新员工培训方面进行合作,优势互补,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入人心,使专业化的工匠精神在学界和业界得到广泛传播,进而推动编辑出版教育深化改革,打好人才基础,输送合格人才,从而培养出更多的编辑出版“大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