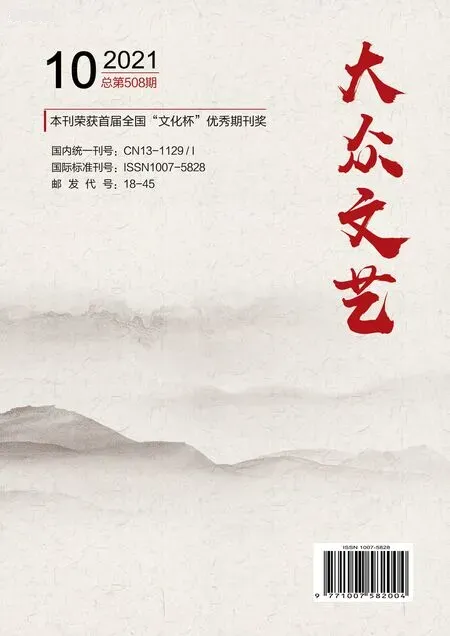吴汝纶古文“声气论”与桐城家法
周晓坤 (河北大学文学院 071000)
吴汝纶古文“声气论”与桐城家法
周晓坤 (河北大学文学院 071000)
“因声求气”论是桐城派始终传承不绝,奉为圭臬的文艺思想,该理论继承古代文论关于“声”、“气”的理论传统,亦有创制之处。吴汝纶作为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也在“因声求气”的具体实践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进行了文章创作的创新,以保护桐城派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延续。
吴汝纶;“因声求气”;桐城派
“声”“气”在传统文论中早已不是陌生的话题,而真正在它们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则始于桐城派刘大魁的探索。吴汝纶“因声求气”的实践需要联系文学的、时代的双重背景,以探讨其理论样式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章创作方面的新变。
一、有迹可循:桐城派“声气论”流变与实质
“声”是文学的声律,或与音乐配合的乐律。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对“声”这一概念的定义,以及对“声”的作用的感知很早便产生。荀子在其《乐论》中提出音乐的重要教化作用:“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已经提出了乐教之“声”感化人心,教人从善的作用,以及对于邪污之气的摒除。汉代《乐记》更是强调,在“声”的审美过程中可以体验到作者、读者之间情感的传递,是所谓“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乐记·魏文侯篇》)。《毛诗序》另有“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句子,亦此意。文字之声韵与文本的意蕴有根本上的联系,共为一体。声音即为文本有机生命体的内在之气韵的表现。声音、气韵、生命情态互为表里。用声言观人,观世,是由外及内,由形于色入于文学生命气韵的重要途径。
魏晋之后,文学的声律化更是建构“自觉文学”的核心要素,从南朝四声八病到唐代音律铿锵的近体声律。从铺张扬厉的两汉大赋,到句齐韵协的骈体律韵,都体现了这一变化。
曹丕“文气说”提出“气”这一命题,并以音乐设喻;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此皆古代文论关于“声”“气”的传统。
宋元以后,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时期,复古主义的诗学和文论,使汉唐文学的声律批评,以及由声律探寻诗文兴象、意旨、气韵的风格论,鉴赏论更加自觉和系统化。明清古文的八股化,以及文学观念复古思潮下诗文体制的交融和汇通,亦使古文家重视古文声律的本体特质。明末以来,古文的闲适化情调和审美追求,亦从美文文学观的视域推波助澜。因此“因声求气”成为桐城古文家借以悟入汉唐两宋古文技法,风调,神情的法门。他们的古文评点,诗文吟诵均是特定表现。而由此又拓展至创作。形成特定的创作论。
桐城派“因声求气”的学说在继承古代文论资源的同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构起了“声”、“气”之间的桥梁,使“气”有迹可循,不再抽象杳渺,而桐城派内部各家的偏重点亦有所不同。吴汝纶毕生推崇的“因声求气”肇始于桐城先祖刘大魁的《论文偶记》,也正是在刘大魁处,基本明确了“声”、“气”间的关系。刘大魁论“声”,总结为“音节”、“字句”,与“气”之关系是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刘大魁认为,文章的“神”是最高的审美追求,气由神主,而音节字句的差异就直接决定了文章气势、神貌的高下。这种论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首次将抽象的“神”、“气”化为音节、字句这些可以感知与把握的具体存在,而桐城后辈也在此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为使“因声求气”的理论更为具体而进行探索。
根据刘大魁的思想,姚鼐提炼出文章的八目,即“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前者为文之精处,后者为文之粗处,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姚鼐对于“因声求气”理论的创制之处在于具体诵读方法的论述,他指出:“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被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与陈硕士》),提出了先急读后缓读,从字句、音节求得感“气”的方式,在刘大魁理论的基础上使之更加具体可行。
曾国藩小学功力深厚,对“因声求气”理论的继承发展体现在读文、作文的“字”、“句”意义的重要性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细致性。他主张在阅读古人文章时,尽可能疏通每个字、句的意义,甚至可以参照《尔雅》《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来进行考据。只有这般,才能在大声朗读时继承古人的“神韵”,下笔成文,气在其间,这也正是吴汝纶论曾国藩“以汉赋之气运之”所描述的作文之法。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舆中读《上林赋》,千余言略能成诵。少时所深以为难者,老年乃颇能之,非聪明进于昔时,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故略记之。”(丁卯同治六年正月),将老年进一步理解《上林赋》归功于对文章节奏、气势、用意的把握,体现出曾国藩深谙音节字句,又精于意义探求的文艺思想。
“因声求气”理论到了吴汝纶这一代,依然得到桐城弟子良好的传承与实践,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与吴汝纶探讨“意、辞、气、法”,又云:“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义与词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故必讽咏之深且久,使吾之气与古人之气契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指出吟诵是古文入门的绝佳途径,读古文必要追求与古人心灵境界的契合,而这种“契合”是把握文章自然神韵的必经之路。吴汝纶观点大体与同门兄弟张裕钊相同,日记曾描绘吴汝纶与张裕钊商榷文章气脉贯注直至子夜的情形,表现出后辈桐城人对此课题进行的深掘。
二、身体力行:吴汝纶“因声求气”的实践与具体方法
桐城派对于吟诵实践的执念之深重,在张裕钊好友方存之话中便可知一二:“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答吴挚甫书》)观吴汝纶日记可知,吴汝纶继承了这种勤于诵读文章的精神,未尝一日去书卷,并以读书为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之大事、难事。其具体的“因声求气”方法,大体可以归为两点。
一是不拘泥于字句。李景濂曾在《吴挚甫先生传》中记录吴汝纶关于“因声求气”的言行,有言曰:“故其为教也,一主乎文,以为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于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远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在吾目中。务欲因声求气,凡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循乎机势之自然,以渐达于精微奥窔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于用。”自刘大魁将追寻“气”的关键列为“音节”、“字句”之后,不少人深陷在对字、句考据的执念中,甚至偏离读文的本来目的,着意于生僻字的考究。与此相反,吴汝纶不拘泥于字句,他更关注对文章整体文气起伏变化的把握,追求随音节变化而变化的,一以贯之的文气,倡导避免因小失大,过于重视个别字、句的释义而人为地割断了对文章气脉的整体感觉、体验。然而,这并不代表吴汝纶的训诂之功有失精凿,在《吴汝纶全集》中,日记卷考证部分,曾记录了吴汝纶考证的“异字”的认真程度:“五月丁酉抄尚书异字,乙巳尚书异字抄毕。此但就陈朴园书中摘出,未尽详备,他日仍当就江艮庭、段懋堂、孙渊如诸书抄之。”(戊辰二月乙巳日记)正是“若汉之相如、子云,文章极盛,小学尤精”,同此理。
二是力求实现自身与古人的冥冥相合。吴汝纶自幼受到姚鼐思想的熏陶,称“自少读姚氏书”,力主吟咏诵读的重要性,其诵读观念与姚鼐甚为相似。同时,又受到恩师曾国藩与友人张裕钊的影响,深受“贯通”之说的浸润。所谓“冥冥相合”,是指在诵读时把自己与古人想象为一体,忘我而仿佛代替原著者读其文,此时文章气脉贯通,对文意理解自然更加深刻。吴汝纶致力于秦汉文章,友人张裕钊称赞其文“深邈古懿”,这般下笔的气势与其平日追求“冥冥相合”的阅读训练是分不开的。吴汝纶在诵读时,尤其注重声音的抗对起伏,认为于此中可以体味原作者的情绪节奏,好像摄取古人文心,与自己合而为一。上文中提到张裕钊追求“契合”的吟咏方式,在这一点上,吴汝纶与好友张裕钊所见略同。刘声木言张裕钊论文“声音最要”,“尽得古人声音抗坠昂扬之妙”。吴汝纶对王安石铭文的深刻感知,亦得益于声音的感受,最终达到“渐觉身非我,都迷王与吴”的境界。
三、推陈出新:吴汝纶创作的新变
在吴汝纶生活的历史年代,桐城派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维新思想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挑战了洋务派的政治地位,造成了桐城派的统治地位及政治基础的动摇;另一方面,新文学方兴未艾,使有着与传统程朱理学一脉相传的“义理”文艺思想的桐城文派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从林纾“桐城谬种”的称号之中,我们便可以想见新文学愈来愈猛烈彻底的攻势了。在这种情况下,吴汝纶的创作也适时地发生了自觉的新变,集中体现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以及“义理”的淡化。
最大的改变体现在西方文化对于桐城文章的浸染。吴汝纶绝不是一位冥顽的卫道士,他在时代中迅速吸收了新鲜事物,甚至做出“直抒大画,奏除科举”的举动,提出:“变通书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十分具有革新意识。这与他广览新书,了解了涉及地理、天文、动植物、法律、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是离不开的,在《与姚叔节》中,他感慨“不信西医者,皆愚人也。”这些言论在晚清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施培毅在为《吴汝纶全集》编写前言时谈到:“读过吴汝纶全集,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氏积极探求西学、介绍西学、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为我国近代教育奋斗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吴汝纶的文集中的确俯拾皆是,如《送曾袭侯入觐序》:“制度因革,每代不同苟其当于人心,不必悉于经典,至若格于时势,虽法出于古圣,必须变通。”倡导学习西方新文化,不必恪守“经典”。再如在著名的《天演论序》中,吴汝纶赞美此书“斯以信美”,对于《天演论》以及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些篇目都把西学纳入讨论范围,宣传新的思想,这是桐城派前所少有的,他在为桐城文章注入新鲜时代因素的同时,也扫除着本派文章的弊病。
桐城派得以成为统治清朝文坛时间最久的文派,与“义理”二字迎合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不无关系。“义理”要求文章内容符合程朱理学,比较典型的有刘大魁“义理、书卷、经济”说,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这在维新思潮兴起,封建统治江河日下的清末,必然因失去实用价值,阻碍思想更替而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吴汝纶的时代焦虑,发出“化雅为俗,中文何由通哉”的感喟,但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保证桐城文章的延续,吴汝纶也同时做出了淡化“义理”,而向审美追求靠近的努力,不失为对桐城家法的一次大胆革新。
所谓“义理”,其实不外乎用传统道德统摄文章创作,为了淡化“义理”,吴汝纶除了很少在文中宣扬“义理”,引入西学新话题而避之为上之外,还致力于对文章“雅洁”的追求。“雅洁”的重点在于对文章语言简练洁适的追求,另一方面,吴汝纶也有用“雅”来表示对白话文雏形时期的“俗”的反击。昔者方苞提出“清真雅洁”,是为控制知识分子思想,适应封建统治,而此时吴汝纶再倡“雅洁”,更注重的是避免文章的繁缛,加强实用性,这一定程度上是与新文学的要求一致的。对时代要求的迎合,文章创作向审美层次的转移,正体现了吴汝纶对于保全桐城派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评吴汝纶:“造语洁适,特为简练”,吴孟复也称其:“气清词洁,确是姚、梅本色。”都体现出吴汝纶文章这种“雅洁”的特点。
吴汝纶作为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自幼谙习桐城古文,又曾入曾国藩幕,列“曾门四弟子”之属。光绪十四年,吴汝纶辞官赴保定任莲池书院主讲,兼有着学者、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其“因声求气”论上承刘大魁、姚鼐、曾国藩等桐城先祖,而又在理论阐释、创作立意等方面有其发展新变,体现出对维护桐城派的努力。作为“莲池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吴汝纶文艺思想的研究是“莲池学派”文艺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价值。
[1]刘大櫆.论文偶记[M].郭绍虞,罗根泽《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M].光绪传忠书局本
[3]吴汝纶著 施培毅 徐寿凯校.吴汝纶全集·四[M].安徽:黄山书社,2000:1125
[4][5]同上p1131、p2
[6]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156
[7]曾光光.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J].江淮论坛,2001,第3期
[8]邓心强,史修永.桐城派文体学研究[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9]赵建章.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0.任雪山.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第30卷第2期
11.味经山房选本.吴挚甫文[M].北京:中华书局,1937
河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HB16WX009)
周晓坤(1996- ),女,河北省保定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