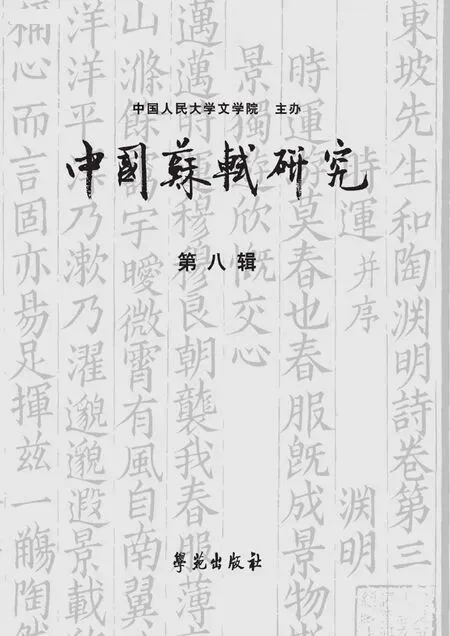苏轼的养生智慧及其当代启示
◇潘殊闲

一、苏轼的养生智慧
纵观苏轼众多的养生理论与实践,苏轼的养生已从个体修炼上升到一种可以沾溉万世的人间智慧,概而言之有五:
(一)心养
苏轼特别强调心神、心灵、心性、心境的调适与颐养。在给李伯时所作《老子新沐图》的赞文中有这样的感喟:
老聃新沐,晞发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与回,见之而惊。入而问之,强使自名。曰:“岂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于人,而丧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则全。四肢百骸,孰为吾缠?死生终始,孰为吾迁?彼赫赫者,将为吾温。彼肃肃者,将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万物生焉,物皆赖之,而况吾身乎?温为吾和,寒为吾坚,忽乎不知,而更千万年。葆光志之,夫非养生之根乎?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苏轼葆持一颗淡然之心、不受外在事物“形役”的自白。若人被周遭的人事所奴役,则丧失了天真与天意。假如人忘却这些林林总总的奴役,则能保全其天真、天意,自然也能保全其天命。所以,当一个人忘却了生死,泯灭了有无,齐同了寒温,就归于淡然,万物丛生,生命亦然。这种本真与自然,就是养生的根本。事实上,一个人的心态是影响其生命质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甚有一种说法,心态决定人的一切。再反观苏轼坎坷的一生,若没有良好的心态护佑,他可能早就在各种莫须有的打击陷害中愤懑而死了。
在苏轼看来,人之一念决定了人之一生,这一念的关键就在于“心”:
自有生人以来,人之所为见于世者,何可胜道。其鼓舞天下,经纬万世,有伟于造物者矣。考其所从生,实出于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复有烈于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万亿世界,于屈信臂顷,作百千万亿变化,如佛所言,皆真实语,无可疑者。
心为万法之宗,是善恶忧乐之源。养心就是养境界、养修养、养气度、养真识。就心境来说,苏轼有随遇而安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心灵的养护。苏轼到哪里,就声称自己是那里的人,我们可以从众多诗文中看到他的这种心路历程:“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在海南,由于条件有限,找不到洗澡陶盆(“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于是,受《云笈七籖》启示,睡前用双手揩摩身体,享受“干浴”的快意与自足,并风趣地以老鸡与倦马作比:“老鸡卧粪土,振羽双瞑目。倦马辗风沙,奋鬛一喷玉。垢净各殊性,快惬聊自沃。”这样的随缘自适,是培育良好心境的秘笈锁钥。何以会有这样的心境,苏轼在《问养生》中揭示了答案:
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谓和?曰: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何谓安?曰:吾尝自牢山浮海达于淮,遇大风焉,舟中之人,如附于桔槔,而与之上下,如蹈车轮而行,反逆眩乱不可止。而吾饮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异术也,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故凡病我者,举非物也。食中有蛆,见者莫不呕也。其不知而食者,未尝呕也。请察其所从生。论八珍者必咽,言粪秽者必唾。二者未尝与我接也,唾与咽何从生哉。果生于物乎?果生于我乎?知其生于我也,则虽与之接而不变,安之至也。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吴子,古之静者也。其观于物也,审矣。是以私识其言,而时省观焉。
这段文字就充满了苏氏智慧,其关键词即“安”与“和”。随遇而安,就能减少身心的伤害,因为“物之感我者轻”,故能保持宁静淡然的心境。而凡事不受外物干扰,与日月寒暑俯仰适变(也即“和”),自然因顺周遭环境的变化,故能与万物顺意,也即“应物者顺”。有这种心态,当然能减少许多莫名的烦恼与无谓的纷争;有这样心境,自然能生理调畅,病邪无由得接焉。类似的智慧,在苏轼留存的文献还有很多,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有这种心态,他就没有跨不过的坎,没有蹚不过的河。于是,他会释然地自我安慰:“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他会自我解嘲地自赞:“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会在简陋穷困中去营建美,欣赏美,不妨来读一读他的这首《次韵子由三首》之一《东亭》:
仙山佛国本同归,世路玄关两背驰。
到处不妨闲卜筑,流年自可数期颐。
遥知小槛临廛市,定有新松长棘茨。
谁道茅檐劣容膝,海天风雨看纷披。
苏轼确如他自己所说,喜欢“到处不妨闲卜筑”。即使远谪海南,他还是喜欢营造之乐。这个东亭临近市廛,又狭小,苏轼用“劣容膝”形容,虽有夸张,但颇为形象。苏轼驻足小亭,一个浩大的世界不禁在眼前敞亮,那就是“海天风雨看纷披”。建筑的小与海天的大形成强烈对比;物质的困穷、仕路的坎坷、人生的失意,与作者精神的富足、胸襟的宏大和生命的张力形成强烈对比。“海天风雨”,既是亭中所见实景,亦是作者心中的象喻。作者的言外之意甚明:人生无常,世路难料,但有弹性的生命,任由海天风雨的纷披,那倒是一种难得的风景,大可以尽情享受。
心养的智慧还在于要减少心的欲望。崇尚节俭既是一种美好的品德,又是一种人生的智慧。苏轼在给李公择的信中曾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少私寡欲,就少贪念;贪念少,失落就少,内心的不安亦少,就会活得轻松。
苏轼在黄州就有著名的“三养”说:“东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先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源于“一爵一肉”的节俭,苏轼发现了其中的三种境界——养福、养气与养财,而三种境界的背后则是安分、宽胃与省费。虽然这是苏轼在黄州困难时期的自白,但从中亦深刻反映了他的人生智慧。
(二)身养
生命在于运动,动静有常,劳逸结合,是养生之秘笈。苏轼深谙其道,他曾用人之一身譬如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有云: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劳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这段比喻非常生动,也十分精到。农夫小民终岁劳苦,却刚健强力;王公贵人衣裘乘舆,养之太过,反而容易患病成疾。苏轼虽非农夫小民,但他好动,闲不住,无论是在得意还是失意之时,他都喜欢劳作,或垦荒,或种植,或酿酒,或烹调,或掘井,或修造,或游览,或访客,总之不喜欢静默呆坐。与苏轼后人及门生多有交往的叶梦得在其笔记中曾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述:“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又载:“吾观自古功名之士,类皆好动。不但兴作事业,虽起居语默之间,亦不能自已……苏子瞻性亦然。初谪黄州,布衣芒履,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晚贬岭外,无一日不游山。晁以道尝为余言,顷为宿州教授,会公出守钱塘,夜过之,入其书室,见壁间多张古名画,爱其钟隐雪雁,欲为题字,而挂适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足坠地,大笑。”这两则轶事可以丰富我们对苏轼好动本性的认识。
运动仅是基本的要求,具体而言,身体的保养还有很多方法。比如气功,苏轼从数百方士之法中拣选简单易行者习之,感叹“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长生不死非虚语”,其具体做法如下: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候出入息匀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津液,未得咽下。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类似于这样的身体炼养,苏轼还有很多种,如静坐法(《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能,题诗寄屋壁。”),还有“寝寐三昧”法。
苏轼对人生的寿长与生命的质量非常看重,所以对道教养生多有兴趣,诸如内丹功、龟息法、胎息法等都是为他所瞩目并努力尝试的。当然,苏轼的身养方法还有很多,如梳头、漱茶、午睡、步行、洗脚、早寝等,都是简单易行且非常有道理的。
(三)食养
民以食为天。食是大事,不可草率行之。苏轼于食养保健颇有智慧,其《养老篇》云:“软蒸饭,烂煮肉。温美汤,厚毡褥。少饮酒,惺惺宿。缓缓行,双拳曲。虚其心,实其腹。丧其耳,忘其目。久久行,金丹熟。”此篇颂文虽综论养生,并不局限饮食,但里面涉及的食养也弥足珍贵。类似这样的食养智慧,苏轼还有很多,如:“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这是与时令相合拍的食养。即便是日日三餐,苏轼也有智慧,主张食不过饱,即所谓“宽胃以养气”。
苏轼一生走过很多地方,无论是为官还是罹祸,他都能就地取材,入乡随俗,各种山珍、蔬果、海味等,都可成为他创意美食的素材与灵感,成为他补充维生素、蛋白质与满足口福的重要来源。于是各种披上东坡灵性与智慧的菜肴香飘久远,如二红饭、豆粥、鱼羹、菜羹、山芋羹、东坡羹、东坡肉、东坡鱼、炙羊脊骨等。
(四)药养
食五谷生百病,祛病强身并非不可用药。药用得好,会和五脏,益寿延年。苏轼这样谈养生:“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药养是不得已而用之。但药养是有讲究的,并非随便用药,而应选择上品之药,这种药性质温和,对人体无害,故久服能强身。反之,不懂这个道理,用劣质药,用猛药,则只会耗损身体,葬送生命。
同理,药养也讲究保健,并非一定要等到生病之后治疗,从本质上说,药养更多的还是强调平时的保健强身,用一些保健药材,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制作服用。事实上,有些药材是药、食同源,药、食双性,或者说是天然的保健品,如苏轼青睐的每天嚼服芡实,还有菊花、枸杞、胡麻(芝麻)、石菖蒲、茯苓、大枣、黄精、松节、苍耳、槟榔、沉香、地黄、当归、玄参、羌活、灵芝、薏苡等,苏轼或作丸,或作散,或浸酒,或作茶饮等。
(五)境养
所谓境养,就是着眼环境的养生智慧。苏轼对生活环境非常看重,着意营造惬意的景致,人们熟悉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见他对优美环境、新鲜空气的倚重超过美味。苏轼每到一处都愿意花费精力营葺园地,改善环境,即使是在贬谪中,也会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改变、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使之生意盎然,惬心舒怀。如死里逃生的黄州之贬,先是居无定所,在定慧院、临皋亭、天庆观流寓,后得州治之东一废弃营地,始奋力垦荒,躬耕垄亩,十分艰辛。苏轼曾有自序:“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懃,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在东坡,苏轼不仅种庄稼,还植种枣树、栗树、松树、桑果、竹林等,“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在东坡,得于邻里朋友的帮助,苏轼还营建了宅屋,因大雪中建成,故取名为“雪堂”:“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雪被称为雨之精灵,是洁净、美好、吉祥的象征,苏轼将其绘于四壁,有“澡雪精神”、瑞兆来年的意味,也是美化居室环境、怡然心境的重要举措。
在惠州,得古白鹤观隙地数亩建居所,白鹤峰新居设德有邻堂、思无邪斋,堂前杂植松、柏、柑、橘、柚、荔、茶、梅诸种树木,景色优美。苏轼在给毛滂的信中这样说道:“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
在儋州,苏轼克服“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窘境,下决心在昌化军城南紧邻天庆观之处购地修茅舍五间,自命为“桄榔庵”,于庵周围环植兰桂竹树等植被,烟雨濛晦,苏轼自言:“近与儿子结茅屋数椽居之,仅庇风雨,……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又云:“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蒙晦,真蜒坞獠洞也。”在《和陶和刘柴桑》中说:“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黄橼出旧枿,紫茗抽新畬。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在《新居》中说:“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可以看出,苏轼是在艰苦困顿中积极去营造美,发现美,欣赏美,“寄我无穷境”,“俯仰可卒岁”。这种境养,助苏轼心与境通达,情与理融贯,美不胜收。
二、苏轼养生智慧的现代启示
养生的主体是人,只有人才会有这样的益身、延寿的主体意识。但养生并非只是一种意识,它需要由意识到行动。人离不开具体的生存环境,离不开周遭的人际关系,因此,养生必定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人、环境、物质。人是根本,环境是条件,物质是保障。就养生这一概念而言,需要明确以下几层概念与关系:
首先是养生的意识。一个人若没有养生的意识,即使身处仙境,即使锦衣玉食,也可能抑郁寡欢,甚或自轻自毁。所以,养生的意识是前提,是关键,缺乏它,其他可能都是空谈。
其次是养生的环境。再有养生的意识,但身处空气、水、土壤、食物等各类高污染聚集的地区,纵然能自我调适,自我炼养,事实上也不能做到“洁身自好”,特别是一些重金属和化学合成物的污染,脆弱的肉身难以抵抗,健康长寿对这些地区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或者是幻想。当然,养生的环境还包括家庭习惯、家族风气、时代氛围、区域习俗、民族特色、人际关系等。
再次是养生的物质保障。一个人有养生的意识,也身处良好的环境中,但若没有基本的物质的保障也是不行的,如物质匮乏、医疗条件落后,也不能保证能够颐养天年。
可见对养生而言,养生意识、良好环境与必要的物质保障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如果说养生意识属于精神层面,那么良好的环境与必要的物质保障就是物质与精神的混合层面。精神与物质必须并行不悖,方可相向而行,实现康养幸福。

一是强烈的养生意识。苏轼作为蜀人,深受蜀中文化的影响。巴蜀地区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其文化禀赋特质在多方面异于中原等地区。最明显的就是杂家风范与创新意识。大禹出生在四川;“易学在蜀”是理学大师程颐的评价;“古蜀仙道”传承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道教就是在古蜀仙道的基础上创立的;佛教在巴蜀有深厚渊源,以至唐末僖宗时已出现了“菩萨在蜀”的说法。巴蜀文人深受这种地域文化的熏染,普遍精通易老庄,杂糅儒佛道,其他诸如纵横之学、炼养击剑,亦多喜爱。苏轼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蜀中之人往往不囿旧说,敢于标新立异,张扬个性,苏轼也是突出代表。苏轼对养生有特别的癖好,养生意识非常强烈。他喜欢结交三教九流人士,喜欢打探琢磨各种养生验方、秘方,并着手实践,且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人,急欲分享。最为重要的是,苏轼对穷与达、荣与辱、得与失、苦与乐等有辩证的认识,能够有意识地调适心态,在人与环境、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我中寻求和谐,因此,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在条件美好还是条件恶劣的地方,他都能很快适应,活得自在坦然,并高度认可与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苏轼活在当下,心底无私天地宽,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尽管各种险恶手段用尽,恨得咬牙切齿,但苏轼在失意中发现属于自己的美:“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此味甚佳,生来未尝有此适。”依然可以“报道先生春睡美”,依然能够“更著短檐高屋帽”,且惊叹“东坡何事不违时”,甚至高唱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无论是被动的远谪迁徙还是主动的劳作运动,苏轼都在劳与逸、动与静、乖与和中努力寻找平衡点,不忘养生的初心,永葆生命的张力。
二是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苏轼一生大起大落,人生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处于人生顺境时期固不用说,单说那些处于人生低潮狼狈难堪的贬谪时期,苏轼稍事安顿之后,总会想方设法力所能及地营造自己满意的住所,并在堂前屋后环植各种植物。这些住所虽然与“华焕”无关,但苏轼善于通过室内的简单修饰与室外的植物映衬与环境烘托,达到屋内小景与屋外大景的相互补充与融通,使自己置身其间,百变风云,俯仰卒岁。如在黄州建造的雪堂,画了满壁的雪,让苏轼兴奋不已,直呼“真得其所居者也”。联想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与飞鸿构成了人生的无限象喻。这首早年和兄弟的诗作,竟真的成了他人生的写照。人与环境往往会构成互动与互融的关系,人们常说“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心与物(相、环境)的确是相通的,也难怪苏轼会有“真得其所居者也”的感慨。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也道出了心与物、情与貌的互动关系。在惠州,苏轼自述其居无定所的窘况:“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居无定所,没有固定安稳的生活环境,也就缺乏生存的安全感,所以,条件再艰苦,也得想办法改善。当白鹤峰新居建成,苏轼情不自禁地叙述那份艰辛与自足:“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青山满墙头,?鬌几云髻。虽惭《抱朴子》,金鼎陋蝉蜕。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青山静待雪浪,如此生意盎然的居所,苏轼满心欢喜,直言“规作终老计”,“俯仰了此世”。可见环境于人是相当的重要。
三是基本的物质保障。精神与物质,是生命的两种形态,或者说两种条件。精神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人毕竟是肉身,衣食住行等都不能少。苏轼自谓平生“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此话貌似愤激之辞,实则是有深刻道理的。人在物质条件好的时候,对生理的基本需求并不会特别在意,只有在生存受到威胁、生命面临挑战的时候,才会凸显出来。无疑,黄、惠、儋三州是对苏轼生存与生命的严峻考验。三州的条件一个比一个差,苏轼必须认真面对。在黄州,苏轼不得不拿起耒耜开辟茨棘瓦砾之荒地,为的是自给自足。他在困苦中善于就地取材,用当地的原材料,创意烹调,享受属于自己的美食与美味。再者,人在艰苦条件中,就要善于保养。人不是一定要等到病了之后才去寻药保健,而应未雨绸缪,立足于强身健体,尽可能减少疾病的危害。前面所述各种食养与药养,大多就是苏轼在现有条件下的各种小创意、小发明、小实践,这些创意、发明与实践在当时就已经使自己及家人受益,并惠及友朋与大众,有的甚至风靡当时,影响久远。今天,苏轼的这些食养与药养智慧与实践,已经变成了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视,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注
释
[1] 钟来茵《苏东坡养生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潘殊闲《叶梦得与苏轼》,巴蜀书社2009年版。
[3](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5] 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潘殊闲《快意雄风海上来:试论苏轼海南诗词的“海”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7](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话》(卷上),石林遗书本。
[8](宋)叶梦得撰《岩下放言》(卷下),石林遗书本。
[9](宋)李廌撰《师友谈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 谭继和《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2] 徐汉明校勘《辛弃疾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