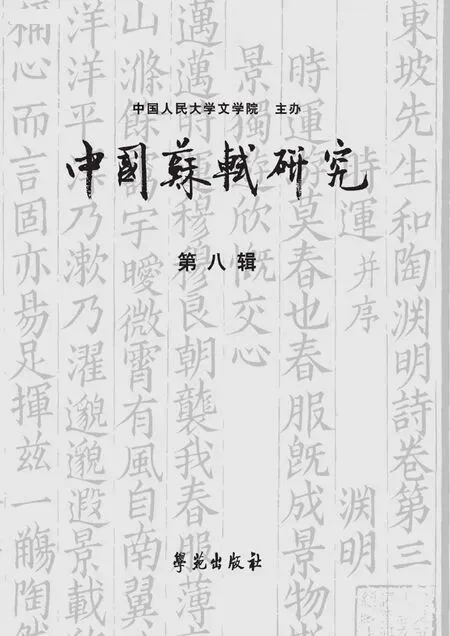论苏轼理趣诗中的悲剧意识
◇包树望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文学小言》)王国维先生认为苏轼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人格典范。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实践者,诗词文皆有巨大成就和贡献,其诗歌创作对于宋诗的最终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如严羽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对于苏诗与前人的不同,刘熙载认为:“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艺概》)这里的趣是和理联系在一起的。“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邵康节诗,直头说尽,有何兴会?”(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将诗中的理语和理趣区分开来。这符合实际,以苏诗为例,与理学家的表达哲学理念的诗歌不同,苏诗的很多理趣诗有着丰富的人生思考、人生哲理、人生内容,其中兴会与寄托的运思、表达机制构成理趣。冷成金先生认为:“宋诗的‘理趣’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不仅以‘趣’来装点‘理’,而且化‘理’为情,在更高的层次上与美的本质相契合。”与理不同,情与现实生活、感性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存真相是悲剧性的,这也就使苏轼理趣诗中的情和理都关涉到悲剧意识。探讨苏轼理趣诗中的悲剧意识有助于深入理解苏轼理趣诗及其中蕴含的苏轼对现实悲剧性的感知、思考、超越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轼“亦自足千古”的人格精神世界。
一、超越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人生有限情无限。”(晏殊《踏莎行》)人要“活着”是人的内在亲证,而人不能永远活着,生命的有限构成了首要的现实悲剧性。在先秦汉唐的政治本体化时代,人们以现实政治秩序、现实社会功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对政治本体的体认与乐感中。但是,政治本体并不能时时处处为人提供归宿,一旦遭遇现实挫折、政治衰败,人们难免对其产生追询、质疑,于是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兴起生命悲剧意识。这在政治本体让位于文化本体的宋代,也多有表现。比如,
西望穆陵关,东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红裙欲仙去,长笛有余哀。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回。自从有此山,白石封苍苔。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现实政治不再能够为生命存在提供价值,在仕途蹭蹬的坎坷生命历程中,诗人环视宇内,打开历史时空,萌生归隐之意,以“狂饮亦荒哉”“长笛有余哀”点出悲剧意识,其后“清歌入云霄”等八句具体写出悲剧意识的兴起缘由和内容,诗人认为清歌妙舞代表的美好的感性生命生活是古之未有,故更加珍重、眷恋,不忍离去,但是生命如同烛膏和朝露般有限和短暂,美好的感性生命生活并不能长久,面对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诗人兴起悲剧意识。诗人并未沉浸于生命悲剧意识,而是超脱出来,“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以佛家思维揭示万物终将消散的悲剧性现实。这并不是对生命悲剧意识采取默认、消解的方式,也不是走向颓废,而是以庄子的无限扩大事物参照系的方式,在诗作的内在理路的作用下予以深情感慨、审美超越。所谓深情感慨就是对现实困境不做直接的对等的回应,不拘泥于具体的事物和功利,而是进行审美观照,指向总体的根本的原则,这种观照是洞悉了人生悲剧真相后的开悟和解脱。最早的典型代表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既然流水不可把握,那就应像流水一样执着现实,把握可把握的,做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有前面对美好感性生命生活的珍视、眷恋,在“人要活着、更好地活着的内在亲证”的动力下,“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不会走向颓废,而是指向对悲剧性现实不做对等回应,超越具体的功利和目的,把握可把握的美好的感性生命生活,对生命过程予以审美化。整首诗并不是空疏、僵硬地说理,内在理路鲜明而深切,蕴理于情,化理为情,不仅是“趣”来装点“理”,更是通过化理为情的方式对理的审美化体认,同时实现了对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
《读孟郊诗二首》(其一)与《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类似: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越,竟日持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读孟郊诗二首》其一)
诗人以丰富贴切的比喻描述自己阅读孟郊诗歌的审美感受,表达自己对孟郊诗歌的审美评价。至“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陡然揭出生命有限而日夜流逝的悲剧性现实,兴起生命悲剧意识。但诗人并不直接回应这种悲剧意识,而以之与读孟郊诗歌的审美感受、诗歌所反映的孟郊的凄清寒苦的心理和悲剧性的现实生活相对比,认为不必再读孟郊诗歌,而是选择玉醪佳酿代表的美好感性生命生活,超越“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的生命悲剧意识。诗人对孟郊诗歌的评论生动贴切,富有理趣,在揭出“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的生命悲剧真相之后,认为“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是理性的选择,但这种理性选择却并不是纯粹概念说理而来,而是以对美好感性生命、现实生活的深情为基础和指向,以“人要活着、更好地活着的内在亲证”为动力,所以是理由情生,化理为情,达到以玉醪佳酿代表的美好感性生命生活对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诗作这种情理互生的内在流程使其富于理趣。与《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不同,《读孟郊诗二首》(其一)中生命悲剧意识的兴起有背景、参照系的意义,并在最后给出了玉醪佳酿代表的美好感性生活生活,而《登常山绝顶广丽亭》则是在“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的生命悲剧意识之后,直接跳脱出来,以“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为结束,从更廓大的视角审视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真相,两首诗内在流程不同,但同样富有理趣,都实现了对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
由此也可看出苏轼诗和李贺诗中的生命悲剧意识的不同。李贺诗(如《天上谣》、《将进酒》等)往往在极尽描写生命、生活的美好之后,猛然翻出永恒的时间映照下的生命的短暂与无常的悲剧真相,并以之给人在绝望中建构价值的冲动,促进价值的崛立,其中情感的因素极为炽烈,苏轼诗中其对生命悲剧意识的表现相对沉静,对生命悲剧意识的超越是情理相互促生而成。
先生依旧广文贫,老守时遭醉尉嗔。
汝辈何曾堪一笑,吾侪相对复三人。
黄鸡催晓凄凉曲,白发惊秋见在身。
一别胶西旧朋友,扁舟归钓五湖春。(《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
首联感叹三人依旧生活贫苦、身世坎坷,为醉尉所嗔斥,表达个人现实境遇的悲剧性;颔联认为那些“醉尉”不堪一笑,诗人珍视的是好友三人又得相聚,以知己重逢、人际温暖超越悲剧意识;颈联写晓晨离别,而三人年华迅速老去,再聚不知何时,再次兴起生命不永、聚少离多的悲剧意识;尾联通过“扁舟归钓五湖春”的渔樵归隐的本真生活,超越生命悲剧意识。
《入峡》也是如此。“……气候冬犹暖,星河夜半涵。遗民悲昶衍,旧俗接鱼蚕。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崄,得米不盈甔。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叶舟轻远泝,大浪固尝谙。矍铄空相视,呕哑莫与谈。蛮荒安可住,幽邃信难妉。”诗人描写峡中自然条件恶劣、百姓生活艰苦简陋,接以入峡艰难,既叹息峡中百姓生何陋,又叹息自己仕宦奔波、羁旅局促,揭示生命的现实悲剧性,兴起生命悲剧意识。“独爱孤栖鹘,高超百尺岚。横飞应自得,远飏似无贪。振翮游霄汉,无心顾雀鹌。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化用《庄子·逍遥游》,写孤鹘虽孤,却高飞、远飏,不贪食、不顾雀鹌之属,得高超之乐,而世人多为物欲观念所束缚,沉溺于世俗富贵荣华之中,两相对比,表达自己不愿仕宦奔波,向往甘心远遁的孤鹘代表的隐逸生活。诗人通过哲理运思,以飞鸟譬喻,超脱富贵、仕宦等代表的非本真生活与观念的束缚,以隐逸代表的本真生活超越生命悲剧意识。
人事无涯生有涯,逝将归钓汉江槎。
乘桴我欲从安石,遁世谁能识子嗟。

清谈美景双奇绝,不觉归鞍带月华。(《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首句即揭示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次句以归隐渔樵超越这种现实悲剧性。三、四句追慕留子嗟、谢安,进一步表达归隐之愿。五、六句写美好自然的自然而然。七、八句写身处这种美景中,清谈、赏景而不觉时光流逝,诗人达到了超越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后的清明、恬淡的美好境界。
二、建构精神家园
从中唐至两宋,悲剧意识从政治本体层面进入了文化本体的层面,对文化价值展开探询,即在现实政治不再作为思考世事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背景下,在生命有限、宇宙中性、价值无解的前提下,追询人生的价值、意义与归宿,兴起价值悲剧意识。苏轼理趣诗中价值悲剧意识突出表现为对精神家园的追询。苏轼在诗词作品中对故乡的思念、归家意识和对家园的追寻随处可见,试看:
故人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寄蔡子华》)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华阴寄子由》)
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
笑指西南是归路,倦飞弱羽久知还。(《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
东南此去几时归,倦鸟孤云岂有期。(《七年九月自广陵召还复馆于浴室东堂……》其三)
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留题显圣寺》)
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题宝鸡县斯飞阁》)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一)
一别胶西旧朋友,扁舟归钓五湖春。(《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
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次韵滕大夫三首·雪浪石》)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其一)
与唐人不同,苏轼对故乡的思念更为具体、深切,归家意识和对家园的追询更为浓烈、执着,对故乡难归有着清醒认识,诗作中的悲剧意识也更为浓烈、深切,苏轼在特殊的文化心理机制作用下,最终找到了精神家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轼将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中一般的羁旅离别之情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富于理趣。首联因人生劳碌奔波兴起理性追询,以偶然、短暂的雪泥鸿爪揭示人生转瞬即逝、漂泊无依的现实悲剧性,给人沧桑变幻、虚无缥缈之感,属于价值悲剧意识。“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表达得更具体。良辰美景、美好的感性生命生活为诗人珍惜、眷恋,但美好难以永恒,命运无从把握,人事无常,人生漂泊不定,给人以无所着落的悲剧感。“这个意思在苏轼诗里屡次出现,例如《十月十五观月黄楼席上次韵》:‘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又《和子由山茶盛开》:‘雪里盛开知有意,明年开后更谁看?’”《和孔密州·东栏梨花》更为典型:“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石花满城。惆怅东兰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清明时节,梨花盛开,随后由盛转衰,而人生中此种美好亦难有几何,使人伤感、惆怅、迷茫,作者将这种伤感上升到人生的高度,揭示出人生短暂、空没、无所归依的现实悲剧性,属于价值悲剧意识。第四句通过飞鸿不为雪泥指爪及其具体指向而挂怀,给出对待漂泊人生应采取的态度,即人生在世亦应采取达观的态度,不为聚散辗转所羁绊,超越了前面的悲剧意识。苏轼以雪泥鸿爪譬喻、思考人生的现实悲剧性,将人生提升到形式的层面,指出人生应遵循的自然之理,是通过理的思考超越了因理的追询而产生的价值悲剧意识。这里的理的追询和理的思考都以对现实人生、现实生活的无限深情、眷恋为基础、指向和动力。
颈联和尾联以具体人事对前两联的情理流程进一步展开、体认。颈联写具体人事的沧桑变迁,具体说明首联、颔联表达的世事变幻、人生沧桑之理和人生空没感,同时也是以之前体悟到的人生之理观照、审视人生的现实悲剧性。尾联以“路上人困蹇驴嘶”表征往日崎岖,超越对过往种种具体细节的执念拘泥,直指生活的形式,体认前面揭示的人生之理。这也是“深情感慨”,对人生现实悲剧性不作对等回应,而是超脱出来,予以审美观照,从容而坚定地面对必然的人生坎坷和漂泊,达到化理为情后的审美的人生境界,从而构建精神家园。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
一二句概括描述自己离乡宦游、不得归家的漂泊人生,内含悲剧意识。“闻道”四句将个人漂泊引入历史时空,在廓大的历史时空背景审视、思考人生,深化悲剧意识。其后写羁旅思乡之情,并因奇异江景,引发深思,认为异景为警,遂以江水为誓,定当归隐。诗人在自然异景的触发下,思考人生,与自然展开对话,超越悲剧意识,不再拘泥于具体地理上的故乡和具体的自然异景,而是有田即归,其实是归于美好自然映衬下的审美的人生范式、人生境界。苏轼思沉而情深,自然异景、鸿落鸿飞都成为他思考人生的契机,以对人生之理的体认、归隐生活的选择,超越现实悲剧性,建构精神家园。
霭霭青城云,娟娟峨嵋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谓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无一物,清江饮君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马下。不用惊走藏,使者我友生。听讼如家人,细说为汝评。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送运判朱朝奉入蜀》)
首句至“跳波吹枕屏”,苏轼语调低柔,娓娓道出对故乡的热爱、眷恋、思念,同时写出故乡难归的悲剧意识。之后,诗人点出赠别主题,并劝慰乡人,然后再次回到自己的归乡意识。诗作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作结,指向审美观照下的自然本真生活。整首诗从寻找家园、表达悲剧意识开始,通过送别友人、劝慰乡人和请友人代为答问的过渡,超越悲剧意识,找到了精神家园。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诗题言明诗作缘由。诗人将梦中得句和梦觉后的清风急雨作为思考与感悟人生的契机。首句至“四顾真途穷”兴起追寻家园而不得的价值悲剧意识。“眇观大瀛海”至“永啸来天风”,以庄子扩大参照系的方式,统观宇宙自然,消弭事物的差别,超越对具体地点、目的的执着。以理性哲思超越悲剧意识,“幽怀”由此“破散”。“千山动鳞甲”至“不闻蓬莱宫”是“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幽怀、悲剧意识经过理性哲思的洗礼,被破散、超越后,所达到的与天地相通的廓大的审美体验、审美境界。同样以日常情景为思考与感悟人生的契机,与前引《游金山寺》《和子由渑池怀旧》《送运判朱朝奉入蜀》三首不同,《行琼儋间,……》的境界更为超脱旷达,这是因为苏轼在岭海时期达到天地境界,建构了审美的精神家园。在这种审美境界观照下,诗人能于功名利禄、贫富穷达、贵贱寿夭等世俗观念、评价标准了无挂碍,“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将内在精神家园的构建视为功业。
就本质而言,生命悲剧意识属于价值悲剧意识,在宇宙中性、价值无解的背景下,因生命有限的悲剧性现实而兴起,所以二者相通,在许多诗作中不能截然二分,而是相互伴生、促生,由生命悲剧意识上升为价值悲剧意识。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首二句先追忆上次见文长老时情景,后写文长老溘然而逝,兴起生命悲剧意识。三、四句用佛典、佛语,将自己对文长老的三次过访与其老、病、死相联,在无限、永恒的时间中审视生命与人生,凸显生命与人生的短暂与无常。第五句写自己因近年好友多有故去,已然惯见、无泪,由具体一人上升为普遍众生,给人空没之感,将生命悲剧意识提升到本体高度,即指向人生价值的价值悲剧意识。但诗人并未因此走向虚无、颓废,仍对故乡、故友、世事人生饱含深情。唐代袁郊所作《甘泽谣·圆观》中,圆观亡前与好友李源相约十三年后相见,李源十三年后得见牧童,牧童吟诗:“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往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苏轼据此作《僧圆泽传》(《苏轼文集》卷13)。七、八句以此故事为喻,表达希望再与文长老相见之情,其实是以深情超越生死、超越悲剧意识,以此深情为精神家园。此深情是指对现实人生、感性生命的深情执着,体现了苏轼执着而超越和以情为本体的思想。《东府雨中别子由》亦如此。
健美操课的学习评价主要评价学生在课中知识与技能与健美操活动中具体表现,通过评价以提高学生体能与技能水平,健全其人格品质。经过调研发现:在河南省健美操课的学习评价不够系统全面,主要是以技术考核为主,很少学校是对学生的专项身体素质和技能的总体考核,不利于提高学生技能水平和学习能力。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东府雨中别子由》)
前八句写梧桐见证兄弟团聚离别。九、十句既是对朝政走势的判断,更是以人生哲理,将前述“白首归无期”的价值悲剧意识进一步深化。最后四句折赠梧桐枝,祝愿健康归来,并以“此时情”为归依,即以人际温暖的情感为精神家园,超越前述悲剧意识。
三、苏轼理趣诗中悲剧意识的意义
在唐宋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学作品中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也转为对文化本体的追询。人们不再以外在的政治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是转向内在文化心理追询,建构价值与意义。苏轼将其坎坷的人生经历、深入的哲学思考、深厚的艺术才能和对世事人生的无限深情熔铸在丰富的诗歌创作中。所以,与理学家不同,苏轼理趣诗不是纯粹哲学理念的描摹表达,而是从现实人生、感性生命出发,有着对人生的深情与思考、深沉的悲剧意识和对悲剧意识的超越。如前所述,苏轼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境作为感悟人生、追寻精神家园、超越悲剧意识的契机,《慈湖夹阻风五首》于此更加典型,其内在情理流程也十分清晰。
捍索桅竿立啸空,篙师酣寝浪花中。
故应菅蒯知心腹,弱缆能争万里风。(其一)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其二)
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
千顷桑麻在船底,空余石发挂鱼衣。(其三)
日轮亭午汗珠融,谁识南讹长养功。
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其四)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其五)
被贬南行,在当涂遇风受阻,诗人描摹风浪中的劳作、生活场景等,感悟人生,作组诗五首。第一首写风大浪高,船工安然,船缆虽弱却能与风浪抗争,内含执着、坚韧。第二首前两句在水浪接天、青山无数的背景下揭示出归路茫然、此生无依的悲剧意识,后两句写风浪中犹有小船卖饼执着生活,并告知村落在前,使悲剧意识为之一缓。纪昀评:“当前之寥落可知。然此二句,乃遇风泊船,初不辨头路人语,惟老于江湖者知之,非道眼前寥落也。”揭示了诗作中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深沉的悲剧意识在苏轼诗作中有更显豁的表现,如:“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淮上早发》)第三首以相似情景表达对韩愈的知己之感和相同的孤独感受。第四首写天空转晴,风雨虽大,却并不能妨碍明月当空,表达积极乐观的态度。第五首揭示出人生本就到处险峻难行的常态和应然之理,并选择不为之所拘束、欹侧而过,超越了前面的悲剧意识。组诗是苏轼在行旅风雨中感悟人生的过程,第一首即点出阻风之题,以篙师、弱缆蕴自然之理,奠定诗作执着而超越的基调;第二、三首抒写悲剧意识,但以小船卖饼、墟落在前和同于韩愈来予以缓解,情中含理;第四首写天空转晴,第五首归为对人生坎坷命运的本然之理的体认与深情感慨,化理为情。悲剧意识由兴起而超越,诗人由此建构价值,找到精神家园,提升人生境界。

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悲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法惠寺横翠阁》)
前八句写吴山、法惠寺横翠阁美景。其后八句先写思乡之情,次写人生易老,再感叹百年兴废,在廓大的历史时空中感叹现实悲剧性,将不能归家、生命不永的现实悲剧性提高到人生本质的高度,生命悲剧意识转为价值悲剧意识。最后两句写自己将与吴山共在长存,既不是以自然比德,也不是赋情自然、融入自然,而是经过悲剧意识的洗礼,自然成为丰富、发展自我的方式和彰显人格的手段。吴山的自然而然的美好、永恒使诗人超越了悲剧意识。
综上,苏轼理趣诗并不是简单地对自然之理、哲学之理的摹写、体认,或简单地以自然之理譬喻人生世事之理,苏轼理趣诗中有此类作品,但这些作品并不是苏轼理趣诗与其他宋代诗人的理趣诗区别开来的代表作。苏轼理趣诗往往与现实人生、感性生命直接相联系,富含现实内容、悲剧意识、本真情感和对现实悲剧性的揭示、思考、超越,哲理是思考人生的工具、超越悲剧意识的梯航(如前引《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行琼儋间,……》),对现实悲剧性的揭示、思考、超越是以情促理、化理为情、情理互生的内在理路的具体表现,比纯粹的哲学理念、自然之理的表达,更为切近、鲜活。这是苏轼理趣诗符合诗的审美本质、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恒久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也使苏轼理趣诗对滋养人们的心灵、促进心灵成长、建构价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苏轼理趣诗中的悲剧意识,我们可以窥见苏轼乐观旷达精神的情感来源和其情感与哲思互生的形成理路,切近地感受苏轼丰富、深微、伟大的人格精神世界。
注
释
[1]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冷成金《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7]《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8]冷成金《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9]冷成金、董宇宇《论李贺诗的悲剧意识》,《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0]钱钟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苏轼词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