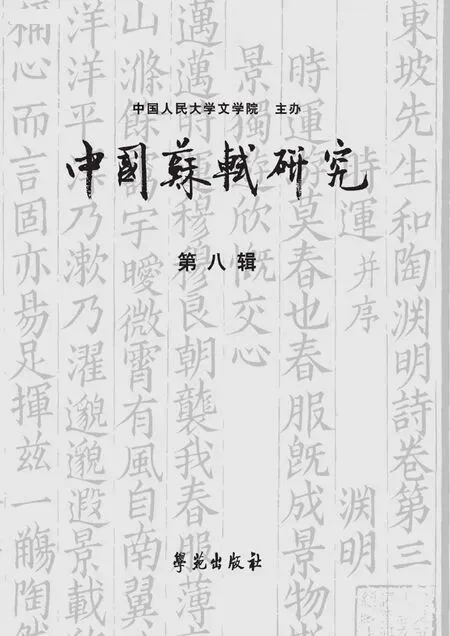悲剧情怀与苏轼形象的理想化
◇宋春光
历史人物形象往往具有先天复杂性,因其脱胎于第一历史,却又非第一历史的再现,而是随着时空的拓展不断生成的。苏轼形象在某个时代的生成,正是由这一时代众人之眼观苏轼而完成的,故而也是这一时代人们思想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形象的历史生成所展现的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在这一历史生成的过程中,苏轼形象有着明显的不断被理想化的趋势。本文仅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处的悲剧情怀的角度,对苏轼形象历史生成中被理想化这一现象加以分析,以期借此管窥悲剧情怀在历史人物形象被理想化过程中的作用。
一、洒脱旷达与诗酒生活
苏轼性格中,自有其洒脱豁达乃至超然脱俗的一面,并且,从相对意义上说,其豁达超然的程度不仅度越时辈,甚至可称千古一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凡此种种皆为明证,世人亦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本人已达到了绝对意义的超然物外。然而,在后世的历史生成过程中,苏轼本人洒脱旷达的性格特点被不断强化、绝对化,乃至脸谱化,并最终成为苏轼形象最重要的性格标志,这也是在客观上促成苏轼形象理想化的重要因素。
苏轼形象洒脱豁达性格特点的强化、绝对化、脸谱化,是与乌台诗案、黄州之贬、赤壁之游的经典化相辅相成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宋人笔下的苏轼并非绝对意义的旷达,更多展现的是其作为凡人临大难时的错愕与惊慌。《孔氏谈苑》记有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捕的情形:
僎(按,皇甫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颇权州事。僎径入州厅,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为服,自以当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二卒怀台牒挂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语,人心益疑。轼惧曰:“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颇乃前曰:“大博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颇曰:“无颇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及开视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狱卒就执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被捕时的仓皇无措在《萍州可谈》中也有记载:
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上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
在去往京师的途中,苏轼甚至想一死了之:
子瞻自维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身入水,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言已有不幸,子由必不独生也。由是至京师,下御史狱。李定、舒亶、何王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常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
被贬黄州,苏轼生活窘迫:
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不仅如此,苏轼还疾病缠身,“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就连苏轼自己都说:“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诸如此类,不一一赘述。诚然,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中的狼狈并非苏轼在宋人笔下的唯一面相,以上宋人所记的真实性或亦有可堪置疑之处,但这些记载的存在本身便足以证明,苏轼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其性格中洒脱豁达尚未被刻意强化。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打破,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不断被理想化,黄州、赤壁也随之成为展现苏轼洒脱旷达的经典场域。
明人陆树声所撰《清暑笔谈》记载:“东坡偕子由齐安道中,就市食胡饼粝甚,东坡连尽数饼,顾子由曰:‘尚须口耶?’”这种“饮酒但饮湿”式的随性洒脱在清人笔下得以进一步的诠释,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中写道:
《经锄杂志》:李太白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东坡《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之意盖自太白诗句中来。夫风月不用钱买而取之无禁,太白、东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风明月之可乐者,世无几人。清风明月一岁之间亦无几日,即使人知此乐,或为俗物牵夺,或为病苦妨碍,虽欲赏之,有不能者。然则闲居无事,遇此清风明月,既不用钱买,又取之无禁,而不知以为乐,是自生障碍也。

与苏轼的贬谪生活相同,苏轼的仕宦生活也被逐渐理想化。作为一代名臣,苏轼有徐州抗洪的政绩,有元祐金莲烛送归的恩宠,但后人更为津津乐道的却是苏轼为政杭州时的诗酒生活。秦观曾戏语道:“十里薰风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这种“公事湖中了”的情景被后世一再提及,不断敷演,将苏轼的仕宦生活诗化,并最终以诗酒生活取代“案牍之劳形”,成为苏轼形象标志性的仕宦生活场景。《梁溪漫志》记载了南宋绍兴一老僧对苏轼的回忆:
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夹道灯火,纵观太守。有老僧,绍兴末年九十余,幼在院为苍头,能言之。
文字间可见老僧对昔年苏轼风神的无比神往,而费衮之所以能够采录这段回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段回忆中所展现的场景深契南宋时人对苏轼仕宦生活的历史想象:泛舟绝湖而来,谈笑间,据案剖决,僚吏剧饮,乘马而归,众人瞻仰,惊为天人。这种将仕宦生活诗意化、将辨讼断案才情化的倾向,所展现的正是人们对苏轼政治生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后世因接受主体而不断理想化。《桃源手听》记载:
东坡为钱塘时,民有诉扇肆负债二万者。逮至,则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偿也。”公令以扇二十来就判。事笔随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才出门,人竞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遂悉偿所负。
《西湖游览志馀》记载:
苏子瞻佐郡日,与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为方外之交,尝同泛西湖。有诗云:“三吴雨连月,湖水日夜添,寻僧去无路,潋潋水拍檐。驾言徂北山,得与幽人兼,清风洗昏翳,晚景分浓纤。缥缈朱楼人,斜阳半疏帘,临风一挥手,怅焉起遐瞻。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传神所歼。”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清代话本《六桥才迹》称,“东坡在杭州做官,不但诗酒流连,就政事也自风流”,直可代表时至清代,世人在诸多前理解的层累之下形成的对苏轼仕宦生活的认知。
二、苏、王对立与圆满结局
通过对宋代笔记的考察可见,苏轼与王安石的对立关系是被逐渐深化并趋于定型的。苏、王二人的对立关系在元修《宋史·苏轼传》已近模式化: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而受到王安石的排挤打压,两人处于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皆源于王安石私德有亏、党同伐异,而与苏轼无关;面对王安石的咄咄逼人,苏轼始终不肯“稍自韬戢”,从未改其立身处世的凛凛大节。这已将此前两宋笔记中苏、王文学层面的智、迂对立上升为政治层面的忠、奸对立。苏、王之间这种忠、奸对立的模式在诸多文学作品中被做以大写意式的敷演,且文学作品中的苏轼最终往往获得喜剧式的圆满结局。
现存的三部元代东坡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花间四友东坡梦》中,均以王安石作为乌台诗案的实际发动者,以此构筑苏、王二人的对立。《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题目为“王安石谗课满庭词”,苏、王对立可见一斑。无独有偶,《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题目为“王安石执拗行新法,李御史举劾报私仇”、正名为“杨太守奸邪攻逐客,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不仅设置了苏、王二人的对立,也昭示了二人的忠奸。王安石开场念白便称:
近见西北二边用兵。财用匮乏。我有一策。要行青苗助役于民间。在朝诸官。多言不便。独翰林学士苏轼。十分与我不合。昨日上疏。说我奸邪。蠹政害民。我欲报复。况主上素重其才。难以轻去。且本官志大言浮。离经畔道。见新法之行。往往行诸吟咏。我已着御史李定等。劾他赋诗讪谤。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亦何难哉。
苏轼则称:
时相王安石。误国害民。创立新法。四海怨望。而御史李定……下官前日具疏。论王安石之奸。
当皇帝宣判苏轼贬谪黄州时,苏轼悲慨:
臣蒙知遇。欲竭愚忠。见王安石一心变乱成法。臣上万言书谏诤。今日反受谪贬。兀的不屈死忠臣义士呵。
而当马正卿得知苏轼被贬黄州后,则感叹道:
近闻学士苏子瞻。上书发王安石之奸。反被言官论劾。贬他来黄州安置。有人传说将次来到。今日下着这等大雪。途路难行。我想忠臣烈士。多遭奸回之手。况苏学士大名。远近钦慕。
苏轼被贬黄州后,王安石仍步步紧逼,要置苏轼于死地方休:
叵耐苏轼毁我。已令台官弹劾。贬谪黄州安置。我心还未得遂。如今黄州杨太守。旧是我举用的。不如写一书与他。教他不要周济他。穷乡下邑。举眼无亲。不死那去。
当圣心转圜,召苏轼还朝,皇帝又当面问道:
卿在黄州。谁是恩人。谁是仇人。
以上所列,处处都充满着忠奸对立。“谁是恩人?谁是仇人?”作为一种提示,隐括了全剧忠奸二元对立的格局——李定、杨太守作为王安石意志的执行者,与王安石同属奸佞;张方平、马正卿于苏轼落难之际施以援手,与苏轼同属忠良。因此,苏、王对立的实质乃是忠奸对立。而这种以苏、王对立为模本的忠奸对立同样存在于《花间四友东坡梦》中。《花间四友东坡梦》开篇苏轼自表:
今有王安石在朝,当权乱政,特举青苗一事。我想这青苗一出,万民不胜其苦,为害无穷,小官屡次移书谏阻,因此王安石与俺为仇。
而后王安石又因此私怨设计陷害苏轼,以致其贬谪黄州:
今有王安石在朝,当权乱政,特举青苗一事。我想青苗一出,小民不胜其苦。一日王安石请俺家宴,出歌者数人。内有一女子擎怀良久,不见其手。俺佯言道:小娘子金钗坠也。那女子慌忙出其手,扪其髻。众官皆发一笑。安石令俺题咏其事,小官走笔赋[满庭芳]一阙。谁想安石将小官[满庭芳]奏与圣人,贬小官黄州歇马。
这种忠奸对立模式在《金莲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前的忠、奸对立主要以苏、王二人对立为中心,《金莲记》中又将章惇、李定、舒亶等人置入王安石阵营。当王安石以青苗法何如相问,苏轼仗义执言:“据愚见。窃谓不可”,“出纳之际。吏缘为奸。且方其饶余。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输纳。虽富民不免踰期。恐州县从此多事矣。”王安石恼羞成怒,贬谪苏轼于杭州。但忠义如苏轼,并未因此折节:
颇期整顿乾坤。誓欲洗清世界。奈奸臣久据。未拔眼前之丁。新法盛行。已剜心头之肉。昨与王介甫辈会议。片言不合。拂袖而归。吾想金马玉堂。虽然清贵。竹篱茆舍。亦自逍遥。何须屈膝低头。效彼逢迎妾妇。只合扬眉吐气。做个慷慨丈夫。
此后,章惇嫉贤妒能,构陷苏轼。苏轼、苏辙骨肉离散,苏辙悲叹:
吾兄之事。由王介甫余虐。以兆祸胎。嗣章子厚当权。遂张谗口。小弟正欲上书阊阖。解职救兄。还期借剑尙方。奋身诛佞。更鞭王介甫九原白骨。庶显苏子瞻一点丹心。
苏轼忠臣义士的形象与王安石、章惇奸邪的嘴脸跃然纸上。
在后世笔下,以苏轼为忠直典范而与奸佞对立的这种模式俯拾皆是,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作品中,苏轼往往获得喜剧式的圆满结局。如上文所述《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皇帝最终幡然醒悟,召还苏轼,官复原职,而苏轼则对以“则愿做白发老参军。怎消得天子重儒臣。那里显骚客骚人俊。到不如农夫妇蠢。绕流水孤村。听罢渔樵论。闭草户柴门。做一个清闲自在人”,辞官归隐。又如,《花间四友东坡梦》以“从今后识破了人相我相众生相,生况死况别离况,永谢繁华,甘守凄凉。唱道是即色即空,无遮无障。笑杀东坡也。忏悔春心荡,枉自有盖世文章,还向我佛印禅师听一会讲”煞尾,苏轼被佛印点悟,潜心修道。再如,《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苏轼“经一载受彻凄凉”后,官复原职,“享荣华依还旧职,掌三台位列都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金莲记》中不仅设置了苏轼本人的圆满结局,还为苏轼满门都设置了世俗意义上的完美结局。皇帝亲见苏轼,称赞其:“忠肝义胆。揭日月于重光。绣口锦心。挽文章于一变。致使浮沉外职。抑且漂泊遐方。已明百折之忠。实是九重之过。”并颁圣旨:
尔礼部尚书苏轼。文字凌云。忠诚贯日。金莲归院。先王叹赏奇才。彩管题词。国士顿遭谗口。栖迟犴狱。奔走鲸波。白叟黄童。尽知为枉。紫宸丹陛。洞察其冤。须进新衔。少偿旧德。特进太师兼资政殿大学士。
此外,父苏洵封太子太师,母程氏封成国太夫人,弟苏辙进太傅兼端明殿大学士,妻王氏封同安县君,子迈、过分别授驾部员外郞、颍昌府郾城县知县,友秦观进工部尚书,实不负“弓裘在望。雅称奕世忠良。袍笏相传。共羡一门荣贵”之誉。
三、悲剧情怀对苏轼形象理想化的作用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情怀对苏轼形象理想化的作用至关重要。苏轼本人词作中便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语,这本身就在悲剧意识的净化下导向对于人生价值的追问与建构:被世俗视为风流人物的现世功业建立者也终将难逃被历史长河湮没的命运,那么现世功业的价值又何在?现世功业尚且没有价值,那么在现世未能建功立业的芸芸众生的价值又何在?这句词正昭示着,生命的有限性必然导致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但人性中的动物性使其在生本能的作用下不会选择集体自我毁灭,“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人要建立价值的永恒动力,在其驱动下,人通过不断地自证来积淀合理价值”,正是在这种理路下,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问题有了被置而不论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一方面,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作为客观事实无法被改变,故而由此而产生的悲剧意识无法被彻底消除;另一方面,以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原初动力的价值建构,避开了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个体生命长度作为生命的外在形式被革除于人生价值讨论的范畴,生命的内容成为人生价值的判断依据,同时,由无法改变生命有限的客观事实而产生的悲剧意识又时刻观照并矫正着该生命内容的应有之义,进而成为价值建构的净化和保障机制。正是在这样的理路下,以悲剧意识为底色的理性思考并未走向对生命有限性的直接应对,而是以深情感慨的方式,在对悲剧真相的不断体认中,使心灵得以净化。悲剧意识每一次的兴起,都使得人们得以超越于凡俗的牵绊来思考人生的价值,这种理性的思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情感认同,悲剧意识从而转化为人们的审美情感,亦即悲剧情怀,它不再是一种理性思考,而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但在现实生活中,身处世俗的人们往往难以超脱现实生活的具体困境。所以,将历史人物理想化正是接受者对生命应然状态的理解与超越现实悲剧性的审美寄托,这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为何是前文所提到的几个方面在苏轼形象理想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苏轼洒脱旷达的性格特点在后世被接受者不断夸大以至脸谱化,其仕宦经历更是充斥着诗酒元素,甚至渐臻以诗酒生活取代政治生活之境。明人有作《十不足》:“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思为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下还嫌低。”语词粗浅却鞭辟入里,而人心不足的背后实是对外在事功的执念。然而,这种执念本就出于人为,人自身的不完美势必导致这个出于人为的“念”在初始阶段就不会是完美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原本就并不完美的“念”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动物性本能的诱导下极易流于庸俗、繁缛、僵化。因而,在生命有限性的悲剧意识之下,这些外在事功就都显虚妄,外在于本真生命的一切执念,就都只是禁锢人好好“活着”的枷锁罢了。故而,对“得”本应无所执,无所执于“得”也就无所谓“失”,从而对待一切是非成败就都应一笑置之,正所谓“孰知荧光火石,不足当高人之一笑也。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忮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假,而标榜猖狂之路绝;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陵之路绝。”这一笑,正是无所执的洒脱旷达的状态。但这种洒脱豁达终因生命的有限性而难逃悲剧意识的底色,而这种以悲剧意识为底色的洒脱豁达,必会将人导向对一切世俗浮华的否弃与对本真生活的追求。那么,何谓本真生活?当拨除一切浮华,渔樵、耕读、诗酒自是生命的本真,而诗酒生活最称审美之境。故而,后世接受者将苏轼的政治生活代以诗酒生活。概而言之,洒脱豁达与诗酒生活之所以在苏轼形象理想化的历史生成过程中被后世接受者突出表现,是因为这两者关乎因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而引发的生存与价值焦虑——人只要活着,就不能“无所待”,且易被凡俗生活蒙蔽本心,难以在得失之间顺随自然,故而,接受者才将洒脱旷达作为苏轼形象性格中最鲜明的标签,进而将苏轼形象塑造为洒脱旷达的榜样。而以诗酒生活取代政治生活,并非要否定以“政治”为代表的现实功利本身,而是要否定因追求现实功利而造成的非本真的生命状态。两者实则都是接受者以其悲剧情怀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
后世以苏轼为主人公的文学创作中,在总体上都存在这样一种形式架构:忠良被奸佞所害,历尽劫波,最终战胜奸佞。从狭义上说,忠、奸是封建意识形态下的价值判断。而从广义上说,忠、奸实为人类总体视域下的善、恶。因此,前文所述以苏轼为主角的文学作品的共同形式则为:善受阻,但善最终战胜恶。其中所隐含的是“举直错诸枉”的社会组织结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善是人类总体意识在当下最合理、最具有开放性的状态,当善受阻,则必然激起悲剧意识。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视域并非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观照整个人类总体的。故而,上述以苏轼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共同形式实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就是:对于个人及其有限的时空而言,善恶对峙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但对于人类总体及其无限的时空而言,善必将战胜恶。也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我们民族的悲剧意识并不会走向颓废乃至毁灭,而是在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的指引下,走向悲极而乐,这种悲极而乐也正是对现实中“悲”的审美超越。现实生活中的“悲”既包括上文所提及的因个体生命有限性而产生的悲剧意识终无以消除的客观现实,同时也包含个体生命因自身德福不能相配而产生的道德宿命意识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生命应然状态的质疑,即善者若德福不能相配,失去现实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即便其自身可实现内在自足,但在现实世界中占据强势地位的恶者会指引社会走向何方?个体善者由此反观自身的价值信念难免产生置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中的苏轼不仅不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苏轼,甚至也不应该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苏轼,因为在作品所展现的这个“有意味的形式”中,苏轼已不再是某个具体时空中的具体个人,而是人类总体无限时空中一个“善”的集合体,正因如此,作品中苏轼形象的命运也正代表着人类总体历史中“善”的命运。文学作品中对于苏轼形象喜剧式圆满结局的设置,是将历史应然化为文学作品中的实然。在文学作品中构筑忠奸对立,并以忠对奸的胜利设置苏轼形象完满的结局,则从人类总体的视角给予德福未必相配的有限个体生命以心灵慰藉,亦是以悲剧情怀实现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
注
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
[3](宋)朱彧撰,李伟国校点《萍州可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宋)叶梦得撰,徐时仪校点《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
[6](明)陆树声《清暑笔谈》,中华书局1985年版。
[7](清)褚人获辑撰,李梦生校点《坚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8](明)毛晋编《六十种曲·金莲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
[9](清)姜鸿儒撰《古本戏曲丛刊五集·赤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宋)罗大经撰,孙雪霄校点《鹤林玉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1](宋)费衮撰,金圆校点《梁溪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2](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清)古吴墨浪子搜辑《中国话本大系·六桥才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4](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15]参见拙文《〈宋史·苏轼传〉与宋人笔记对苏轼的塑造及其文化机制——以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为中心》,《中国苏轼研究》第五辑。
[16]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明)臧懋循编《元曲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8]冷成金《论语的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9](明)冯梦龙编著,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中华书局2015年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