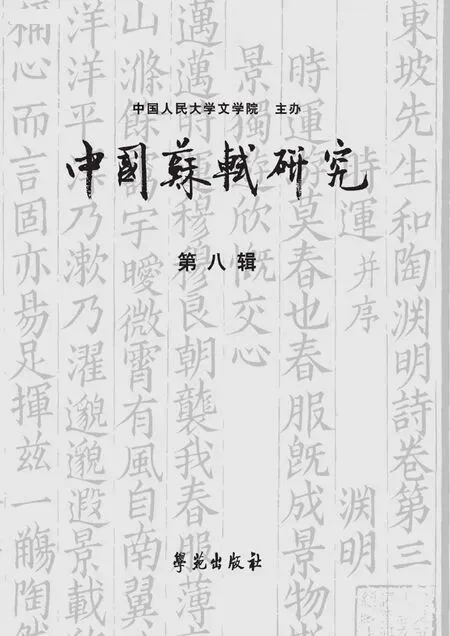苏轼恤狱之仁研究
——以《乞医疗病囚状》为基点
◇彭林泉
元丰二年正月,苏轼在知徐州时,撰写了《乞医疗病囚状》。这是一封奏议,也是一篇重要的法律文献。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苏学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法学界提及或研究此文的也不多见。中国法制史学者徐道邻先生曾对此文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这篇文字又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东坡是一位十分内行的司法官”。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事实,从监狱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苏轼的恤狱思想,包括其态度演变以及背后的法理基础和意义,对苏轼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有所补益。
一、《乞医疗病囚状》的恤狱思想
“用监狱来长期囚禁罪犯,使之成为一种刑罚,在宋代还未正式成立。”“宋代监狱既是刑事被告、未执行犯人和干连证佐之人的看守所,又是民事诉讼案当事人的收容所;既是已决犯的羁押场所,又是死刑犯的侯刑场所;既是协助审判的司法机关,又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它集多种职能于一体,并非限于刑事领域及已决犯。
在《乞医疗病囚状》一文中,苏轼主张医疗病囚,并阐述了理由。他先后引用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令和宋英宗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诏,肯定这是尊重人生命的善政。这从“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狱者,民命之所系也”“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等说法以及提出的医疗病囚等措施可以看出,构成了苏轼主张医疗病囚的正当性。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进行详细分析。
苏轼认为,朝廷重惜人命,哀矜狱案,可以说做得够好了,但是病囚死亡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汉代和宋代均是如此。监狱中究竟有多少病囚,病囚死亡的又有多少?苏轼文中没有明说,从史料来看为数不少。《宋史·刑法志》指出:“囚多瘐死。”瘐死就是囚犯在监狱饿死、冻死、病死,或受拷打致死,有学者把因饥寒而死也算入,严格地讲二者是有差异的。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上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监狱人满为患,牢城溢额现象严重。“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有无力请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为两词赂遗,苦楚而死者。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狱吏非法拷囚也令人发指。(《宋史·刑法志》)可以说宋朝囚犯瘐死严重,神宗在诏令中也承认“瘐死者甚多”。这与监狱条件恶劣,狱吏狱卒虐待、敲诈有关。可见宋朝虽有悯囚之制,但刑狱的淹滞冤滥仍较突出。
苏轼认为,“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积其冤痛,足以感伤阴阳之和”。这里揭示了在病囚死亡上的问题和责任的缺失。
英宗手诏是认识到监狱的重要性(“狱者,民命之所系也”),针对“瘐死者甚多”的现实和对“狱吏与犯法者旁缘为奸,检视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悯焉”的担心,根据《尚书》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原则,才形成的法令。它规定:
其具为今后诸处军巡院、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岁内在狱病死及两人者,推司狱子并从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系五县以上州,每院岁死及三人,开封府府司军巡院岁死及七人,即依上项死两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狱之官推狱经两犯即坐本官,仍从违制失入,其县狱亦依上条。若三万户以上,即依五县以上州军条。其有养疗不依条贯者,自依本法。仍仰开封府及诸路提点刑狱,每至岁终,会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门下点检。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议更加黜责。
这里的“典狱之官推狱两犯即坐本官,仍从违制失入”,意思是病囚死在狱中,超过了年定限额,在发生了一次时,有关官员虽然犯了罪行,但只是予以记录在案,并不执行;如果发生了两次,那么法官和狱卒就要被判杖六十至一百的罪名,而其所属长官按“违制失入”的规定论罪。《刑统》一一二条规定,“违制”犯的是两年徒罪;《刑统》四八七条规定,“失入”(非故意地判无罪为有罪)者,各减三等,就是杖一百的刑罚(做官的有“以官当罪”的办法,并不是真的挨板子)。“其有养疗不依条贯者,自依本法”指当时有关养疗病囚的其他许多法令而言,如《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四有十条关于病囚的敕令。
手诏是一条很重要的可行的诏令,可惜“行之未及数年,而中外臣僚争言其不便”,就不再执行,善政效果未充分显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熙宁四年十月二日中书札子规定,狱囚病死不追究狱官之罪,这与手诏是相矛盾的。苏轼引用手诏后,认为这是“陛下好生之德,远同汉宣,方当推之无穷”,他理解手诏的立法精神,批评“郡县俗吏,不能深晓圣意,因其小不通,辄为驳议。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碍,乃举而废之”,认为这样做过分了。
不过苏轼也承认,狱囚病死,使狱官坐罪,实感于心未安。因为“狱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责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惧罪,多方以求免。囚小有疾,则责保门留,不复疗治;苟无亲属,与虽有而在远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于在狱”。在这种两难的情形下,苏轼考虑折衷的解决办法。黄震云:“此文具载治平手诏、熙宁札子,折衷其说,毋坐狱官罪,而课医病者功罪。”(《黄氏日钞》卷六二)“课”指考课。这里揭示了本文的主旨,也道出苏轼为主张医疗囚犯的原因。
苏轼在引用《周礼·医师》后,提出医疗病囚的对策:
臣愚欲乞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量本州县囚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者不计数外,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从。其上中等医人界满,愿再管勾者听。人给历子以书等第。
若医博士、助教有阙,则比较累岁等第最优者补充。……
这些措施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官府派人专掌医疗病囚犯。军巡院是审理刑事案件的机构,司理院掌狱讼勘鞠之事,“曹司”指曹吏、州县胥吏,这些都是专门的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衙前”是宋代差役最重的一种,职掌官物保管、押运等。从“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可以解决临时抽人或让民间医人轮流医疗病囚的不足。
二是提出佣钱来源。苏轼提出用免役宽剩钱和坊场钱作为报酬,这其实是对王安石“免役法”的推广应用。新法从民间征收免役钱、助役钱,以供官府雇人充役,此外以备灾荒为名增收,谓之“宽剩钱”。增收多少呢?当时是二分。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论给田募役状》说:“臣窃见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过二分,以备灾伤。”“坊场钱”是宋代官设专卖市场所收税钱,主要是酒税。苏轼认为,根据一年期限内犯人数量减少情况确定应给予的佣钱,减少40%以上要处以刑罚。结合后面所说“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其费甚微”,在经费上是有保障,而“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
三是对医治病囚尽心尽责,经多年考核为上等者,可以补医博士、助教官缺。宋承唐制,每州设医博士一名。苏轼提出,如果医博士、助教有空缺,就考察历年评比中等级最优秀的医者补充,这样就会人人用心,像是疗治其家人一样,由此可以救活很多系囚。这是以《周礼·医师》为依据采取的措施,相对于设狱医或法医。
苏轼分析了此法存在的唯一弊端,提出了补助办法:
若死者稍众,则所差衙前曹司医人,与狱子同情,使囚诈称疾病,以张人数。臣以谓此法责罚不及狱官、县令,则狱官、县令无缘肯与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狱官、县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监医官及本辖干系官吏觉察。如诈称病,狱官、县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为公、私罪。
“同情”指同谋。“分故、失、为公、私罪”是唐宋律一贯的立法精神。做官的如故意作弊,就算私罪;不是故意的,犯了公事上的错误就算公罪。同等刑名,私罪的后果比公罪严重得多。
从上引的法令和使用的法言法语来看,苏轼有很高的法律素质和司法水准,他希望朝廷详酌,早赐施行。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未被采纳,这是一大遗憾。
二、苏轼恤狱思想的发展
这篇重要的法律文献作于苏轼地方官任上,集中反映了苏轼对病囚的同情怜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凤翔府任签判期间,苏轼接触到囚犯,奉王命“减决囚犯”,对积欠而被关押的人给予同情,对选择性执法表示不满。嘉祐七年二月十三至十九,苏轼访所属各县“减决囚犯”,并作《奉诏减决囚禁,记所经历》。诗开头写:“远人罹水旱,王命释俘囚。分县传明诏,循山得胜游。”当时凤翔府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欠官府的债务而被关押。苏轼曾掌管理欠,经常鞭笞小民,却只能收回很少一点积欠,他的心情并不好,为此主张免除积欠。苏轼《上蔡省主论放欠书》说:“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但贪官污吏借此敲诈勒索,有钱行贿则赦,无钱行贿者照样关押,甚至赦免六七次后照样未赦。苏轼愤怒地说:“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违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俱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耶?”建言“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以便这些欠债之人“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
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体恤因谋生而被迫“贩卖私盐”的囚犯。宋代对盐实行专卖,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新法在江浙一带还兼行盐法,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在同苏辙讨论这一问题时,王安石认为私盐未绝是“法不峻”造成,办法是“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一二止,帮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取贩也”,但这可能坐变。盐禁引起一些老百姓的不满,一些敢于反抗的贩盐者往往杖剑自随,“吏卒不敢近”。因违反新法而被捕入狱的人很多,仅杭州因违反盐法而获罪的人,一年就多达一万七千人。苏轼曾和王安石就“盐铁法”的内容及弊端争辩过,还面圣条陈,但没想到在行施中给百姓造成如此不幸甚至灾难。他一到杭州就忙于处理囚犯,不得休息。他在《和蔡准郞中兄邀游西湖》中说:“君不见钱塘游雇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戏子由》一诗中写:“平生所惭今耻,坐对疲民更鞭捶。”当时受到惩处的盐犯都是一些贫苦的“疲民”,鞭打他们是自己平生所耻的,现在却习以为常、不以为耻了。这是悲伤之极的结果和发自内心的诉说。甚至在除夕之夜,他也在处理囚犯,不得还家。《都厅题壁》一诗中说,除夕夜,囚犯因营食堕入法网而不能回家团聚,自己也因恋薄禄不能早归,“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竟把自己同囚犯相提并论,并因自己不能对囚犯“暂纵遣”,让其在节日与家人团聚而深感有愧于前贤(“前修”)。这首诗的一大特点是表达了对“囚犯”的深切同情和面对这些“囚犯”时的无奈、悲伤、痛苦,最集中的体现是“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两句。在恶法亦法的情形下,作为地方官员和司法官的苏轼只能执行,何况当时“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没有“挂冠”的打算,审问“囚犯”时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体现了他的人道精神。苏轼认为,只要盐法宽平,像汉代的龚遂那样鼓励反抗的农民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何劳劝农使者促耕;而那些贫而懦弱、靠采笋蕨充饥的村民,就吃不上盐了。《山村五绝》其三写道:“老翁七十自腰镰,渐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是对新法的讽刺,后来成了乌台诗案的罪证之一。其实“迩来三月食无盐”不是夸张,是现实的反映。后来元祐五年除夕,身为杭州知州的苏轼来到监狱检查,发现“囚犯”都已获释,狱中空空如也,这与过去除夕之时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苏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捕,几乎丧生,对狱政问题有了真实体验和切肤之痛。这是北宋一起有名的文字狱,苏轼因诗获罪,是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政治挫折。他被关在乌台狱内,由一个朝廷命官成为囚犯,不仅连续受到审讯,定上种种罪名,而且“狱吏稍见侵”,故意讥笑侮辱他。他自度不能堪,苦闷中写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梁成设法转给苏辙。他被关押审讯长达一百多天,审讯结果被判处“徒二年”的刑罚,被贬到黄州去任团练副使。后来回忆狱中情况说: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口,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若泪读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
苏轼从政期间,多次面对囚犯,或减决,或审讯,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囚犯,受尽屈辱。死里逃生后,他对狱政问题的不满之情也流于笔端,对囚犯的态度也上升到新的层次,为往后医疗病囚的态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理性地对待囚犯方面有其独特之处。
三、苏轼为政和恤狱之仁
《乞医疗病囚状》一文中,苏轼开篇引用的汉宣帝诏令已经涉及恤狱之仁这一问题。诏命说:“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可逆人道也?”其中使用了“人道”一词,并说“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汉宣帝还曾诏曰:“夫决狱不当,使有与邪,不幸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延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汉书·刑法志》)他把“决狱不当”看成令其深感悲痛的问题,为此下令设置专门的司法官员审理疑狱,努力做到审判公平,这也反映了人道化的司法观念。这种“人道”与“仁道”含义相近,尽管与人道主义不能画等号。
自汉代以来,除允许囚犯自己服辩外,给囚犯必要的衣物和医药,体现了唐律中慎重对待囚犯的思想。《新唐书·刑法志》记载了一些对囚犯日常生活进行管理的规定,如“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校粮饷。治不如法者”。这些规定对囚犯的日常饮食及身体健康等给予关注,是基于仁道而制定的。明代法律思想家丘濬认为“此唐人恤狱之仁”(《大学衍义补·慎刑宪》),这是很高的评价。
苏轼的恤狱之仁也就是对囚犯的仁道待遇。《乞医疗病囚状》在主张医疗病囚时,多次提到“人命”这一价值观念,“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用宽剩役钱与坊场钱“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并且其恤狱之仁不限于这篇重要的法律文献。
与医疗病囚的主张相关的是,苏轼率先建立安乐坊,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公立医院,成为公共福利之一的先河。《宋史·苏轼传》记载:

他还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经费来维持这所“安乐坊”的日常运营,从此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安乐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安济坊”,直到苏轼去世时还在正常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绍圣四年,苏轼在惠州写信给广州知州王古,建议在广州设立病院以预防疾病;被贬儋州,又写信给友人程天侔索求药物,以救济当地百姓;建中靖国元年北归途中停留虔州期间,还时常携带药囊漫游市肆、寺观,遇到病人就随手施药、开具药方。
苏轼长期在地方官任上,特别是多年担任知州,施行仁政,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在徐州期间,除了抗洪、开采煤矿,他还在思考治盗和医疗病囚的问题。杭州任上,除抗灾外,他还防治疾病;元祐六年他被朝廷召还,途经润州时发现那里的大米高达每斗一百二十钱,心有隐忧,就写信给接任杭州知州的林希,叮嘱他一定要继续关注饥荒。这封信被朱熹刻成石碑,称其为“仁人之言”。在密州时,他收养弃婴。在黄州时,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建议官府颁布赏罚之法来制止溺婴的陋习。
苏轼在《策别八》一文中还主张劝导亲睦。他说:“各相亲爱,有急相赒,有喜相庆,死丧相恤,疾病相养。是故其民安居无事,则往来欢欣,而狱讼不生……”这令人想起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是监狱外的场景,但在疾病相养或扶持方面是相通的。
这些与医疗病囚的态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均体现了苏轼的仁道,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诚如莫砺锋教授所说:“对于东坡来说,儒家的仁政已经沦为肌髓的自觉信念;为百姓解除疾苦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行为。”作为地方官员,在地方行政事务中推进仁政;作为地方司法官员,在司法实践中同情囚犯,体现仁道。提出医疗病囚的出发点是尊重人的生命,把病囚、囚犯作为人来对待。站在这个高度来理解苏轼的主张及对策,才见仁道之术,否则难以理解苏轼的意旨和实践。
四、苏轼恤狱之仁的意义
有学者在谈到苏轼的政见时指出,苏轼在地方官任上所写的三封奏议,即熙宁七年在密州时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元丰元年在徐州时的《徐州上皇帝书》及次年的《乞医疗病囚状》,“其内容本皆就具体的地方事务而发,但他批评的锋芒,常指向着新法”,但亦如苏辙所说,有“因法以便民”的成分。
表现在熙宁七年“中书札子”,针对狱囚病死不追究狱官之罪,他则要求官府派人“专掌医疗病囚”,指出免役法未使贫富得利,只是“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而已;另一方面,“主张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来雇用医专掌治疗病囚”,这又是将“免役法”推广施行了。这与先试探神宗是否纳谏不同,与《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中全面激烈甚至逐条批驳王安石新法更有别,是有所节制和客观的。《乞医疗病囚状》指出“而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其费甚微”的问题,似乎蕴含着对免役法的批评。毕竟苏轼曾强烈反对过免役法,后来在实践中感到免役法也有益处,转而持维持的态度。而单就这一篇来说,虽有反对免役法的成分,但并不多,在杭州等地反对新法的态度更为多见和突出。苏轼还主张用免役宽剩钱和坊场钱作为雇医专掌治疗病囚的佣钱来源,无疑是将免役法推广施行的体现。肯定这一点,对于准确完整地理解《乞医疗病囚状》的主题是有帮助的。此文不仅是苏轼政见的体现,也是他作为法学家的体现,不仅是他在地方官任上反对王安石新法实施的体现,也是他重视民生、推进仁政的体现。
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苏轼对新法的大部分措施持反对态度,但并不全面否定,而是择善而从,凡是于民有利,就加以推广。从他的这一法律思想,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他关注狱政改良、恤狱慎刑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十分钦佩他实事求是、“因法便民”的伟大人格。从生命法律的角度来看,已有所超越。医疗法律与生命伦理密切相关,其中也有科技与伦理的遇合,包括人性的认知、面临医疗科技发展带来的困惑和对生命伦理价值的探索,已引起学界的关注。
苏轼的恤狱之仁,“让我们体味着古人基于生命伦理与社会正义而展示的一种人道情怀。正是这样一种人道情怀,才为中国古代司法植入一种温情因素和人性根基,才冲淡并抑制了暴虐司法带来的副作用,并为社会和谐架起了一座‘正义之桥’、‘仁道之桥’”。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尽管还谈不上人道主义,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对于今天构建“监狱文化”也有借鉴意义。
从我国监狱史的角度说,唐宋时期较关注囚犯的日常生活环境,苏轼的恤狱之仁是其中重要的一页。《宋刑统·断狱律》引唐律说:“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杻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减窃囚食,笞五十;以故致死者,绞。”这些基本制度是比较健全的,继承了汉律和唐律的内容。宋代还吸取后唐置病囚院的做法:“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治疗,痊后据所犯轻重决断。”病囚可暂时去掉刑具,允许家属看视,并允许家属一人入内服侍,监狱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由于病囚一律入病囚院,容易交叉感染,又规定徒流以上“即于病牢将治”,杖以下“许在外责保看医”(《宋会要·刑法》)。监狱设有“医人”,州三人,县各一人,经官府登记入册,受官府约束管理,由民间医生轮流充任。并且宋朝对流刑罪犯也有“宽恤”规定。真宗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责保于外”(《宋史·刑法志》)。对久系未决或年老多病的系囚,实行“听还本土”制度,作为防止监狱枉滞的措施之一。这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狱指导思想有关,但在实践中也有走样的,效果并不如预期。
监管管理状况可以折射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状况,反映出政府对待犯罪、罪犯惩罚和改造方面的价值取舍。清末以来监狱制度在转型,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发生了重大而可喜的变化,如在科学定位监狱、囚犯方面,监狱形态方面,监狱地的设置、搬迁方面,不仅理论上多所突破,实践中也有很大改进。特别是监狱法已载明囚犯是作为人存在的,大大改善了狱囚及病囚的生存环境,体现了人文关怀。尽管从现实来看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如何思考更高层面的中国现代监狱理论,事关道德与权利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曾宪义先生认为,“记述历史、研究传统的宗旨就在于彰显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大义’。就法律文化研究而言,这个‘大义’就是挖掘、扬传统法文化的优秀精神,并代代相传”(《从传统中寻找力量——〈法律文化研究〉》卷首语)。这也是笔者研究苏轼法律文化的目的所在。苏轼秉承“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法律原则,痛砭狱政痼疾,并提出对策,所有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监狱文化中的和谐人道精神。尽管苏轼文中的分析并非无懈可击,也未被采纳,且传统法律文化中“仁道”除了感化外还有“教化”,在司法实践中运行还可能产生一些问题,与理想尚有差距,但不管怎样,这是一篇具有人道内涵的重要法律文献,与苏轼在地方任上推行仁政的实践相呼应,值得认真研究。
注
释
[1] 原文及注释参见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徐道邻《作为法学家的苏轼》,《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
[3] 戴建国《宋代的狱政制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4] 王云《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用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之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
[6]曾枣庄《三苏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
[7] 崔永东《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 莫砺锋《漫话苏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 年版。
[9]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秦文《因法便民 为民自重——苏轼人体法律理念的现代解读》,《理论月刊》2009年第1期。
[11]陈光明《走在监狱——监狱制度转型的未来絮语》,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12]孙平《文化监督的构建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