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联、行动选择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
——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
倪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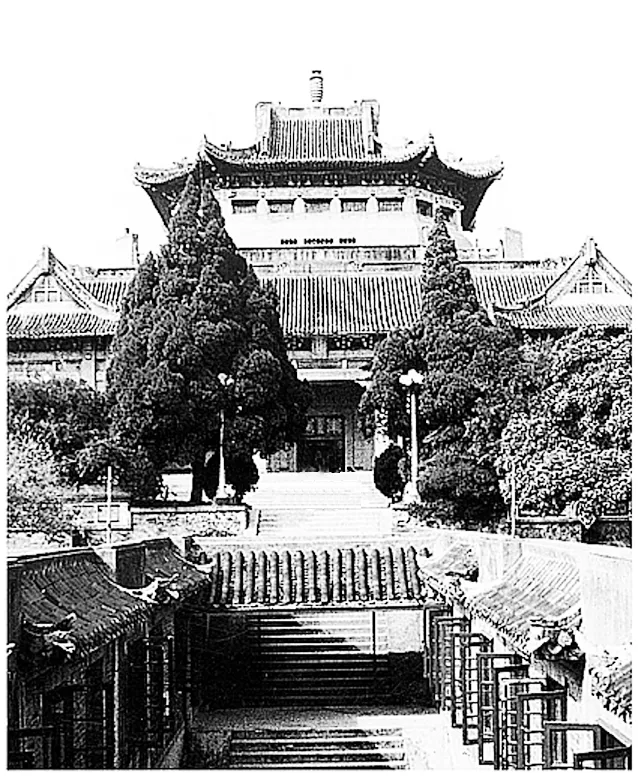
利益关联、行动选择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
——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
倪 星
现有廉政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共权力代理人——公职人员,而从公共权力委托人——社会公众角度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腐败是一种社会问题,根除腐败既需要对公共权力代理人的控制,也需要来自社会公众方面的努力。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进而实现腐败零容忍,是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通过对G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公众腐败容忍度可分为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和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而环境、绩效、认知和经历等因素对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体现自律意识的利益关联容忍度会显著影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行动选择容忍度。因此,当前我国政府必须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增强公众的信心,重视廉洁文化建设,有效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进而实现从官方反腐向社会反腐的转型。
腐败容忍度; 利益关联; 行动选择; 公众参与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打老虎、拍苍蝇”,“照镜子、正衣冠”,党和政府从预防到监督,从惩罚到治理,掀起了一场火力迅猛的反腐攻坚战,并力推反腐工作常态化,建构一种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制度环境。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举措正在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17-01/06/content_5157361.htm.2017-01-06。。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当前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局部地区和部门的腐败仍然屡禁不止,甚至死灰复燃,新的腐败案件屡屡曝光,以身试法者不在少数。此外,在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中国大陆近年来的排名虽然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然不高。其中,中国大陆2014年的排名为第100位(样本总数175),2015年的排名为第83位(样本总数168),2016年的排名为第79位(样本总数178)。相比之下,新加坡、香港的清廉指数排名却常年稳居全球前列。一般认为,新加坡、香港之所以能够保持高度清廉是与其严惩腐败的策略有关;但是,中国大陆近年来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仍未能将腐败斩草除根?这种困境的出现,除了腐败本身具有隐秘性以及政府反腐工作成效的显现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等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被忽略?
正如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新加坡在1959年实现自治前腐败也曾泛滥成灾,而如今却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这既得益于政府持续高压的反腐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其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对于腐败零容忍的文化(于文轩、吴进进,2014)。同样,香港的反腐成效卓著,不仅在于拥有一个强大的廉政公署,社会公众对腐败现象极低的容忍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廉洁文化氛围也至关重要(公婷、王世茹,2012)。腐败在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与公共权力的侵蚀,倘若作为公共权力所有者和委托人的社会公众倾向于容忍腐败,对腐败现象视而不见、不以为然,不愿意采取行动去反对腐败,那么即使政府层面的反腐力度再大,也很难彻底根除腐败。在现实中,还有一些公众虽然口头上表示反对腐败,但当腐败涉及自身利益时却倾向于容忍腐败,成为腐败的参与者甚至发起者,直接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从公共权力委托人——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分析腐败问题,其蕴含的深层次逻辑是:根治腐败问题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公众才是反腐败斗争成败的关键,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形成社会反腐的局面(肖汉宇、公婷,2016)。在理想的状态下,公众不仅不容忍官员腐败,也能够严格自律,保证自身不会参与腐败。在发现腐败线索时,勇于揭发和举报,扮演好权力监督者的角色。这一视角给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深刻启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当前政府反腐足够努力但抑制腐败效果不彰的困惑。
当然,要实现社会反腐的愿景并非易事,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只有公众从内心排斥腐败,不容忍腐败,才能形成廉洁的政治文化氛围,增加潜在腐败者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成本,进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综上所述,本文将研究问题明确为:现阶段我国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总体水平如何?个体之间的腐败容忍度存在着哪些差异?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本文基于G省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利益相关时的腐败容忍度和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两个维度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将研究视角从公共权力的受托者和代理人——公职人员转向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和委托人——社会公众,剖析公众腐败容忍度的现状及其生成机制,与现有研究文献进行对话。同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有效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构建廉洁政治文化、推动社会反腐转型而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和实践指导,从而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
二、 概念界定与文献评估
本文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明确研究的范围和界限;再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评估,指出现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和重点。
1.核心概念界定
腐败容忍度。容忍度是指宽容某项行为或事务的范围,超出了这一范围则该行为不被允许。腐败容忍度可以理解为个体对腐败行为所能宽容或者接受的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一范围或阈值,则腐败不被允许。本文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界定为社会公众在面对腐败行为时所做出的接受与否的判断,对腐败行为倾向于接受或认可的表明其容忍度高,倾向于拒绝或反对的表明其容忍度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包括两个维度,即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以下简称“利益关联容忍度”)和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以下简称“行动选择容忍度”)。前者是指个体出于私利而有可能参与腐败(如行贿等)时,所体现出的对自身腐败的容忍程度,可以用腐败参与意愿等来衡量,其容忍的对象是公众自身。后者是指个体在决定要不要采取实际行动(如举报等)反对和制止腐败时,所体现出的对他人腐败的容忍程度,可以用举报意愿等来衡量,其容忍的对象是他人尤其是公职人员。显然,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分别反映了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自身的腐败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他人的腐败。只有两个维度的容忍度水平都降低,才会在公众层面逐渐形成对于腐败的零容忍。
腐败零容忍。大部分学者是从党政机关惩治腐败行为的视角来界定腐败零容忍。如廖晓明、罗文剑(2012)将其定义为容忍程度的一种状态,即对过分行为和现象的不宽容、不忍受,即使是轻微的违规或犯罪也要严格彻查和惩罚。龙太江、盛欣(2010)认为腐败零容忍是指对各种腐败行为都要严查严惩,不允许任何官员有任何腐败行为发生,哪怕是性质轻微的腐败行为,也要与之进行彻底的斗争。从社会公众层面界定和研究腐败零容忍的文献并不多见,如公婷、王世茹(2012)将公众的腐败零容忍理解为人们不仅自己拒绝参与贪污腐败行为,同时也认为他人的腐败行为是不道德和不可接受的。对于腐败的零容忍可以用不同情腐败、愿意举报腐败、支持对腐败的严格惩处等来衡量。本文对公众腐败零容忍的界定包含对自身腐败行为的零容忍与对他人腐败行为的零容忍,这一界定更加全面,更具现实意义。
2.相关文献综述
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关于公众腐败容忍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四种逻辑,即环境氛围感知逻辑、政府反腐绩效逻辑、腐败概念认知逻辑和人口统计学特征逻辑等。
环境氛围感知的解释逻辑认为,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受其所处文化氛围的影响。社会生活中某些广泛流行的态度倾向和行为方式会深刻影响个体的心理感知与行为判断,伴随着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普遍化,腐败氛围逐渐产生了文化上的心理调控功能,无形中控制了人们的言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Myrdal,2001:161-162)指出,如果公众普遍认为每一个拥有权力的个体都可能为了私利而滥用权力,在这种心理暗示的影响下,人们对腐败的愤恨渐渐地就会转变成“对于有机会通过不光彩手段营私之徒的羡慕”。阿比盖尔等(Barr & Serra,2010)对40多个国家的抽样调查发现,一国腐败的普遍程度与其国民的腐败容忍度和腐败参与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汉尼兹科等(Hanitzsch & Berganza,2012)的研究发现,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与行贿指数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桑德赫兹等(Sandholtz & Taagepera,2005)也指出,最初腐败行为仅是一种直接的物质交换,后来则变成为了一种普遍且持久的事实,进而成为人们心中默认的社会惯例,从而在观念上提高了对腐败容忍的程度。如果人们意识到腐败广泛存在,则可能逐渐衍生出对于腐败现象默认、麻木、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的消极心理,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腐败容忍度升高,导致公众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反腐败的可能性降低。
政府反腐绩效的解释逻辑认为,政府的反腐败工作绩效或者反腐败努力会影响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一方面,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越大,越能够对现有和潜在的腐败分子产生震慑,这些人出于风险考虑越不敢参与或继续参与腐败行为,有利于降低个体利益相关时的腐败容忍度。另一方面,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越大,反腐败的效果越好,公众越会受到正面的激励和鼓舞,采取实际行动举报腐败的可能性和积极性越高,有利于降低个体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公婷、王世茹(2012)发现,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每提高一个级别,其在行动上的腐败容忍度会降低一半,越倾向于举报腐败。
腐败概念认知的解释逻辑认为,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判断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意愿,进而影响其行为。在某些人看来属于腐败的行为,在其他个体看来可能是正常的,并不具备腐败含义。而这种认知判断、概念界定上的差异,可能影响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有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腐败概念界定越严格的人,越会觉得有更多的领域存在腐败或更多的行为属于腐败,对性质轻微的腐败行为的认知和批判就越深刻、越严格,进而催生出更高的道德评判标准,对自身和他人的腐败行为更不能容忍(公婷、王世茹,2012)。杜治洲(2013)也认为,公众对腐败的认知会影响其参与举报腐败的行为,公众对腐败的危害和性质认知得越深刻,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动举报腐败。
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解释逻辑认为,某些个体特质会影响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达纳尔等(Dollar et al.,2001)的研究发现,女性较之男性可能拥有更高的伦理标杆和行为标准,对公共利益更加关心,其腐败容忍度较低,从而使得女性出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更小。罗斯·艾克曼(Rose-Ackerman,2001)指出,公共部门中普遍存在的低收入和弱监管,提高了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增加了其参与腐败的动力。李文(2010)从相对剥夺的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低收入人群有更高的腐败容忍度,而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其腐败容忍度会下降。但郭夏娟(2013)对在职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MPA)的调查发现,月收入水平的升高并没有带来腐败容忍度的下降,反而是个体的收入水平越高,其相应的腐败容忍度越高。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相对而言政治和道德素养更高,因而行动上的腐败容忍度更低,更愿意参与反腐败(Gatti et al.,2003)。
3.简短评述与本文的研究方向
相关学者的研究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但是,很多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忽略了腐败容忍度具有多维度的事实,往往只观察到人们对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容忍度,而忽略了公众自身利益关联时的容忍度。在具体分析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因素时,已有研究大多是从某一种解释逻辑出发,缺乏对微观生成机制的全面探究。而且,现有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或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缺乏大样本定量实证分析。相比之下,公婷等的研究最为规范,但也缺乏对腐败接触经历这一因素的考量,而且其研究对象为香港在校学生,结论是否适用于制度环境等条件迥异的中国大陆,尚待进一步考证。在内地学者的研究中,测量腐败容忍度的样本往往为在职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MPA)、在校大学生等,缺乏以普通公众为对象的调查,研究的代表性容易受到质疑。
本文以G省为研究对象。G省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水平均居全国前列,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以G省为研究对象,颇具代表性。此外,选择一个省份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地控制制度环境变量,减少偏差。另外,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独立开展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样本量大,采集过程规范,数据具备较强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同时,该调查面向G省的全体社会公众,而非某一类特殊群体,更能反映整个社会的腐败容忍度现状。
三、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由上述文献评估可知,现有研究将公众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归纳为四种逻辑,即环境氛围感知(环境因素)、政府反腐绩效(绩效因素)、腐败概念认知(认知因素)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特质因素)等。在本文的分析中,将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将另外三种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此外,由于个体过去的经历会影响其现在和将来的态度与认知,进而影响其未来的行为选择,有必要将个体过往的腐败接触经历(经历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同时,公众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影响着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一个在利益诱惑面前能够严格自律的人,往往在反腐参与时的表现更为积极,更愿意承担起监督权力的社会责任。因此,本文将利益关联容忍度作为行动选择容忍度的解释变量纳入补充模型中。
1.环境氛围感知与腐败容忍度
公众身处社会网络之中,个体自身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如果个体觉得腐败是大多数人用以攫取私利的有效方式,且这种方式普遍存在和流行,那么受此影响,出于对参与腐败可能获得回报的乐观预期,个体便会强化同样参与腐败的意愿,从而提高了其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而如果涉足腐败的人与没有涉足腐败的人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各种人际关系的融合,使得人们逐渐产生所谓的“痛感”与“麻木感”并存的心理,进而导致“无可奈何”和“听之任之”的消极反馈,从而提高了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感知到的腐败现象越普遍,其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参与腐败的意愿越强。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感知到的腐败现象越普遍,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弱。
2.政府反腐绩效与腐败容忍度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正式制度能够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偏好形成有效的约束。公婷、王世茹(2012)的研究却发现,正式制度设计如廉政公署的教育和培训计划等对香港公众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公众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这一主观指标对个体的腐败容忍度影响显著。已有证据表明,公众主动参与的腐败基本上是一种寻租行为,明显受到政府反腐败工作的制约。个体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越高,说明其意识到的政府反腐绩效越好,理性人出于风险考虑,越不会主动参与腐败。与此同时,政府的反腐败工作越彻底,打击腐败的力度越大,对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回应和保障越到位,公众举报腐败的可能性越高(杜治洲,2013)。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其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越低,参与腐败的意愿越弱。
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低,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
3.腐败概念认知与腐败容忍度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巴内特等(Barnett & Vaicys,2000)的研究证明,人们的认知判断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意愿,进而影响其行为。在某些地区或群体看来属于腐败的行为,在其他地区或群体看来,可能非常正常,并不具备多少腐败色彩。这种认知上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腐败容忍度。通过实证分析,肖汉宇、公婷(2016)发现公众对腐败的界定范围与举报腐败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腐败概念的认知越严格,其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越低,参与腐败的意愿越弱。
假设6: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腐败概念的认知越严格,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低,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
4.腐败接触经历与腐败容忍度
人格心理学认为,态度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准备状态,它通过经验组织起来,影响着个人对情景的反映。根据理性人假设,当某种行为给个体带来相关收益时,这种行为容易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个体有过主动行贿的经历,并获得了相应的收益,那么就会给其以经验启示,形成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正如理查德等(Richard & William,2010)所阐明的,个体在与腐败行为的互动中屡次成功,将使其形成一种经验总结和认识范式,进一步强化参与腐败的动机,相应削弱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如果个体有过被索贿的经历,其自身利益遭到侵害,则容易产生某种程度的剥夺感,就越有可能对腐败深恶痛疾,因而更有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反腐败。杜治洲(2013)也认为,一般来说那些亲身经历腐败且深受其害的人,更愿意举报腐败。而那些直接参与腐败并获益的人,则不愿意揭露腐败。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行贿经历的人与没有行贿经历的人相比,其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参与腐败的意愿越强。
假设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行贿经历的人与没有行贿经历的人相比,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弱。
假设9: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被索贿经历的人与没有被索贿经历的人相比,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低,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越强。
5.补充模型:利益关联容忍度与行动选择容忍度
要实现对腐败的零容忍,公众既需严于律己,也需严以待人,同时从利益关联与行动选择两个维度出发,降低两个方面的容忍度。本文将这两种容忍度作为两个独立的因变量,分别探究其可能的影响机制,但这两种容忍度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关联呢?从理论上看,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代表了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和自律意识,而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折射了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在腐败面前能够严于律己的人,对他人的腐败行为也会持较强的负面态度,也即公众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会直接影响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与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 数据收集、变量选取与描述
2014年12月,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对G省下辖的所有地级市、县市区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询问居民关于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调查采用移动电话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受访者是年龄18至65岁、在G省生活不少于两年的公民,总样本量为7502。由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较为敏感,公众在回答问题时有所顾忌,进而产生样本缺损情况,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919份。
1.因变量
本文中的因变量是公众腐败容忍度,具体包括两个维度,即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和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有关行为意愿的研究认为,人们当下的意愿和态度是预测其未来行为的最为接近的测量指标,故通过设定情景的方式获取被调查者当下的态度和意愿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真正面对腐败行为时的容忍度水平。
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问卷中询问公众:“为了办事方便,您是否愿意向本地公职人员请客送礼?”对于回答“愿意”的赋值为“3”,“不愿意”的赋值为“1”,“看情形,很难说”的赋值为“2”,其他选项的赋值为缺失。被调查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得分越高,意味着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即为了自身利益越倾向于参与腐败。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次调查中93.89%的被调查者认为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属于腐败行为,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该问题衡量的是利益关联容忍度,而非对腐败概念的界定。
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问卷中询问公众:“如果发现本地的腐败线索,您是否愿意向相关部门举报?”对于回答“愿意”的赋值为“1”,“不愿意”的赋值为“3”,“看情形,很难说”的赋值为“2”,其他选项的赋值为缺失。被调查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的得分越高,意味着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即越不倾向于参与反腐败行动。

图2 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水平

图3 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水平
2.解释变量
本文中的解释变量包括环境氛围感知、政府反腐绩效、腐败概念认知、腐败接触经历等。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环境氛围感知。问卷中询问公众:“总的来说,您认为本县/市/区党政机关腐败的普遍程度如何?”对于回答“很不普遍”的赋值为“1”,“不普遍”的赋值为“2”,“一般”的赋值为“3”,“普遍”的赋值为“4”,“很普遍”的赋值为“5”,其他选项的赋值为缺失。被调查者的得分越高,意味着其感知到当地的腐败氛围越严重。
政府反腐绩效。问卷中询问公众:“过去一年中,您对本县/市/区反腐败工作的满意程度如何?”对于回答“非常不满意”的赋值为“1”,“不是很满意”的赋值为“2”,“一般”的赋值为“3”,“比较满意”的赋值为“4”,“非常满意”的赋值为“5”,其他选项的赋值为缺失。被调查者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对当地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越高。
腐败概念认知。问卷中列举出公职人员“把办公室纸笔带回家自己使用”、“为私人事务使用公车”、“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找工作”、“接受监管对象请客吃饭”、“接受监管对象送的钱财”等五种行为,要求公众逐一判断其是否属于腐败。对于回答“是”的赋值为“1”,“不是”的赋值为“0”,“看情形,很难说”的赋值为“0.5”,其他选项的赋值为缺失。通过加总被调查者在这五个问题上的总分,得分越高说明其对腐败概念的认知越严格。

表1 G省公众的腐败概念认知情况
腐败接触经历。腐败接触经历包括行贿经历和被索贿经历。对于行贿经历,问卷中询问公众:“过去一年中,您或您的亲友是否有向本地公职人员请客送礼的经历?”对于被索贿经历,问卷中询问公众:“过去一年中,您或您的亲友是否碰到过本地公职人员索要好处?”回答“是”的赋值为“1”,“否”的赋值为“0”,其他选项的赋值为缺失。
3.控制变量
本文中的控制变量为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居住地、收入等。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赋值换算成相应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分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共青团员和群众,居住地分为城市和农村,个人的月收入由受访者自报。其中,性别、政治面貌与居住地为虚拟变量。表2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取值情况,包括因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观测值、取值范围、均值、标准差等。

表2 各变量的取值情况
五、 统计模型与分析结果
本调查中的所有样本均取自同一省份,制度因素得到了较好控制;同时,因变量为定序型分布,考虑到数据结构类型,本文采用ologit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本调查以县市区为具体抽样单位,考虑到同一县市区内的个体可能具有较多相同特征,因此模型操作时以县市区为聚类单位,以获取更加有效的标准误,使得统计推断更加有效。具体的分析结果如下:

表3 统计模型及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p<0.1,**p<0.05,***p<0.01,采用县市区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模型2和3只是针对那些没有遇到过腐败行为的受访者,故观测值比模型1少1000个左右。本次调查显示,有1524个受访者表示遇到过腐败行为,占比为22%。
Wald Chi2检验表明模型的预测变量是有效的,显著不同于0。Pseudo R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模型拟合度,但仅供参考。我们主要参照Count R2检验模型拟合度,该统计值表明有60%以上的预测是有效的,说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可以接受。另外,ologit模型需要进行模型平行假设检验。由统计值可见,模型1和2用一个模型和两个模型进行估计并不存在明显区别。模型3在0.1的显著度水平上显著,存在差异的变量仅仅是性别和年龄,因其并非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故可以采用单一模型进行估计。
在模型1中,环境氛围感知与利益关联容忍度正相关,且非常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感受到地方腐败氛围越浓,认为腐败现象越普遍存在,其利益相关时的腐败容忍度就会越高,越倾向于参与腐败活动。这与破窗理论的解释相吻合。政府反腐绩效与利益关联容忍度负相关,但不显著,假设3没有通过验证。这说明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力度对个体为了私利而参与腐败的震慑不尽如人意,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本文开篇所提出的困惑,即政府高强度反腐败努力未必一定能够根除腐败,而社会文化氛围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个体参与腐败的影响更大。腐败概念认知与利益关联容忍度负相关,假设5得到验证。这说明如何定义腐败确实会对个体的腐败参与产生影响,有着更严格腐败标准的人,行为选择更为谨慎。行贿经历和被索贿经历均显著影响着利益关联容忍度,假设7得到验证,即有过腐败经历的人更倾向于再次参与腐败。
在模型2中,环境氛围感知与行动选择容忍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假设2没有通过验证。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对公众参与反腐败的行为可能产生着某种影响,但一旦纳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环境因素的作用就不确定了。政府反腐绩效与行动选择容忍度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假设4得到验证。政府的反腐败努力和反腐败绩效是影响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要广泛动员全社会揭发举报腐败的积极性,政府就必须作出表率。与环境因素的影响相比较,绩效因素对于行动选择容忍度的意义更加明显。哪怕公众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腐败泛滥,但只要政府具有坚强的反腐败决心,不断强化反腐力度,公众就会作出积极的反应。腐败概念认知与行动选择容忍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假设6得到验证。公众对腐败的界定越严格,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越低,越愿意采取实际行动反对腐败。在腐败接触经历中,行贿经历与行动选择容忍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有过行贿经历的人参与反腐败行动的积极性更低,假设8得到验证。令人诧异的是,被索贿经历与行动选择容忍度之间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9没有得到验证。从理论上讲,有过被索贿经历的人,因为利益直接遭到剥夺,可能对腐败更为痛恨,进而有更高的反腐败意愿。但事实上,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即有过被索贿经历的人更害怕打击报复或被某些案件牵连,从而逐渐稀释了对腐败的痛感,变得随波逐流、任人宰割。
在模型3中,利益关联容忍度与行动选择容忍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假设10得到验证。一个在腐败诱惑面前不能够严格自律、善于通过不光彩手段获取私利的人,不可能高举起反对腐败的大旗,难以担负澄清世风、弘扬正义的社会责任。而一个有着较高的道德素养和自律能力、不放任自身涉足腐败的人,往往也会主动承担公民责任,积极与腐败行为作斗争。
六、 研究结论与讨论
现有廉政研究文献大多将视角聚焦于公共权力受托者和代理人——公职人员,讨论官员任期、履历、薪酬以及经济绩效等因素对腐败行为的影响,而从公共权力所有者和委托人——社会公众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根据G省调查数据对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发现G省公众的腐败容忍度水平总体较低,在利益关联和行动选择两个维度中,具有较低水平容忍度的受访者分别为56%和58%,均超过了一半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相当部分受访者具有较高水平的容忍度,说明当前仍有不少人愿意或敢于参与腐败活动,而参与反腐败行动的积极性不高。
在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的诸因素中,本文发现:首先,公众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受到环境因素、认知因素和经历因素的显著影响,而与绩效因素的关系不显著。女性、收入较低者和农村居民在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较低,更不倾向于参与腐败。其次,公众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会受到绩效因素、认知因素和行贿经历因素的显著影响,而与环境因素的关系不显著。女性在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较高,更不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反对腐败。最后,体现个人修养和自律意识的利益关联容忍度会显著影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行动选择容忍度。
显然,打击腐败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担当。只有社会公众都坚持严格自律、不参与腐败,并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反腐败斗争,再加上来自政府层面的制度性努力,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腐败零容忍氛围,对腐败分子形成全方位的震慑,最终实现政治清明的目标。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优化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政府必须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通过反腐败斗争的实际绩效赢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由此降低个体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进而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广泛动员和吸引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实际行动。第二,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政府必须营造出更为廉洁的社会文化氛围,增加公众对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由此降低个体利益关联时的腐败容忍度。尤其对于腐败案件的报道要注意策略,既让公众感受到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又避免让公众产生腐败越反越多的错觉。第三,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宣传、文化教育等多途径出发,从严界定腐败的标准,尽可能消除模糊地带,降低公众在两个维度上的腐败容忍度,促进公民的廉洁自律和反腐败参与。第四,因为个体的腐败接触经历对其腐败容忍度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必须重视公众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到的基层贪腐和执法不公等问题,严惩“蚁贪”,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第五,因为个体利益相关时的腐败容忍度会显著影响其行动选择时的腐败容忍度,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在严格自律的基础上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权利意识,进而推动公众积极投身到反腐败的实际行动中去。
当然,由于腐败容忍度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学术概念,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腐败容忍度的概念界定、维度划分和具体测量,尚待完善。运用主观调查数据开展研究的科学性、可靠性,尚需要不断检验和深化。
[1] 杜治洲(2013).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影响因素及其挑战.理论视野,3.
[2] 公 婷、王世茹(2012).腐败“零容忍”的政治文化——以香港为例.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
[3] 郭夏娟(2013).腐败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比较的视角.伦理学研究,6.
[4] 李 文(2010).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5.
[5] 廖晓明、罗文剑(2012).“零容忍”反腐败:内涵、特征与进路.中国行政管理,1.
[6] 龙太江、盛 欣(2010).中国实施腐败“零容忍”策略探论.求索,6.
[7] 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200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8] 肖汉宇、公 婷(2016).腐败容忍度与“社会反腐”:基于香港的实证分析.公共行政评论,3.
[9] 于文轩、吴进进(2014).反腐败政策的奇迹:新加坡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公共行政评论,5.
[10] Abigail Barr & Danila Serra(2010).Corruption and Culture:An Experimental Analysi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94(11).
[11] T.Barnett & C.Vaicys(2000).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Ethical Work Climate on Ethical Judgment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JournalofBusinessEthics,27(4).
[12] D.Dollar et al.(2001).Are Women Really the “Fairer” Sex? Corruption and Women in Government.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46(4).
[13] R.Gatti et al.(2003).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Corruption:Do Social Effects Matter?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 (3122).
[14] T.Hanitzsch & R.Berganza(2012).Explaining Journalists'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cross 20 Countries:Media Freedom,Corruption,and Ownership Matter Most.JournalofCommunication,62(5).
[15] R.Richard & M.William(2010).Experience Versus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Russia as a Test Case.GlobalCrime,11(2).[16] S.Rose-Ackerman(2001).Trust,Honesty and Corruption:Reflection on the State-building Process.EuropeanJournalofSociology,42(3).
[17] W.Sandholtz & R.Taagepera(2005).Corruption,Culture,and Communism.InternationalReviewofSociology,15(1).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s role in anti-corruption,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ublic’s tolerance of corruption.Zero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helps to foster an honest social culture,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eporting corruption and the risk of committing corruption,and eventually eliminate corruption.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G province in China,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what is the level of public’s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there any variance of individual’s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If yes,what are the explanatory factors?
The data comes from a random sampling survey conduct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2014.This survey is conducted by cellphone and covers all the municipals and counties or districts of G province.The sample size is 6919 individuals.Surveying one province helps the researchers to control the local institutions.The researchers inquire respondents’ opinions of corruption,including the tolerance of corruption.We use two variables to measure the tolerance of corruption:individual’s tolerance when the respondent is interest related with the corruption activity and considering whether to offer a bribe,and individual’s tolerance when the respondent decide whether to report corruption.For the explanatory factors,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e definition of corruption,the experience of corruption,and the government’s anti-corrup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such as gender,education,age,location,income and political status,are all controlled.We use Ordinal Logistic model in the data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For the tolerance of corruption,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 corruption undesirable.Only less than 30% of respondents view that corruption is somewhat acceptable.For the variance of tolerance,results of statistic analysis indicate different patterns for the two measurements of tolerance.First,individual’s decision of engaging corruption is mostly explained by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orruption,the definition of corruption and experience of corruption.The factor of government’s anti-corruption is not significant.Second,individual’s decision of reporting corruption is related with the government’s anti-corruption,definition of corruption and experience of offering bribe,and unrelated with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orruption.Third,for the control variables,females are less likely to tolerant corruption.Low-income and rural respondents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offer a bribe.
The findings may interest those study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It contributes a fresh view of the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 framework of explaining it.This research also sheds some lights on how to achieve a better outcome of anti-corruption by educating the public and fostering a social culture of zero-tolerance of corruption. Key words:tolerance of corruption;interest-related; activity choice; public participation
■责任编辑:叶娟丽
Interest-related,Activity Choice & Public’s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G Province
NiX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has launched an in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ince the CCP’s 18thnational congress.However,corruption in China is never eliminated.Many factors result in corruption.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mostly take a perspective of agent,focusing on the behaviors of governments and officials,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that feed corruption.What is left to study i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It is hard to eliminate corruption by only relying on the government.Eliminating corruption requires efforts from all aspects of society.Public participation is significant in anti-corruption.
10.14086/j.cnki.wujss.2017.04.012
D035;D26
A
1672-7320(2017)04-0118-11
2017-0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3&ZD011)
■作者地址:倪 星,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以兴安中学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