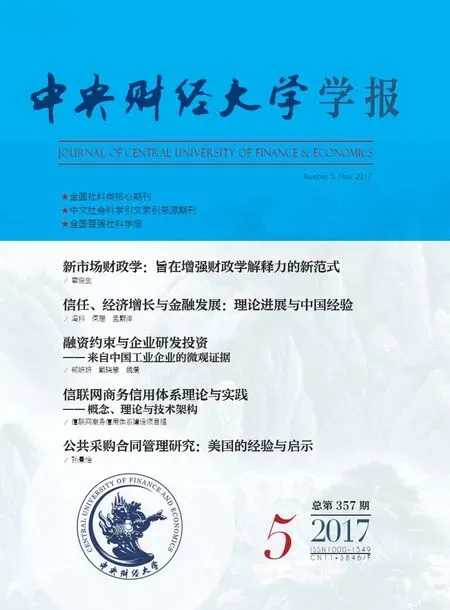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存在门槛效应吗?
洪 源 吕 鑫 李 礼
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里实现了起飞,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我国自在1998年迈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2010年人均GNI达到4 496美元,2015年人均GNI更是超过了8 000美元,正在实现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门槛的跨越(如图1所示)。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世界发达经济体人均GNI普遍达到40 000美元以上,而我国距离人均GNI 11 0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上限尚有较大差距,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期间,前期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结构失衡问题在2008以后集中爆发。根据中国社科院 《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提出的经济结构失衡指数,我国2011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高达0.96,进入完全失衡的边缘。这种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居民有效消费不足会使得经济无法持续增长,从而很有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1]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相对于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有效消费不足将成为造成我国未来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症结与根源。而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迈向高收入国家最为关键的10年。[2]因此,如何扩大居民有效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我国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适应消费加快升级,不断增强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作用,并通过一系列举措,破除居民消费层面的后顾之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图1 1990年以来我国人均GNI变化情况
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能够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财政重建设轻民生,对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不足,进而严重制约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预期。要想从根本上扩大居民有效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扩大财政对上述方面的支出,减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后顾之忧。因而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让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由此民生财政一词首先出现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并迅速成为我国财政运行的主要模式。在民生财政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显然,从民生财政的内涵来看,保障民生,激活和释放有效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并将经济发展落实于惠及民生是其应有之意。那么,在当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背景下,民生财政到底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民生财政收支活动能否起到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效果?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厘清民生财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进一步优化民生财政机制,充分发挥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调控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有关财政与居民消费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自Bailey等 (1973)[3]最先提出了一个有效消费函数,研究得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以后,就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到底是挤入还是挤出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Barro (1974)[4]、 Brunila(1997)[5]在 Bailey (1973)[3]的基础上将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引入居民最优的消费决策中,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 相反,Alesina和 Rodik (1991)[6]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得出政府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呈现一种互补效应。而与上述研究思路不同,Giavazzi和Pagano(1990)[7]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和丹麦两国发生的财政紧缩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支持了Feldstein (1980)[8]提出的 “紧缩性的财政扩张”,即财政政策通过影响居民预期而对其消费存在非凯恩斯效应,这也将财政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由线性关系研究扩展到了非线性关系研究领域。此后,国外学者纷纷展开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检验和研究。 Bertola和 Drazen (1991)[9]理论上构建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最优化模型,研究得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目标点 (target points)的上下存在非线性效应。 Amano和 Wirjanto (1998)[10]构建了两时期的持久收入模型,利用美国1953—199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GMM估计实证发现,随着个人消费的期内替代弹性与跨期替代弹性大小的不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Wang和 Gao (2011)[11]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在国内研究方面,近年来学者们也遵循了类似于国外的轨迹,开始侧重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方红生和郭林(2010)[12]基于中国1978—2004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虚拟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预期机制。储德银和李善达 (2014)[13]利用可以内生划分财政调整时期的STR模型,研究发现1980—2012年间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影响居民消费预期而呈现不同程度的非线性效应。毛军和王蓓 (2015)[14]、毛军和刘建民 (2016)[15]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不同的外部因素影响下,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
已有的研究为认识财政因素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启示,但其局限性表现为:第一,现有文献更多是从总体财政收支互动的视角来研究其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鉴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收支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而相对于其他财政收支活动而言,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当前优化改善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具体的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二,经典的消费理论一直将居民收入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考察财政收支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时,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居民收入变化对它的作用和干扰。因此,在研究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还有待结合目前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背景约束,从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来考察民生财政影响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背景约束,将民生财政运作模式下的支出与税收活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础上,系统探讨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居民消费的效果差异,以及在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民生财政收支活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从理论上系统分析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第二,借鉴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方法,运用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影响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据此提出当前优化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机理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背景约束下来开展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分析,首先需要解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背景到底对探讨民生财政影响居民消费问题产生了怎样的约束。鉴于居民收入因素在居民消费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显然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因居民收入因素的条件变化而出现显著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从居民收入这一关键因素出发来解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民生财政影响居民消费所带来的约束。首先,从居民收入静态结构来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并且社会分配格局还远不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而是底部偏大、中上部偏细尖的金字塔型。[16]在这种居民收入结构下,居民收入分配失衡会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动机和行为发生改变,从而使得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特征存在明显差异。[17]这就要求回答民生财政对于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其次,从居民收入动态变化来看,今后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势必需要经过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的动态变化过程。[18]而在这一过程中,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是否会出现一种非线性影响效果?这也是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下文我们试图在将民生财政运作模式下的支出与税收活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民生财政的支出与收入活动两方面来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阐述与解释,进而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假设。
(一)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差异机制
首先,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的视角来看,近年来民生财政支出活动最大的特征在于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快速增加,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明显提高。[19]例如,2002年我国民生财政支出总额为4 911.4亿元,到2014年民生财政支出总额则达到49 187.37亿元,13年间扩大了10.01倍,同时民生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由2001年的25.98%提高到2014年的36.41%。具体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差异机制来看 (如图2所示):一是对于低收入人群,由于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特征是受到收入较低和较强流动性约束的双重限制,虽然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和意愿,但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的收入,且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20]因此,民生财政支出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主要在于通过其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就业等方面的资金投入,间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升消费能力促进该群体消费。二是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由于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特征是面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不确定预期,其预防储蓄动机强烈,当期收入没有进入当期消费。[21]因此,民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主要在于民生财政支出能替换出一部分居民今后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 “大额刚性支出”,进而改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通过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来释放居民消费。三是对于高收入人群,由于制约这部分人群消费的因素并非主要是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而是受我国当前消费品供给结构和环境的限制,尽管有消费能力,但其实际消费意愿偏低。因此,相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提升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预期来刺激高收入人群消费的效果要弱一些。

图2 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机制图
其次,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的视角来看,由于民生财政资金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中的税收,因此民生财政收入活动主要体现为支持民生财政运作模式的税收收入活动。从近年来民生财政收入活动的特征来看,伴随着民生财政支出快速增长,我国税收收入也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从我国税制结构来看,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却一直远高于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22],因而间接税的增长与民生财政支出的增长之间有很强的同步性。例如,2002—2014年,在民生财政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间接税收入额也由2002年的12 106.59亿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76 697.97亿元,14年间增幅达6.34倍,与此同时,间接税所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的水平,2014年间接税比重为63.68%,远大于直接税28.42%的比重,其主体地位十分明显。具体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差异机制来看 (如图2所示):一是对于低收入人群,由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通过税负转嫁机制提高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使得低收入人群在同等收入情况下其实际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力降低。即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通过税负 “收入效应”抑制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另一方面,根据恩格尔定律可知,低收入群体由于其恩格尔系数较高,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较大,且需求弹性较低,因此,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导致居民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的 “替代效应”在该部分群体中并不明显。二是对于中等收入人群,间接税为主的税收除了通过前述的 “收入效应”抑制中等收入人群消费之外,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特别是在缺乏社会保障税这一直接税的背景下,该部分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将会大大增强,因而在间接税增长从而不断形成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预期之后,对该部分人群所产生的增加个人储蓄而减少消费的 “替代效应”也愈发明显。三是对于高收入人群,较低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中的高档消费倾向,决定了间接税抑制消费的 “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在这部分人群中都不会很明显。同时由于这部分人群对享乐型的高档消费需求更加突出,理论上间接税中的消费税可以对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结构起到一定的调节引导作用,但考虑到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比较窄的实际,故间接税对高收入人群消费产生的 “结构效应”也不明显。
(二)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果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3]以韩国为例,由于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增加,其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因而仅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党的十八大报告将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中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不仅抑制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实际进程,而且难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今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在于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同时,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此基础上,结合今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居民收入分配目标,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今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的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低收入人群通过收入增长向中等收入人群转变的特征,在此过程中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逐步扩大,这是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关键;第二阶段是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中高收入人群,特别是高收入人群比重逐步扩大,经过这一过程最终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根据上述居民收入动态变化的过程,结合前面所述的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机制,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非线性影响的假设。
假设1: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效果 (如图3所示)。第一,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的第一阶段,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低收入人群通过收入增长向中等收入人群转变的特征。由前述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机制可知,对低收入人群,民生财政支出活动主要是通过相关的社会保障、就业支出来提升该部分人群的消费能力,而对于中等收入人群,除了能够提升消费能力之外,关键是民生财政支出活动能够通过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具体支出来替换出居民 (主要是中等收入人群)一部分今后在这些领域的 “大额刚性支出”,进而改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刺激即期消费。因此,在这一阶段,随着中等收入人群占比的逐步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是递增的。第二,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第二阶段,由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机制可知,民生财政支出活动通过提升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预期来刺激高收入人群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因而,这一阶段,随着高收入人群占比的逐步扩大,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将有所减弱。
假设2: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也是呈现出 “先增后减”的倒U型效果 (如图3所示)。第一,在居民收入整体水平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的第一阶段,由前述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机制可知,对低收入人群,民生财政收入活动主要由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所产生的税负 “收入效应”来抑制该部分人群的消费,而对于中等收入人群,除了 “收入效应”之外,随着该部分人群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间接税不断增长带来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预期将会对该部分人群产生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的 “替代效应”。因此,在这一阶段,随着中等收入人群占比的逐步增加,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是递增的。第二,居民收入整体水平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第二阶段,由于高收入人群消费结构中的高档消费倾向,决定了间接税通过提高普通商品劳务价格来抑制消费的 “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在这部分人群中都不会很明显,同时我国现行消费税税制设计对于该部分人群消费结构的引导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在这一阶段,随着高收入人群占比的逐步扩大,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

图3 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最后,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面两条假设在民生财政运行的过程中,民生财政的支出和收入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一方面,民生财政支出活动通过提升消费能力和优化消费预期,进而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支持民生财政支出的收入活动来看,当前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却通过所产生税负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而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费的效果。最终,民生财政运行模式下的这两种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方向和效果取决于上述两种不同效应的综合对比。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影响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由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非线性关系。由于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受到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这一条件因素的制约,因而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受居民收入条件的变化而表现出一种倒U型门槛特征。那么,我国的实际数据是否支持本文的这一理论假设呢?下面我们以我国2002—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借鉴以Hansen(1997)[24]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对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一)门槛效应模型设定
本文将基于 Hansen (1997)[24]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建立 “门槛效应”模型,其中结合前面提出的假设实证检验需要,将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从而考察在收入动态变化的不同区间下,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差异性结果。同时,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有必要来区别研究民生财政对城镇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进而扩展到多门槛模型。本文拟建立的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如下:


其中,式 (1)和式 (2)分别为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和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于居民消费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的模型组。为了减弱模型各变量的数据异方差问题并提高模型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在此对模型中所有变量做取对数处理。
在式 (1)所示的模型组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zconsit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ncconsit;为了考察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于居民消费存在的门槛效应,解释变量为民生财政支出变量msczit,具体由i省份t年的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来表示其活动特征,门槛变量在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时对应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zincit,在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时则对应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ncincit,模型中I(·)为指标函数,η1和η2为待估测的门槛值;在式 (1)模型组中的其中一个关键控制变量是与民生支出相对应的民生财政收入变量idtaxit,它具体由i省份t年的地方间接税收入总额来表示其活动特征。另外,为了考察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最终共同影响居民消费的综合效应,还特别加入了民生财政支出与收入活动的交互项 (Lnmsczit×Lnidtaxit)。除此之外,模型中Xnit表示一组其他控制变量,它由对于居民消费可能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来表示,在此我们选取了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zincit、城乡收入差距变量cxgapit(具体由i省份t年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经济发展变量gdprit(具体由i省份t年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变量openit(由i省份t年的进出口总量与GDP之比来表示)、流动性约束变量liquit(由i省份t年的人均储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来表示)。此外,μi和μ′i为模型中不能观测的个体异质性,εit和η是模型残差。
在式 (2)所示的模型组中,相对于式 (1),为了考察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居民消费存在的门槛效应,主要的变化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换成了idtaxit,而模型的关键控制变量则换成了民生财政支出变量msczit和民生财政支出与收入活动的交互项(Lnmsczit×Lnidtaxit)。至于式 (2)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门槛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设定则与式(1)保持一致。
(二)门槛效应模型估计方法
在进行门槛估计时,首先要估计出门槛值η和模型变量参数估计值,然后进行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并求出门槛值置信区间。具体步骤为:首先,可将任意η0作为初始值赋予η,并且对于给定的门槛值,我们可以用OLS估计得到模型各参数估计值以及对应的残差平方和s1(η); 然后,我们可以最小化s1(η)值来获得η的估计值,进而可以得到变量参数估计值以及对应的残差向量。在得到参数估计值以后,我们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假设检验,第一个是门槛效果是否显著,第二个是估计的门槛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第一个假设检验在单门槛模型下原假设为H0:α1=α2,备择假设构建统计量其中S0为在原假设下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检验的原假设为相应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为,由于F1和LR1统计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Hansen提出的自抽样法 (bootstrap)来构建其渐进分布继而构造其P值以检验其显著性。在确定门槛效应显著的情况下,根据Hansen(1997)[24]的研究,在显著性水平κ下,当LR1(η)≤C(κ)时,不能拒绝原假设,其中在95%的置信水平下,C(κ)=7.35。
除上述检验一个门槛值以外,还必须确定是否存在多重门槛值。以式 (1)和式 (2)中的单门槛模型为例,可进一步设定双重门槛模型如式 (3)和式(4)所示:

将估计出的一个门槛值η1作为已知。再进行下一个门槛值的搜索,可用同样的原理和方法对不同分组数据做进一步检验判断是否存在更多的门槛值,同时,由于多重门槛值检验与单一门槛值检验原理相似,此处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来源与变量说明
由于我国自1998年起开始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同时一般认为我国开始民生财政的转型和建设是始于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民生财政”一词的出现,因而本文选用了我国2002—2014年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上述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5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财政年鉴》、 《中国税务年鉴》以及CCER数据库。考虑到价格指数的影响以及数据的平滑性,本文对相关变量指标以2002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具体数据见表1描述性统计。

表1 模型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在数据来源方面,在模型的解释变量方面,民生财政支出变量来自于各地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具体来自于各地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以及住房4个项目支出的总和。鉴于2007年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上述项目统计口径的影响,2007年之前的民生财政支出采用的是教育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卫生经费以及社会保障支出4项财政支出之和来表示,2007年之后则用支出功能分类中的教育、社保和就业、医疗卫生以及保障性住房4项支出之和来表示。另一方面,民生财政收入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各地间接税的收入额,其中,间接税的数额用各地财政收入中的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资源税5个项目的税收收入之和来表示。此外,在模型的控制变量中,Zeldes(1989)[25]认为当消费者在高收入预期下无法借款来维持当前消费时,就存在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得居民不能通过借贷来平滑生命周期中的消费。由于我国金融信贷市场还不是十分完善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等原因,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流动性约束变量的数据来源,我们参照余仁成 (2009)[26]构建流动性约束代理变量的方法,用各省份居民人均储蓄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测度各地区流动性约束程度,其中的储蓄是按照广义储蓄概念 (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支出之后的余额)来测算。显然,按上述测算方式,居民人均储蓄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越高,则说明流动性约束程度越低。
(四)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为了验证本文构建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具体形式和相应的门槛个数,首先需要对式 (1)和式 (2)中设定的门槛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本文采用自抽样法 (1 000次)反复抽样后模拟计算得到F值及伴随概率P值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2具体显示了在以民生财政支出变量 (Lnmsczit)为解释变量的式(1)和以民生财政收入变量 (Lnidtaxit)为解释变量的式 (2)中,分别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Lnczincit)和农村人均纯收入 (Lnncincit)为门槛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情况。检验结果显示,式 (1)和式 (2)中所有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门槛效应则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门槛效应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因此本文具体将采用如式 (3)和式 (4)所示的双重门槛效应模型来开展计量分析。

表2 面板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确定门槛的个数后,还需进一步对双门槛效应模型的门槛变量估计值进行估计和检验。即在数据自抽样为1 000次的情况下,在Lnczincit和Lnncincit为双重门槛效应均较为显著的情况下,确定具体的门槛估计值。表3列出了以Lnmsczit为解释变量的式 (3)和以Lnidtaxit为解释变量的式 (4)中 Lnczincit和Lnncincit为门槛变量及其各自两个门槛值和置信区间。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门槛值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我们还展示出了以Lnmsczit为解释变量的式 (3)中Lnczincit和Lnncincit的似然比函数图(如图4和图5所示)。从图4和图5可以看出,门槛参数的估计值是指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η的取值,在式 (3)中Lnczincit和Lnncincit的各自第一个门槛值分别为9.403和8.695,而各自的门槛估计置信区间则是LR值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C(κ)即7.35的η所形成的区间。具体从表3来看,就以Lnmsczit为解释变量的式 (3)而言,Lnczincit的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分别为9.403和9.773,Lnncincit的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分别为8.695和9.251;就以Lnidtaxit为解释变量的式 (4)而言,Lnczincit的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分别为9.403和9.748,Lnncincit的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分别为8.695和9.251。

表3 各门槛变量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图4 Lnczincit门槛值和置信区间 (Lnmsczit为解释变量)
出于我国目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以及本文估计结果解释的需要,本文根据上述测算出的门槛个数和门槛值,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Lnczincit)和农村人均纯收入 (Lnncincit)都划分为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收入阶段。以Lnmsczit为解释变量的式 (3)为例,在城镇居民收入阶段的划分中,我们将Lnczincit≤9.403划为下中等收入阶段,9.403<Lnczincit≤9.773划为上中等收入阶段,Lnczincit>9.773划为高收入阶段;在农村居民收入阶段的划分中,我们将Lnncincit≤8.695划为下中等收入阶段,8.695<Lnczincit≤9.251即划为上中等收入阶段,Lnczincit>9.251划为高收入阶段。对于以Lnidtaxit为解释变量的式 (4)中居民收入阶段的划分情况以此类推,在此不赘述。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图5 Lnncincit门槛值和置信区间 (Lnmsczit为解释变量)
在确定门槛估计值后,我们可以根据式 (3)和式 (4)所示的面板双门槛模型,对模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进行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估计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存在于居民收入的双重门槛效应。
一方面,对于城镇居民消费 (Lnczconsit)而言,在城镇居民收入 (Lnczincit)≤9.403的下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弹性系数为0.040 3,而在9.403<Lnczincit≤9.773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应迅速提高,弹性系数达到了最高的0.043 7,最后在Lnczincit>9.773的高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应有所降低,弹性系数降至0.032 6,这也验证了前面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1的结论,即由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优化居民消费预期方面的作用,使得民生性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效应为正。与此同时,在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转变阶段,随着中等收入人群占比的逐步扩大,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对城镇居民消费预期的改善作用不断放大,因此,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刺激城镇居民消费的效果也有较明显的增强。而在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阶段,随着城镇高收入人群占比的提升,高收入人群在消费结构上发生了较大改变,消费供给结构和环境成为其扩大消费的最关键制约因素,而当前我国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刺激城镇居民消费的效果有较显著的减弱。

表4 以Lnmsczit为解释变量的面板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居民消费 (Lnncconsit)而言,在农村居民收入 (Lnncincit)≤8.695的下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为正,弹性系数为0.080 3,而在8.695<Lnncincit≤9.251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应有所提高,弹性系数增至0.084,最后在Lnncincit>9.251的高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应进一步提高,弹性系数增至0.091。总体来看,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效果要大于城镇居民,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通过专门针对民生财政的转移支付使得民生财政资金更多地向 “农村倾斜”的结果。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没有如前面假设1中结论那样,随着收入的动态变化而出现 “先增后减”的倒U型的影响效果。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0年以后城乡收入比一直都在2.5以上,在农村中的“高收入”实际上在城镇中更多的还处于 “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从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门槛值对比中就可以直观看出,农村居民收入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的门槛值为9.251,这一数值甚至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由下中等收入阶段向上中等收入阶段转变的门槛值9.403。因此,从我国农村“高收入”人群消费特征来看,其消费受制约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故在农村居民收入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效果仍然是递增的。
表5的估计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显著存在于居民收入的双门槛效应。

表5 以Lnidtaxit为解释变量的面板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一方面,对于城镇居民消费 (Lnczconsit)而言,在城镇居民收入 (Lnczincit)≤9.403的下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0.045 2,而在9.403<Lnczincit≤9.748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进一步提高,弹性系数为-0.052 3,最后在Lnczincit>9.748的高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效用有所降低,弹性系数为-0.040 5,这也验证了前面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2的结论,即由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通过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使得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效应为负。与此同时,在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转变阶段,随着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扩大,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消费边际倾向的逐步降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通过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将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储蓄 “替代效应”逐步显现,因此,民生财政收入活动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的效果也有所增强。而在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阶段,随着高收入人群占比扩大,其高档消费品倾向决定了间接税通过提高普通商品劳务价格对高收入人群消费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同时我国间接税中消费税因具体税制设计原因对于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引导作用也有待加强,因此,民生财政收入活动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的效果有显著降低。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居民消费 (Lnncconsit)而言,在农村居民收入 (Lnncincit)≤8.695的下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为负,弹性系数为 -0.081 2,而在8.695<Lnncincit≤9.251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效应有所提高,弹性系数为-0.095 2,最后在Lnncincit>9.251的高收入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效应进一步提高,弹性系数为-0.105 6。总体来看,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效果要大于城镇居民,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具有 “累退性”,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越低、恩格尔系数越高的农村居民实际上承担的间接税税负越重[27],因而间接税对农村居民消费所产生的 “收入效应”也就越明显。与此同时,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并没有如前面假设2中的结论那样,随着收入的动态变化而出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影响效果。这其中的原因仍然如前面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样,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得我国农村居民的 “高收入”水平实际上更多的相当于城镇中的 “上中等收入”水平,因而在农村居民收入由 “上中等收入”向 “高收入”转变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通过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 “替代效应”仍在不断增强。
在此需特别注意的是,从代表民生财政收支活动综合效果的Lnmsczit×Lnidtaxit交互项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在表4还是表5中,Lnmsczit×Lnidtaxit的系数一直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例如表4中 Lnmsczit×Lnidtaxit对于城镇居民消费(Lnczconsit)的估计系数为 0.019 5,在表 5中Lnmsczit×Lnidtaxit对于城镇居民消费 (Lnczconsit)的估计系数为0.003 6。这说明在同时综合考虑民生财政的支出活动和收入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两种正反作用效果之后,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最终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向的,即综合来看,最终我国民生财政收支活动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和效果。
此外,从表4和表5中所示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来看,除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变量和对居民消费有着预期中的显著正向关系外,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度、经济增长率以及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其中,在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Lnczincit和Lnncincit)方面,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中,收入对消费有决定意义,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而实证结果中显著正向影响与上述理论预期保持一致。在城乡收入差距 (cxgapit)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表明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中高收入阶层,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虽然有较强的消费意愿,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因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向的。这与娄峰和李雪松(2009)[28]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对外开放度 (openit)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经济复苏缓慢,外需低迷,使得我国大部分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企业盈利持续下滑,企业信心不足,这也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率 (gdprit)方面,经济增长快的地方,居民增加的收入可能大多用于投资和储蓄,并没有转化为高消费。在流动性约束 (liquit)方面,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导致个人为抵御未来收入下降的风险而进行预防性储蓄。[29]相比城镇居民,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用体制不健全,农村居民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因而更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而增加储蓄。
(六)以民生财政为门槛变量的扩展性检验
前面的实证检验主要是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不同收入变化阶段下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用进行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如果从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的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整体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处于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的阶段,并且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仍然呈现出底部偏大、中上部偏细尖的金字塔型,而非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那么在这种居民收入发展阶段下,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对于居民消费是否也存在较为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这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对当前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绩效进行评估。
我们可以在式 (1)和 (2)所示的门槛效应模型基础上,将模型中的门槛变量由原来的居民收入变量更换为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变量,进而对上述问题进行扩展性实证检验。具体来看,仍然分为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估计以及变量估计系数分析两个步骤。
首先,从表6所示的门槛变量显著性检验情况来看,无论是以民生财政支出活动为门槛变量还是以民生财政收入活动为门槛变量,所有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双门槛效应也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门槛效应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因此可以判定在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作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仍然采用双门槛效应模型来开展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表7进一步列出了分别以民生财政支出活动(Lnmsczit)和民生财政收入活动 (Lnidtaxit)为门槛变量时的门槛值和相应的置信区间估计情况。具体从表7中两个门槛变量的门槛值来看,当以民生财政支出活动 (Lnmsczit)为门槛变量时,无论是以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时,第一门槛值都基本相同,为4.75,这说明无论是对城镇居民消费还是农村居民消费,民生财政支出活动的非线性影响变化趋势较为相同;而当以民生财政收入活动(Lnidtaxit)为门槛变量时,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第一门槛值有较大差别,分别为5.723和7.123,这说明相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来说,民生财政收入活动会在其数额更早阶段就对城镇居民消费带来非线性影响。

表6 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表7 各门槛变量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表8和表9所示的面板双门槛模型的各变量估计结果,对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为门槛变量下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应进行分析。
一方面,在以民生财政支出活动 (Lnmsczit)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如表8所示的估计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消费(Lnczconsit)还是农村居民消费 (Lnncconsit)的影响都显著存在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的双门槛效应。具体来看,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在Lnmsczit≤4.750、4.750< Lnmsczit≤6.484、Lnmsczit>6.484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逐步增加的三个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70 4、0.072 1、0.076 5,说明随着民生财政支出活动的不断扩大,其在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即期消费中的规模效应就越明显,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果也就不断提升;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在 Lnmsczit≤4.750、4.750< Lnmsczit≤6.925、Lnmsczit>6.925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逐步递增的三个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09 3、0.117 0、0.126 2,说明随着民生财政支出活动的不断扩大,其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果也同样不断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都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消费,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其收入明显偏低且中低收入人群比重更大的情况下,民生财政支出活动通过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预期来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在农村更为明显,因而近年来我国民生财政的资金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具有其合理性。

表8 以Lnmsczit为门槛变量的面板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另一方面,在以民生财政收入活动 (Lnidtaxit)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如表9所示的估计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消费(Lnczconsit)还是农村居民消费 (Lnncconsit)的影响都显著存在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的双门槛效应。具体来看,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在Lnidtaxit≤5.723、5.723< Lnidtaxit≤7.144、Lnidtaxit>7.144的间接税收入规模逐步递增的三个阶段,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88 7、 -0.094 4、 -0.112 6,说明随着间接税活动的不断扩大,其在抑制城镇居民消费中所产生的 “替代效应”就越明显,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效果也在不断增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在 Lnidtaxit≤7.123、7.123<Lnidtaxit≤7.533、Lnidtaxit>7.533的间接税收入规模逐步递增的三个阶段,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81 8、 -0.090 6、 -0.104 7,说明其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效果也同样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绝对值都要显著高于城镇居民消费,说明民生财政收入活动通过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居民消费产生抑制效果在农村更为明显。这主要是间接税税收负担随收入增长具有 “累退性”,因而在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其收入明显偏低且恩格尔系数更高的情况下,其对于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的 “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也更显著。

表9 以Lnidtaxit为门槛变量的面板双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最后,从表8和表9中Lnmsczit×Lnidtaxit交互项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Lnmsczit×Lnidtaxit的系数仍然一直为正,且均通过了至少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综合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之后,当前我国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最终仍然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和效果。
此外,从表8和表9所示的模型中各项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通过与表4和表5中相对应的变量估计系数对比可以发现,模型中各项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绝对数额和正负方向上都没有大的变化,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相关变量设置和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七)不同门槛变量分组下各省份空间分布情况统计

表10 不同分组变量下2014年各省份数据分布统计
从表10中可以看出,以门槛变量城镇居民收入(Lnczincit)为分组变量的省份空间分布情况显示,Lnczincit≤9.403的8个省份都处于西部地区,9.403<Lnczincit≤9.773的12个省份则以中部地区为主,Lnczincit>9.403的11个省份则主要以东部地区为主。另外,既作为解释变量又作为门槛变量民生财政支出 (Lnmsczit)和民生财政收入 (Lnidtaxit)在双重门槛划分的三个阶段也有着与上述Lnczincit类似的省份空间分布情况,即在小于第一门槛值的第一阶段分组中,主要以西部地区的省份为主;在大于第一门槛值且小于第二门槛值的第二阶段分组中,主要以中部地区的省份为主;在大于第二门槛的第三阶段分组中,则主要以东部地区的省份为主。与此同时,以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消费 (Lnczconsit)为分组变量的省份空间分布情况显示,居民消费最低的8个省份除了山西之外,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而居民消费最高的11个省份中,有8个来自东部地区。上述统计结果表明,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与解释变量以及门槛变量之间在地域空间部分上都基本保持了一致,从而也进一步印证了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分阶段非线性关系和 “门槛效应”特征。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背景约束下,首先探讨了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差异机制以及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果,在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的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出 “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门槛效果的理论假设。即:在居民收入整体水平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且中等收入群比重不断提升的第一阶段,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是增强的,而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且高收入人群比重不断提升的第二阶段,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是递减的。然后,结合我国2002—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无论是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还是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都呈现出 “先增后减”的倒U型双重门槛效果,而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的 “高收入”水平实际上在城镇中更多的还处于 “上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使得上述倒U型双重门槛效果并不明显,而是呈现为不断递增的双重门槛效果。与此同时,综合了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两种正反作用之后,最终民生财政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进一步地,考虑到当前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还处于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的第一阶段,本文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本身为门槛变量,对当前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绩效进行了实证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居民收入所处的发展阶段下,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果都是随着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而门槛递增,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效果也都是随着间接税收入规模的扩大而门槛递增。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虽然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体进程中,随着居民收入的动态变化,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将呈现出 “先增后减”的非线性门槛效果,但是鉴于当前我国整体居民收入水平仍主要处于由 “下中等收入”向 “上中等收入”转变的阶段,且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仍呈底部偏大、中上部偏细尖的 “金字塔型”,特别是随着今后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不断扩大,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将会不断增强显现。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今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优化民生财政运行机制,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扩大升级的建议。
首先,在民生财政支出方面,应通过不断加大民生财政资金投入和优化民生财政资金结构,进一步发挥民生财政支出在刺激居民消费方面的作用。在保障民生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今后政府应将民生财政支出政策目标定位于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的民生性公共产品服务。一方面通过扶贫和社保方面的资金投入来增加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和福利,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养老、医疗、安居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来改善居民在这些方面的预防性储蓄预期,提高居民即期消费意愿。与此同时,鉴于当前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刺激消费效果更为明显,因而在民生财政资金的具体投向上应该也要向这部分人群倾斜,通过在农村义务教育、城乡医保补助标准、扶贫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的 “扩围提标”,确保民生财政资金能用在刀刃上,发挥其在扩大居民消费上的最大效益。此外,随着今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增长以及高收入人群比重的提高,民生财政资金还应在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优化居民消费环境等领域加大投入,通过创新供给来引导激发居民潜在消费意愿。
其次,在民生财政收入方面,应在稳定既有税负水平的条件下,通过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同时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在进一步发挥直接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功能的同时,降低现有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其中,间接税改革方面应在我国全面推进 “营改增”试点的背景下,通过切实调低增值税税率来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居民对于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预期,减少中低收入人群购买相关商品劳务的税收负担,与此同时,通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加强消费税对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引导作用。直接税方面则应通过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构建持有环节征税的房产税制度、择机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于民生水平提高的现代税收制度,减少现行税收活动在抑制居民消费方面的“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1]刘伟.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4-11.
[2]李稻葵.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路线图[J].经济研究,2014(1):23-25.
[3]Bailey D,Harry D,Johnson R E,et al.Oscillations in Oxygen Consumption of Man at Rest.[J].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1973,34 (4): 467-70.
[4]Barro R 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6): 1095 -1117.
[5]Brunila A.Current Income and Private Consumption-Saving Decisions: Testing the Finite Horizon Model[J].Bank of Finland Discussion Papers,1997,30 (1): 1-24.
[6]Alesina A,Rodrik 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9 (2): 465 -490.
[7]Giavazzi F,Pagano M.Can Severe Fiscal Contractions be Expansionary? Tales of Two Small European Countries[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90,1 (5): 75-111.
[8]Feldstein M.Government Deficits and Aggregate demand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0,9 (1): 1 -20.
[9]Bertola G,Drazen A.Trigger Points and Budget Cuts: Explaining the Effects of Fiscal Austerity [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91: 45-48.
[10]Amano R A,Wirjanto T S.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nd the Permanent-income Model[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1998,1 (3): 719 -730.
[11]Wang L,Gao W.Nonlinear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Private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World Economy,2011,19 (2): 60 -76.
[12]方红生,郭林.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理论和实证[J].经济问题,2010(9):10-14.
[13]储德银,李善达.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2):44-55.
[14]毛军,王蓓.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正向传导还是反向倒逼[J].财政研究,2015(2):8-11.
[15]毛军,刘建民.财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研究[J].财经论丛,2016(1):19-28.
[16]苏海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啃 “硬骨头”[N].光明日报,2016-07-04.
[17]洪源.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诠释与中国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9(10):51-56.
[18]迟福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要求[N].光明日报,2016-06-22.
[19]洪源,杨司键,秦玉奇.民生财政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7):3-20.
[20]姜洋,邓翔.收入分配失衡下的消费需求异变[J].经济问题,2008(10):13-17.
[21]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4.
[22]高培勇.论完善税收制度的新阶段[J].经济研究,2015(2):4-15.
[23]郑功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要点与路径[N].光明日报,2016-06-29.
[24]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7,93 (2): 345 -368.
[25]Zeldes S P.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Rodney L White Center for Finan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s,1989,97 (2): 305 -46.
[26]余仁成.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D].长沙:湖南大学,2009:27-30.
[27]杨森平,周敏.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税收政策研究——基于我国间接税视角[J].财政研究,2011(7):72-74.
[28]娄峰,李雪松.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3):109-115.
[29]金晓彤,杨晓东.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四个假说及其理论分析[J].管理世界,2004(1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