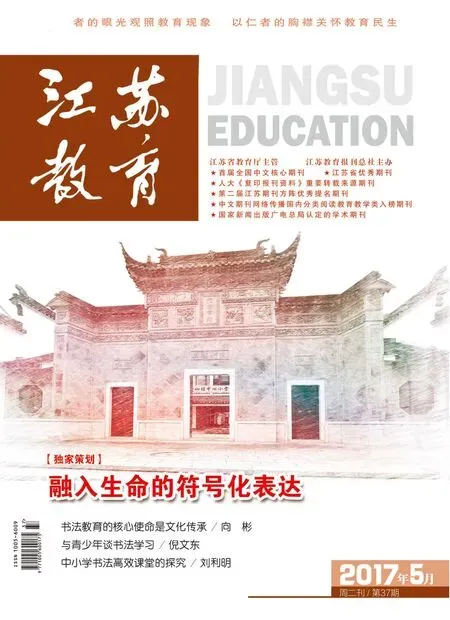中和之美
——《石鼓文》临摹分析
薛元明
中和之美
——《石鼓文》临摹分析
薛元明
《石鼓文》作为“经典”是由无数人来完成的。《石鼓文》在笔画、结构、章法上呈现出一种方整、严谨、肃穆的风格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后来秦小篆走向统一化做了铺垫。若临摹取法,对风格特征的把握可从四方面入手:笔“婉”;体“匀”;意“畅”;气“清”。
石鼓文;中和
对书法史产生影响的实质上有两条线:一是明线,历代社会风俗、文化礼制乃至书体演变等各种因素。一是暗线,这是书法非常独特的一点。被埋没的诸如汉简、墓志等被发掘之后,进而为书家所取法,甚至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书家,生前因为各种原因被掩盖,重新被“发现”,比如王铎在当代的影响。中国历史极其漫长,历朝很多器物被掩埋,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后重见天日,本身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了文物,书法始终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印记。清代金石考据兴盛,甲骨、汉简、青铜、石刻等研究走向高度系统化。相比之下,《石鼓文》在唐代已被发现,成为历朝书家所关注和取法的对象。
《石鼓文》从一个“个体”发展成一个“系列”乃至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说明了一点:“经典”是由无数人来完成的。不单是取法者、研究者的功劳,还包括那些珍藏者、整理者。只有保护经典、发掘经典才能传承经典、成就经典。《石鼓文》数经迁徙,历经辗转,文字磨损极甚,原有七百多字,宋欧阳修所见时有四百六十多字,现仅存二百多字,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被凿成舂米的石臼。唐拓本无传。现存最佳拓本为北宋时期,像中权本、先锋本、后劲本等皆影印名本,翻刻则更多。
《石鼓文》聚集了太多人的目光,从历代名家的品评论述中可以找到对个人临摹有一些启示的关键话语。
一是唐宋名诗人的关注。也许最初是对上面的四言诗感兴趣,无意间却开启了后世论书诗的先河,从中能够看出《石鼓文》受到的关注程度。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韩愈《石鼓歌》:“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鼉。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苏轼《石鼓歌》:“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瞉。”已经成为经典名句,临摹之初,不可不详加了解。
二是书家和理论家的关注。唐张怀瓘以四言诗来评论:“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欧阳修评为“其字古而有法”,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古朴雄浑。元潘迪曰:“其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知也”。明朱简《印章要论》言:“《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清孙承泽赞:“遒朴而饶逸韵,自是上古风格。”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总结一下,不外两个字:古法。
针对《石鼓文》的理解,关注书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存在鉴赏、摹刻、注释、音训等综合价值。《石鼓文》在近代考证被确认为战国时期的秦物。以四言诗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本称“猎碣”,唐人不识,就其形而起“石鼓文”之名,沿用至今。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有的专家建议将石鼓十诗与《诗经·秦风》放在一起综合考察。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周、秦历史与《石鼓文》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作为十枚石鼓排序的依据,进而以“诗”“地”“时”“史”进行确证。由上述分析能够看出,临摹《石鼓文》需要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些准备工作如果不做的话,依样画葫芦都谈不上。临摹一本碑帖就像与一个朋友相处,因为了解熟悉而能更好地沟通。当然,对于书家而言,不一定要非常精深,但要尽可能地了解,流传后世的《石鼓文》集联,正是建立在综合修养基础之上的。
《石鼓文》是秦始皇统一之前,在相对封闭地理环境下的产物。周朝对于礼乐有超乎想象的执着。对于美的向往、美的追求,最终被地处偏西的秦国完整地继承下来。进入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政治分裂局面的出现,各自不同的地域特征,使得文字出现强烈的地域化变异,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书法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有些地区所出现的美术化、工艺化、装饰化倾向,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历史有偶然性。秦最终统一了六国,保留了西周正统文化,就书法而言,对称、均衡等法则极大地影响后世审美。《石鼓文》在笔画、结构、章法上呈现出一种方整、严谨、肃穆的风格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后来秦小篆走向统一化做了铺垫。陆维钊曾说:“(《石鼓文》)与《宗妇鼎》《秦公》颇相近,圆转停匀,钟鼎文与秦刻石之中间过渡物也……其书体已由参差俯仰而趋于工整,无钟鼎文之奇伟逸宕,也未至秦刻石之拘谨。”如果要切实地理解,临摹时可与《虢季子白盘》和《泰山刻石》加以对比来读帖,体会《石鼓文》所具有的过渡时期特点。
《石鼓文》的特殊性可以用“四个唯一”来概括:一是唯一的字体。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籀文”至今已无迹可考,现今能看到属于此种文字体系的,仅《石鼓文》。二是唯一的形制。《石鼓文》乃“石刻之祖”,预示了材质的转变,金文通常把文字刻在器物内壁,《石鼓文》则是以籀文刻在覆钵形的石礅外表侧面。三是唯一的绵长脉络。对《石鼓文》的关注研究从唐开始,历代各方面的研究者难以计数。四是唯一的分水岭。当《石鼓文》作为一种字体基本定型出现之后,接下来便有两种方向,一是向更为规整的方向发展,一是向草化的方向发展。前者的结果是使得字体得以完全确立,后者的结果便是产生新的字体。小篆和诏版便是最典型的一组。小篆更加齐整规范,诏版的草化书写导致隶变。
若临摹取法,风格特征的把握可从四方面入手:
笔。“篆尚婉而通”,核心在于一个“婉”字。笔画圆润匀整、自然雅致,质朴遒劲、静中有动。
体。与东周西土系极似,较西周金文更加整练,概括成一个“匀”字。大多平行笔画呈装饰性排布,遒劲凝重、自然朴茂。值得注意的是,一字之中各部分的组合搭配和笔画之间的平行穿插,尽量把斜线变为圆转的弧线,追求平衡、对称之美。《石鼓文》已经注意到避免异体字出现,像“君、车、马、来、既、道”等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其”字则有二十多个,但只有一种写法。
意。笔笔中锋,结体停匀,布白宽舒,行列均衡,纵横成列,总结成一个“畅”字,其中蕴藏着敦厚的力量,滋润而不软沓,流动而不浮滑,既有力度又有厚度。

吴昌硕临《石鼓文》
气。字形如“铁索金绳,龙腾鼎跃”,但大小如一,自然天趣,毫无造作,故谓之“清”。
取法《石鼓文》者,不外四类:一是终生规模,如吴昌硕,前半生写原版《石鼓文》,后半生是写自己。二是参用,如邓石如的大篆《阴符经》,杨沂孙的《在昔篇》,吴大澂将小篆融入金文的尝试,萧退庵和邓散木的篆书,能直接看到《石鼓文》的影子。三是怪异,这一类人数极少,如朱耷和陶博吾,一家风范,如此而已。四是偶尝,涉猎《石鼓文》,喜爱之情可见,但不是主攻方向,所以未必谈得上开拓性,这一类人数最多。

杨沂孙集联

吴大澂集联
吴昌硕之前,大多关注原版《石鼓文》。自吴氏横空出世,《石鼓文》的临摹演变出两个方向,一是“原版石鼓”,一是“吴派石鼓”,需要区别对待,能够相互启发,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原版石鼓文》和《吴派石鼓文》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美,前者是中和之美,后者是激越之美。换一种说法,吴昌硕按照自我审美进行了改造,必然招致了一些喜爱原版《石鼓文》雅致中和书风之人的反对和批评。审美观点的冲突甚至对立可以理解,有些则需要区别对待。有的人态度很激烈,如马宗霍云:“以其画梅之法为之,纵挺横张,略无含蓄,村气满纸,篆法扫地矣!”“村气满纸”乃格调问题,在当时的世俗化、商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吴昌硕属于习气和个性并存的书家,要“善于学”。商承祚所言“变鼓文平正之体高耸其右,点画脱漏,行笔骜磔,石鼓云乎哉!后学振其名,奉为圭臬,流毒匪浅”。“流毒匪浅”确实夸张了。但不可否认,吴昌硕的篆书存在一些错别字和生造字的问题。然而,马宗霍和商承祚的篆书作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商承祚更多被视为文字学家。而像萧退庵说“天下篆刻之坏,始于吴昌硕”,事实上自己的篆书却受到吴昌硕影响。吴昌硕《石鼓文》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不可阻挡,一旦上手,很难摆脱,没有办法回头。这一点与取法老米者极其类似。诸多写米者,不免轻佻,轻薄而失去沉着,需要留心,“非不可学,实不易学也”。
吴昌硕影响巨大,一方面是个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距离当下太近,能见的资料太多了。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能承受多大诋毁,就能承受多大赞美。吴昌硕一生命系《石鼓文》,所投入的精力为常人难以相颉颃。吴氏强调“出己意”“贵有我”,他的确做到了。他不只是涉猎《石鼓文》,青年时期效法秦篆,不脱吴大澂窠臼,五十岁之前主取邓石如和杨沂孙,而后着意秦汉,吸收汉碑的魄力气度,将钟鼎陶器文字体势杂糅其间,融入金石之气,最终自成风貌、独出机杼。纵观书史,从未有哪个人像吴昌硕这样,对《石鼓文》临习最多最深且最有独到之处,呈现出一种令人激动的个人风格,高度纯熟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拿来借鉴。吴昌硕曾在临帖后跋语:“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然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唯其中古茂雄秀气息,未能窥一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说的是肺腑之言。
从本质上来说,吴昌硕也只是取法石鼓之一家者,更要看到吴氏的取法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成就了他。不能因为目光过多地聚焦吴昌硕而忽略了其他书家,更不能因此而忽略、轻视原版石鼓。在吴昌硕同时代的人物乃至晚辈之中,可能会受到吴昌硕的影响却能摆脱影响者,取法原版石鼓而成就不凡者,仅王福庵等一二人。王福庵篆书的古穆闲雅无疑从石鼓中来,然气息明显不同。其通临之作,给人以息气静心之感。观其父王同所临,对王福庵影响巨大。写工稳一路篆书的人,多半刻板和单调。王福庵能在工稳中体现性情,带有一点装饰化的成分,甚至还融入工艺美的成分,同时却能做到潇洒自然、流利俊美而不俗气,并且将这种风格演绎到极致,难能可贵。盱衡当世,罕有其匹。

黄士陵集联

马公愚集联
早年直接取法吴昌硕,而后自出己意者,无疑是朱复戡。朱复戡对诏版和青铜极其用功,由此拉开了与时人的距离。朱因为人生经历原因,少年得志,晚年不遂意,所以缺乏圆融,有些作品显得很生硬,从章草就能看出来,笔画坚硬如铁,形若砍刀。但朱复戡篆书确实摆脱了吴昌硕的影响。另一个推崇吴昌硕而能摆脱吴氏影响的当属陶博吾,陶的篆书卓然一家,但扭曲过甚,也只是一家罢了。甚至更早的像朱耷等人,都是特定的个人性情之作,非常人所能模仿,可作“旁观”。

朱复戡临《石鼓文》
清末以来取法原版石鼓的书家很多。如杨沂孙、黄士陵、黄易、吴大澂、罗振玉、简经纶、邓尔雅、黄少牧、伊立勋、马公愚等;有些非篆书名家,仍喜临摹,如翁同龢、沈曾植、任政等。总的来看,可以分两类,一部分描摹守成,一部分有个人风姿,时出己意。由此能够看出《石鼓文》存在的广泛影响。
如前所述,《石鼓文》有中和之美,故从取法来看,注重溯源而上,取法原版石鼓乃上上之选,能够按照不同的个人理念来加以“改造”。所谓经典,就是能够按照自身的要求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取法“吴派石鼓”,存在一定限制性,既是捷径也是框框,甚至会难以自拔。如果要打造自己的风格,需要另起炉灶。不过,真是出于个人喜好,选择“吴派石鼓”也无可非议。或者对于《石鼓文》只是博涉过程当中的一家而已,则另当别论。如果风格不显,首先要从自身找原因,或功夫不够,或才情不够,或时间不够,或体悟不够。因为关注《石鼓文》的人多,所以有时不免会受到他人影响。但要知道,书法是一种个体行为,临摹靠的是定力,就像王福庵那样。定力之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人理解力,是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所临摹的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现实世界的观点和潮流保持关注,但永远不随波逐流。
J292.1
A
1005-6009(2017)37-0028-04
薛元明(南京,210000),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多家专业报刊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