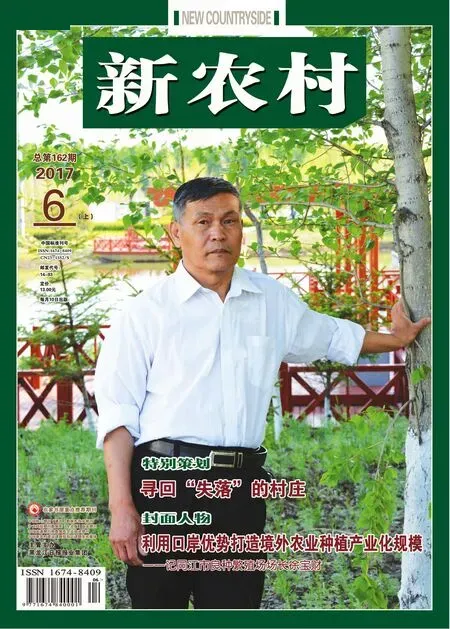晒谷记
□伍中正
晒谷记
□伍中正
为城市输送粮食和大树的村庄,永远有我抹不去的记忆。
夏天,村庄的农人们在田里抢收抢种。“双抢”那阵,是村庄里最忙的时候,小孩子就派上了用场,多在家里晒谷。
我也跟其他的小孩一样晒过谷,不光晒过,还晒过好多年。我能熟悉谷子的水分、色泽和温度,深切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那时候,我在自家的土禾场上晒谷。太阳暴晒过的土禾场有裂纹,父亲总在禾场上糊上一层薄薄的稀牛屎,免得禾场上的土屑掺进谷里,也免得那些谷子掉进裂纹里。稀牛屎糊过的禾场,晒起谷子来,相对来说,好扫些。
晒谷那几天,干牛屎的味,湿牛屎的味,谷子的味,一直在我的鼻孔里钻来钻去。我在树阴下纳凉。纳凉时,我看书,一本一本的看连环画。树上的一只蝉傻傻地叫。
隔一会,就得耘一次晒着的谷子。有时候,我用那把老式谷耙子耘。有时候,我用双脚耘。有几粒金黄的谷子扎进了我的趾缝,有点生疼。
晒谷最怕来暴风雨。风暴雨急,雨点也大。弄不好一阵暴风雨来,晒得差不多要干了的谷子,又被雨淋湿了。
村庄里,好多小孩为晒谷还挨了打。黑牛屎就挨过打。

胖爹家有一树好枣,树上红红的枣惹了黑牛屎的眼睛。他经常跑到树下打枣,打得树上的枣七粒八粒地落。有一回,暴风雨来了,黑牛屎还在树下捡枣。没想到暴风雨很大,等到黑牛屎跑到自家禾场上时,谷子早就淋湿了。黑牛屎的爹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后来,黑牛屎跑过来,在我面前脱下裤子,我一看,他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原来,他爹下手,一点也不轻。
谷子散了收,收了散,一场谷往往要晒三天。谷子晒干,车完后,就归仓了。
在土禾场上晒谷,不太好收拾,土屑难免进入谷中。家家户户盼望土禾场变成水泥禾场。后来,禾场终于在父亲的美好想法里变成了水泥禾场。在水泥场上晒谷好扫、好耘,谷子也极易晒干,也不用父亲再糊牛屎了。
前几年,两条高速公路穿村而过,大片的农田和山地成为了高速公路的路基。种田晒谷已不可能。黑牛屎家的田也没了。那天,他小声对我说起小时候晒谷的事,说得很投入,说得我痴痴地笑。我笑着对黑牛屎说,用手摸摸你屁股上的伤疤。他回过神,很正经地说,早就没了。我没有想到,黑牛屎住在高大宽敞的楼房里,还回忆到了小时候晒谷的事。原来,是我低看了他。
现在,我居住的安置小区,家家户户的禾场都硬化了。夏天的每一片禾场上有的是闷热跟空荡,再没有谷子可晒。
晒谷日子已远,晒谷的情景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