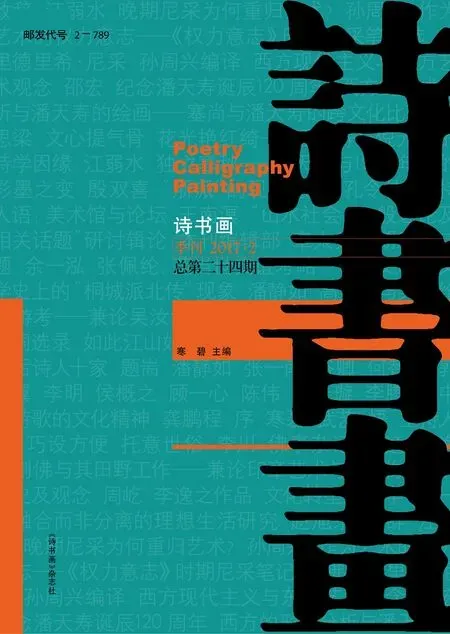逸之刻佛与其田野工作—兼论印章艺术与文、物、图的历史及观念
周 屹
逸之刻佛与其田野工作—兼论印章艺术与文、物、图的历史及观念
周 屹
前段时间,逸之在北京做了一个展览,名曰“行方便”,副标题是“刻者李逸之”。以“厕事”为创作主题,即遭不解,原因是“方便”虽生活常见的排泄行为,但不洁净,造反于一般意义上的信仰观念,如赵之谦因敬畏之心而造佛像缅怀妻女。那么“刻者”呢,与逸之篆刻者本色有关,但他的目的却要与当下拉开距离,强调展览所刻绘的佛教僧侣形象与篆刻乃至肖像印章之别。只是很多观者依然毫不犹豫地把逸之的“刻”这一行为视为“篆刻”的范畴,此即传统印学观念在起作用。基于此,本文专论两方面,这或可视为一种策略,考察篆刻家,如李逸之绘刻佛像印章的创作,以及他面临同样的问题时的处理办法:一是他刻佛像背后的田野工作,这一点甚为重要,尤其在当代佛像印创作强调风格创新的境况之下;第二点是传统印学中关于文、物、图转化的历史及观念,是如何在宋代印学形成初期影响篆刻艺术的,这一点的关键,不只是常论逸之“出格”“传统”的说法,而是在大的经义里面,逸之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常有观者论逸之所刻佛像就是绘画,或因此,笔者本想以“写生”二字作题目,但传统绘画的写生之笔墨,亦不能等同于逸之的铁笔、朱泥,随即放弃。从而转向其创作的背后,尤其他在藏区的佛教艺术考察,即二十年的佛教信仰区的“参与式观察”的田野工作。目的是在某些层面上论述其于佛教地区生活、工作对其创作的影响之重要,这不但不会遮掩逸之所刻画佛像的精彩,反而更能凸显他与本行当的佛像印家不同之意义。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或文化考古学等现代学科的工作方法,意指亲临某地参与地方群人的生活,从而对地方知识—吃、穿、住、用、行的文化、历史、语言,以及艺术等等深入地、整体地、多维地考察。逸之于藏区体验他们所体验、观看他们所观看,于藏传佛教信仰者的生活氛围里参与观察那么久,就其所编著的藏传佛教美术史和佛像作品而言,不仅能看出他深入的程度,亦能彰显出作为当代刻佛像者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乃至其他学科的不同视域。
一、文本的采集: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
且搜集逸之藏传佛教信仰地区的考察“笔记”(也包含其于汉传佛教的经历)。李逸之对藏传佛教地区的考察,自一九九六年开始,至今历经二十年。他说高原之景观壮美,古代的宗教艺术繁富,而且藏族文化艺术的深邃可能是外族很难体会的。尽管深入西藏艺术史的研究,但还是愈发觉得各种艺术交汇及渊源比现知的复杂得多。
天葬 逸之十几年前在直贡的寺院生活了很长时间,住的地方离全藏最大的天葬台很近。他看到很多去世的人在天亮前被送来。那时他在寺院住着,只要愿意早起就能看到,据逸之说在这里天葬就能上天堂。他看到人的尸体被分割成若干,骨头被天葬师砸碎,喂给秃鹫,它们迅速吃掉碎尸,直到吃干净才离开,而最后天葬台上仅剩血渍。对于生死乃至死后尸骨的下场,亲历尸骨分解的一般汉人多会有生理上的恶心感。逸之说每次看完天葬都会饿,到处找东西吃,见到冷馒头拿了就啃。
宗教仪式场域 逸之刻过一系列的剧场作品,据其所言,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古代西藏的寺庙殿堂里是利用藻井上方的室外光线投射到最中央、最重要的大型佛菩萨身上,这时殿内周遭依然黑暗,唯独耀眼的光束投射着主佛的身躯,借助自然光线,营造出明暗。逸之的体验,当进入这个场域的时候,身体一下子有了那种对神明神秘感的莫名崇拜的冲动。他说北京雍和宫的大殿,宗喀巴的像就是这样的办法,而后又推判西藏寺院建筑的传统。主佛旁边的巨大彩色帷幕,极像一幕戏台的视觉氛围,逸之强调这样的景观恰巧符合其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即周遭戏剧性的荒诞感。
擦擦 擦擦是逸之考察的主要历史、文物及艺术。逸之的研究表明,从遗留下来的擦擦来看,古格艺术家的擦擦创作很开放,容纳了当时艺术交流中的所有风格式样。克什米尔艺术对古格地区的影响最直接,托林寺兴建于九九六年前后,仁钦桑布(958-1055)多次从克什米尔招募艺术家,来古格建造寺庙,使得克什米尔的文化移植到藏西地区,甚至部分擦擦作品与克什米尔的相较,难辨彼此。从造像的特征尤其躯体的造型来看,写实与抽象有融合倾向。繁复的装饰,贴体袈裟的对称、密集的曲线衣褶,衬托躯体形态。再如印度佛学家和佛教艺术家逃难到尼泊尔西部和克什米尔地区,甚至翻山越岭到达藏西。这种迁徙是文化艺术融汇的重要因素,导致藏西的各种艺术潮流混合交织,也正因如此,今天梳理和归纳造像艺术的工作困难异常。古格时期的擦擦造像,除了对外部风格的追逐和接纳外,同时加以整合,如波罗式的艺术风格添入中亚式的卷草纹饰头、身光,或克什米尔样式加入波罗因素的着装、饰样等,所以今天所看到擦擦的喜玛偕尔邦、斯瓦特、吉尔吉特等因素,不足为奇。但是现在有学者把这种混杂了多种艺术的现象归为古格早期风格,并不恰当,还有多种复杂情况,如“综合多种因素的衍生风格再传入古格”“外籍艺术家在古格制作”“古格艺术家模仿制作或自觉整合式制作”等。所以,看到李逸之的这些整理成果,就不难发现其所刻作品中的各种复杂风格的搭配渊源了。
肉身剔骨 逸之说自己不信佛,但关于《剔肉记》,他说,时间是部美妙而伟大的氧化机器,氧化万物,谁都逃不过这个过程。生命是物质的,在氧化作用下老去,最终只剩下白骨。时间也是剔肉刀,剔度任何人和物,这里面没有情感可言,剔不停歇,不管美丑,公平而残忍,一切为皮相,万物存在因短暂而美。很多人认为“剔骨”系列意外或惊艳,按逸之的说法古代佛教绘画里早就出现骷髅的形象,而且义理源自佛教“白骨观”,是很重要的修持佛法的法门,目的是熄灭对色身的贪恋。禅法修持,色空不二,是证得空相的最直接方式,在西藏古代壁画、唐卡等等里常出现这一场景。逸之说在修悟的某个阶段把自己置身天葬台数月,想象晚上只身目睹着月光下零落残剩的皑皑白骨是怎样的一种场景,这就是修悟空相的直接途径,也是骷髅和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绘画里常见两个并排跳着舞蹈的骷髅形象,叫尸陀林主,就是跟这个概念有直接关联的形象。逸之说刻《剔肉记》,除了上述这些,就是他自己觉得“剔肉”二字有疼痛感,因为他觉得佛像也是皮相,只不过在观者习惯思维的作用下,《剔肉记》里失去知觉感的佛像们显得突兀了。
方便、污秽与神圣 逸之见到一个老唐卡,一件本生故事图绘,多个严肃的佛教场景中,一个修者喇嘛在厕事,逸之描述道:这么大大方方地画在唐卡里面,于是对“行方便”的争议引刃而解,寻常事罢了,问题的焦点转回到了为什么人们自觉回避这个日常、寻常得再也不能再寻常的厕事,不能容忍出现在神圣的佛教叙述中。世俗认为大小便是人身的排泄,排泄物是污秽的,佛是神圣的,是人们祈求保佑福祉的,怎能随便将污秽和神圣放在一起,刻绘僧侣大小便的形象?
每个族群都存在着关于“洁净”与“污秽”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出现与其信仰、伦理密切相关,而且隐藏在社会结构的深层,拥有严密的逻辑支持和限制。对“洁净”“污秽”的分类,一种行为、物体乃至社会现象被一族群视为“洁净”,另一群人有可能认为是“污秽”。很多时候“洁净”与“污秽”作为价值和象征的观念体系来区分不同文化的边界。不止唐卡有绘制僧侣方便的形象,在藏传佛教信仰者的观念中,天葬师、铁匠、屠夫等被视为污秽,因为他们不洁的工作,佛教伦理道德有轮回转世,很避讳杀生。铁匠制作刀,可能伤害、杀死人与动物,因此他们也是污秽的。污秽可以遗传和扩散,波及到亲属和后代,因此具有与生俱来,不可消除的属性。暂时性的污秽则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不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僧侣或是俗人、男人、女人,但可以通过佛教的一些手段加以消除。如使用煨桑等、沐浴节期间的沐浴、寺庙拜佛念诵六字真言等等。藏传佛教的洁净、污秽观念和我们不同,藏密上师及弟子用污秽之物“五甘露”,大香,是上师的大便;小香,是上师之小便;脑髓,是上师死后脑髓保存下来;红菩提,是女上师空行母(明妃)的月经、淫液;白菩提,是男上师的精液。所以藏族所认为的洁净与污秽更多是精神、观念的宗教层面,而并非是外在、物质的有形层面。
佛祖的骷髅骨架 二○○七、二○○八年逸之在白马寺生活,他说那是一段很自在充实、无人打扰的时光,虽然往返于藏区,但是这里却让他深深体会到气候的变化,尤其是中原白马寺的四季分明。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两千年的历史了,逸之一谈到它,就说唐代一度成为政治的戏台,打打杀杀,一次一次的烧毁……文革时代又是一出一出的戏,当然,戏肯定没完……一次在离逸之住处很近的地方挖出了一具元代和尚的完整的骨架,盘腿合掌,逸之说“莫名其妙地感动死了”……按逸之的说法,这件事情对其影响最深,他说白马寺的和尚看了尸骨都在一旁双手合十落泪。一起出土的还有石棺铭文,写着白马寺第多少任方丈某某,但在现存文献资料里始终没有查到这位方丈的任何信息,这里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逸之说,“我那时每天去斋堂吃饭还必经过这个地点”。

佛造像

佛造像
二、宋已降的印学与文、物、图的历史及观念
印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产生很早,存世最早的三方殷商纹饰印章,以及一九九○年陕西扶风出土凤鸟纹图像印(容庚《商彝周器通考》考得流行于西周中期),秦汉图像印章包括龙凤、麒麟、虎、神人、武士、歌舞、杂技、牛耕、车马到鱼、蛙等,多与原始信仰有关。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与中国艺术融合,但没有出现佛像印。宋代佛教与儒家融合而成理学,且研习佛教的文人很多,逸之说理论上宋代存在佛像印章,但据现存资料最早见元代有佛像印章。明代宫廷佛事用印不少,佛像印的材质是软质石头,还雕有龙钮及边款,显然文人参与了制作。但图案押印,包括动物、人物,以及器物等图形押记还不能笼统等同于秦汉肖形印。
之前印章是工匠制作,宋以后不管是刻文字还是图像,都变成了文人的艺术。但文人篆刻家刻佛像却很晚才出现,赵之谦是第一人,而后是吴昌硕、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所造佛像形象特征,多来自汉传佛教经书中。来楚生取法汉画像和敦煌壁佛画像,厚拙泼辣,现代佛相印多来氏一脉。因为刻佛像印章的多是篆刻者,且所用材料也是流派家发见的青田石、寿山石等,使用的办法也都是蘸朱钤印,所以才视其为印学的一部分。逸之虽刻行方便、剔骨等,但并偏离出印学的真脉。
值得注意的是,逸之所说“直到接触到元代佛经插画精湛的线绘,就挪用到了印上”,这既是取法经传文本中的图像,和上一章谈到的取法佛教僧侣生活及擦擦等文物不同。经典传承的文本中的佛像,一般认为是附会经书的插图,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从宋代文人发明的、历经明清直至今天还在使用的、以描绘摹刻的办法,把经典文本或金石器物转化为图,而后再用图转化为器物的观念和技术谈起。这一观念伴随着金石器物考古之学的兴起而勃发,金石家把金石器物描绘图像,而后摹刻在石头或木头上,再拓下来,即把可视觉的物象转化为二维的图像文本。这即是文物转化为图像方法。关于文、物、图转化的历史及观念的形成,简要述之。
先说依照经典文本绘图,我们且称之谓“依文绘图”。经学的传统里,尤其汉唐间解经注经,到了宋代依然延续,而这一传统下的宋代《三礼图》即是“依文绘图”的代表,即把儒家经史中叙述的关于祭祀礼仪的器物的描述文字转化为图,而后依照图像铸造礼器。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以“国家兴儒,追风三代”为朝政主纲,他祖召集儒士,删定聂崇义奏上的《三礼图》,而后将此书中的礼仪图像绘在国子监的墙壁上,且颁行全国府州县,自此《三礼图》大行于世。
《三礼图》大半篇幅是图像,文字注解仅占少半。就中所绘图像,多遵从东汉至隋唐间的注经。书中图像对不同身份的人物在不同场合的穿衣戴冠有着精微的呈现,以示严格之规定。天子祭祀时的服饰与冕官的图像亦有说明,如祭拜先公时需戴瞥冕,祭拜四望山川时需戴霖冕,祭拜社翟时需戴烯杭冕等。对礼仪服的材质和纹饰,以及佩戴首饰都有具体要求。而这些图像能够直接地呈现礼仪情况,易于掌握,可明确区分。
《三礼图》雕版雕工严谨,对当时的图学影响至深,但随着金石学的兴起而它的问题开始暴露。窦俨《新定三礼图》序言:“博采三礼旧图,凡有六本,大同小异,其犹面焉。”“博采三礼旧图”,即以汉唐间书本所载名物传统知识为依据,新订三礼器物之图像。汉唐间,鲜有专门研究金石器物者,经学家往往在解经时,遇到关涉礼制的器物词汇,才做研究。而研究方式的则是对相关器物名称、形制注疏,包括经典记载的礼器和礼制的关系等。《三礼图》根据经典经文“揣测”绘制图像,而不是根据古代礼器实物,那么根据金石器物绘制的图像方法,我们称之谓“依物绘图”。
嘉祐六年(1061),经学家刘敞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常于长安古墓荒基搜出土古物,这即是现代学科所谓的考古的田野工作,“荒墓破冢,耕夫牧儿,往往有得”,刘氏“悉购而藏之”,归长安,“所载盈车”。后将所得秦鼎彝十多件,摹刻上石,绘制图象,考其文字,辑成《先秦古器记》一卷。此书即绘制摹刻器物图像。
元祜七年(1092),理学家吕大临作《考古图》,较
欧阳修《集古录》所辑数量更多。吕氏从官、私藏品中录自商周至汉的青铜器210种,玉器14件,描摹刻录器物的图像和铭文,测其尺寸、重量、容量,追究出土地、收藏者等,并间考证、说明,下附释文。《考古图》不止对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等进行准确记录,而一改《集古录》只摹拓铭文、未录器物“图形”的缺陷。

古格系列

雪团打雪系列
说到吕大临,就不得不谈参与金石学的大画家李公麟,因吕氏的《考古图》所录器物含李公麟所藏的58件铜器和14件玉器。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公麟“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李氏《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不传)辑夏、商以后钟、鼎、尊、彝,而后考定器物世次,辨识其款识,图绘器物上的花纹、铭文及器形,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以及用途,还作前序和后赞。
作为画家,传神写照的绘图技艺对李公麟来说亦非难事。王明清曾于王厚之处见到李公麟自画所藏古器图,感叹李氏所绘器物“真一时之奇物也”。李公麟还曾针对所藏的玉镇,推断古人“几案间,多有此类”,认定“玉镇”乃汉代席镇,压住座席四角之用。李氏这种印证器用及时代的办法,也属于“依物绘图”的影响氛围之内。
那么,《三礼图》是如何受到挑战的呢?
“依文绘图”的《三礼图》认为“爵”与“雀”同音,把的“爵”绘成麻雀背负杯子的形状。苏轼得到胡穆赠古铜器,作诗咏叹:“只耳兽啮环,长唇鹅擘喙。三趾下锐春蒲短,两柱向张秋菌细。”双柱三足,显然是“爵”,但胡秀称其为“鼎”,因为和《三礼图》中的图像不一样,苏轼怀疑,却无证据,只得依其说。陆佃作《礼象》(此书已佚)引文彦博、李公麟等所藏古铜爵,确认“爵”“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并绘其形,依此纠正《三礼图》风气中误会的“爵”是“雀”背“杯”的形制。
在复兴儒学的风潮中(像《三礼图》自上而下的礼教行为),文人最大的梦想,莫过于想见儒家先贤时代的风气,当他们看到三代金石器物,犹想周公、孔子等先贤所见到的风物一样。窦修《三礼图》序:“率文而行,恐迷其形范,以图为正,则应若宫商。”文士们看到三代出土器物,以物象鉴察《三礼图》,一改“望文想象”而“观其形范”,据金石器物图像批评当道的《三礼图》。政和五年销毁国子监及郡县学堂的《三礼图》现象,即反应了金石考古在当时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以物绘图”对“以文绘图”胜出。
尽管《三礼图》属于完备的“制礼作乐”的“经书”图解,但在当时的文化观念来看与金石学的研究并非绝对边界。徽宗时,制礼局(制作礼器的部门)的详议官翟汝文推崇李氏的《考古图》,将其所藏著录“每卷每器,各为图叙,其释制作镂文、窍字义训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制礼局其实就是借鉴了李公麟的绘图考察制作礼器。而且徽宗《宣和殿博古图》也是仿李公麟《考古图》,大量搜集金石学家所藏金石器物。
说完了金石器物之学与文、物、图在宋代的大略情况,再说这一风气里古玺印章、集古印谱以及宋代文人用印问题。
宋代常被后来文人视为印章的衰落期,原因就是官方用印非秦汉传统。《宋史·舆服志六》记载:“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当时将“屈曲缠绕”称为“缪篆”,米芾“填篆”其实也是如此,认为“屈曲缠绕,以模印章”就是秦汉印章的传统。时下有学者为了与汉代缪篆区分,将唐宋印章的篆书称之为“后期缪篆”,但未明其中变化原因。宋代制作印章,其实和《三礼图》一样,官方依照前代文书记载制制作本朝的官印,但经典记载的文本,并不是秦汉印章实物,自认为是秦汉传统,其实相去甚远。
然而,印学的转折点在于宋代金石器物之学的兴起。金石学家把古玺印章作为金石器物描摹绘刻,而后拓出,制作成谱。但是,沙孟海先生认为印学的形成标志是篆刻家自己画印稿自己刻,米芾是第一代篆刻家。而集古印谱未被重视。
陈振濂先生言:“最早的印谱该是杨克一的《集古印格》,成于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其次则是《宣和印谱》。自宣和之后,高宗在位三十多年,不见有印谱著录的史籍。至乾道淳熙间,《啸堂集古录》出,同时有王顺伯的《复斋印谱》。王顺伯是乾道进士,其谱估计与《啸堂集古录》同时或稍后,再后则是颜叔夏、姜白石诸谱了。”据孙向群先生考察:“还另有二十二部其他人汇集的《集古印谱》存在。这些集古印谱的编者分别为吕寿卿、邓挺器先、袁起岩、沈虞卿、张橐元辅、荣次新、孟信安氏、汪季路、杨伯虎、元延之、颜景周、徐概景平、张南轩敬夫、潘柽德文、李次膺、汪圣锡、谢伯任、朱至、董令声(声当为升)、赵师锡、韩肃可允寅。”所以,集古印谱显然应被视为印学形成的标志之一。
所以,集古玺印章和米芾等文人篆刻同样重要,都是宋代印学形成的标志。这也道出了除了官方用印外宋代印章的两种使用形态:一是米芾代表的鉴藏印,这一路径其实就是唐宋朱文的传统,后来被视为文人篆刻艺术的开端,与书画并称;另一个即是金石学家研究器物风潮中的集古玺印章,这一研究方式与集古印谱的文化、“印宗秦汉”的思想紧密关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宋代金石学家以及很多文人的用印出现秦汉印式,显然师法秦汉印章已经存在。
那么,印学的形成与文、物、图的转化有何关系呢?需要陈述两点:
王俅的《啸古堂集古录》收辑三十七枚古印章,绘制印章实物的图像。这样的集古印谱的方法直到今天一直存在,虽然多数已经是原打印稿,但观念无异。吴云《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序:“爰先检官印,去其重复者,得若干钮,属汪文学泰基肖摹钮制印式于前,而以原印印之于后,复逐印加以考订,其或官名、地名不习见者,虽旁引曲证,证必援据诸史以为论断,不敢逞臆穿凿,务使千百载之典章制度与古人篆法,精微灿然,必陈于目前。”考清同治三年的《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书影,吴氏把印章的原钮绘出,在左旁蘸朱泥印出原印,右上角附释文,右下录藏者。金石学家将搜集来的古玺印章与金石器物一起摹绘刻成图,事实上篆刻艺术的赏会印拓的传统自此开始,历代所论篆刻艺术,皆是依据印拓展开。这是其一。
第二个是,宋代印章的一种—押印。黄惇先生主编的《隋唐宋印风》中载“桂轩”,古鼎形状;“叔刚”,锺形状。孙慰祖先生主编的《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载有不少钟鼎,乃至人物、动物等器物形状的图像印章。金石学家收辑古玺印章绘制摹刻的同时,金石器物也成为印章的取材与摹刻对象。这种摹刻方式亦是器物转化为图像的代表。虽然与前代的肖形印章有着很大的区别—一个是压泥等,一个是钤于纸上,但是从取物绘图的经义而言,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隋唐宋印风》还载有一方乾卦符号印章,这与宋代学人如朱熹、郑樵等的图学观念亦是密不可分。朱子著《周易本义》即把洛书河图放在书之首。郑樵《图谱略》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曰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廪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故作《图谱略》。”图像文本与书籍传承的文本形成了经纬交织的经史系统,“左图右书”则是汉以前文士主要的学问路径。而到了汉代,发生了变迁,人们开始掌握今文,尤其今古文之变以后,今文著述、注疏取代了古书图文结合的方式,以至于出现“困后学而堕良材”窘境,这种做法导致了“成功者少”。郑樵勾勒了图由盛及衰的情况,他指出刘向、刘歆父子编纂《七略》的错误,在目录学著作中,只收书而不收图。自此以往,学者因循,终致图谱之学衰落,影响学术的整体发展。
在这种图学文本盛行的风潮里,各种图像类型的书得以发展。北宋之前虽有图本,但限于技术,传播有限。《三礼图》作为国家行为需要大量摹刻复制传播,只有刊刻成雕版印刷才能达到目的。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摹拓与印刷技术提高,图像文本独立成为“显学”。比如从仁宗中期之前存世的十种金石器物图谱,如《传国蜜谱》一部、《礼器图式》一部及两部古文字图谱,其他六种均为器物铭文的拓本。国家行为的还有乐器图谱《皇祐新乐图记》、建筑图谱《营造法式》、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图谱《宣和博古图》,以及医学图谱《大观本草》等。私人更不用说了,欧阳修、吕大临等金石学家的著述基本都未离开图谱。而其他的如李孝美关于制墨工艺与墨形制的《墨谱法式》,司马光的清玩类《壶新格》、《古局象棋图》等,图像文本的门类包含了金石、书法、音乐、医药、建筑、清玩、地理、天文等。
这就是宋代的图像文本兴盛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大量的文人参与到金石器物的考古摹绘刊刻,印章这一文物转成为图像文本—集古印谱,进而影响到印学的发展道路,印章最终欣赏的是视觉可见的印拓。当代印学批评者,于图像印审美上常以风格展开批评讨论的时候,依然以而秦汉以降的肖形印为风格为基础,往往忽略金石学与印学的中介—文、物、图的转化观念。李逸之刻绘佛像,不管题材来自藏传还是汉传,乃至日常的吃喝拉撒,其方式以及其篆刻家的身份,都在这一观念里,如擦擦、佛经书的经典形象转化于逸之的印章上,我们欣赏其作品时,尽管对其所刻的石头、技术有着百般的神秘感,但对其作品的雅俗判定,或展开批评工作,都要根据其印出的佛像印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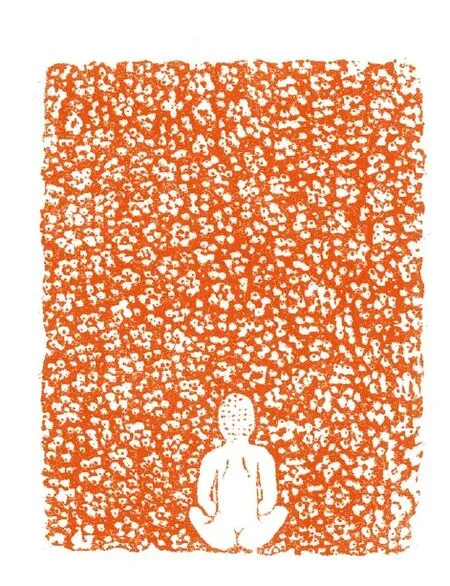
雪团打雪系列

雪团打雪系列
转化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即是刻划。试想,假若艺术家追求的只是图像,那么他们摹刻石头、枣梨木显然是多馀,无需钤盖或拓在纸上,直接绘图不更省事?
显然,篆刻家乃至李逸之这样的刻者追求的不只是描摹绘画。也就是说刻画的刀即笔,与中国古老的刻器关系极为密切,甲骨刊刻、凿刻铜器、刻陶等等,与域外模押戳记(李逸之考察的擦擦即为此类)有所不同。古玺印章中,除了铸造,很早就出现了刻印,而“刻”,唯独在宋已降艺术家手中得到发展,且成为艺术,不管是金石家刊刻枣梨木,还是米芾自己刻鉴藏印。宋之前文人对文字及工具毛笔已经熟练掌握,到了宋代他们又把本来属于工匠的刻刀也抢了。而押封泥也变成了图像文本的印拓,而封泥也被拓成黑白的图像文本。
宋代,将物转化为图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工匠行为,而是艺术家自觉的掌握刻画,经过大量的摹刻锻炼,画印稿、拎刀刻印自不在话下。而且每个人的刻画有着很大的区别,还能体现作者的风规格局以及修养,且能用书画欣赏语汇平移而来展开批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宋已降的印章艺术,是一个欣赏印拓以及印拓里的文字、图像的艺术。
结语
讲完宋代金石器物研究的文物的采集,以及文、物、图转化的历史、技术与观念,再回过头来看逸之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文物考古及绘刻。
首先是多重文本的融会。
根据本文第一章,逸之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参与藏传佛教信仰区信仰者的生活中,即体察僧侣及信仰群众的吃穿住用行,以及宗教仪式、场域等等;一是对古代佛教遗存文物的考察,例如擦擦、佛像雕塑、经卷、唐卡等等。前者属于参与观察,后者则是文物考古,而且两者在并非明显界限,而是多维交叉。
就当代篆刻家刻人物、动物或其他金石器物之形象的方法而言,大多的路径即是参照古代遗留文物(篆刻方面就是“印宗秦汉”,并非文本意义上的缪篆)。来楚生师法的对象即是古代石刻佛像,沿着这一路径的时下篆刻家,很常见。由于古代石刻的历经风雨剥蚀,残旧浑然成为所谓“写意”肖像印人追求的意趣。所谓“金石气”,也与此有关,如齐白石重“刻石”,黄牧甫重“凿金”。其实这都是摹仿的金石器物的路径。至于考古田野的方式,宋至清的考古学家一直有这样的研究方式。清代乾嘉金石学大兴,文人对文物的考察常常会绘制访碑图之类。对文物的摹拓更是较前代先进得多。篆刻家往往享用他们的成果,尤其是金石学家研究器物铭文之后,篆刻家拿他们考定的文字入印。但篆刻家很少参与田野工作。即便如今书法篆刻专业的研究者常常到各地考察古代金石器物,这都和李逸之不同。
与清代刻佛像的篆刻家相比,逸之除了参与观察工作,也没有放弃图像、文字等文本意义上的佛教经义。逸之说:“二十年来采集擦擦样品766种,涵盖古格建国的十世纪中叶到灭亡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背后即是一部古格佛教艺术史。多年古格擦擦造像的田野考察积累,影响了佛印创作,自然吸收藏佛美术的诸多因素,如壁画、擦擦等等,将古代西藏艺术史的田野体验挪移到佛印创作,使之溯源有本,意与古会。每年在西藏腹地做古代美术田野考察,自然想着要把藏传佛教造像融入印中,开始没有头绪,毕竟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糅合到一起要解决其中相互妥协的问题。直到接触到元代佛经插画精湛的线绘,就挪用到了印中。再后来在一次考古现场,目睹墨拓明代玛尼石,豁然开朗,于是成了古法隔世受益者,生欢喜心。”元代佛经以及佛经中的插画,作为经典以经书文本传承,李逸之不仅不因藏区田野工作而排斥,反而将二者结合。
文人流派篆刻家敬造佛像,例如赵之谦“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惠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即出于信仰。弘一法师为书作,即使用或刻佛像印章。而到了来楚生,已经变成了一个主题明确的风格追求,不再局限于信仰之内,转向趣味审美的探究,表达自己对章法、刀法的理解。逸之的田野考古,在藏区发见文物进而转化为图像的研究工作,并不能因为其所刻“污秽”而被笼统视之,况且“洁净”与“污秽”的观念,而笼统视之为反抗印章在经典书籍中记载的传统,因为这并非一简单视觉的问题。生活日常与宗教仪式之间拉开的巨大间阈,逸之并不信仰佛教,而且除却不同于前面篆刻家的工作—田野参与观察之外,相同处又能直接将佛教经义绘刻成作品,作为艺术家,逸之的这种理解并非“知识主义”的,他所建构起来的历史和其他的艺术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元代佛教经卷上的佛像,亦是宋已降的图学传统,而不是真正的佛陀。
其次,关于版画。
逸之不解道:有人认为我的作品有版画的倾向。他解释说:篆刻实际钤印效果同样有版画的属性特质,尽管一个是关于文字类,一个关于绘画类,但不能否认两者的很多类似部分。逸之还说,刻制、线质、印制等,和版画一样,都充满篆刻线的特殊意味,甚至篆刻里的“金石味”版画里也有,“印的肖形类更是一种小型版画,有的版画还就是用石板来刻制的,但有没有批评界批评版画的篆刻倾向,但篆刻界好像比较在乎这个,我实际上没有这个主观上的有意倾向。当然,最近创作的佛印我认为确实是版画了,只是利用了所有篆刻的工具,比如刀具、石头、印泥、宣纸等,说到底是利用了印的形式,更说明印和版画的微妙关系,但谁是谁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可能是我认知有问题吧。”
鲁迅《南腔北调集·序》:“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鲁迅的版画意在反照世间万象,即便逸之所绘刻之佛,技术手段和版画有所交叉,但印章艺术的边界为何要仅被视为一种死去的知识观念上呢?
李逸之的主题性创作,我们完全可以从其篆刻家的实践展开讨论,即其创作拥有与版画一样的特质。做过木匠、刻过木版画的齐白石事实上亦有很好的实践,刻一些山川鸟虫之类,既有印面钤盖印泥,也有边款,多是其在乡下的生活体验与观察。然而李逸之的所刻的主题,那种生活化的体验,博物馆玻璃框架内的断头佛像目视着下垂的蜘蛛网,这种直接进入印面的取法,也有了视觉的入侵,这就是“刻篆书”之外,印学走向现代的一条很可观的探索。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点。
第三,当代艺术、众生相与佛像。
自宋代文人掌握绘刻技术开始,当代的文物形象如钟、鼎等被刻如印章之中,还有古琴、乾卦、人物等等。而逸之所刻的众生之相—戴墨镜、听音乐即是平常生活,博物馆残破之相组成的碎片化的历史,等等这些世间万相,意指现世生活。人人都是这世间之相,事事皆可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体。这就是当代艺术。文字、器物,乃至人物、动物,在宋代绘刻成印章里的图像,就绘画的视角来讲,最易与当代艺术发生关联。
然而,篆刻的特殊在于文字。就书法、篆刻作为艺术纳入现代学院教学,乃至现今艺术的基本呈现方式—展厅,入印文字也开始被视为视觉改造的对象。可是篆刻艺术还是以“篆”为主。某国外学者认为没有汉字基础的人可学习篆书,因为它是象形文字,可以直接视觉理解。这虽然道出汉字之特别—“象形”,但荒谬的是将“象形”和“图像”等同。篆刻艺术之所以一直传承至今,而不像绘画那样,原因就是篆字与刻画的统一。也就是说刻印进入现代的路径绝非从视觉展开。
所以,评判逸之的工作,总会纠缠在传统佛经文本经义、篆刻传统,以及田野考古所得佛像器物之间,当为了实现刻绘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一目的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参照当代艺术观念。现代艺术家观看到的人、物,乃至大千世界各种形象的存在场景,以及所看到的更早时期的人们对世间万物的描绘—岩画的人与动物、墓室里的娱乐场景、卷本上的文士雅集或隐居、宗教仪式使用的神器上的装饰等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李逸之尝试着将古人所绘再摹一遍,不管是对文物传达的精神能否有精准的把握,还是历代佛教徒所经历的山川等自然的景观的体验,当他回到工作室,视觉的记忆的幻象,营造的是一个不同于考察地以及文物的、具有预设的艺术场域。这一场域不仅不同于佛教艺术家的创作境况,更找不到万物的映象。说白了,逸之根本没有把表相的世界视为绘刻的底片。
青田石、寿山石虽能在逸之的手中轻易把玩,但其在佛教信仰区的体验显然无法完完整整绘刻于石头之上,尺寸早已设定好的边框,不管石头是何种形式,正方形、长方形,乃至多边形、无规则形,其取舍佛教人物形象,注定是依照这些形附势造像,而所选择的佛教形象也只是“片面的”。但这并不重要,亦不能妨碍逸之表达自己的感受与体验,当某个形式更适合僧侣配戴墨镜或戴耳机听着音乐、摆着某个姿态、大小便等等,众生相,日常生活的片段,都是他截取的某个意义。
我们完全可以用篆刻的语义去理解逸之的工作,比如他对石面上的人物的俯仰向背、计白当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等等的把握,乃至其对绘刻佛像时刀法的变化无常的表现,都与其以前篆刻实践训练的关于文字的章法、不同风格流派的冲、切、削等经典刀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然而,这种被定格的观看法则,好像只能配合篆刻艺术较早期的创作范式,而不能配置在“剔骨”“行方便”之中。

雪团打雪系列

雪团打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