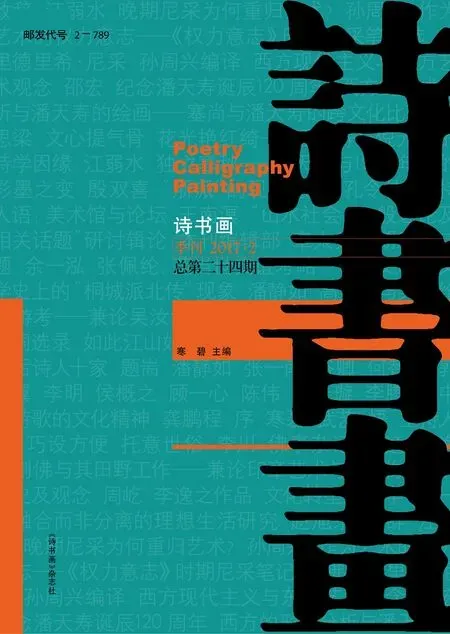佛事杂记
李逸之
佛事杂记
李逸之
我不信佛,信空,但空又有佛教属性,关系就有点牵扯不清。
《剔肉记》系列创作的想法……简单说,时间是美妙的东西,是部伟大的氧化机器,氧化万物,谁都逃不过氧化过程。生命是物质的,在氧化作用下老去,到最终还能留下的是白骨。时间也是剔肉刀,剔度任何人和物,这里面没有情感可言,剔不停歇,不管美丑,公平而残忍,一切为皮相,万物存在因短暂而美。
很多人认为“剔骨”系列意外或惊艳,倒也不是。古代佛教绘画里早就出现骷髅的形象,源自佛论“白骨观”,这是很重要的修持佛法的法门,目的是熄灭对色身的贪恋。白骨观是禅法修持色空不二,证得空相的最直接方式,在西藏古代壁画、唐卡等等里常出现这一场景。简单说,就是在修悟的某个阶段,把自己置身天葬台数月,想象晚上只身目睹着月光下零落残剩的皑皑白骨是怎样的一种场景,这就是修悟空相的直接途径,也是骷髅和佛教的关系,源自古代佛教理论体系。藏传佛教绘画里常见的一个形象,就是两个并排跳着舞蹈的骷髅,叫尸陀林主,就是跟这个概念有直接关联的形象。
最初刻佛像,想法就是要做自己的佛像印,不只是停留在对古代佛形象的复制,如果跟现代、当下接得上关系,则是我最想要的。刻《剔肉记》,就是自己觉得“剔肉”二字有疼痛感,不知别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佛像也是皮相,只不过在观者习惯思维的作用下,《剔肉记》里失去知觉感的佛像们显得突兀了,……其实一切都是皮相,不用多解释,况且我刻的佛像骷髅红灿灿的,绚烂啊,多喜庆色相啊。
佛教双修与春宫不同。以前刻春宫图刻了一阵,但禁不住传播得快,色相还是抢眼球,其实数量不多,这几年没刻。藏传佛教里有双修空运,和春宫是两个概念,色相是空,佛教里强调的是这一点。
一庐先生,是个心胸坦荡荡的爷们,我打心底尊敬他,不光在艺术方面。这些年他一直安静地创作,陶醉在自己乐趣中,我很羡慕他的状态。我离开广西后他从不干涉我干什么、怎么干。我的作品集里他写的序言表扬我,我对此诚惶诚恐,尽可能做好自己吧,
藏传佛像引入创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多年积累的西藏艺术史的认知,很容易受影响。我在西藏二十年了,主要在西藏西部地区,几乎每年都去。高原自然景观壮美,古代的宗教艺术发达,藏族文化艺术的深邃可能是我们这些外族很难体会得到的,尽管我也介入西藏艺术史的研究,但越了解越发觉得各种艺术交汇及渊源比现知的复杂得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了解真相过程的中途状态。应该说我的作品得益于对西藏文艺的兴趣、一庐先生的启发,以及自己技术上的优势。
十几年前我在直贡梯寺住过一段时间,这个寺院在半山腰,山顶就是全西藏最大的天葬台,相传在这里被天葬必上天堂,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死后在这里天葬。所以特别多的去世的人在天亮前送到这儿,举行仪式后立即送到山顶进行天葬。那时在寺院住着,只要愿意早起就能看到。看过很多次,但不恐怖,整个过程就是秃鹫们迅速吃掉尸体,骨头被天葬师砸碎再喂食,最后秃鹫散去时,天葬台上只剩下一点血渍。一般汉族多数人会有生理上的恶心感,我每次看完都饿,到处找东西吃,见到冷馒头拿了就啃。
我不信佛,不知道什么是“色即是空”,也没到那个领悟的份上,我只是“消费”了佛教中“白骨观”的观念,传递其形象,也没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一直存在着。“空相”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佛教独有的,多种宗教都有各自的阐述,甚至无宗教信仰人士也清楚人最终的空。
刻佛像的原因可能是买过一本《来楚生印谱》之后吧,不记得了。当时就模仿楚生那样刻,大约刻了十年,只是到了后来觉得总那样没劲了。
白马寺住了两年,二○○七、二○○八年。那是一段很自在充实的时光,四季分明,无人打扰。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两千年的历史了,到唐代一度成为政治的戏台,打打杀杀,一次一次的烧毁。文革时代又是一出一出的戏,当然,戏肯定没完……一次在离我住处几十米的地方,挖出了一具元代和尚完整的骨架,盘腿合掌着,莫名其妙感动死了。
……一次和方丈逛集市,买了一把斧子,方丈问干嘛用,我说刻印用的,方丈说那要小心手。
也正是在白马寺住那段时间,寺里出土古代的骷髅,这件事印象深刻。当时离我住的地方几十米的地方挖出来一些元代遗物,其中有盘腿合十的骷髅,和尚看了在一旁双手合十落泪,我也有莫名的感动。一起出土的还有石棺铭文,写着白马寺第多少任方丈某某,但在现存文献资料里始终没有查到这位方丈的任何信息,但这里面一定有上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我那时每天去斋堂吃饭还必经过这个地点。
有人认为我的作品有版画的倾向,我一直觉得篆刻实际钤印效果同样有版画的属性特质,尽管一个是关于文字类,一个关于绘画类,但不能否认两者的很多类似部分,比如刻制、线质、印制等。我看大量的版画作品都充满篆刻线的特殊意味,甚至篆刻里的“金石味”在版画里也有,印的肖形类更是一种小型版画,有的版画还就是用石板来刻制的,但有没有批评界批评版画的篆刻倾向,但篆刻界好像比较在乎这个,我实际上没有这个主观上的有意倾向。当然,最近创作的佛印我认为确实是版画了,只是利用了所有篆刻的工具,比如刀具、石头、印泥、宣纸等,说到底是利用了印的形式,更说明印和版画的微妙关系,但谁是谁、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可能是我认知有问题吧。
洛可可并非西方独享,印度、尼泊尔等地都有,包括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的宫廷、民间也曾风靡。当然,我个人也喜欢,但肯定不会在造像的时候总是表现出来,会腻。我在刻藏传佛像,在某些局部会用到繁复的洛可可样式,但这还是源自西藏,而是印度、尼泊尔的文化,但最终却成为一种藏传佛教的符号。
舞台剧场景效果,跟我很早注意到古代西藏的寺庙殿堂里是利用藻井上方的室外光线投射到最中央、最重要的大型佛菩萨身上,这时殿内周遭依然黑暗,唯独耀眼的光束投射到主佛身上,一下子让人有了那种对神明神秘感的莫名崇拜冲动。你去北京雍和宫的大殿看宗喀巴像就知道西藏寺院建筑的传统,而旁边的巨大彩色帷幕像极了一幕戏台视觉,恰巧符合我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即周遭戏剧性的荒诞感。
记忆模糊,最初如何刻起石头,有点想不起来了。刀法是慢慢琢磨出来的。后来因为每年在西藏腹地做古代美术田野考察,自然想着要把藏传佛教造像融入印中,开始没有头绪,毕竟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糅合到一起要解决其中相互妥协的问题。直到接触到元代佛经插画精湛的线绘,就挪用到了印中。再后来在一次考古现场,目睹墨拓明代玛尼石,豁然开朗,于是成了古法隔世受益者,生欢喜心。
佛教艺术叙述真是个庞大复杂的仪轨系统,我不能有丝毫怠慢的态度,我想,我还能敬畏地刻我的理解。
这是个荒诞的时代,无从选择的,我还是热爱这个时代,热爱曾经和正在经历的生活,热爱此时的阳光。穿梭古代和现代之间总能让人喜悦,观照所见,我在石头上自由想象和表达,所刻甚至常常给我新的提示,感谢所有机缘,对我来说,每一件作品都是完成自我救赎的表达过程,都是机缘的结果。
修行者平凡而神圣,一切生者的日常排污纳新,如呼吸一般,片刻不可或缺,悟道的神圣感和排污后的满足感,都俱足神奇,不分贵贱,是谁给了厕事的污秽感,谁能真正回避的了厕事,都是当下最直接的精神本质问题。
曾见老唐卡有本生故事图,绘有多个严肃的佛教场景,一个修者喇嘛在场厕事,没错,就是这么大大方方的画在唐卡里面。关于绘刻“方便”,争议瞬间引刃而解,寻常事罢了。问题的焦点转回到:为什么人们自觉回避这个日常、寻常的不能再寻常的厕事,不能容忍出现在神圣的佛教叙述中,带着反思,观者慢慢离去,艺术欣赏成为延伸的一种效果。

剔骨系列

剔骨系列


剔骨系列


古格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