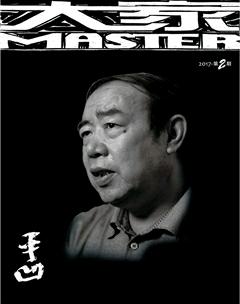小说的城堡
女孩的喉咙发不出她想象中的声音但她的脑中自有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女孩不需要夜以继日不断地吆喝“一件一百”“三件两百”。女孩纤细的手指在空中书画舞动,无形的字迹,无声的歌曲,女孩很小就知道如何使自己脱离这所在的世界。那时她还不是一个小说家,但已经显现出那姿态,女孩的脑中充满了故事,想象与虚构是她存活下来的方式。
二十二岁写下第一篇正式的小说,二十五岁出版第一本小说。二十年过去,我总是认为小说家不该对自己的小说谈论太多,至今我仍这样想。
经常,爷抽着烟斗,摊开满地的照相簿子一本一本说给她听。爷一定去过好多好多地方才能拍出那些厚厚的相片,婆婆会端來香热的牛奶,煨两个鸡蛋。爷说女孩身子弱要多补充营养,一口一口喂给女孩吃。爷教女孩读书,弹琴,带她认识院子里的花草树木,给女孩听音乐。
爷的烟斗里吞吐出烟雾,烟草香四下弥漫,女孩光着身子趴在地毯上画图,爷的手指在她身上写字,大狗在一旁打呼噜。那时候女孩已经开始写故事了,她用爷爷给的笔记本书画着心里无法对人叙述的。女孩读书,爷爷读女孩写的故事,想着如何像书架上摆放的那些大书本里记录的许多许多。有一天,女孩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写下那些故事的人,好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在那个真实里不存在的屋子,被一个传说中的怪人呵护着,女孩知道这里是她想要的真实。爷将世界隔绝在这屋子以外,女孩宁愿留在这与世隔绝的屋子。她自己的家庭就在不远处,但好像跟她没有关系。其实她应该回家做饭,然后照顾弟妹洗澡,如果是假日就该等着爸妈的车子一起去夜市。但她不想离开,假想着这时其实她可以从世界消失,没有她的存在家人依然继续存活。她想离那个残酷的现实远一点,想做一个真正的小孩。如她想象中的孩子应该享有的童年,或者像普通人那样简单快乐地生活。她害怕回到那始终嘈杂凌乱的闹市,没完没了的营生;害怕回到那已经没有妈妈的屋子,必须扮演母亲的角色照顾年幼的弟妹;害怕看见辛苦操劳的父母;害怕自己因为她所不理解的悲剧而逐渐阴暗扭曲的性格;害怕那无法停止的忙碌、嘈杂纷乱,每一件事都让她痛苦。
像被人拯救了一般,在爷爷的屋子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她暂时离开,那伤痛的真实离她非常遥远,
爷的声音听来非常温柔,无望而悲伤的时候,女孩经常悄悄溜到爷爷的屋子,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那消失的瞬间,无人知晓她的行踪,那是她向上天偷来的短暂时光。
最初,引发我想要写作的动力是想写出“我自己想看却没有看过的书”,对写小说的想象根生于年少时渴望从有限的生活里脱身的经验。那时的我还不懂得小说为何物,不知小说理论、技巧、美学观念,只是用文字写下幻想出的故事。我喜爱沉浸于想象的时刻,写作的时刻是“偷来的时光”,透过想象的微光看见未曾看见的事物,透过虚构让自己能够化身成不同的身份、到达其他想去的地方。那时的我透过写作体会了“故事的力量”。
2001年冬天,导演副导演摄影灯光等等工作人员与陈春天一行六人走进那个夜市,公共电视台有个节目要拍摄关于小说家陈春天一个二十几分钟的纪录片。前两天都在台中县龙井乡的望高寮附近一片宽阔的红土上拍摄,陈春天一身黑色皮衣皮裤戴着墨镜长发被狂风吹乱,铺设成圆形的轨道让摄影机绕着陈春天旋转,述说着多年写作经历。导演说镜头里整个场景看起来很美,大片红土上陈春天像一只黑色剪影随风旋转,一串一串吐出的话语似乎随时都要被风吹散,狂野的、放荡的、迷乱而不可捉摸。那是陈春天早期小说构筑出的世界,自从第一本书出版开始就是个极具争议的小说家。但陈春天从未写过关于自己成长的故事,还没。
拍完一身劲装的陈春天,隔天接着要去拍陈春天成长的环境,那个跟着父母到处摆地摊的小孩长大后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如此种种。其实陈春天心里知道,镜头无法捕捉那已经失去的时光,无论是开始还是经过,过程都无法再现更难以诠释。
陈春天知道她的父母企图在这些夜市朋友面前制造一个新的身份,一种新的过去,那作为跟日后陈春天透过写作以及作家这身份所努力创造的非常类似。取消过去,改写过去,掩埋过去,透过与对他们过去一无所知的新朋友眼中所看见的恩爱夫妻美满家庭,并且使自己相信这个。
不巧那时,那时正是陈春天记忆大反扑的时候,所有已经遗忘或刻意隐藏的不堪记忆逐渐逐渐地,一一浮现。于是她更害怕去看见爸妈所努力要营造的那个景象,因为她知道或许有一天,她就会是那个把真相说破的人。
陈春天看着画板上歪扭而笨拙的字迹想起弟弟原来至今仍无法分辨注音的四声,那时她清楚知道一个事实,自己无论用多少力气和时间与之搏斗都无法取消那些曾经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的童年时光。而或许她一本又一本写着完全跟自己的人生无关却让读者信以为真的奇情小说,那样的举动跟小时候自己话幻灯片说故事是一样的心情。创作一种新的生活与身份使原来的自己消失,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而事实摆在眼前,脱离那个说书人小说家的身份,此时陈春天正在处理一场攸关生死的大事。她的家人环绕身边,无论多么疏离尴尬也无法切断那血脉的关联。荒谬的是,就在这时候出版社正在排版印刷一本陈春天的小说,满满一本写的都是陈春天的童年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家族秘密。
陈春天这几天下来对附近环境也熟悉许多,每天都吃着地下楼美食街的食物。到康是美采买各种医疗用品,她也曾到美食街附设的诚品书店买过一本书,1月份的某家文学刊物刊登了陈春天那本小说其中一篇,而书下个星期就要出版了。感觉时空错置而自己被放错了空间,非但没有出书的喜悦反而感到惊惧。陈春天在写完那本小说后的某一天做了噩梦,梦里她正在老家看电视,一楼依然堆满了各种手表及生财器具。有许多人冲进他们家来抢搬那些手表,陈春天跟妹妹赶到楼下去阻止,却无论如何阻挡不了那一波又一波涌入的人潮,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啊!”精疲力竭的陈春天跟妹妹瘫坐在地板上。“还不都是因为你!”妹妹说。“为什么是我?”陈春天一脸茫然。“你自己看!”妹妹指着屋子外面的贯女老少。
那些人,好多好多都是陈春天认识的,导演、作家、評论者、读者、电视台记者,还有她的亲戚朋友,汹涌的人潮挤满了陈春天家外面小小的空地,大家都七嘴八舌在讨论着什么。原来,他们都在等着看陈春天家人出现,大家碎嘴地讨论着陈春天的家庭,她书中并没有提及的隐私全都被知道了。“别说了!”陈春天吼叫着。“还不是因为你!”妹妹说,“你那样写,我们都不要做人了。”
那个荒谬的梦境里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首先,陈春天绝对不会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既不会有电视台来访问她,其他作家同业也不会把她的一本小说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梦境里透露出的不安与焦虑却是不争的事实,确实正如自己所担心那样,写一本书,讲一个故事,这是小说家的专长。而被写进去的人却没有发言的权利,于是跑到梦境里来纠缠。多少年过去,那些纠结在心里的往事并非小说素材也不是非得对谁倾诉的,她只是没有办法不写出来。唯恐自己会在一次一次编辑重组的过程里离那些记忆更远,一切都更加扭曲变形。而她走过那些损坏之后却被自己的头脑给逼向疯狂。她必须在这过程里,如同掀开一层一层表皮,不是为了发掘真相而是为了安抚自己。
时光迢迢难以追捕,她得趁着自己发疯之前把一切说出来。
以上文字出自“陈春天”,就时间点来看,那似乎可以作为我写作前十年整个心境的总结。
许多评论者将我的《桥上的孩子》与《陈春天》这两本书描述为“自传性很强的小说”,甚至将内容一一与我个人的生活对照解读,也有记者直接问我“陈春天有百分之多少的陈雪”。我一直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不是我写作的重点。如今我在此引用书中的内容来描述自己的创作心境,此一行为似乎是不打自招。但小说不是自传,我写的也不是私小说,我感兴趣的也不是告白,我引用这些句子是因为小说最能表达一个作者曲折反复的想法。无论小说的内容是奠基于自己的经验还是想象虚构,正如福楼拜所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小说角色能够代替作者自况心境,不管身份性别年龄背景的差异,作者经常借由小说人物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我在此引用这些书中字句也是这个用意。
写作对我而言是漫漫的旅程,从二十岁开始写作时的懵懂,我几乎是在没有自觉的状态下写出第一篇小说。我只知道要写故事,却不知小说为何物。在写作《恶魔的女儿》那一年我逐渐理解自己想要追求的小说世界不再只是“说一个故事”,开始懂得技巧与形式如何影响小说的内涵,也是在那一年我确定总有一天要成为一个专业小说家,也愿意为此做好各种准备。
我写过女同志,写创伤与精神疾病,写夜市与菜市场里求生的人们,我写各种来去我生命里的人物与故事。无论是将写小说视作故事魔法的展现、美学的表达、身份的转换,记忆身世的拼凑重整,还是写的疗愈力量,每一本书都像一个个不同的房间,一个又一个虚拟的时空却建造出坚实的城堡。我透过写一本又一本书让自己更加了解小说之于我的意义,了解我要继续写下去会面对何种困难,我要如何继续锤炼自己。
若以我的作品为坐标来标示我自己,我更在乎的是,写完《陈春天》之后自己会走到哪里去。我知道我是个小说家,小说建造了我,而我建造了我的小说世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作品,作者不需对自己的观念多做说明解释,只有作品能够为我回答。
二十年来我已经书写过不同题材,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城市到乡村,在持续创作长篇的过程,除了不断开发新的题材,也尝试各种小说形式及语言的实验。《陈春天》之后的新书中,我将小说里的时间感透过叙事方式的改变来展现“浓缩的时间里绵长的过去”,希望透过更长的篇幅描绘几个不同年龄性别身份背景的人物其内在肌理。
李美云对赵云描述那个湖上的高脚屋与浮土田是如何的吸引了她,以她不曾在小说之外的地方使用的描述方式,“人们在那个湖泊上种植番茄,薄薄一层田土其实是某种奇异的藻类与泥土混杂而成。起初我并不理解为何可以在湖水之上种植东西,还用手探进湖水里去翻搅,突然间我发现那跟我的生命好相似,上下两面中间仅以某种单薄的东西连接,根浅枝短。其上是用树枝编连而成的大片支柱,只有一二十厘米高,一大片枝叶繁茂的番茄便这样哗啦啦四处繁衍起来。其下只是黑幽幽不见底的湖水,还有鱼穿游而过,而我的生命则是一间又一间漂浮的房间。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房子,不是家,也不是屋,而只是一个又一个从门口直接可以望进墙底的狭窄房间,床铺,书桌,吊灯与来去的人影”。说到这里她就止住了,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对他说话,说这些要做什么。
李美云最畏惧描述感受,她甚至无法用口说的语言描述她看过的一部电影或一本小说,更遑论谈及她所见到的人事物。她说话的方式总像是写在录像带或书本封底那些可笑的本事与简介,她不能说得更深,因为每个描述的细节都让她惊恐。
她害怕的就是那些细节。因为她整个生命都像是纸糊的,一戳即破。浮土田靠着空气与浊黑的湖水就可以结出甜美硕大的番茄,但她的生命可以结出什么呢?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的恋爱,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故事,在那些不断地填充与拔除的过程,除了移动时留下如蜗牛黏液般的印痕之外什么都没有。
写小说多年之后我深刻体会到,故事跟魔法会存留下来,记忆是故事的来源,而时间便是那魔法。以时间作为小说城堡里的梁柱与基石,不但切割了空间,也展开了纵深。生命经验通过想象,所见所闻所听所感无一不可成为材料。但小说家面对自己小说之时的态度无比严肃虔诚,我深深理解小说艺术不仅是发挥说故事的魔力,还是如同建造作者生命的大教堂。
像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加速,拉起机头,骤然飞起,像老旧的巴士载满乘客在灰尘满布的道路上歪扭地爬行最后冲撞道路边的消防栓,爆出大量的水柱。李美云的哭声逐渐变成一种奇怪的吟唱,然后慢慢停下了她的手,喉咙里还兀自发出声音,整个面庞都已溽湿。在她怀里的赵云突然动也不动地静止,那时她还以为自己已经把这个男人杀死了。
她低下头,有一点害怕。然后赵云睁开了眼睛,轻声地说:“没关系,都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一连串的淚水好像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陌生地从她自己的眼睛里渗出来止也止不住。她用力捶打着赵云的身体却像在求救,她那些号叫声或许是在呼喊着挣脱自己身上紧绷的束缚。答案不是只有一个,路径也不会只有一条。她不想变强了,她只想成为自己,或许软弱,会犯错,或许别人会来伤害她,或许她也会伤害了谁。但她想要真实地活着,会笑会哭,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去体会七情六欲,痛苦悲伤,她好累啊!那让自己钝化石化的过程她失去了好多东西,她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
这一路上遇见的人仿佛都来到这个清冷的房间,熟悉的陌生的美丽的丑恶的,男女老少,在那些叫卖声中飘移闪现。那些风景,尘土,金碧辉煌的庙宇,那湖上飞舞的海鸥,船桨划过水面划破的浪花,zu zu脸上的香木粉,win微笑时眼角眯出的鱼尾纹,吉米专注地看着电视练习日文,还有好多好多。李美云甚至想起了当时她被抛弃在洛杉矶那个小屋里,有一次她企图走出屋子到对面去跟那些高中生说话。她连hello都不敢说,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中间她经过了很多人,她确实爱过也被爱过,那些都是真的。
时间被冻结在那个简短的句子里,没关系都过去了,没关系,都过去了。这些那些,这个人那个人,伤害,爱情,麻木,痛苦,欢愉,那许多如刀割般的画面,火焰尖端般炙人的细节其实都跟赵云没有关系,都过去了。有很多很多回音在李美云耳朵里回荡,会过去的,他们看着彼此的脸许久许久。等到一切声音都静止,大片的静默来到,等待狂暴的激情或离别的伤感都消退,他们等待着,维持这样的姿势;等待着时间将一切都挪移到另一个时空里完整地保留下来,他们可以安全地度过这一夜,然后各自回到原有的生活里。
那时李美云知道,这次的旅行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十年,在《陈春天》之后,我写出了《附魔者》,是我第一本二十万字以上的长篇,也确立了长篇小说家的位置。这本小说时间横跨二十个年头,之后我生了病,有很长时间无法提笔写字,连用计算机打字都很辛苦。我用复健自己的方式,每日写五十字,慢慢进展到一百字,两百字,花了三年时间写下了《迷宫中的恋人》。《附魔者》写作是一趟穿越时空的旅行,而《迷宫中的恋人》则是找回时间的过程。
我希望在我自己的小说里“时间”不再仅是线性地流动,过往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是埋伏的按钮。一旦开启,即将扭转眼前所见的人事物,这些关系紧密的人物背后拉扯出一连串对自己与他人的“再诠释”,过去与现在、此时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自己与他人不断的相互对照与辩证。写作,开启不同的入口让书中人物以不同的口吻、形貌进入这个“小说中的房子”。小说中人物时而独处时而交错,时而自语时而与彼此交谈。
在我的世界里,那是一座会不断变形的城堡,那是一座无法附着于土地、总是不断迁移着自己的城堡。随着时间经过,它仍在寻找自己的形状。我想起我不断写着小说的那些时刻,那是透过正在成形的作品,又再次成功地重塑了自己。
我们都正在成形,且不断被自己摧毁,然后重建。无论打造什么样的城堡,都是把生命打碎,重新建造起,仅属于自己的居所。
到了2015年写作《摩天大楼》,我想就是我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消化吞吐,将自己自我规训成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所能写下的“属于小说家的小说”。而且它是那么象征性地,以一座参天大楼、天空之城的姿态存在。
我不知道我过往的小说里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但我清楚知道一点,我追求的永远是,下一本,尚未命名,正在成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