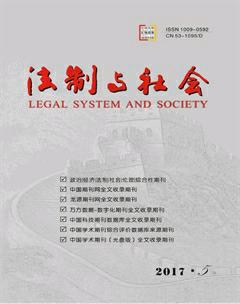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加重刑的质疑
林晓波 何程雯
摘 要 面对愈演愈烈的执行难现象,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增设了“情节特别严重”之法定加重刑,这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当前的司法现状下,加重刑的增设面临着缺乏可行性和效率性,以及与轻刑化趋势相悖的质疑。因此,本文认为不应该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增设加重刑,而应该寻求其他方法解决执行难题。
关键词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加重刑 执行难 轻刑化
作者简介:林晓波、何程雯,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405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得到广泛运用,但生效裁判如何有效执行是当前的难点。为了解决执行难,国家从刑法层面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并在其后不断对其进行了修改、完善。由此可见,立法者对拒执罪解决执行难题寄予了厚望。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的第三十九条增设了拒执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然而,结合司法现状,笔者认为,这一加重刑的设定,未能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并且面临着来自可行性、经济性以及轻刑化趋势的质疑。
一、拒执罪的立法变迁
通过对拒执罪立法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出拒执罪的创设和每次修改都是对司法实践的“执行难”现象的回应。
针对“文革”期间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发生的暴力抗拒现象,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得不到执行,司法权威受到严重损害,1979年《刑法典》创设了拒执罪,拒执罪与妨害公务罪合并规定在第一百五十七条之中,统摄于“以暴力、胁迫手段”,开始了以刑法犯罪打击拒不执行行为,为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提供了刑法的制度保障。随着经济发展,抗拒执行的手段愈发隐蔽,被执行人不再简单地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原有的刑法规定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打击拒不执行行为的需要,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难以有效执行再次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为了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在1997年《刑法典》中,拒执罪被单独规定在妨害司法罪一章中的第三百一十三条,删去了“以暴力、胁迫手段”,并增加了“情节严重”的构成条件。至此,无论是暴力、胁迫手段抗拒执行,还是采用隐蔽、躲藏手段拒不执行,只要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便触犯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虽然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纷纷出台了各自的法律解释,对“情节严重”进行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由于法律解释只能局限在原有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创设新的规定。针对不同的拒不执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千差万别,原有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法定刑并不能对社会危害性较重的行为进行有效地惩治”。 因此,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对该罪进行了修改,不仅增加了单位犯罪,还增设了一档较重法定刑,即“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拒执罪加重刑之质疑
反观拒执罪加重刑的立法目的:一方面,过于侧重对行为人的惩戒;另一方面,从预防犯罪层面,加重刑的增设并不能改变该罪预防效果差的现状。该罪预防犯罪目的难以达到,一方面是由于生效裁判执行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善使行为人有机可趁,另一方面由于拒执罪本身定罪难,导致行为人抱有强烈的侥幸心理。而两方面导致的预防效果差,并不是增设加重刑所能改变的。相反,笔者认为,加重刑的增设面临着来自可行性、效率性以及轻刑化趋势的质疑。
(一)加重刑缺乏可行性
刑法作为保障被害人权益的最后手段,不应被束之高阁。从前文所述的立法目的来看,加重刑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执行难问题,然而由于加重刑立法规定内涵不清晰,使得该加重刑的规定缺乏可行性,难以发挥效果。
法律条文由于篇幅的限制,要用精简的文字囊括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社会危害行为,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特征。但是,法律的设置又是为了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规制来达到社会的有序状态,这就需要条文与具体犯罪的准确对应。所以,往往在法律条文的自身特质与其目的之间,会出现法律适用不准确、适用具有随意性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法律解释加以“填补”。“司法解释针对法律适用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进行了说明,就拉近了法律条文与事实的距离,便于法官准确地适用法律裁判案件。” 法律解释对于使法律与具体犯罪行为精准对应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方面,基本刑的构成要件“情节严重”,便面临着法律解释的困境,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均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解释,但在面临错综复杂的案件情况仍难解决适用困境。在此情形下加重刑的出台,仍然需要面对法律解释难题。另一方面,即便在基本情节基础上以程度不同为判断标准,那么何谓“特别”?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对于“特别”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法律角度来看,我们只能比较客观的说,那是比“情节严重”社会危害程度更深,主观恶性更大的行为。那么问题又变成了何谓“更深”?何谓“更大”?它们是否有程度的标准?这样下去,只会不断地在法律解释中不断循环,并不能解决司法中发生的问题。在这种立法规定不清晰,法律解释不明确的情况下,法官便可能基于二审、再审改判的压力便不敢适用该档加重刑,从而被束之高阁。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从《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生效之日起至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1622篇关于该罪的裁判文书, 一审中适用“情节特别严重”这一加重刑的案件判决书仅有两份, 并且其中一份的判处该档刑罚的最低刑“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加重刑的适用少间接证明了该档法定刑必要性的存疑或者存在难以适用的情况。
此外,适用界限过于模糊,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也会加大法官寻租的可能性。该加重刑与基本刑“情节严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予以区分,法官得以在两档法定刑之間随意适用,在无形中过分扩大了法官裁量权,使法官的司法伦理和职业操守面临巨大的危险,容易造成法官寻租,加重刑难以发挥效果。
(二)加重刑缺乏效率性
刑罚的经济分析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将有限的刑罚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发挥最大的威慑效果。 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说的:“以最少最轻和最合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配置,确定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刑事诉讼和刑罚手段的成本要比生效裁判执行制度的成本高昂的多。因此,为解决生效裁判执行难题,首要的应该是完善生效裁判执行手段。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执行程序仍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1.刑罚资源的有限性。国家对刑罚资源的使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用于侦查、逮捕和审批;另一个方面是用于刑罚的执行。前者影响惩罚概率,后者影响刑罚严厉程度。在刑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者呈现出反比例关系,即要么“严而不厉”,要么“厉而不严”。同样,国家不可能将所有的刑罚资源都用于拒执罪,因此,拒执罪的刑罚资源也面临着“严而不厉”与“厉而不严”的选择。
根据考特·尤伦模型对拒执罪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应该侧重提高拒执罪的惩罚概率,而不是提高刑罚严厉程度。
假设对拒执罪的犯罪成本只考虑预期刑罚,那么当预期刑罚增加时,随着犯罪成本的增大,犯罪数量则会趋向减少,刑罚的威慑力越大。而预期刑罚是惩罚概率和刑罚严厉程度的乘积。在国家打击拒执罪投入的刑罚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可以得出图一:
图一:考特·尤伦的基本模型与拒执罪
通过将拒执罪放进考特·尤伦的基本模型,可以发现:在理论上,在投入拒执罪的刑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拒执罪发挥最大威慑力的情况,即支出线E与高威慑线D2相切的切点A,当将惩罚的概率控制为y1,惩罚的严厉性控制为x1时,达到了将现有的刑罚资源发挥最大效益的目的,此时威慑力最大,最具效率性。
上述模型虽然抽象,并且各项因素难以具体量化,但是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我们应该根据定罪率与惩罚严厉程度的相对成本配置刑罚资源。无论是将惩罚严厉性从x2降至x1,还是从x3提高至x1,都能趋近点A,但由于两者的相对成本不同,使得降低(或增加)相同幅度的刑罚严厉性带来的威慑力并非一致。因此,有必要在进行具体分析,选择最合理的趋向方式。
2.行为人的犯罪理性。不仅经济学存在“理性人”假设,刑法也存在着同样的假设。正是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刑法可以通过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进行调整行为。当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行为人便会实施犯罪。因此刑法只需要将犯罪成本提高,使其大于(或等于)犯罪收益时,便可以减少犯罪。
从犯罪理性角度分析,增设加重刑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成本-收益认识产生下列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在酝酿犯罪活动时,由于信息不完全对称,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刑罚成本难以进行准确评估。在存在多档法定刑并且适用界限不明确的情况下,行为人往往会作最坏的打算,行为人有更大的动机隐藏自己的犯罪行为,如加强反侦察和证据销毁,从而加大侦破难度。另一方面,对于拒执罪行为人,由于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再犯的可能性极低,无须适用自由刑(实刑)的方式剥夺犯罪能力。相反,适用较长期限的自由刑会加大行为人在刑满释放后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包括拒执罪)。
行为人极容易在监狱内发生“交叉感染”。人身危险性不仅没有减少,还很有可能增加。其次,监禁刑的执行使行为人长期脱离社会,刑满释放后出现再社会化困难,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加大,“累犯”正恰恰说明这一点。从犯罪理性的角度仍然能对其合理解释。首先,拒执罪行为人在刑满释放后,由于长期脱离社会以及前科报告制度,使其难以获得相对简单、体面的工作。这时,行为人对犯罪收益会产生估价过高的认识,并且犯罪时间成本和刑罚机会成本降低。其次,行为人对刑罚成本会评价减低,因为在监狱里“耳濡目染”了众多犯罪技术,反侦察能力上升,对自己被惩罚的概率取值降低。 因此,在行为人的主观判断中,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其便会理性地再次实施其他类型的犯罪。
可见,拒执罪加重刑不仅不利于现有刑罚资源最大效用的发挥,而且还会出现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收益的情况,导致行为人理性地选择犯罪。
三、总结
如上所述,拒执罪加重刑的设立并不能达到预期立法目的,并且在多个方面仍面临着质疑。在诸多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应该增设拒执罪的该档加重刑。而对于执行难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不妨从其他角度,如完善生效裁判执行措施等加以解决,而刑罚本身作为一种最严厉的手段,不应该成为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甚至不该成为主要手段。
注释:
赵秉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317.
刘峰.论司法解释的地位与作用.东方企业文化.2010(15).
检索时间范围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
案号分别为(2016)鲁1525刑初240号、(2016)冀0828刑初61号.
案号为(2016)鲁1525刑初240号.
卢建平.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1997(2).
高铭暄.刑法肄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25.
虽然刑法对累犯要求从重处罚,但是只要行为人认为存在逃脱的机会,其便会忽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胡志军.刑罚功能新解.濟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
[2]王利宾.刑罚的经济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