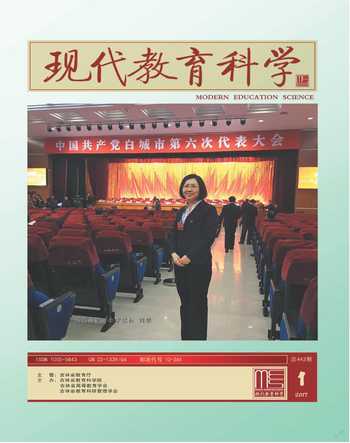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的情理困境及对策
[摘要]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过程中,既要处理好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提出的法律诉求,还要处理好情感抚慰、“讨要说法”、道义责任等情理诉求。相对法律诉求而言,情理诉求因贴近人们的心理需求而容易引起社会共鸣、博得舆论关注,从而导致事故处置复杂化。情理诉求处理得当则有助于促成矛盾纠纷的解决,处理不当则可能引发“次生伤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并善用情理要素的社会治理功能,在“法治”框架下充分运用柔性的“说情论理”艺术来消解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的情理诉求,不失为破解情理困境的上策。
[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情理困境;情理文化;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G4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7)01-0030-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01006
近年来,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不当的案例日趋增多,引发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事故处置中之所以会引发社会对高校的负面舆论,不仅仅是因为高校在法律问题上处理不当,还有高校在诸多情理問题上处理不妥的原因。一方面,高校因过于正视情理诉求而备受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牵制。例如,为维护校园稳定一味迎合受害学生的赔偿诉求,超越法律底线花“天价”买平安,将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混同处理;为消解受害者家属的泄愤情绪,任由家属在校园里做出各种出格行为,对“校闹”的胡作非为无所适从,以致严重干扰了教学秩序;为防范类似伤害事故的发生,学校不惜违背教育规律而采取一些“因噎废食”的做法,等等。另一方面,高校有时也因无视情理诉求而引发与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激烈冲突。例如,有的高校在事故处置中隐瞒实情,从而招来社会的质疑、诘责甚至是谩骂;有的高校对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情绪发泄行为不能冷静处理,希图借助公安部门采取高压手段进行压制,从而引发更加激烈的对抗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导致“次生伤害”;有的高校在对外发布学生伤害事故信息时不顾及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感受,措辞生硬冷漠或企图混淆视听,让社会感觉高校有规避责任之嫌疑,从而引发社会舆论的指责或批判,等等。相对法律问题而言,情理问题因容易博得社会舆论的关注,从而导致伤害事故处置的复杂化。因此,研究情理诉求的表达方式、情理要素的作用机制、情理问题的疏导方法、情理文化的治理功能以及情理诉求与法律诉求的互动影响机制,对处理好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大有裨益。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情理元素及现实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1]。“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中国传统情理文化要素是中华法系立法的价值取向。
(一)情理文化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一般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横以情、理、法为说 [2]。这说明“情理入法”早已形成了立法惯例,情理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情理文化的发展从丰富的成语寓意中可窥见一斑,描述情理关系以及情理的社会治理功能的成语不胜枚举,如通情达理、于情于理、寓情于理、由情入理、情理难容等成语讲的则是情和理密不可分;人之常情、以情感人、情有可原、理所当然、以理服人、以理释法、理法并用等成语讲的则是情和理的社会治理功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称之为中华法系文化。中华法系是世界上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它以儒家思想为灵魂,以儒家法律文化为根基,标志性的法律文本是《唐律疏议》。自法律儒家化以来,我国古代便设计出了“天理—国法—民情”三者相辅相成的国家治理模式,通过“礼法”来规制政治统治、社会秩序和各阶层的行为。
礼法,顾名思义就是以礼制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古代礼制已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包含家庭伦理、宗法伦理、主政伦理、行为伦理等。礼法的制定通常以特定时期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为标尺,确立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实为“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数千年来,“礼法之治”在世人心中产生了顺天应人、为政以德、得乎丘民的政治合法性,彰显了礼仪之邦的治国风范。在礼治社会化之后,“为国以礼”“非礼入法”“出礼入刑”等礼治秩序逐渐得到稳固,直到新中国逐渐走向法治社会之后,这种礼治秩序才逐渐被弱化 [3]。由此可见,礼制和礼法之所以在古代能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礼”所规范的秩序都是应天理、顺民情的,是已形成社会共识的情理得到社会普遍尊崇的结果。因此,情和理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以现代法治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是立法要立善法,而立善法就要融入情、理之价值,无视情、理要素而制定的法律会被称之为“恶法”。
现代社会所主张的“道德入律”和古代的“情理入法”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情、理依然是道德的评判标尺,且“道德入律”也是中国现代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中国现代法治文化的发展是开放包容的,不再一味强调传统礼制的合法性而忽视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不仅仅照搬西方的法治文化,而是采取“折中融西”的方式。坚持两条腿走路,即回采法的历史,发掘传统中华法系的智慧,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严格来讲,情理文化只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等同或替代法律文化本身。相应的,现代社会中的亲情、伦理、事理等情理元素也只能归类为“泛道德”的规范,这种规范主要依靠人的内心来约束,而非依靠国家强制。只有当这种“泛道德”的规范在社会变迁中顺应了社会的强烈需求并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应得到普遍遵守的共识时,才可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习近平同志曾强调“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的提升” [4],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情理文化具备社会治理功能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经验来看,情理要素在矛盾纠纷解决中具有两面性,既可能成为加深矛盾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化解矛盾的柔化剂。一方面可能因为对情理诉求的非正常表达,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畴而成为干扰依法处置的障碍;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对情理诉求的合理疏导,切中了利害关系人的心理需求而取得缓和、化解矛盾的效果,即发挥了社会治理功能。情理元素之所以能在传统社会中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是因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情理元素被统治者写入了礼法、礼制或律例,并赋予了社会治理规范的法定功能,由此形成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情理文化观念。
在崇尚法治的现代社会中,情理元素依然能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以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为例: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法制尚不健全,教育法治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宗法伦理和道德伦理的影响,社会公众在看待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的态度上还存在着观念上的认识误区。以亲情、伦理为基础的道德义务常被人为法律化,使法律观念有时候受制于道德观念。在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以情感受到伤害为由要求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判别是非过错。相比较而言,道德准则却更易被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在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情形下,人们更容易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已经受到道德原则影响的法律关系,而置法律本身的要求于不顾 [5]。事实上,情、理、法冲突已成为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到底是情理让位于法,还是法迁就于情理,拟或是相互妥协?在现代法治理论上虽不存在悖论,但在实践中却很难拿捏,处理不好就会使利益各方的矛盾扩大化,导致既伤情,又损法。因此,一旦陷入情理困境,处置者要回到情理文化视野下充分利用情理元素的社会治理功能,以“论情说理”艺术来化解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提出的情理诉求。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事故的处置都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的。无论是和解还是调解,个案中情理因素的把握都是相当重要的。处理不好情理问题,高校可能会备受社会诟病;处理好了情理问题,高校可能在事故处置中赢得社会赞誉。这充分体现了情理元素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的社会治理功能。
二、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的情理问题表征
(一)无法自控的情绪宣泄
部分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生家属因情感上接受不了现实而难免会“闹情绪”。面对学生家属的情绪失控,高校应该视之为“人之常情”而包容相待,还是视之为“无理取闹”而断然拒绝?在“情”与“理”之间,在“同理心”与“自己立场”之间,高校需要特别谨慎地把握,做好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情绪管理工作。在情绪管理上稍有不慎,受害学生及其家属就可能与高校剑拔弩张、走向对立,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情绪管理既包括对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情绪引导,也包括高校管理者自身的情绪调节,目的是在事故处置中促成当事人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以推动伤害事故的妥善处置 [6]。
(二)向高校和政府讨要说法
讨要说法,在乡土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影视剧《秋菊打官司》深刻地描述了在中国农村自古以来人们都奉行的“讨要说法”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揭示民间矛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在于当事人各方是否“討到了说法”和“出了口恶气”的本质。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也正处于法治观念的转型时期,守法自觉、司法公正、执法严格、立法科学的法治梦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因此“讨要说法”的社会观念依然盛行。乡土中国的传统差序格局与法治中国的现代法治理念虽然正在走向融合,但要走的路还很远。
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过程中,受害学生及其家属出于本能想到的是要和学校“论个理”,即向学校“讨要说法”,要求学校对伤害事故的发生原因做出合理解释,并据此断定学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在“讨要说法”时,受害学生及其家属通常都是带着悲愤情绪和索赔意图的,因此在“论理”的过程中极易陷入“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困境。例如,因独生子女在校被同学毒杀,家属执意要求相关部门以“杀人偿命”的逻辑严惩凶手。有时候“论理”也极易陷入“论死理”的境地,如在校学生因自身体质原因在体育活动中猝死后,家属不分青红皂白地煽动众亲属以及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校闹”,给学校施加压力,要求学校对意外伤害事故负责。
(三)寻求同情弱者的从众效应
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的博弈过程中,谁是弱者?置诸公众面前的伤害事故,如何形成同情弱者的“从众效应”?这也是由情理诉求主导的干扰因素。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总会被视为弱视群体,当他们与“强大”的高校博弈时,就意味着不平等。因此,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时常会利用大众同情弱者的心理,借助媒介炒作,以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而媒介正好会抓住这样一个热点标签,为吸引公众眼球,赢得曝光率和知名度,一味地迎合受害者和不明真相的大众,使“真相”在炒作中遮蔽于杂乱无章的舆情信息之中。当同情弱者的社会舆论掩盖了事实真相,高校则需要在承受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把握好分寸,力求突破同情弱者的从众效应,以还原事实和消除社会的不满情绪。
(四)要求高校承担道义责任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社会普遍认为高校应给予成长过程中的大学生以充分的人文关怀。换言之,高校对大学生既负有法律上的教育管理责任,也负有道义上的呵护成长责任。在诸多校园大学生意外伤害事件中,高校虽根据法律规定可免于承担法律责任,但却免除不了道义责任,否则事件一般不会轻易平息。另外,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引发的矛盾有时候是相当复杂的,它参杂了生活、情感、事理、习俗、舆论、利益等多种因素,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转化的矛盾发酵体,高校在处置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触发矛盾的并发症。此时,依法处置即便能解决利益上的纠纷,也无法抚平家属的情绪、平息社会舆论的非议、填补受害者的心灵创伤,故而需要从情理的角度再做一些辅助性补救,于是就产生了“道义责任”。
三、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的情理问题应对
有人说,大学生是成年人,一旦发生伤害事故,只需要按照侵权责任法进行处理即可,不值得去深究其特殊性。若是一味强调主体的特殊性,就自然会在处置中无视甚至是破坏法律规则。此观点不无道理。然而,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是,若仅仅机械地按照法律条文处置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总会有利益相关方不与其配合,结果往往是一厢情愿。因此,在处置实践中,事故处置者既要坚守法律底线,还要通情理。
不同类型的学生伤害事故所涉情理因素的干扰是不同的,但总体看来,情理因素最终都会成为受害学生及其家属与校方进行利益博弈的筹码。在事故处置中,受害学生及其家属常常利用情理诉求借题发挥、制造压力,或指责高校的管理体制,或指责高校缺少人文关怀,或指责高校缺乏担当,或指责高校不积极作为,甚至是将矛头指向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因此,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必须剥离情理诉求中的情理干扰因素,充分利用情理元素本身的社会治理功能,找到情理诉求的疏导方法。
(一)做好情感抚慰工作,排除情绪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少数干部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其实,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或是目中无人,对群众缺乏感情;或是身无才干,做工作缺乏底蕴;或是手脚不净、形象不好,在人前缺乏正气。” [7] 情感抚慰是群众工作中常用的方法。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情感抚慰实际上是要求事故处置者在沟通对话中运用语言、情感、态度、情怀等要素打动受害学生及其家属,赢得信任和支持。
1要有接受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情绪宣泄的“同理心”。在部分致命的学生伤害事故中,受害者家长的“子嗣后继”“望子成龙”“支撑门庭”等希望瞬间破灭,因一时难以弥补情感上的裂痕而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于是通过在校园里摆放花圈、布设灵堂、烧香祭拜等方式寄托哀思。面对这些举动,学校应该带着“同理心”做好情感抚慰工作,认同“从俗即是从心” [8]的道理,引导家属适度宣泄情感。同时,还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引导受害学生家属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哀思,比如主动组织学生召开追思会、请心理专家为受害学生家属提供心理危机干预等,以抚慰受害学生家属受伤的心灵。而表达“同理心”主要依靠语言艺术,要用老百姓的生活语言来对话,以形成语言上的共鸣。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校方事故处理责任人和受害学生及其家属在沟通对话中切忌用冠冕堂皇、生硬晦涩的法律语言,而要用平实的话语来诠释法律规则和精神,引导利益相关者理性回归到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处理。
2要排除情绪干扰“讲清理”。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实践中,情理因素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论情和说理密不可分。古语云,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高校管理者在与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对话中,要善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寓情于理;要善用情绪管理方法,排除情绪干扰,对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提出的非法诉求和不合理诉求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高校在安抚好家属的过激情绪后,还需进一步耐心细致地做好如下“说理”工作:一要找准家属提出不当诉求的根源。有些不当诉求源于传统观念上的认识误区,比如认为高校是公家的单位,办学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故有完全赔偿能力,也理應“花钱消灾”,主动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有些则源于对法律认识的错误,比如认为高校是“无限责任法人”,即认为将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则负有全方位的教育管理责任,一旦发生伤害事故,可追求学校教育管理上的不作为责任。有些则源于社会舆论的误导。舆论总是倾向于同情弱者,因此难免会做出有失公允的导向,以致误导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提出非理性诉求。二要能引导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控制过激情绪,理性回归到现行的法治框架下解决纠纷。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纠纷的最终解决必须遵循章法,不能因人而异和因“闹”而异,高校也不能以“玩太极”的心理战术来压制受害者的正当诉求,只有依程序、依政策、依情理综合考量案情,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令人信服。三是事故处置者要克制自身的情绪。面对家属的哭闹、指责、谩骂、围攻,校方事故处置者难免也会产生焦虑、愤怒、恐惧、无奈的情绪,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做好自身情绪的调节和管控,保持积极主动、乐观冷静的心态 [9]。
(二)及时给予合理说法,力求公正评理
面对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讨要说法”,高校要第一时间查清事故原因,及时给个“说法”,真实地陈述事实,客观解释原因,而不能主观臆断、避重就轻、含糊其辞。不论家属以何种方式“讨要说法”和宣泄情绪,高校都应该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根据查实的真相及时给予答复。另外,受制于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观念,人们习惯认为,不论发生何种伤害事故,高校都是第一责任人,且高校是有赔偿能力的责任人,因此家属惯用“讨要说法”的方式来主张不合理的诉求。在此情形下,高校也需耐心地解释为何不能满足超出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的诉求,做到公正“评理”。同时,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高校也要合理地予以回应,务必做到开门纳谏、直面矛盾,而不应置之不理。
(三)主动应对舆论监督,避免二次伤害
舆情引发后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引导,则会爆发舆情危机。而当舆情失控转化为危机时,通常不会就事论事,更多情形下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极易对利益相关方造成“二次伤害”。因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引发的舆情,实际上是利害关系人利益诉求的表达、社会公众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的反馈、意见领袖和网民在争议问题上的思想交锋、官方与民间在处置过程中的意见交换等各方面意见的集中反映。一旦伤害事故处置引发了舆情危机,高校要精准研判事故发展态势、适时公开事实真相、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友好主动的姿态和舆情展开互动,通过真诚对话树立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社会形象,而不能以回避、抵抗的方式企图通过对舆情源头的遏制和围堵来强硬应对。在对话内容设计上,高校应侧重从情、理、法、义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帮之以需。
(四)积极承担道义责任,充分给予人文关怀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这确定了高校在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下,可以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也就是人道主义的帮助责任。它本质上属于道德责任,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责任。道义责任不同于法律规定的公平责任。以经济补偿为原则的公平责任是法定责任,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而以经济帮助为原则的道义责任则是道德责任,是当事人基于道德和情感而自愿负担的。两者在性质和适用条件上完全不同。高校对受害学生进行经济补助,是以具备经济能力为前提的,同时还要结合直接责任人的赔偿能力和受害学生的家庭状况等实际情况而定,不能强制履行 [10]。
在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置中,受害学生及其家属非常在意高校是否积极承担道义责任。因为承担道义责任是高校给予受害者人文关怀的体现。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涉及大学生伤害的事故都是“大事”,社会一般会给予高度关注,因此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置中更需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树立负责任的道德形象。具体而言,就是要及时主动给受害学生及其家属送上一份“抚慰”,体现出同情和帮助弱者的道义,让家属充分感受到高校在行动上“近人情”,这样才能快速消解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不满情绪,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假若高校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受害学生及家庭不施以适当的援助,不仅不利于消解受害学生及其家属的激愤情绪,也很难平息社会舆论的抨击。因此,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中承担道义责任,既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需求,又符合当今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有效化解矛盾的方式。
(五)处理情理问题时需把握好“度”
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实践中,高校事故处理责任人无法回避情理诉求中的情理问题。但受害学生及其家属提出的情理问题合理与否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高校做好甄别工作。事故处理责任人若能酌情考量情理诉求的合理成分,则可以促成利害关系人在事故处置中较快达成合意,同时还可以消除对“法律无情、司法冷漠”的误解。当然,也要谨防不合理的情理诉求对依法处置的干扰,例如在事故处置中家属以无法用金钱弥补情感伤害为由而要求侵害人“以命抵命”,家属为索要“天价赔偿”以无节制地情绪宣泄来给校方施加压力、制造麻烦,因宿舍矛盾引发的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置中受害学生及其家属要求学校强制调换宿舍或班级,等等。换言之,事故处理责任人在情理诉求的疏导中要把握好“度”,既要运用好情理元素消解矛盾纠纷的社会治理功能,又要走出“人情大于国法”“以言代法”“徇情枉法”等认识、操作误区。同时,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置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受害者的现实需求,又要兼顾学校的经济负担,同时还要理顺学校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之间的责任分担关系。理想的模式是通过购买意外险或校方责任险来构建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在保险受益范畴内通过保险理赔代行道义补偿。
参考文献: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20,210
[2] 陈顾远中华文化与中华法系[M].台北:三民书局,1969:275
[3] 俞荣根,梁国典应天理 顺人情——儒家法文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3
[5] 朱勇,成亚平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J].中国社会科学,1996(1)
[6] 王沛,陈少平浅析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情绪管理[J].思想理论教育,2012(12)
[7]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6
[8] 費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9] 王磊,李进付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引发的舆情危机研判及疏导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6(5)
[10] 文铭,张欢试论大学生伤害事故中高校责任的归责原则[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