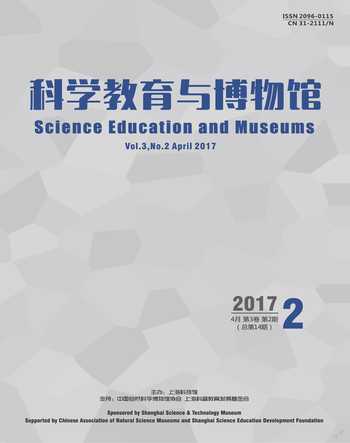博物馆学习对学校课程教育的影响及改善策略
陈曦 傅翼
摘 要 通过讨论博物馆学习的特点,分析博物馆学习对学校课程教育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方法。实物收藏和陈列展览使得博物馆学习具有实物性、直观性、系统性以及自由选择的特点。因此,博物馆可以从原真的学习体验、联系先前知识挖掘学生的兴趣、社会化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对强调抽象性、同质化、个体化的学校教育产生影响。研究强调博物馆学习和学校课程紧密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三种可以改善学校课程学习效果的方式,即衔接课程内容与博物馆展示内容,做好参观前的准备以及跟踪利用参观后的长期影响。研究还指出学校教师和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对学生学习起着重要作用,加强二者的联系对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意义深远。
关键词 非正式学习 正式学习 博物馆学习 课程教育
0 引言
非正式学习是人们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式学习通常指发生在学校课堂上的学习,而非正式学习则是发生在课堂之外的学习。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共同组成了人的整个学习生涯,相互影响彼此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二战之后博物馆被普遍认为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途径,但实际上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现代博物馆的由来一样古老。[1]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明确将教育列为博物馆三大功能之首,自此博物馆教育和学习愈加受到教育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们的重视。
学生是博物馆最重要的教育对象或学习者之一。不少研究发现,学生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学习、巩固知识,产生长期的记憶,激发对某一主题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而且博物馆里的活动可以满足他们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的需要。[2-3]博物馆学习往往被认为可以修正学校学习的诸多弊端,包括枯燥乏味的教育形式、刻板机械的教育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校科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极少数的科学家而不是拥有科学常识的普通人。[4]
但是,文献很少系统地分析为什么博物馆学习能够弥补学校正式教育的不足,以及博物馆学习应该如何与学校教育合作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将通过讨论博物馆学习的特点,分析博物馆学习对学校课程教育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方法,从而为学生的博物馆非正式学习以及学校正式学习提供实践和学术的参考。
1 博物馆学习的特征
博物馆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狭义的博物馆,即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的场所。[5]广义的博物馆,包括所有的校外学习环境,涵盖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中心、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等,即所有可以作为非正式学习环境的场馆。国内有人将博物馆学习称为场馆学习,[3]强调了博物馆非正式学习环境的情境性,同时为不理解博物馆广义概念的读者消除了认识歧义。因此,根据当前对博物馆学习的研究,“博物馆”已不只是传统认识中狭义的博物馆,而是包括大量非正式学习的环境和场馆。
博物馆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博物馆学习具备与学校课程学习迥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学生在博物馆里主要通过观察、感受实物进行学习,这有别于通过书本和图片进行学习。严建强将实物界定义为“真实、实在,并具有一定体量性和三维性的物”。[6]博物馆的实物首先是原始和本真的,它们体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的物质性,不是虚构的或抽象的。博物馆里的实物既保存了信息的真实(实物所体现的信息),又保存了信息载体(实物本身)的真实,其比文字资料或图像资料更容易使学习者得到生动、具体、深刻的印象。这是通过其他传播途径进行教育所不具备的特点。例如,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昆虫知识,课本中的图片是平面的;但在自然博物馆中,学生可以直接通过观察昆虫标本获取最真实的、最原始的信息。
其次,博物馆的实物和展览能激发学生的感官感受,所以直观性也是博物馆学习与学校课程学习的差异性所在。前文提到的静态三维实物比起文字和图像能给学习者带来更深刻的直观感受。除此之外,博物馆运用现代化展览技术手段为学习者创造了具有原真体验的学习环境。[7]感官的刺激也被证实能帮助学习者更容易地理解信息、改善学习效果。例如,美国斯图尔草原先锋博物馆(Stuhr Museums of Prairie Pioneer)通过动态的历史重现手段,让学习者模拟先辈的吃穿住行。[8]而中国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运用模拟场景、立体模型、多媒体技术重塑过去,再现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并鼓励学生参与现场操作。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学习者的听觉、视觉、嗅觉以及触觉都得到激发,这无疑更有助于其学习有关工艺技术的发展历史。
第三,博物馆“广博性”的特征决定了博物馆学习具有系统性。博物馆门类众多,藏品种类也纷繁多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地解释同一项学习内容的诸多问题。比如,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生物地质学、昆虫学、植物学等等的证据共同解释自然历史的变迁,学生可以通过化石研究岩石的“年纪”、确认昆虫的演变、有毒植物的变化等等。因此,博物馆里丰富的、跨学科的实物证据使学习者得到的信息突破了学校依据学科划分确定的边界,更加系统、全面。
最后,博物馆学习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非正式学习,具有“自由选择学习”的特点。在博物馆内,展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组织排列,但是其为学习者提供了非结构化的学习方式。[9]这种学习方式往往是自发的、开放式的、学生主导的、非评估性的、不要求知识结果的连贯、好奇心驱使程度高、社会性更高的,这明显不同于学校学习具有的正式学习的特征,即学校学习更受教师控制,结构严密,有预期和可测量的成果。[10]尽管部分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学校教育局限在“正式学习”的框架里,因为在相对正式的学校学习的环境里,也存在着“非正式学习”或者“自由选择学习”。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博物馆里进行的学习方式多数情况下更接近后者而非前者,其强调学习应该是由下而上、个体驱动的,而不是由上而下、机构驱动的。
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学生参观博物馆体现的学习自主性和自由选择的权力,也有其隐患——这一点往往被众多强调博物馆教育效果的文献所忽视。博物馆拥有大量的展品和展示装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博物馆对多数学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学生在参观时可能会接收到来自展品、场景以及周围环境所传递的各式各样、内容丰富的信息。如果他们趋于好奇心大量地接收各种信息,其中展品所传递的知识很可能只占一小部分,那么他在博物馆会获得较差的学习经历。研究发现学生感知新奇的水平将影响其好奇行为,最终影响非正式环境下的认知学习成果。[11]类似地,美国教育学家约翰·福尔克(John H. Falk)认为,最佳水平的学习发生需要适当水平的感知新奇。低水平的感知新奇带来低水平的好奇行为,其结果很可能是低水平的学习;过高水平的感知新奇带来高水平的探索和信息集中,但这会优先于有任务、有目的的学习,从而导致低水平的学习。[12]在博物馆空间内,由于学生自由选择学习的特点,如果完全缺乏教师的引导,以及参观前的准备,即学生完全凭借自己的好奇心参观展览,既可能因其他干扰事件而分心,也可能错过提供学习知识的展品,最后并没有从博物馆参观学习中获得丰富的收益。因此,博物馆自由选择的学习特点应该要发扬其优势,同时减少其“过于自由、没有重点”的缺点。不过,这一缺点可以通过加强与学校里由教师引导的课堂教学的紧密联系得以修正以及改善。
2 博物馆学习对学校课程学习的影响
学校和教师之所以愿意花精力和时间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博物馆学习可以补充学生的专业知识,丰富课余活动,还因为学生在博物馆学习对其学校课程学习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起到辅助学校课程的作用,[13]从而达到改善学习效果的目的。
2.1 原真的学习体验有助于深化、巩固抽象教育的成果
博物馆学习之实物性和直观性的特点,使其能提供一种原真的学习体验。学生平时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大多数来源于课本上的文字和图片,辅以幻灯片和影像资料等,多数课程均以教师讲课教授的形式进行学习,学习的知识往往是抽象的。学生在博物馆里的学习,主要依赖博物馆内真实、实在的物(例如各种化石、标本)、高科技手段创造的仿真环境(例如历史情景再现)、互动装置、科学(模拟)试验以及专家的现场展示等等。学生在书本上读到的内容可以在博物馆内找到具体的存在,从而帮助他们将抽象的知识转换为更为直观的声像保存在记忆里,从而更好地理解课堂所学的知识。由于目前多数中小学的校内实验室难以具备进行原真实践活动的条件(比如与科学家在真实环境里的科学活动一致的实验),对此科技博物馆能为之做出非常有效的补充和帮助。[14]其实在历史教育、艺术教育等等方面,博物馆能起到的辅助作用也類似。
2.2 加强与先前知识的联系,提高学习兴趣,刺激将来的学习
学生“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15],这对于学校教育和博物馆学习都适用。但是由于学校教育多数情况下运用高度结构化的学习方式——统一的教材、同样的教学方法、“教师-学生”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严格的评估手段、周密的时空设置,学生差异性的先前知识和经历很难在这样同质的环境里产生不一样的影响。而在非正式的、自由选择的学习环境中,学生会把博物馆看成是一个快乐的参观场所,他们会更加轻松自由地将先前(包括在学校里得到)的知识及经历与参观内容建立联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选择,[13]从而激发更大的学习热情,并进行深入的学习。博物馆学习能积极地改变学生对待知识的态度,包括激发他们发自内心的学习兴趣,这会对学校的课堂学习产生长期的影响。[16]而这要比增加某一个知识点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同时,参观博物馆是学生自主应用课堂所学知识于实际情况的机会,他们的先前知识能帮助其吸收博物馆里获取的新信息。
因此,部分学者建议,如果能将学校里的结构化教育和博物馆的非结构化学习进行有效连接,将学校教育传授的先前知识在博物馆学习空间里发挥作用,将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用。[15]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其学习兴趣,从而在学习效果上产生积极影响。
2.3 社会化的博物馆学习是个体化的学校课程教育的补充
尽管多数学校都在课程中设置了一些强调团队合作的学习形式,比如集体讨论、小组实验等,但是强调教师传授、学生学习依然是学校教育最重要的特色。与之相反,博物馆最主要的参观形式是多人参观,包括学校参观、家庭参观、与朋友参观等等。比如,根据2015年浙江省科技馆的调查,多人参观占总参观人数的81.6%。因此,博物馆学习是一个强调社会性的学习过程。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发生在与他人谈话中以及特定情境中的过程,[17]学习者在个人和社会活动中需要积极地选取和不断积累他们的知识以获得意义。认知科学家把学习看作是在个人先前知识和经验的范围内,对所要处理的新信息进行解释过程,为了使学生建构自己的理解,必须要提供他们机会去表达想法,通过对话检验这些想法,并与相关的个人经验建立联系。[2]
前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斯基(Lev Vygotsky)为了强调社会交流在儿童思维开发中的重要性,设想儿童学习发生在最近发展区,这个区是在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和受到大人或更有能力的同龄人的指导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从前者到后者的过程叫做社会调解。两个个体看上去对同一个话题有相同的想法,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并不一定一样,当他们同更有学识的大人或同龄人交流时就能体现出来。[18]最近发展区的大小与学习效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交流和互动的文化情境里进行学习是博物馆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17]在博物馆里,学习者若想要了解未知的知识,可以与他人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自己的最近发展区。这种社会性的学习形式有助于学习社群中的成员更好地建构自己的理解,并有利于课堂交流活动的开展,从而最终改善学习效果。
3 通过博物馆学习改善学校课程学习的策略
博物馆学习和学校课程学习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扮演不一样的角色,两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当前现状来说,学校学习依然占据主导位置。但是,博物馆学习能对学校课程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可以借助学生在博物馆的学习经历来改善学校课程学习的效果。笔者就此提出以下三种促进博物馆学习和学校课程学习紧密合作的策略。需要强调的是,教师以及博物馆教育工作者都在这三种策略中起着重要作用——完全不受引导的学生学习(尤其是青少年的学习)往往学不到任何知识。[19]
3.1 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充分结合学校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博物馆的参观内容
如前文所述,博物馆学习和学校课程教育各有千秋:前者重视实物,后者关注抽象意义;前者重视直观体验,后者关注概念传授;前者重视全面系统,后者关注学科分野;前者重视共同建构,后者关注个体学习。充分结合两者可以帮助学生在博物馆的情境下,将课本知识与展览活动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联系,从而帮助其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因此,学校和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校课程教育和博物馆学习的特点,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充分建立互相衔接的关系,让学生的先前知识和经历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大程度地挖掘学生的个体兴趣,提高其学习热情、改善其学习态度,从而进一步刺激学校的课程学习。如果学校和教师无力良好地衔接课程内容和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博物馆参观往往会沦为形式,学生的学习效果很难得到改善。而且,学习内容上的这种调整,需要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作相应的变化——课堂教学的方法如生搬硬套到博物馆学习中,对学生学习也没有积极影响。因此,学校教师有必要加强与博物馆教育专家的合作,运用更适合博物馆学习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19]
3.2 从博物馆里的学习到博物馆外的学习,做好参观博物馆前的准备
虽然博物馆的参观学习是一个短时间的学习过程,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博物馆学习研究应该从更长的时间线上对参观者的学习进行调查。因为看似简单的博物馆经历会产生长期的记忆,在之后遇到相似的情境时会联想起曾经的博物馆经历,换言之,博物馆学习将给学生漫长的学习生涯带来影响。因此,研究参观者的博物馆学习不能仅仅局限在博物馆的时空范围之内,而要将博物馆外也纳入到研究范围,为此约翰·福尔克将学生的博物馆参观学习划为三个阶段:前博物馆阶段、博物馆内的经历以及后博物馆阶段。[20]所谓博物馆学习的意思并不是“在博物馆里学习”,还是“从博物馆学到”。[2]
最能影响学生博物馆学习的前期准备有三类:学生的先前知识、为在博物馆认知学习所做的具体课堂准备、关于参观环境的方位准备。[19]这其中,前两类准备已在前一部分有关加强学校课程内容和博物馆参观内容的联系中涉及。“预定向项目”的策略能为关于参观环境的方位提供准备,即根据最佳水平的学习发生需要适当水平的感知新奇,令学生在参观博物馆之前预先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向学生介绍所要参观博物馆的整体概况、场地设施、行程安排等,降低学生对博物馆环境的好奇心,并且提前得知重点展品的方位情况。[11]参加预定向项目的学生虽然降低了好奇心却提高了学习效果,这是因为学生的感知新奇降低到了一个合适的水平,同时由于提前被告知与学习内容有关的展品方位,因而不会在眼花缭乱的展厅里因为展品的摆放位置或是本身尺寸而错过。
任务单也能够更好地将博物馆学习与学校课程学习联系起来。有组织结构的学校集体自由选择探索既能满足教师联系学校课程的期望,又能保留博物馆自由选择学习的特征,而使用任务单可以使博物馆参观结构化,帮助学生学习课程相关内容。[13]任务单可能会使学生陷入课堂学习般的约束,但也可能提高学生参观学习的质量,关键在于任务单的设计。曾有研究通过分析教师准备的任务单来研究教师的意图如何影响学生的博物馆体验,根据任务密度、方向提示、位置特征、信息来源、选择度和认知水平六个特点来评价任务单的合理性。[21]根据这些特点,另一研究对某自然博物馆网站上的“监护人指南”进行了评估。作为指导学生以学习科学课程为目的进行参观的工具,“监护人指南”的设计十分合理,少量的任务使学生有自由探索的机会,方向提示可以方便学生找到与课程相关的展品,参观内容与课程知识的结合既注重部分基本概念学习,又提供开放式学习的机会。[13]从而可以发现,提前设计准备的任务单可以帮助学生在博物馆自由选择地学习,也可以用来传递教师的教学目的,使学生在开放、不受控制的环境下仍能联系课程进行学习。
3.3 发现和利用“后博物馆阶段”博物馆参观对学校教育产生的长期影响
除了做好参观博物馆前的准备,还要注意发现和利用博物馆学习在博物馆参观之后对学校教育产生的长期影响。博物馆学习带给学生的积极结果不仅有认知上的变化,还有情感上的变化。[14,18]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研究并没有直接发现参观博物馆给学生的认知方面带来明显变化,[22]不过它们证明参观博物馆的经历能激发学生想要继续学习博物馆展示内容的动力及其他情感。因此,博物馆学习带给学生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变化,是博物馆为学生学习生涯带来的独特经历,应当善于利用学生的“后博物馆阶段”。教师在学生参观博物馆后应该继续将博物馆参观主题延续到学校学习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的各种学习连贯、完整。而在学生结束参观之后,博物馆也应该继续跟踪调查学生相关的学习情况,了解学生的“后博物馆阶段”,提供教师联系博物馆的课程教学帮助,并获得反馈以更好地改善学生的博物馆学习体验。
4 结论
博物馆学习是辅助学校课程学习的重要手段,联系学生的博物馆学习和学校课程学习,能使学生在两者的学习上都获得收益。首先,博物馆具有实物性、直观性、广博性的特点,其实体展品、真实的物理情境可以加强对感官的刺激,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理解知识内容有助于补充学校的抽象教育,使学生可以结合课本知识在博物馆实物展品上获得更多的信息内容。其次,学生先前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在博物馆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可以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的新知识,并将原有的知识结构应用在实际情况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其学习兴趣。另外,博物馆学习强调社会性的学习过程,学生在博物馆的环境下以互动的形式进行学习,有助于学习社群中的成员更好地建构自己的理解,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将这种社会性的学习形式带回课堂,帮助课堂交流活动的开展。
因此,充分利用博物馆学习可以改善学校课程学习效果,为达到这一目的有许多策略。第一,要充分将博物馆学习与学校课程内容进行结合,将课本知识与展品信息进行联系,从而帮助其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第二,参观博物馆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有助于学生在博物馆的学习。为学生制定预定向项目,提前告知博物馆概况、展品方位、行程安排等,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在学习而非其他事物上,并且提醒他们重要展品的位置以免错过。而任务单的使用可以使博物馆参观相对结构化,学生享受到自由选择学习的乐趣,但又能保持與学校课程学习的紧密联系。第三,要注意发现和利用博物馆学习在参观博物馆之后对学校教育产生的长期影响,包括学生认知上的变化和情感上的变化。教师和博物馆方要在学生参观完博物馆后继续利用博物馆学习带来的影响,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受益。
参考文献
[1]Hein G E. Museum education[M]//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West Sussex: Wiley-Balckwell, 2006: 340-352.
[2]Falk J H, Dierking L D, Foutz S. In principle, in practice: 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s[M]. Lanham: Rowman Altamira, 2007.
[3]伍新春,曾筝,谢娟,等.场馆科学学习:本质特征与影响因素[J].北京師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3-19.
[4]Goodrum D, Hacking M, Rennie L. The status and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science in Australian schools[R]. Canberra: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2001.
[5]王宏均.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严建强.博物馆与实物[J].中国博物馆,1999(2):22-26.
[7]Fu Y, Kim S, Zhou T. Staging the 'authenticity' of intangible heritage from the production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Craftsmanship Museum Cluster in Hangzhou, Chin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5, 13(4): 285-300.
[8]Handler R, Saxton W. Dyssimulation: Reflexivity, narrative, and the quest for authenticity in “living history”[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88, 3(3): 242-260.
[9]鲍贤清.博物馆场景中的学习设计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10]Wellington J.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ing in science:The role of the interactive science centres[J].Physics Education, 1990, 25(5): 247-252.
[11]Anderson D, Lucas K B. The effectiveness of orienting students to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a science museum prior to visitation[J].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1997, 27(4): 485-495.
[12]Falk J H. Field trips: A look at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learning[J]. Journal of Biological Education, 1983, 17(2): 137-141.
[13]Mortensen M F, Smart K. Free-choice worksheets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curriculum during museum visits[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007, 44(9): 1389-1414.
[14]Braud M, Reiss M. Towards a more authentic science curriculum: the contribution of out-of-school lear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06, 28(12): 1373-1388.
[15]周甜,李洋.从建构主义学习观看博物馆青少年儿童教育[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2(9):206.
[16]Rennie L J, Mcclafferty T P. Science centres and science learning[J].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1996, 27(1): 53-98.
[17]伍新春,谢娟,尚修芹,等.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科技场馆学习[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6):60-64.
[18]Falk J H, Dierking L D.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s experiences and their making of meaning[M].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0.
[19]Griffin J. Research on students and museums: Looking more closely at the students in school groups[J]. Science Education, 2004, 88(S1): S59-S70.
[20]Falk J H. The director's cut: Toward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from museums[J]. Science Education, 2004, 88(S1): S83-S96.
[21]Kisiel J F. Teachers, museums and worksheets: A closer look at a learning experience[J]. Journal of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2003, 14(1): 3-21.
[22]Borun M, Flexer B K. Planets and pulleys: Studies of class visits to science museums[R]. Philadelphia: Franklin Institute Science Museum,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