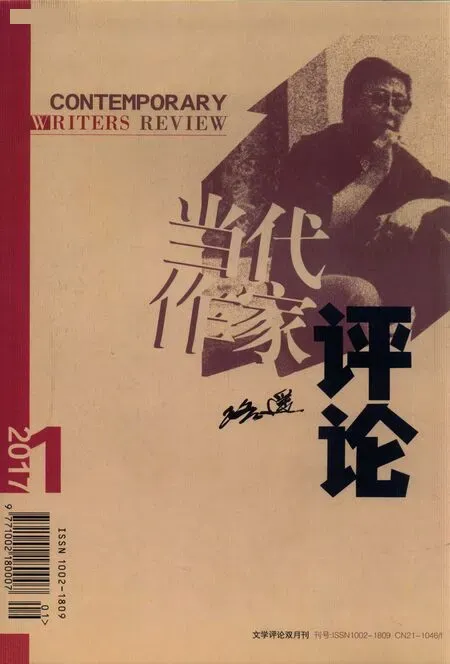历史文体学视域中散文诗的文类归属与界说
张 翼

历史文体学视域中散文诗的文类归属与界说
张 翼
中国现代散文诗是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而在新文学土壤里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新生文体,但它在百年发展进程中始终摆脱不了面孔“模糊”的命运。散文诗何所属、何所为,文体特质又为何,这些疑问引发了对散文诗文体定义的追问与文类归属的焦虑,不断给创作和评论带来困扰。面对这些难题,理论界和创作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除了把散文诗或归入诗歌或归为散文或视为独立文体这三种常规看法外,有些研究者表达了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诗人曾凡华反对纠缠于文体分类的理论问题,认为散文诗是一种跨文体创作,作者就应从生活和内心出发,能创造艺术的可能性即好。持这种跳出文体分类观点的学者认为:鲁迅创作《野草》时就没有考虑文体分类的理论问题。相近的观点认为文体分类固然需要,但暂无法分类时则不必勉强,可借鉴现象学中“悬置”方法。这似乎跳出散文诗文体归类的难题,但看看各国领土的争端,就明白“搁置”只是暂缓之计,不能根本上解决文类归属的论争。
学者灵焚认为散文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他例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10卷本《中国新诗总系》中只选入极少量的散文诗。鲁迅分行诗的成就远不能与《野草》相提并论,但在1917-1929年的选编中收入其分行诗七首,《野草》集里则没能入选一首。灵焚认为散文诗正在遭受“冷暴力”。诗评家吴思敬作为《中国新诗总系》编委会成员之一则坚持“分行”是新诗确认自身文体身份坚守的最后底线,因而《中国新诗总系》才没有收入“不分行”的散文诗。灵焚的“不平则鸣”与吴思敬的“坚守底线”印证了“悬置”带来的争议和困扰。
一些台湾作家曾提出“取消论”。诗人余光中对“散文诗”的文体命名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其“非驴非马”;诗人纪弦也非常反感“散文诗”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名称太灰色了,为了处理上方便,我的意思是:干脆把它取消拉倒。”诗人罗青也认为“散文诗”是不恰当的文体名词,要将“散文诗”更名为“分段诗”。
有些学者甚至持“返古”的看法,认为文体归属无需争议,此种体裁古已有之,只是它的命名在近代。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就认为:“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朱光潜认为:“中国文学中最特别的一种体裁是赋。它就是诗和散文界限上的东西:流利奔放,一泻直下,似散文;于变化多端之中仍保持若干音律,又似诗。”
笔者认为古代虽有类似散文诗的文字,尤其是抒情小赋,但并不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诗文体出现。有类似的文字或作品不等于古代就产生散文诗的文类概念。诗与文的对话传统悠久,其间确有不少作品跨入诗文交融的境界,但散文诗在古典文学中并没有明显地成为新文类,也没有哪个作家曾自觉进行该文体的创作。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我国散文诗创作确是受西方文学理论及自由精神的启发,才成为自觉性的文体创作。中国散文诗的文体观念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逐步形成,当时人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体裁?这些认识在后来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到底发生哪些衍变?究竟何时产生对散文诗的身份焦虑?文类归属的困惑又意味着什么?厘清这些繁杂纠缠的问题,需要返回历史的原初现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散文诗文体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置放于复杂的文学场域,考量其在各阶段所扮演的文学角色及在文坛所处的地位。
一、历史的最初定位与错位
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动摇了传统诗学观念,开启了诗歌通俗化、大众化的序幕。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总结: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即1918年)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此后,刘半农、胡适、沈尹默、俞平伯等人开始理直气壮地增多诗体,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别增无韵之诗,用新形式抒写新思想,希望最终实现“别创诗界”和“新文体”的艺术旨归。散文诗的引入正值新文化狂飙运动之际,是符合时代文化需要,承载社会思潮的“革命性”文体。当旧有的形式格局所负载的公共象征无法装下现代社会的精神容量,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渴望形式的更新、转换来为新的生活内容与审美追求予以表现的便利。散文诗的自由精神应和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其移植引进和创作繁荣与新文学革命息息相关。它最初的历史定位是推广白话诗的中坚力量,协同新诗与古体诗为代表的旧文学作斗争,自然也就模糊了散文诗本身的文体特征与现代意义。
作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青年》以稍显激进的方式对新文学尤其诗歌部分进行改革,从最初的反文言而白话,到后来有韵无韵、散文诗体等尝试,为白话诗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平台。随着新文化运动逐渐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并成为时代风潮,不少刊物因应时势,也开始刊登新文学作品。当时的报刊、杂志刊登白话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髦。诸多新旧报刊、杂志都有以“诗”命名的栏目,不仅文学性的刊物《小说月报》与综合型的文化刊物如《新潮》《星期评论》有之,就连时政类的刊物、报纸《太平洋》《国民公报》,甚至专门刊登科学类论文的《科学》上都时有诗歌发表。此时挂名“诗”的作品五花八门,既有改良的旧体诗,也有新创的自由诗、民歌和散文诗等,可见当时刊物中“诗”的名下包罗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作品,新旧不分,文体不拘。
散文诗在当时不同的刊物或同一刊物上先后发表时,曾被编辑放在不同的栏目上。1918年《新青年》五卷“诗”栏目上发表的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常惠的《游丝》是最早登载的现代意义的中国散文诗。刘半农在1918年《新青年》四卷上已正式介绍过“散文诗”这种新文体,作为编辑之一的他在第五卷尚未意识要把散文诗作为新文体从“诗”中独立出来,且五卷“诗”栏目里只刊登了三首又都是散文诗,何不设置“散文诗”栏目?可见刘半农作为域外散文诗的引进者和散文诗的首创者,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尚未意识到要为散文诗设专栏,或把散文诗从诗或其他文类中独立出来,虽认识到“散文诗”的与众不同(五卷中他翻译屠格涅夫的《狗》和《访员》则标明为“散文诗”),却仍将它们归在“译诗十九首”里,仅把散文诗作为诗体的一种。
鲁迅在1919年8、9月的《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上连续发表一组以《自言自语》为总题的七篇散文诗,是早期散文诗的精品。鲁迅发表这些散文诗时,似乎也没有认识到其文体的独特性,编辑也大一统之的放在“新文艺”中而没有作什么说明。
《太平洋》是时政刊物,却常设有“文苑”栏目,刊登杂剧、诗歌、小说等。1920年刊登了吴芳吉的散文诗《别上海》,杂志栏目的名称是“诗”,编辑们的归类不是“散文诗”,甚至不是“新诗”,而是“诗”。可见,此时“散文诗”的自觉意识,甚至“新诗”的自觉意识,在非文学类刊物的编辑身上并没有形成。1922年,《太平洋》刊物出现了“新诗六首”这样的栏目标题。六首诗中,有译诗《吾爱之复活节》,有自由诗《偿毕宜车站别诸友》《泪歌》,也有徐丹歌的散文诗《光明和黑暗》。编辑们用“新诗六首”的栏目把散文诗与其他诗刊登在一起,对“散文诗”与其他诗体没有给予特意的区分。由此推之,当时非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散文诗文体的自觉意识更没有形成,此时的散文诗只是新诗的一部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们毕竟是时政杂志的编辑,但栏目设置从“诗”到“新诗”,不能不说随着新文学的日渐繁荣,不论编辑、作者,还是读者都意识到新旧文学的不同,已是文类区分的进步。
随着域外散文诗不断被译进,加之创作中的体悟,人们逐渐意识到散文诗的不同之处。1920年12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郭沫若一组四章《我的散文诗》,是当时作者最早明确标明“散文诗”文体而发表的作品。1921年《小说月报》(11月号)给刘半农翻译的散文诗设置了“散文诗”栏目,译载《王尔德的散文诗五首》。这是刊物第一次出现专门的“散文诗”栏目。可见,部分编辑开始不再将散文诗当作新诗看待,而是作为新的独立文体,至少是新诗中别具一格的诗体。一些文学编辑已拥有较明晰的文体细分视野,这种视野促使他们开始设置“散文诗”专栏。与文学刊物的编辑们相比,其他刊物的编辑们对“散文诗”的文类意识显然落后不少。
通过对部分报纸、刊物及设置栏目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初始阶段,散文诗发表在“诗”、“新诗”或“新文艺”等综合性的文学栏目中,几乎没有设置专栏,更遑论其他刊物。新文学的首要任务是语言的口语化,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才是新文学的重中之重,而新文学作为逐步推动民国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诸种力量中的关键,有政治性因素的考量,也有启蒙精神的导向,至于文体的探索则是后话。先推出白话诗而不管采取何种诗体,则是新文学媒体的一种宣传策略。打破文言的束缚,在白话诗日渐被接受后,再考虑诗体的探索、定位。当时的“散文诗”有很多今天看来,并不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诗,而只是诗体解放后出现的与旧诗相对立的一种“新诗体”。新诗最明显的特征是“散文化”:诗句可长可短,不必讲究韵律。文学革命伊始对散文诗的文体概念还没形成明晰的认识,不仅新诗和散文诗没有太明确的界定,就连新诗和散文的界限也很模糊,甚至主张“要作诗如作文”。文体概念使用“错位”现象的产生,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特殊使命所致。新诗的发轫期,总的倾向是诗体的大解放,胡适有言,唯有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能跑到诗里去。”当时散文诗的“定位”就是——新诗,甚至还涵盖新诗以外所有的白话诗。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历史任务的重心主要在于用白话代替文言,解放旧文学而创制新文学,许多新诗被取笑为艺术上的拙劣之作,艺术的手法还顾不上,文类的细分更无暇顾及。
由于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感悟到散文诗与其他文体的不同,同时,一些理论家在评论过程中也渐渐注意到散文诗的文体个性,于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辨析新诗、散文诗与散文。这标志着创作领域与理论界逐渐认识到文体间的差异,以及意识到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散文诗应该有自己特殊的文体内涵。当新文学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并力求创立文体典范时,作者和理论家开始逐渐重视文类的划分,而不得不面对文体的中间地带、模糊地带,归属的困难唤起单独命名它们的需要。当时的评论家和作者虽没有清晰阐述自由诗和散文诗本质上的区别,但不断刊出周无、田汉、李思纯、郑振铎等人的理论文章至少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体裁间的不同。“散文诗”如果不是“自由诗”,那么它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在新文学革命初步取得成功后文体细分意识的觉醒,是现代文类意义上——散文诗之为新文体的文类意识的萌发,预示着文学革命初期新诗和散文诗之间原本混沌涵容的状态正逐渐被清晰勾画。当时文化前辈的历史任务仅是对旧文学的解放,而不是划分文学细类并创制经典。随着历史的演变,分行的自由诗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独立的文体与不分行的散文诗划清了界限。散文诗在新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定势后,已然完成了自己与新诗并肩作战的历史使命,开始对自身的身份寻找新的确认。散文诗该有自己特殊的诗体内涵,只要散文诗的文类意识开始发蘖,后来的创作者和理论家总会归纳出它真正的诗学内核。散文诗在助力完成新文学的拓荒任务后,从历史最初“定位”的“错位”里抽身而出,探寻自身的合理位置,以自身的包容性体式、可塑性书写和审美的现代性,逐渐显示出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内涵。
二、创作机制内部的朦胧与出版界的混乱
域外散文诗第一次被翻译、引进时,即被错误地冠以“小说”身份。1915年7月1日《中华小说界》登载刘半农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被误归“名家小说”类,总题为《杜瑾纳夫之名著》发表。初时不仅译者对散文诗文体尚未有正确的认识,出版者更是不辨文体。1918年刘半农在《新青年》第五卷2号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散文诗两首,在目录标为“诗两章”,而在正文部分则特意点明为“无韵诗”。刘半农和编辑都误把泰翁的“散文诗”当作“无韵诗”。同年刘半农在《新青年》第五卷3号上发表“译诗十九首”,其中仍有泰翁的散文诗七首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两首,刘半农在翻译泰戈尔的散文诗时,译后注明为“以上是印度R·Jagore氏所作无韵诗七首”,而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时,却在译作后注明“以上俄国Ivan Turgnev所作散文诗二首”。这说明刘半农虽把“散文诗”当作诗体的一种新形式,仍归为诗这个文类中,但至少已开始辨析“无韵诗”与“散文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形式,只是对新文体的区分还未精确,以至把泰戈尔的“散文诗”当作“无韵诗”。刘半农作为新文化的先驱,首位译介外国散文诗作品,也是第一个将其文体概念引进中国文坛,同时,还是第一个写出成熟散文诗的作家,尚且还会混淆“散文诗”与“无韵诗”,更遑论其他的作者和编辑。
刘半农的例子很好说明新文学的提倡者是从译介外来作品中逐步领悟到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审美品格,并把这些感悟融汇到创作中,逐渐形成文体自觉,意识到散文诗的文体独特性,且应作为独立的文类来建设,而这是后话。任何一种新文体都要经历发现、认识、接受的渐进演变过程,散文诗也不例外。五四新文学的起步阶段,刊物的编辑们对新文学的作品并未产生明晰的文类意识,他们在“新诗”、“散文诗”、“无韵诗”,甚至“诗意的散文”之间还未寻得真正的文体区别,因此在栏目的设置上并不明确。新文学的创作者,也未必对自己的作品有更清晰的文体意识,他们忙于拓荒白话文的疆域,还兼顾不到或也茫然于自己作品的类属。文学发展,向来是先有新文体而后有理论概括,“立名责实”总是后于写作实践。周作人的《小河》在1919年2月发表时,在诗题下注明文字说:
有人问我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周作人在写作《小河》时,更多的是源于创作内在需求,根据自我情思的涌动自然地产生与之相适合的作品,对文学样式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对作品的文类归属也不甚清晰,甚至觉得无甚关系。
俞平伯的《〈忆〉序》是一篇散文,为自己的诗集《忆》写的序,发表在1923年5月15日新诗月刊《诗》上时,却特别表明是“散文诗”。这篇散文被标明为“散文诗”有两种可能,一是俞平伯自己,二是编辑添加上的,但刊物——《诗》是1919年俞平伯与朱自清等人创办的我国最早的诗刊,即便是其他编辑另加上的,估计俞平伯也是不反对的。为何他要把这篇散文注明或认可编辑标明为“散文诗”呢?合理的解释其一可能是俞平伯希望作品被归入诗的类别,特别表明是“散文诗”而刊登在《诗》的刊物上以名副其实。中国作为诗的国度,在作者乃至读者眼中,散文总是矮诗一截,诗歌总是处于高雅的地位,连朱自清也未能免俗,其散文集《背影》序中称:它不能算作纯艺术作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分。由此推知,当时一些称为散文诗的作品未必是真正的散文诗,因诗的身份更为“高贵”,不少带有诗意性的散文就被有意无意地归为散文诗。其二是编辑和作者当时都未对文体产生明确的文类意识,而散文诗的文体定位当时也不是太明晰,因而没有细分的必要。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冰心、朱自清等其他作家身上。1924年郭沫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品六章》,他在小序中写道:“我在日本时虽赤贫,但时有牧歌的情绪袭来,慰我孤寂的心地,我这几篇小品便是随时随处把这样的情绪记录下来的东西。”“小品六章”是六首堪称“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精品,为何要标作小品发表?郭沫若早在1920年《时事新报》就发表了《我的散文诗》,是最早自己明确标明“散文诗”文体而发表的作家。1920-1921年他与友人们的通信中曾多次探讨过散文诗的文体特征。1920年他在致宗白华的信中提到:“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自身本是具有音乐与绘画之二作用故。”这说明郭沫若已明确地把自由诗与散文诗作为不同的诗体而相提并论。1921年,郭沫若致李石岑的信中认为散文诗是具有内在音乐精神的“裸体的美人”:“试读太戈儿的《新月》《园丁》《几丹伽里》诸集,和屠格涅夫与波多勒尔的散文诗,外在的韵律几乎没有。惠迭曼的《草叶集》也全不用外在律。”他甚至例举域外散文诗名家作品来论证:散文诗只要拥有纯粹的内在律,即使没有外在的韵律或音律的外在形式,也不影响它作为诗的存在。1922年,他在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本序中还特意阐述了对散文诗的见解:“古人称散文其质而采取诗形者为韵文,然则称诗其质而采取散文形者为散文诗,正十分合理……有人始终不明白散文诗的定义的,我就请他读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吧!”文体的讨论说明当初文坛对散文诗的认识还未达成普遍共识,同时也看到郭沫若前期一以贯之地坚守并呼吁散文诗文体的独特性。为何他后来又把散文诗与小品混为一谈?显然,他还缺乏对散文诗本体美学精神和形式结构上的自觉的理性认识。可见,当时的作者对小品与散文诗的文类界限并没有明确到位的体认,而编辑更不会对散文诗当作小品发表的行为提出异议。总之,新文学时期,不论作者还是出版界,对散文诗都还缺乏足够理性的关注与探讨,而且文体之间的混淆持续了很久的时间。在1935年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茅盾的一些散文诗还被选入,阿英曾这样评价茅盾的散文诗:“茅盾的《叩门》《雾》一类小品,当然是还不够那样精湛伟大,但这些小品,正象征了一个时代的苦闷。”显然,作为文艺理论家的阿英当时对散文诗与小品间的文体区分也是混沌、感性的,并没能自觉意识到不同文体的美学追求与个性差异。
灵焚教授认为:“自觉”这个概念,在哲学上与“自我意识”基本相同,其基本特征是具有“自我同一性”的认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创作则需要明确自己要以什么形式(体裁)进行创作,这种题材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等等,而自发的创作只需要源于内在的需要,根据内在的需要自然地产生与这种需要相适合的作品即可。从哲学范畴看,不少人在创作散文诗时,并不完全具备作品与创作间的“自我同一性”认识。他们往往最初不是明确要采取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只是遵从内心表达的需要,写着写着就写成散文诗;有的作者不确定自己的作品是什么体裁,而权且采用“散文诗”这个名称;有的作者在创作时,是介于自觉与非自觉状态之间,《野草》的写作估计就是这样。鲁迅在1932年回忆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为何鲁迅认为:“散文诗”就比“短文”夸大点呢?《野草》里不少作品的篇幅都比他的短文篇章更短小,无疑是散文诗的创作比短文需要更多的构思和诗艺!他曾告诉章衣萍:“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在致萧军信中也提到“我的那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鲁迅作为杰出的文体家,善于驾驭各种体裁,也有多种形式的作品问世,而他在《野草》中那些难以言说的心声恰是其他文体形式无法承载。不同的内容会选择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鲁迅显然感受到散文诗的体裁跟当时内心的困惑、苦恼有着异质同构的契合,只是未去进一步深思:为何偏是这种文体样式能接纳他当时全部的哲学思想,且运用到高超的艺术技巧?采取这种文类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要求作家在创作时去自觉地作理论探讨是一种苛求。创作出经典作品后,作家已然完成光荣使命,但作为理论研究者,却有必要分析哲学题材与其他题材在文体表达形式的需求上有何不同?散文诗体裁为何善于表现这类题材呢?
郭风在《叶笛集·后记》中曾谈及写作散文诗的切身体会:“写作时,有些作品不知怎的我起初把它写成‘诗’——说得明白一点,起初还是分行写的;看看实在不像诗,索性把句子连接起来,按文章分段,成为散文。”什么原因将创作自由诗的初衷转变为散文诗创作呢?当作者感到分行排列的方式不能真实地呈现内心情感流动的结构时,就会放弃分行的形式选择更为舒缓扩展的分段来表达。郭风意识到作品虽采取了诗分行的外在形式,但其表现的艺术内涵还是散文诗的范畴,而不是自由诗的内容。郭风在创作原初并未想到要写散文诗,但在写作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散文诗的样式与其表达的内容更为恰切。穆木天早就有这种文体觉悟,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散文诗有时不一句一句的分开——我怕它分不开才不分……所以要写成散文的关系,因为旋律不容一句一句分开,因旋律的关系,只得写作散文的形式。”
诗人方敬为何会感慨自己的散文诗往往是写诗不成,写散文又不成的产物呢?这关系到作家写作散文诗时特殊而微妙的创作机制:需要超越自由诗较为严谨的分行格式以无拘无束地自由表达,同时又要以精练和诗意的表达收拢散文行文的“散”。虽然作者有时内在创作机制混沌模糊,但内心至少已感受到散文诗的文体形式和审美内涵对表达某种情思的特殊召唤。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本身昭示了不同的表达内容,形式与内容不是二元对立或截然分离,它们时常互相召唤、同时发生并融合在作家创作机制的内部。形式本身往往即是内容的解码。由于散文诗文体形式的包容性与自由度,往往使作者对自己选择的文体形式产生不确定。不少作者虽留下重要的散文诗作品,然其内部创作机制却处于自觉与非自觉之间;也有些作者只是根据内心表达的需要书写,自发地完成了散文诗作品;甚至有些人一边否认散文诗的写作而一边不自觉地进行着属于散文诗的创作。
散文诗文体的兼容性、自由性,也是其独特性和个性所在:冲破诗与散文的形式局限,展示文学表达域的更大可能性。正是其特殊的文体样式导致长期以来多数散文诗作者内部创作机制暧昧不明。日本散文诗人粕谷荣市曾明确的表明虽然自己:“长期以来写散文诗,近四十年了。然而,没有一次想到是在写‘散文诗’。是想写诗的,自然地成为那样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不中用吧!为了自由,至少可以说,写作的时候我希望是自由的。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采用了这种形式。”他的创作剖白说明表面上看似乎复杂幽深、难以言传的情思需要自由表述时,内心的波动让作者无法顾及形式的规范而不得已地选择此种文学体裁,其实是散文诗自由的文体特质在召唤作者对它的选择。散文诗是一种对应着人类“新感性”之原真状态的新载体,具有诗和散文无法取代的现代审美功能,不然,作者何苦去僭越常规文体,挑战原有体裁分类的纪律?
散文诗作者多数是不自觉地采用这种体裁写作,尽管创制之初诞生了《夜哭》《野草》《魔鬼的舞蹈》等杰出的作品集,但开创者缺少真正意义的文体自觉,对所建构的话语体式与艺术技巧没有深入阐述,导致散文诗的写作技艺无法得到应有的传承。在自觉与非自觉之间徘徊的散文诗创作现象一直持续存在。诗人昌耀的晚年作品,诗人西川近年来的许多诗歌都可归入散文诗,可他们本人却不认为、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散文诗。文体混淆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也许是内在创作机制的模糊,也许是散文诗文体特征不够显豁,亦或是多数人的心中——“诗”始终代表一种传统的贵族体裁。朱光潜就曾说:“散文诗又比自由诗降一等。它只是有诗意的小品文,或则说,用散文表现一种诗的境界,扔偶用诗所习用的词藻腔调……”不少人的心目中,诗似乎比文更显高贵,自由诗又比散文诗更胜一筹。
散文诗自诞生以来,许多作者尚处在自发状态下创作,如何有意识地、自觉地按照文体个性与美学原则进行创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确认与正视。再加上出版界的多数编辑对散文诗与自由诗、美文也未有明确的体认与区分,出版时无法仔细辨析文类,更有甚者张冠李戴,这些都加剧了散文诗归属的混乱与困惑。
三、文体发展的鲜活更新与文类划分的笼统滞后
文类划分是漫长的文学历史逐渐演化而来,起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应用的方便,而建立一个便于理论研究与创作交流的互动渠道。文类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通过苏联美学家莫·卡冈的美学著作《艺术形态学》可以了解到西方文论史上对于文学类型的划分至少有:以题材划分、以作品的认识容量划分、以材料划分、以创作方式划分等九种,根据外在的形式进行归类往往比内容的区别容易得多,因此从外在文体样式上划分是文体分类最常用的标准。诗与散文在外形式上最显豁的区别是诗分行,而散文不分行,但有些“诗”即使分行了,其艺术内涵还是文而不是诗;而有些美文,如做分行处理,远比一些诗更具语言艺术张力,更接近诗的本质。诗的散文序有时胜过诗本身,如陶潜的《桃花源诗》、王羲之的《兰亭诗》都较序文《桃花源记》《兰亭集序》稍逊一筹。诗与散文似乎很容易辨认,然而仔细推敲,寻常所认出的分别不免因有些例外而衍生出问题。西方文学从亚里士多德起,就有过诗和散文的文类之争,我国也有“文”、“笔”之争。
散文诗在外观上与散文几乎一致,以段的形式铺展开来,而在艺术形式上主要采取的却是诗的技艺。作家李广田认为散文的长处在于自然有致,而无矜持的痕迹,它的短处却常常在于东拉西扯,没有完整的体势。散文诗人灵焚认为散文诗的内容:“除了不可缺少的意象手法的运用之外,其中细节性、场景性、故事性等内容,也都是通过意象、意蕴、象征、寓言等因素的叠合,形成意象性细节或场景,并让这些细节、场景在跳跃性展开中重构世界,呈现抒情或叙事的审美场域。”正是这种外在形式与内在技艺与通常文体划分规则的背离,招来了“非诗非文”的诟病,使得散文和诗歌领域都拒绝散文诗与自己同族。可以说“散文诗”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不通、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无论在创作还是阅读接受上,谁都无从否认散文诗的本体存在。称为“散文诗”,命名上虽造成类型归属上的麻烦,却真实反映出文类相互渗透后容易在文类交界处产生新文类的文学发展现象。学者陶东风认为:“文体变易的一个常见的途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体之间的交叉、渗透,并进而产生一种新的文体。这种交叉、渗透实际上是多种结构规范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妥协和互相征服。”从文体繁荣发展的长远看,文体的分类是必要的,文类的划分和设置是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和形式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并作出界定和阐释的标准和规则。但分类不是僵化的,而应是发展和动态的,从历史角度看,文类的内涵和外延常处在变化中,严格说来,文类其实是无法精确定义,它只是一种区分功能,并非创作准则。人们一旦给文类下了定义,随着新作品的出现,马上又会有逸出文类的现象。文体定义的本身是一种无穷尽的追逐过程,先前普遍采用的西方文类的“四分法”显然无法囊括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文学样式。文类的划分总是滞后于文体鲜活的发展进程。
我们大抵承认这个作品属于什么文类,但并不愿意过多地去解释什么是诗?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小说?它们的定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就如诗的本质界定是可以解构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诗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都认为文学类型就如同制度一样,会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文学的种类是一个“公共机构”,正像教会、大学或国家都是公共机构一样。它不像一个动物或甚至一所建筑、小教堂、图书馆或一个州议会大厦那样存在着,而是像一个公共机构一样存在着。一个人可以在现存的公共机构中工作和表现自己,可以创立一些新的机构或尽可能与机构融洽相处但不参加其政治组织或各种仪式;也可以加入某些机构,然后又去改造它们。”现代文学类型研究的趋势并不限定可能有的文学种类的数目,也不轻易给创作制定规则。新的理论研究发现传统的种类可以被“混合”起来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种类,例如悲喜剧、诗剧、诗体小说等。契科夫的《樱桃园》、易卜生的《群鬼》、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属于什么文类?文类可以在单纯的基础上构成,也可以在包容其他文类的基础上形成。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有不少文体就是在包容其他文类的基础上形成。赋是战国末期萌生的一种具有半诗半文性质的新型文体。刘勰认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既有诗的整饬和声韵之美,又有文的灵活和陈述之便。魏晋时期诞生的骈文虽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一种特殊文体,却是散文辞赋化的产物,其间也受到“永明体”诗的影响。它和诗一样讲究声韵节奏,追求对偶、藻饰之美,但骈中有散,讲究长句和短句结合,运思行文不像诗那样跳跃多变,更接近于文的流动畅达,开启了散文诗化的先河。魏晋时期,还才产生“笔记”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体。笔记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陈平原教授指出:“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对于散文和小说来说,借助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以介入、有与之渊源甚深“‘中间地带’。”元代的曲当初也是一种新文体,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散曲,还与戏曲结合形成杂剧,是古典诗歌繁荣的一种特殊方式,带有某些“混合”或“杂交”的特征。文类交叉互动而生成新文体的现象古已有之,由于文学形式能随世递迁,不断涌现新文体,诗剧、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才促成艺术上佳构迭出、百花竞放的繁荣景象。
对文类的划分或定义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在应用上不至为不同的称呼或定义而争论不休。为文类下个合适且被广为接受的定义,以建立沟通交流的途径,这不仅是散文诗研究也是所有文类研究都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不过因散文诗是近代社会而诞生的新文类,跟散文、诗歌、小说等古老的传统文类相比,其文类特质显然还不够稳定,对它的理论建构目前还是开放式的,有着一定的自由度和包容性,因而,它的定义和归属目前尚难以被广泛接受。现代的类型理论明显是说明性的,并不限定可能有的文学种类的数目,也不给作者们规定规则。它假定传统的种类可以被“混合”起来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种类。类型可以在“纯粹”的基础上构成,也可以在“包容”或“丰富”的基础上构成,既可以用缩减也可以用扩大的方法构成。我们不必急于为“散文诗”文体划定清晰的类型边界线,也无需贴上固定的本质化的文类标签,而是要深入到丰富的文本中去感受散文诗“混血”的魅力,领略它在不同文类边界间自由游走的活力,享受这个新文体包含不同文类特性而给予的新奇而熟知的阅读感受。
文类不是自太初就有,随着新作品的增加,文类概念也会改变。文类之间不是壁垒森严,互不侵犯的,林以亮学者指出:“在艺术中,正如同在大自然中一样,有许多地方并不是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的……就像白日与黑夜之间,存在着黄昏、黑夜与白日之间,存在着黎明一样,散文诗也是一种朦胧的、半明半暗的状态。我们很难提出一个确定的时刻,说在这以前是白天,在这以后是黑夜。这是一种过渡时期,虽然暂时,却是真实的,而且是大自然必有的现象之一。”文类的概念并非绝对,也无法作终极定义。班固眼中“君子弗为”的小说与梁启超定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无论其内涵与外延都相距甚远。文体随着社会发展而鲜活地变化更新中,总会打破原有的文类划分,破与立的更替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当新文体出现时,需要用新的理论或分类法为其归纳、定位。各文体间相互渗透、融合,同时也互相竞争,使其在演进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源头活水乃至挑战,才能推动一代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文体学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1062)前期成果;2016年度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李桂玲)
张翼,博士,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