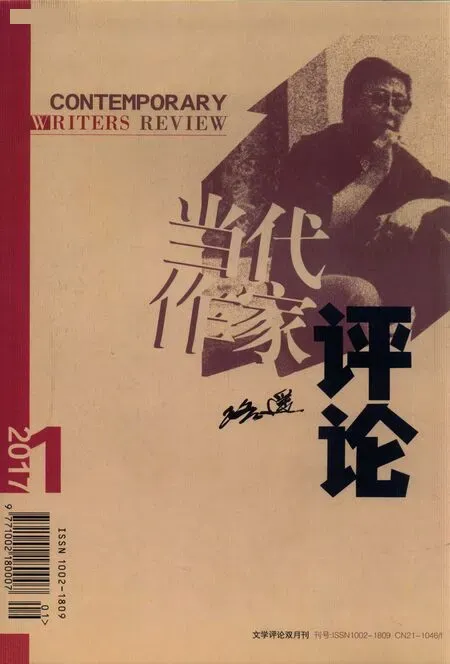非虚构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观照
——以陈歆耕《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为例
郝 雨 杨欣怡

——以陈歆耕《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为例
郝 雨 杨欣怡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坛的非虚构写作极其活跃。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散文等长篇创作更是备受推崇。2016年初,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传记——陈歆耕著《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很快受到文学界、史学界以及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本书注重和尊崇史的真实,又有较高的文学创造价值;不仅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代文字之雄”龚自珍的传主形象,而且特别在传记写作的范式和表现手法上显示出了独特的探索和创新。对于整个非虚构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传记文学写作的真实性与文艺性、历史性与当下性等核心问题,都提供了一定经验。
一、非虚构写作中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兼融
胡适提出传记写作两个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与“传神写生”。“纪实传真”是对真实性的要求,“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这里强调了传记的史料价值。“传神写生”是对文学性的诉求,“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这里强调了传记要活灵活现写出传主的性情人格。他认为真实性与文学性都很重要,希望能达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双重目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对今天的传记写作仍具有借鉴意义,陈歆耕先生的《龚自珍传》就是在严谨的史料梳理与考证前提下,同样有可圈可点的文学价值。
龚自珍在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陈歆耕在写作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传记时,首先充分认识到传主的思想文化价值,从而也特别懂得传记作品之真实的力量。所以,在传记体裁必须坚持求真的非虚构写作中,作家的创作始终以“实”为最高准则,恪守这样的一种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研读龚自珍著作及史料,真正从中深入到传主的精神深处。尤其对于龚自珍诗文的解读,作者在传记中,尽量避免一己理解的偏见,一再强调自己只是简单的翻译,未必准确,提醒读者一定亲自阅读龚自珍诗文本身。而对于几无史料的部分,或者不能完全核实只凭后人猜测的地方,比如龚自珍的妻子段美贞的早逝是否因水土不服?在扬州逗留期间,前辈学者阮元是否资助过囊中羞涩的龚自珍?龚自珍辞官先行离京的原因何在?陈歆耕也有自己的揣测,但是他会明确告诉读者这是作者的猜测。这种实,使写作不是以精神导师或凌空虚蹈的形象出现,这样就大大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这种写实不仅体现在案头功夫,还体现在作者深入实地的环境感受与体验式调查。为了能够设身处地了解龚自珍的许多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陈歆耕实地走访了天都庙、云阳书院、翁山墓地等历史遗存,确实掌握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在本书《尾声寻踪》一章中我们看到,陈歆耕通过对龚自珍踪迹的实际探访发现,有些历史建筑已经无迹可寻,有些遗迹虽然还在,但盛况远不复当年。“根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天都庙是一处人气很旺的著名庙宇。但我看到的天都庙是大约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很小的庙,夹在拥挤的住宅之中。”而龚自珍纪念馆,也成为杭州人气最低的人文景观之一,这些现状让作者深深叹惋。对龚自珍踪迹的探访,实际上是对龚自珍纯正品性的一种环境寻踪和身感心受。在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中,这样的对历史人物踪迹的实地探访,虽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具体的故事或传闻,但是,这种设身处地,身感心受,也能够达到向传主精神世界靠拢的境界。在《龚自珍传》一书中,陈歆耕先生努力追求真实性和准确性,尽力避免想象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可能会使作品略显拘谨或逊于文采,却严格遵循了“非虚构”的文体要求,保持了学术的严谨。
在文学价值方面,此书更有很多值得评说的地方。传记文学是“传人”的文学,基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象与虚构,这是传记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最大的区别。但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要把传记写好,把传主“写活”,又离不开文学性的表达手法。所以,传记写法很多,但写好不容易。很多作者摆脱不了一般传记写作手法的约束,或写成年谱式的,或写成大事记式的,或者就是写成传主文章经历事迹的串联与解说。这类写法或许能够把传主的生平经历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真实还原,但是,传记文学又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罗列,需要文学价值的有机融合。陈歆耕的《龚自珍传》避开了这种堆砌式的呆板写作,在文本结构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一定突破。在标题上作者用了“剑魂箫韵”四个字提纲挈领,其中“剑”与“箫”两个意向鲜明象征了龚自珍的性格特征与人生追求,把人物最鲜活的特点直接提炼出来。然后,在全书的文本内容中不断把传主的人格得到印证。全书谋篇三大版块。分别选取了“巨匠”、“困兽”、“春泥”三种形象,把龚自珍的生活背景、家学熏陶、朋友影响、求学仕途、情感世界等情形铺展开来。上部“巨匠”,作者首先对龚自珍辛辣批判的清王朝进行了俯瞰式扫描,其中清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无疑是关注的焦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的两句诗揭露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衰世”之下,批判性思维方式贯穿了龚自珍的一生。中部“困兽”,考察龚自珍的成长历程,但作者并没有以传主年龄的增长为进程,避免陷入准年谱式的“流水账”中,在“家族”与“交游”两小节中,作品直接从对龚自珍人生产生较大影响的家人、朋友入手写起。在接下来的“顿挫”与“彷徨”中,作者详细描写了龚自珍每次科场考试经历,将一幅“仕幸不成书幸成”的跌宕仕途图景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引发联想:以龚自珍狂放不羁的个性与直言不讳的品性是否真的适合当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下部“春泥”,作者带领大家看到这位思想大家、文化巨人的另一面侧影,他的浪漫情怀,他的对女性的态度,他的收藏爱好,是龚自珍有情趣的一面,让我们对龚先生有了更鲜活的认识。作者敢于突破编年体限制,建构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传主的不同侧面,把龚自珍“剑”的人格和“箫”的人格非常立体全面地展示出来。
在叙事风格上,陈歆耕的《龚自珍传》不只是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处处流露出理性的批判与深刻的思考,甚至是在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思想对话。评论家韩石山就在对此书的评论中认为,作者有意识地引入了一种论辩的风格。传主龚自珍本人的创作就长于论辩的风格,而陈歆耕用龚自珍所具有的这种思辨的风格来写龚自珍,恰恰表明,作者与传主真正有着精神上的联通。正如作者用“剑”和“箫”两种截然对立的意向来反映龚自珍人格形象的多元特质,在全文中都保持了这种辩证性的思考:想做“名臣”,却成了“名士”,想做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践行者,却成了“文章惊海内”的诗文大家。郁达夫曾经认为,在传记写作中对传主的选择是一种身份认同和心灵相通的过程,“这种身份的认同,不仅为作者揣摩传主心理活动铺设了便利的通道,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架设了桥梁”。龚自珍的气节与思想深度千古流传。作者在品读龚自珍的诗文时,就强烈感受到横贯诗文中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作者无法撇开这一点来谈诗文,这本书里有作者大量的判断层面的思考,对于龚自珍性格中有趣的一面,对于龚自珍性情写照的诗文,作者都表达了自己的心有灵犀的见解。这样的叙事风格实际上保持了作者之前文化随笔中那种直抒己见的文学批评文风。在史实的镣铐,材料的局限,现实的种种掣肘之下,作者依然能够尽最大可能抒发自己的所感所想,以一种明快的节奏论述作者与传主的情感共鸣。
当然,传记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而作为文学,虽然不能对人物故事进行虚构,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必须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在这一点上,此书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趣味性上,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时很注重“有趣味”这一要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但是他将自己构建的传记理论投入创作实践时却深感无力。不得不感慨自己“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在传记写作中专注于严谨的历史叙述,体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史料价值,却削弱了传记文学的可读性与趣味性。陈歆耕的《龚自珍传》在趣味性上得到很多作家及读者认可。评论家李建军曾经评论这本传记是一本有趣的书,被书中很多有趣的细节打动。如龚自珍评价自己的父亲“稍通气”,评价自己的叔父“一窃不通”,说完之后哈哈大笑。这些细节的描画也有赖于作者对龚自珍资料掌握的详实,同样写过《龚自珍传》的雷雨先生就在专栏中写道:“看得出来,陈歆耕先生几乎搜集到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龚自珍的资料。”正因为资料的扎实,才能让人物如此鲜活可爱。除此之外,有趣也是作者本人的非常赞赏的品质:“人无趣心胸必逼窄、必蝇营狗苟于算计他人。”作者在开篇就指出龚自珍本人的富有趣味。“在龚自珍复杂而多元的人格中,我想在开篇的简短文字中特别强调一点:龚先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这些句子让人眼前一亮,在后文的阅读中感受到作者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语言的精妙。
二、历史叙事的当下性体现
创作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英雄传记的罗曼·罗兰,一直以史学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待史料,但是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他对传记写作有更高的要求。他希望借助这些英雄人物的力量来唤醒人心,变革现实。针对20世纪初法国日趋颓废的世风,着重刻画传主的伟大心灵,颂扬他们追求自由、伸张正义的超凡精神,并在写作中投射进自己对英雄的敬仰。这显示了一部传记的当下性意义与价值。胡适也曾指出“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如果一部传记只是单纯的还原史实或是就事论事,那么这部传记的思想价值,创作意义以及对读者的启发都会非常有限。陈歆耕在传记写作中一直保持着当下性思考,在谨慎的史料考证上,时刻保持对当下现实的关照,让历史人物具有当代性意义。
《龚自珍传》可以用“古事今情”来形容,作者没有简单止步于就历史写历史,就事论事,而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与历史深处的龚自珍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而通过这样的心灵对话,更加深入地理解传主的内心世界,从而提出了龚自珍在今天重读的意义。正如作者在龚自珍墓地时想到西方传教士的一句话:“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如果仅仅从文学价值上评判龚自珍的成就,那将掩盖了龚自珍一半的锋芒,他诗文中揭露出来的对社会现实的洞察与批判,他那些讥切时政的政论文流露出的勇气与见地更值得后人评说与学习。一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道尽了龚自珍内心的忧愤与抑郁,他想当一个践行者,写了多篇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然而终究没有施展出自身的抱负,但是流传下来的这些政论文却拥有更加旺盛饱满的生命力。作者认为,时弊,往往并不是某个社会阶段的一时之弊,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一旦气候和土壤适合,便可成持久之弊,所以,龚自珍的那些政论文至今仍具有存在价值,仍有借鉴意义。作者在写这部著作时常常把自己放进去,用当代人的眼光解读,领略龚自珍政论中闪射的思想锋芒,这种智慧可以观照当下,警醒后人。
龚自珍的诗,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本书中就特别把这个特点加以突出。其中很鲜明地表达了一个严肃的人才呼吁与人格培养的问题。对此,郜元宝教授曾指出,判断一个时代有很多标准,但是这个时代有没有人才是一个本质的标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最后还是要靠人。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才能的施展。作者陈歆耕在这个传记的开篇,就从清王朝的“文字狱”写起,揭示出言论闭塞,思想禁锢导致社会僵化,人才匮乏的结局。龚自珍最早发出了清王朝走向“衰世”的警示,制度性的压制长期屠戮人心,这种软性的摧残人才的方式会把有志之士的人格、意志、全盘抹杀。一个有才华之人被平庸之辈压制的时代,知识分子谋取的只是自己碗里的“稻粱”,谁还来为国家出谋划策,直言不讳?清王朝在表面的繁盛之下终会走向衰落。作者发现龚自珍的思想有一条主线脉络,就是聚焦于人,人才,人格。他的所有批判性也是围绕此轴心展开。作者亦将龚自珍与另一位思想巨人鲁迅做了比照,二者对社会现实批判都聚焦于大写的“人”身上,龚自珍是对“病梅”的哀叹,鲁迅是“救救孩子”的哀叫,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二人都极力渴求一个健康的“国民性人格”的树立,唯有此,国家才能立足,社会才会发展。
同样,这部具有批评意识的传记,也彰显出作者强烈而鲜明的批评的姿态和批评的立场。当下社会强调人才问题似乎已经是老调重弹,因为对人才的重视与培养已经成为普遍认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物质世界的丰富,各行各业竞争的剧烈,当前社会个人面临格式化困境。龚自珍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在今天许多人面临着严重的被格式化的境地,所以人才和时代的关系,在今天重新提出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优秀的传记作品一方面再现历史的真实,把更加真实的历史人物提供给广大读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记作家本人的个性、修养与精神追求。传记的目的是认知,传记也有纪念和教诲的价值。这更需要传记作家的史识和史德。传记作者陈歆耕用四年时间为龚自珍写出这部新的传记,写作过程虽有艰难和痛苦,但龚自珍的那些文字总能振奋人心:“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作者感受到这种智慧能够让后人学而时习之,付出的辛劳也是值得。
(责任编辑 王 宁)
郝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欣怡,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