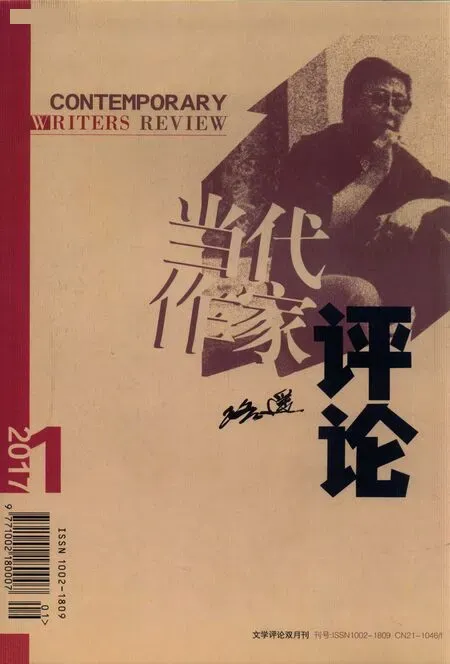散文诗写作之于当代诗坛的意义
荣光启

散文诗写作之于当代诗坛的意义
荣光启
引 言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和小说、散文、影像文化相比,诗确实遭到了公众话语的冷落。但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诗歌写作可以由此切实回到“个人”,回到一种文学写作应有的自然状态。当时代、社会不再对诗歌写作提供意义订单和价值承诺,诗人的写作只能是个人单独地面对自我与世界,作品的问世,除了自我心灵得到一定的慰藉,除了自认为在写作中又进一步认识了自我与世界,很难说还有更值得期待的价值。
所以我们很快看到,诗在社会层面的被边缘化,在具体的个人写作层面,却是全民化的。心灵的困苦、尘世间的烦愁欢欣,通过写作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宣泄。写作此时不依附任何他物,完全出自心灵的需要。在这个人人需要慰藉的生存境况中,诗人们以诗交友,大家以诗人之名建构小团体,在缺乏人情味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彼此挤身取暖,获得小群体之内的相互认同。有一个著名的南方城市,这里的“诗会”直接宣告,我们的活动就是“友谊第一,诗歌第二”。当下的汉语诗坛,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繁盛的时代,遍地都是诗人。谁都可以写,写什么、写成什么样都可以,诗歌写作脱离了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场景,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诗歌甚至参与了人际关系、社会和谐的建构。但在这种自由中,由于对诗歌这一文类的基本规则、艺术难度和价值期许有意无意的忽视,诗歌写作一方面在表面上显得空前繁盛,但在文本、诗质层面,又不免叫人感觉空虚。
我们注意到,一些近几年频频获奖的知名度甚高的诗人,作品却出奇地好读。也许我们可以推论,不仅民众在享受简易的写作带来的快慰,过去或激进或严谨的诗人们,也乐意加入这种分享感动的全民运动。这种状况对于诗歌写作的普及并非没有意义,但对于一些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似乎又觉得不能满足。1970年代出生的人,会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文学那种一意孤行的探索性和实验性,那个时代,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其先锋和前卫的部分,那精神与形式的光芒,至今回望,都异常地炫目。
就像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新诗的现代性的期许,既在李金发那奇特的象征主义实验里得到一定实现,更是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当中得到极大的满足。《野草》的许多篇章,是奇绝的风景,没有人会否认这是现代诗里边最复杂最动人的部分。而对于当代诗歌,这种讶异感与满足感也许在散文诗的领域你还可以寻觅。自从灵焚、周庆荣、李仕淦、爱斐儿、章闻哲、黄恩鹏、语伞等人的散文诗出现,以及《我们·散文诗丛》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我们也许需要重新打量当代诗坛的格局了。我们在评价当代汉语诗歌时,除了要关注通常所说的新诗,还要关注散文诗这一独特的领域。
一、当代文学中散文诗之存在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散文诗写作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今天当我们回望先锋派作家的写作,会看到他们有些实验性的文本,将之归为散文诗这种诗性文体也不算错。当孙甘露写下《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和《请女人猜谜》这些梦呓一样的“小说”时,人们看到的其实是散文诗的影子:“诗人在狭长的地带说道:在那里,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那是候鸟的天空。它们已经在信使忧郁的视野里盘旋了若干世纪了。它们的飞翔令信使的眼球酸痛。这些冬季的街道因此在信使的想象中悠久地如此神秘而又神圣。世俗的无限世纪使路经它们的时候已经成为可能。/信风携带修女般的恼怒叹息掠过这候鸟的天宇,信使的旅程平静了,沉睡着的是信使的记忆。我的爱欲在信使们的情感的慢跑中徒然苏醒,和信使交谈的是一个黑与白的世界,五彩的愉悦是后来岁月的事情。”在这样的小说里,人们找不到传统小说的元素,哀叹这样的写作是“小说的挽歌”。
比这个小说发表更早的另一个“实验文体”——李晓桦的《蓝色高地》,一开始就有一种清晰可辨的诗性:“当大地反射出一片幽兰的夜光的时候,那个牧羊的孩子发现自己迷路了。是他把家丢了呢?还是家把他丢了?路的尽头有一颗小星星。他开始向前走去……你在一条河里死命挣扎着。那流水是红红的,像一滩熟透的稀烂的番茄又被打翻了。水很烫,烤得你都快糊了。你想跳出去,但是一动也不能动,水很黏,像是最稠的浆糊,你的鼻子、眼睛,都已被黏住。”张承志评价说:“……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他也不得不提到该文体的形式:“其实形式远非那么重要。”后来人们将之称为“长篇散文诗作品”。
在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中,很多人的作品其实是散文诗,但由于散文诗这一文体的独立性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缘故,诗人作品中的“散文诗”部分,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好好考察其存在的意义。
在隐隐约约的远方,有我们的源头,大鹏鸟和腥日白光。西方和南方的风上一只只明亮的眼睛瞩望着我们。回忆和遗忘都是久远的。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磨难中句子变得简洁而短促。那些平静淡泊的山林在绢纸上闪烁出灯火与古道。西望长安,我们一起活过了这么长的年头,有时真想问一声:亲人啊,你们是怎么过来的,甚至甘愿陪着你们一起陷入深深的沉默。但现在我不能。那些民间主题无数次在梦中凸现。为你们的生存作证,是他的义务,是诗的良心。时光与日子各各不同,而诗则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
……走出心灵要比走进心灵更难。史诗是一种明澈的客观。在他身上,心灵娇柔夸张的翅膀已蜕去,只剩下肩胛骨上的结疤和一双大脚。走向他,走向地层和实体,还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就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是已故诗人海子(1964-1989)的一次写作,它的说话方式明显是属于是散文诗的,但很少有人会将海子与散文诗联系起来。诗人西川在1992写作的著名的长诗《致敬》其实也是散文诗的形式:
苦闷。悬挂的锣鼓。地下室中昏睡的豹子。旋转的楼梯。夜间的火把。城门。古老星座下触及草根的寒冷。封闭的肉体。无法饮用的水。
似大船般漂移的冰块。作为乘客的鸟。阻断的河道。未诞生的儿女。未成形的泪水。未开始的惩罚。混乱。平衡。上升。空白……怎样谈论苦闷才不算过错?面对岔道上遗落的花冠,请考虑铤而走险的代价!
痛苦:一片搬不动的大海。
在苦难的第七页书写着文明。
多想叫喊,迫使钢铁发出回声,迫使习惯于隐秘生活的老鼠列队来到我的面前。多想叫喊,但要尽量把声音压低,不能像谩骂,而应像祈祷,不能像大炮的轰鸣,而应像风的呼啸。更强烈的心跳伴随着更大的寂静,眼看存贮的雨水即将被喝光,叫喊吧!啊,我多想叫喊,当数百只乌鸦聒噪,我没有金口玉言——我就是不祥之兆。
欲望太多,海水太少。
幻想靠资本来维持。
……
在名作《帕斯捷尔纳克》之后,诗集《游动悬崖》显示,王家新也很早就以散文诗的体式在写作,只不过诗人自己将这种体式称为“诗片断”,以此与《瓦雷金诺叙事曲》《日记》和《卡夫卡》等“诗”区别开来:
长久沉默之后
“长久沉默之后”,叶芝这样写到,而我必须倾听。我知道,这不是叶芝,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将对我们说话。
诗
我在昨晚写下了:雪,今天,它就在城市的上空下下来了。这不是奇迹,相反,这是对一个诗人的惩罚和提醒。你还能写什么,什么才是你内心生活的标志?看看这辽阔、伟大、愈来愈急的飞雪吧,只一瞬,室内就彻底暗下来了……
《反向》(1991)、《词语》(1992.11-1993.1)、《临海的房子》(1992年冬)、《另一种风景》(1993.9-11)、《游动悬崖》(1993、1994)和《蒙霜十二月》(1995)等作品其实都是当代汉语诗歌序列里杰出的散文诗作品。第三代诗人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散文诗的写作及其为当代汉语诗歌在形式上的创新,功绩不言自明。很可惜,由于人们对散文诗文体之独特性的漠视,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被单独提出来。
二、“最上乘的诗歌才是散文诗”
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散文诗的写作,在各类文体中,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它对应着特殊的内在需要,对作者的要求也很高。就像林以亮所说的:“散文诗是一种极难应用到恰到好处的形式,要写好散文诗,非要自己先是一个一流的诗人或散文家,或二者都是不可。……写散文诗时,几乎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内在的需要才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诗或写不好散文,才采取这种取巧的办法。”也就是说,写作者在选择散文诗这一文类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他里边那种“不可避免的内在的需要”迫使他要使用这一文类,甚至可以说,不是他选择散文诗,而是散文诗选择他。这样讲绝不是将文类神秘化,而是强调文类自身的艺术特征:也许只有一种文类最适合作家某个时刻最想表达的心灵状态。作家的任务是要认识文类,是要寻找合适的文类。
鲁迅为什么在写作《彷徨》的同时也写作了《野草》?这里边一定有《野草》作为散文诗的独特功能,这个功能小说难以做到。小说是叙事性的文体,无论你想表达什么,都不应该脱离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讲述。但散文诗在表达人内心的复杂心境方面,无疑更自由、更深入。“《野草》呈现了一个昏暗、冷漠、敌意、憎恶的世界,甚至时间和空间都是暧昧不明的。自我来到这个世界里,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身不由己地被抛进这个世界里,从而自始至终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紧张的关系……但是,尽管自我与世界处于如此紧张的对立之中,却不得不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我’正是这个令人恶心的世界里的存在,并且在最深的根底里充满了与这个自己厌恶的世界的联系。由此,对世界的憎恶与这种意识到的同世界的联系便构成了‘我’的内在分裂……”《野草》里边的“我”,是现代人生存处境、自我质疑的极端象征,其抵达人心的深度和话语的丰富、繁复与转折,其奇妙、混合的诗意,都是现代文学里绝无仅有的,所以它是散文诗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写《野草》的那一个鲁迅,也许只有用散文诗才能表达出来。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经用一个词表达了一种文类那独立性的存在:“小说的智慧。”他说小说家“在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另一个声音。他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该改换职业”。他还说:“在艺术中,形式始终是超出形式的。”如果说是比小说家更聪明的“小说的智慧”牵引了小说家的写作,那么,在散文诗这一文类中,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同样的审慎与敬畏?有没有属于散文诗的那种在抒情和叙事上的独特智慧与力量?散文诗的形式也有超出此形式的丰富意味?散文诗是当代诗坛还不太被普遍重视的一种文类,有的人是太轻看它,有的人是因为了解太少而忽视它。这种状况和日本文学界对散文诗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据灵焚介绍:“诗评家岩城达也先生在谈到日本从大正到昭和初期的散文诗的三大特征时概括了三种印象:1.抒情色彩浓;2.故事性强;3.艺术表现极其前卫。把这种观点与前面谈到的荻原认为散文诗要求思想含量高、哲学要素浓的问题综合起来,我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散文诗并非一种好写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对作者的学识、修养、艺术、思想等都有极高的要求。”萩原朔太郎(1886-1942)对散文诗的理解是:“最优秀的、上乘的诗歌才是散文诗。”
三、“必须从景色进入元素”
新诗研究专家王光明先生曾经概括了散文诗的文体特征:“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有自己的性质和特点。散文诗是有机化合了诗的表现要素和散文描写要素的某些方面,使之生存在一个新的结构系统中的一种抒情文学形式。从本性上看,它属于诗,有诗的情感和想象;但在内容上,它保留了诗所不具备的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又不像散文那样以真实的材料作为描写的基础,用加添的细节,离开题旨的闲笔,让日常生活显出生动的情趣。散文诗通过削弱诗的夸饰性,显示自己的‘裸体美’;通过细节描述与主体意绪的象征两者平衡发展的追求,完成‘小’与‘大’、有限与无限、具体与普遍的统一。”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的,不过,当代散文诗的写作,常常流于“小”,给读者的印象是:散文诗就是写一些小感触、小情景,语言上比诗歌好懂;经验上又比诗歌浅薄;那些情趣性的东西、优美的地方又显得不触及现实,总之,在言说“大”、人类心灵的普遍经验与生命的无限境界方面,让人不满足。“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1960年代余光中对散文诗的批评,有些时候对当代汉语诗坛的散文诗写作来说,还是存在。
今天的散文诗作者,相当多的人自觉追求这“大”的层面,首先,在作品的言说对象上,他们不满足过去的题材与旨趣,对散文诗这种“大诗歌”,有极高的抱负:诗“是人类生命的一种本能性需求的艺术……我们所追求的大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诗歌呢?……‘它是探索人类起源性综合史诗要素回归的诗歌美学追求’……‘大诗歌’,它远远不是一种新诗和散文诗,再加上诗词等诗歌文学的统合概念,不仅仅只是为了打破当代文学的诗歌版图,完成一种文体健全发展的吁请这么简单的问题。它应该是一种反思当下诗歌写作所必须具备的意义、视野、情怀以及美学追求的集合问题。它的追求应该是最终打破所谓的新诗、散文诗的区别,超越于这两者的文体独立性意义的狭隘论争,完成一种回归生命原初诗歌的抒情性与叙事性在当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何做到有机融合的、崭新的诗歌艺术的抵达问题。”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对散文诗作者队伍的高要求:“散文诗作者素质的偏低是散文诗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素质偏低一是体现在写作者对深层民族文化缺乏深入体悟,二是与之相关的写作者思维空间的狭隘、艺术境界平庸有关。所以,他们的散文诗只能以贫乏的想象去夸张肤浅的感触,只能以小感触去观照复杂的宇宙人生,其结果只能使人轻看散文诗。
“当代文学对深层民族文化思考成为主流……散文诗的表现应该加入这种巨大的文化体系中,并按照自身的特质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做出艰难的选择。从作品来看,文化背景的关注和呈现成为必然的追求。一部作品,如果缺少超越作品本身、达到人类普遍意义的暗示力量,它的存在只是瞬时的,这种普遍意义的暗示力量,主要是通过文化背景的呈现来实现的。”灵焚这篇作于1987年6月19日的文章,与其在上述谈论“大诗歌”时提出的“探索人类起源性综合史诗要素回归”显然一脉相承的,这和诗人海子(1964-1989)对当时的中国诗歌的相关言论的认识完全是同时的(只是月份的差别)。与他们在当时是否相识无关,但完全可以看出,两位杰出的诗人在对当代汉语诗歌的抱负上,心心相印。
(2)新型电网规划体系的核心是处理与分析各种各样的多源异构数据。建设电网规划数据信息库是十分关键的,数据库能够整理并存储大量数据,数据库的工作支撑是先进的内存计算技术和索引机制,能够大大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数据处理的主要步骤有四个:清洗修正(即查找错误数据并对其进行修正),特征提取(即对不同类型的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关联分析(即分析不同类型数据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挖掘预测(即依据数据相关性来预测未来的数据)。而根据以往的和现有的数据来分析与预测未来的数据体现的正是大数据理念。
海子说:“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大众中救出来,从散文中救出来,因为写诗并不是简单的喝水,望月亮,谈情说爱,寻死觅活。重要的是意识到地层的断裂和移动,人的一致和隔离。诗人必须有孤军奋战的力量和勇气。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自我中救出来,因为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唯一的真诗。‘人民的心’是唯一的诗人。在写大诗时,这是同一个死里求生的过程。”有意思的是,海子的“大诗”不仅是为了超越“诗”,也是为了将诗“从散文中救出来”。如果考虑到当代汉语诗歌一定程度上的世俗化和口语化,海子的说法就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建议。他的许多发言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的诗坛,他曾直言:“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
一个写作者的理想就是能够直接地关注生命存在本身,“景色是不够的。好像一条河,你热爱河流两岸的丰收或荒芜,你热爱河流两岸的居民……你热爱两岸的酒楼、马车店、河流上空的飞鸟、渡口、麦地、乡村等等,但这些都是景色。这些都是不够的。你应该体会到河流是元素,像火一样,他在流逝,他有生死,有他的诞生和死亡。必须从景色进入元素……不仅要热爱河流两岸,还要热爱正在流逝的河流自身……”要关注生命中那些像“元素”一样最基本的东西,也许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才能更深入地穿透生存的表象、寻思生命的真谛。曾经的灵焚说:“用整个生命与世界相遇。”现在的灵焚仍然在说:“这样面对四季,金的属性为什么总让我们空手而归……我们该如何在四季中提取金的元素,找到那些自然的秩序里可以让生命打磨的含量?”
虽然海子从没有用“散文诗”来标识自己的文字。但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有些散文诗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更有表现力、更有形式感、更有文化意味、更有生命深度的言说方式。考虑到灵焚的写作与海子同时,这不免让人遐想:高举海子诗歌成就的人们,不熟悉灵焚,是否正因为灵焚走了散文诗写作之路?
四、不断“向源头聚拢”的文字
灵焚在一首长诗的序言中写道:“一群白色鸟在远方启程。时光尚未抵达,只有文字在纸上醒着。/向源头聚拢,就连大地的呼吸也不例外。/那些奔跑的露水与大气交换了比重,任你把夜幕抬高,高到足以放飞/成千上万的花瓣接住怒放的啼声,直达生命的起点。”他似乎是在表明,散文诗的文字,正是这种不断向“源头”聚拢的、醒着、奔跑着的文字。
大海在一场酣畅淋漓的涛声过后重新恢复辽阔,岸上还没有灯火,一阵风的转身提醒我们天地已经剥离。时间嫩芽般爬出水面,星光刚长出绒毛,还不能结伴飞翔。
这是最安静的时辰,就连我们紧扣的十指也不再呢喃。
湛蓝,这就是你要揭秘的第五元素?
此时,雨应该正在临近,而火也在星光的羽翎里准备动身。当太阳从地平线上辉煌走来,第五元素将从这些湛蓝的躯体里现出真身?
如果这样,那些在源头重新被孕育的人类,每一个都应该是你合格的情人。他们从此懂得爱,懂得万物不是尤物,不是为了承受毁灭而降生。
那么来吧!让我们在天地之间站立,峰峦般抱紧,尚未挂起树叶的裸体沐浴干干净净的阳光,以花朵的姿势,重新开始芳香四溢的吻。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灵焚喜欢用的“情人”意象,这个意象与爱情无关,所指向的是自我的更新及对人类的某种期许,那个理想中的“人”。“元素”和“源头”亦是常用意象,传达了灵焚这样的散文诗作家的一贯的旨趣。这是他们的特点,你可以说他们的写作太远离当下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但不能否认在关于生命本真、人之本质、宇宙真相、历史深处、文化根源等向度上的追寻上,这些文本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境界。
伏于大地上——其实,这是一个虔诚的生命的姿态。神是欣赏这样的姿态的。如此时,我只是一只斑斓的老虎,且安详而懒散,全无逼人的气势。我在丛林中无疑更像一只巨大的蝴蝶。作为一种自然的点缀和组成,我受到了低处一切生命的欢迎。
音乐就在这时响了起来。一定是我伏于大地的姿势使神感到了我的虔诚,不然,音乐如何会响起呢?
章闻哲的作品,里边常常触及许多当代诗人的盲区,比如神性、救赎和罪的问题,但她并不是在布道,而是个体的沉思与独语。她的作品,思绪深远、境界阔大、意象庞杂,情感的推动和想象的涌现急促而磅礴。很难想象这样的文字出自一个写散文诗的女子之手。她的《色诺波词:重复和延续的词》八千余言,从标题到结尾,读完了你的印象用当下的话说可能是:这又是一个当代诗歌的“神文本”。也许,叫“大文本”更合适。
之七:万物理论或灵
一切因你而生,一切都是你的创造,从最小的颗粒直到恢宏的天体构成。
天未老、地不荒,你开辟的果园枝繁叶茂,我是你埋藏土中的一粒种子,悬挂于枝条上的一颗果实,如此剔透、晶莹。
是的,一切灵光闪现。
李仕淦的《天光》《这场春天让我们流泪不止》《旅行者和旅行者的琴》(上篇)、《旅行者和旅行者的琴》(下篇)和《河流》等作品也是这样的大制作,这样的作品除了让我们看到作者的文学才华,也显现了当代散文诗作者的人文素质、知识视野和精神取向,也更契合“大诗歌”之“探索人类起源性综合史诗要素回归”的美学探索与精神诉求。如果30年前灵焚在检讨散文诗作者队伍素质的说法正确的话,今天,这个状况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第七日,空寂、神秘、纯净;万物祭典,圣洁、浩大、辉煌。/生命如此神奇、美丽,巨大的盛宴正摆向所有星座,银河流觞曲水,万灵列坐其次。/呵,此刻,一切正在行进,我的马匹长鬃飞扬,在光的任意维度上遨游、飞翔。/阳光普照,七种色彩斑斓迷离,一种呼唤、一种牵引、一种全新的肇始——/太阳在上、明月高悬,我与你同在,光芒高举,无边无际……”在《天光》里,李仕淦触及到宇宙大爆炸、时间和空间的起点、智慧设计论、上帝的创世七日等和世界发生、人类起源相关的信息,在作者的磅礴思绪和激越想象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信息、形而上的终极存在之思与个体当下的生命困厄激烈碰撞,产生出境界阔大、诗意深远的奇诡诗篇。当代散文诗作者对于“大诗歌”追求,不仅仅只是一种宣言,而是付诸于作者的创作实践与诗歌表现之中。
五千年,两千年的传说,三千年的纪实。
一万茬庄稼,养活过多少人和牲畜?
鸡啼鸣在一千八百零两万五千个黎明,犬对什么人狂吠过两万个季节?
一千年的战争为了分开,一千年的战争再为了统一。一千年里似分又似合,两千年勉强的庙宇下,不同的旗帜挥舞,各自念经。就算一千年严丝合缝,也被黑夜占用五百。那五百年的光明的白昼,未被记载的阴雨天伤害了多少人的心?
周庆荣是散文诗作者中风格独特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他的文字传递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有理想的人》《有远方的人》《沉默的砖头》和《破冰船》等作品绝对是励志之作,但周庆荣是用诗意的形象来说话的,作品不是宣传话语或口号演绎。某种意义上,周庆荣纠正了诗歌尤其是散文诗写作中惯常的颓废、痛苦、虚无、怪诞之风,将眼光投向了这个时代和身边现实中的朴素之物,我们若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主体情思或诗意境界感到不适的话,其实不是周庆荣的问题,而是我们在一个负能量的个人世界和文学世界里待得太久了。周庆荣的写作还呈现出一个勇于承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不会总是迷失于这个变幻无定的时代之中,而是常常提醒自己:“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责任又是什么?他的作品,是男性的诗篇,有一种久违的清新、质朴之美。《数字中国史》是一首反响不错的散文诗,但它只能是散文诗,像这种数数模式的写作,出现在诗歌里,会叫人不适。但因为是散文诗,它的说话方式就显得合理,在说到“五千年”时,他可以增添关于这五千年的细节。这种细节可以称之为“意象性的细节”,它是散文诗的必需。它成就了散文诗在叙事上的一种丰富性。
结 语
总的来说,今天的散文诗写作,已经呈现出一种大气象。著名新诗研究专家刘福春先生,收集、掌握了诗歌文学无数的历史文献与现场资料,他有一次在散文诗研讨会上感叹:“在新诗无边界审美拓展的创作乱象中,只有散文诗还在坚守着诗性的本质。”这里的“坚守”和“诗性的本质”是指什么?从作者的角度,恐怕一是他们始终对诗歌文学的神圣性的坚持;二是对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文学的自信;三是对散文诗写作的难度的要求;四是他们认为散文诗有着重塑诗歌文学的叙事性和抒情诗之融合的特殊使命。从作品的角度,你会看到在个体的感觉、经验、想象力的言说方面,这一文类和分行新诗一样努力,但其语言和意趣始终在追求对现实的超越性,不会将诗歌文学变成描摹现实或略高于现实的口语分行;散文诗写作在精神取向、想象之境、文本结构和语言美学的追求上,始终有一种高蹈的品性(这种“高蹈”肯定有人不喜悦,但对于有“崇低”之风的当代诗坛,未必不是一种有益的参照)。而在诗歌文学的抒情性与叙事性的整合方面,散文诗因其特有的优势,已经呈现出“现代诗歌文学”、“大诗歌”理念下才有的许多杰作,如本文所说的“大文本”。
这些“大文本”,在文化、哲学的深度上它连接着人类的知识前沿,在宗教、信仰的层面它触及到罪与救赎等基本的精神命题,在叙事上它传达的当代人的生存经验极为深切,在抒情上你也明显能感受到写作者那磅礴的情感与超绝的想象,面对这样的混杂、复杂又意蕴精深的写作,我们会非常吃惊:这是诗吗?这是散文诗的常态吗?应该说,关注类似“我们·散文诗丛”作者的高质量的散文诗写作,对当代汉语诗坛不无益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4BZW145)
(责任编辑 李桂玲)
荣光启,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