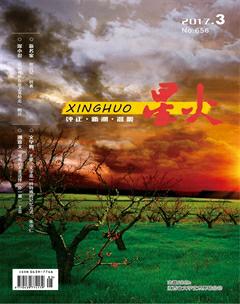文学的故宫(对谈)
宁肯 祝勇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197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第二分院中文系。做过多种职业,教师、记者、广告公司主管、编辑。著名小说家,“新散文”代表作家,北京作协理事、签约作家。现为《十月》副主编。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女人》《天·藏》,中短篇小说《后视镜》《词与物》《我在海边等一李书》,散文集《大师的慈悲》等。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奖等。
写作就是与寂寞的对抗
宁肯: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之前,是在《十月》杂志专栏发表,专栏名字就叫《故宫的风花雪月》。2013年做了一年,2014年又开设了一个专栏,叫《故宫的隐秘角落》。
《十月》杂志是双月刊,他一共写了六篇,我是祝勇这些文章的责任编辑。
祝勇:宁肯老师是第一个看这些文章的。
宁肯:祝勇有这个想法之初,我们有过交流。那是他刚刚到故宫不久,想从故宫的角度写一组系列文章,我觉得这个想法好。我作为编辑和作者一拍即合,这是一重关系。
再往前说,我和祝勇都是北京作家协会的理事,也都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合同制作家。那时北京作协开会常是在郊区,一开两天,晚上住在酒店里,我们总是四五个人凑在一个房间,或者坐在大堂聊天,其中我和祝勇,就是骨干分子。
我最早知道祝勇,是从我的朋友苇岸那里。他是一位关注生态、关注我们的天空、关注我们的大地的先驱性作家。时间推移得越久,他的意义越大。今年是苇岸去世15周年,所以前几天我们在三联也做了一个活动。
我在1997年认识苇岸的时候,就知道了祝勇,祝勇也是苇岸的朋友,在北京大学蓝月亮酒吧搞过一次活动。
祝勇:那次我没去,没有想到两年后苇岸就去世了,让我深感痛悔。前不久我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程光炜,我说初次见面,久仰久仰,他说,那次蓝月亮的朗诵会你没去,如果你去了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
宁肯:没错没错,那次祝勇没有去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祝勇这个人挺各色的,不太露面。没想到之后我们很快见面了。我记得当时祝勇在做一个电视栏目的嘉宾主持,叫《西藏往事》,在798一个艺术空间里。我本人在西藏生活过几年,我的创作也和西藏有很大关系,当时我作为《西藏往事》的嘉宾,口述1984年去西藏的经历。那次是祝勇采访我,与我对谈。
因此,我和祝勇有着种种不同的关系。
祝勇:可以说关系复杂,假如要写交代材料,一时半会儿还真写不完。
宁肯:今天我们继续聊文学,只是阵地转移到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也别有意味。三联韬奋书店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特殊,它率先实行了24小时的阅读开放,这就更使它成为中国的特殊之地。某种意义上来讲,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中心在哪呢?应该就在三联韬奋书店,三联韬奋书店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地标。我们能够在这里谈谈写作,是一种幸福。
祝勇:写作这项创作跟其他那些文艺形式都不一样,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劳动,没有表演性,相比之下,歌唱舞蹈、绘画书法都具备现场性,都可以表演,可以聚众围观。唯有写作,大部分时间是面对自己。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书页进行的,是间接的,而且这种交流有时间差,因而也不是共时性的。一部作品的价值,可能几十年后才能被读者认识到,也可能永远消隐于时间的长河中,这是写作这个行当的特别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就是与寂寞的对抗,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对抗,孕育出无数伟大的作品。
发现了另外一个时间
祝勇:我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是写故宫收藏的书画的。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180万件套,故宫博物院有很多研究者对这些藏品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丰厚,我们有学刊、院刊,不断发表各种学术论文,对故宫各种文物进行考证研究。
这些论文比较关注文物的物质性,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去关注文物的精神性。任何物品物质都是由人创造的,更是为人服务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冰冷的文物后面,都站立着活生生的人,演绎着活生生的历史。历史是一种时间现象,从来不会驻足一步,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后人永远无法见证,然而,当我们触摸、面对一件文物,我们实际上是在跟它背后的历史,和它背后的人在对谈、交流。所以我觉得文物本身是有生命、有感情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写雍正的十二美人图,我的兴趣不仅仅是判定这十二个美人到底是谁,我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她们张嘴说话。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试图通过文物,表现历史的复杂性和人存在的复杂性。所以,当有人知道我在写王羲之《兰亭序》,写韩熙载的夜宴时,他会说,这不是有人写过吗?我想大言不惭地说,我写的,从来没有人写过。
宁肯:祝勇去故宫工作以后,故宫在我心目中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祝勇带给我的。在祝勇去故宫之前,我从没在意过故宫,或者说,那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故宫,是常识的一部分,但与我无关。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个故宫,祝勇去工作以前的故宫和祝勇去工作以后的故宫。
当然故宫本身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自己,因为祝勇调入故宫工作以后,他常带一些作家朋友去故宫,使我们开始对故宫有了个人化的体验。之前,我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去故宫了,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故宫是一个不必要的存在,至少是一个不必需的存在,甚至于我很少带外地朋友去故宫,宁可去长城或者颐和园。这说明了故宫的存在基本上是静态的、固化的,除对皇帝生活的好奇,沾一点“皇气”,好像并没有去那里的冲动。我们当然知道故宫有厚重的文化、豐富的文物,但是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因此,故宫是一个占据着我们城市的中心,却与我们的生活无缘的存在。许多北京人,可能二三十年都没去过故宫一次。
当祝勇去了故宫工作,我觉得非常新鲜,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居然是故宫的工作人员,这让我感到神气。我想在只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时候去看看故宫,有一次祝勇就满足了我的这种要求,带我们去了一些“隐秘角落”。我记得那一天还有林白、格非、李洱,我们一直待到黄昏,在故宫闭馆之后,体验到了那个空旷寂寞的“紫禁城的黄昏”。
当时给我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一个在我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感觉。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恋恋不舍,而且还出了点小状况,因为他们都走了之后,我自己又偷偷地回来了。我没有出门,我又往故宫里面走,一直走到景运门外珍宝馆那个地方。我在那天发现了另外一个时间。我们有格林威治时间,有北京时间,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时间。总的来说,这些时间都是现在时的,而并非过去时的。但是那一天,当我一个人在太阳慢慢落下,月亮慢慢升起的时候,在那么浩瀚的宫殿里漫步,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现代,而是生活在古代。在这个空间里,时间绝对是独立的时间,而不是北京时间,更不是格林威治时间,它就是故宫时间,是历史时间。当时我就觉得,故宫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变得和过去不同了。
第二个不同是,在那种时间的感觉里,我有了一种潜在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像故宫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存在,时间的存在,怎么没有人用一种现代的语言,用一种个人化的眼光去讲述它呢?
所以,在那个夜晚,我和故宫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个人和故宫的关系。我对故宫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内心里面充满了语言,充满了一种讲述的欲望。我就想跟别人讲一讲我此时此刻在故宫的这种感受。我也希望跟故宫这些亡灵,这些过去时的宫女们,进行一些交流,做一些对话。
我的这种欲望被祝勇实现了。很多故宫的研究者、解释者,他们缺少一个个人化的灵魂,他们都在那做说明文,这个东西是什么,哪年哪月,全是在考据。就像文物的擦拭者,把某件文物拿起来端详一下,再把它擦擦,年代不清的重新写上年代,然后再放在那。这个物品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它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都不做说明,都不做解决。
这些考据,难道就是这件文物的一切吗?当然不是。一个物品包含了太多的东西,罗丹说过,我们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对美的发现。一件物品一幅画,它里边有着无声的语言,有着无声的历史。这个历史和一个人的认识有非常大的关系。和个人化的认识,和创造性的发现有极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始终缺少发现。中国地大物博,历史丰富,文化典籍那么丰富,但是缺少一个现代的、个人化的叙述,缺少一个活体的生命去感知它,讲述它。
不仅仅故宫是一种静态的、固化的存在,我们整个历史都有这种特征。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文学、哲学的人,研究文化的人,研究古玩的人,都是盲人摸象,摸着什么是什么,没有人,或者很少人用我们每个普通读者都能感觉到的个人化的视角,感同身受的东西去解读它。
祝勇:美国有一位重要的汉学家,名叫约瑟夫·列文森。1951年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伯克利有雄厚的汉学基础,我当年去伯克利做访问学者,主要是冲着伯克利出过列文森这样的汉学大师,而另一位重要汉学家魏斐德正在那里工作。列文森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被博物馆化了。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灵里,而且可以看得到,有时还可以摸得到,但这些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很大的生命力,对社会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博物馆化。如果讲得露骨一点,很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把历史和文物完全对象化了,就像研究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宝物,和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尽管可以做出很好的描述。
杜维明先生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特别举故宫博物院为例。当然,他是指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他说,很多来台湾的学者,无论东方的、西方的,来的目的就是到故宮博物院。他们看完了就走……我有几位朋友到台湾,任何地方都不去,就是到故宫博物院。他们说这就是古代中国……但因为博物馆化了,跟埃及文化一样。埃及文化现在在大英博物馆里,在本地已经找不到了,要到最好的博物馆才能看得到。好虽好,但它是死物,已经是对象化、外在化了的东西。①
宁肯:我们认识事物首先要靠感知。我们有感觉,我们首先要感觉它,然后才知道它。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完全背道而驰,是把感觉给切掉,我们先知道它,把它变成知识、概念、辞条,而不是生命或者时间的一部分。那些割裂的研究,割裂的讲述,割裂的著作,著作等身一年一年在那堆积,与我们的感觉、生命无关。
故宫是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因为中国历史这么大,这么漫长,你从哪里下嘴去讲?整个中国历史,故宫是一个缩影。怎么才能激活它呢?祝勇这样一个现代的人,中国一个新散文作家,他让故宫有了温度,有了气息。
祝勇去了故宫,太好了。
祝勇:刚才宁肯说,故宫有它自己的时间,听到这里,我心里一动。我们的生活、思想,都被一个共同时间格式化了。时间意味着规则,甚至是规训。我今天晚上七点钟必须赶到三联,参加这场活动,这是时间规定我的,我不能违背时间的意志,否则我必然会背上失信的罪名。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面时间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按照共同的时间去工作和生活。当游客进入故宫的时候,尽管他们来路不同,身体各异,却被一个共同的时间同化了,有无数信息在提醒着他们共同时间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共同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他自己。为什么宁肯在那一瞬间,感到共同时间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故宫自己的时间?那是因为在晚上,时间的信息消失了,共同的时间也就不存在了,故宫返回了它的自身,故宫中的人,也返回了他的自身。
很多年前,我曾经陪着白先勇先生在深夜的故宫走过。我在宫殿里,这就是“我”的宫殿,而不是“别人的宫殿”(张锐锋一本书的名字)。我把“我的宫殿”转移到纸上,就是我的作品。在这里,我有充分的权利,所有一切都要服从我的意志,连皇帝也不例外。我在《血朝廷》里过足了“摆布”皇帝的瘾,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里,雍正皇帝也要听我的评判。在这个时刻,他们归我来掌握。
这个时候,如宁肯所说,写作的冲动会非常强烈。这并不是像电视剧里面所说的,一下就穿越了,在那一瞬间,几百年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和几百年前的那个人是贴在一起的。为什么我要把故宫里这些文物当成活的来看?原因正在于在他人眼里,在我们与文物之间横亘着漫长的时间,而在我眼里,这个时间并不存在,假如我能够触摸到文物,我也一定能够同时触摸到“古人”的手。只有把文物当科学研究对象的时候,才有时间的横亘。当我们把它当成情感交流对象的时候,时间就不存在了,时间被抽空了,我们和文物背后那个人是紧紧贴在一起的。
每一件物体背后都有人。举一个简单例子,我现在手里这个手机,我相信再过十年它就会成为文物,再过100年,我们都不存在了,它就会被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的电话簿,他就会去研究这个手机的主人是谁,和电话簿里的这些名字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而不仅仅是研究手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什么型号。这个时候,他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这是一幅画,很简单。但是我在面对它的时候,它既是一幅画,又不是一幅画,它是一扇窗口,你的视线是能透过去的。如果它仅仅是一幅画,视线就到这儿停止了,如果它是一扇窗户的话,里面每一个小人儿都会活起来,你会看到当年在这个桥上活动的每一个人,看到他们的命运,看到他们各种各样的往事。他们是带着各自怎么样的命运被一个叫张择端的人一笔一笔画下来,经过上千年的流转之后,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画的面前,你的视线得以延长。古代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是一样的人,甚至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他们跟我是平等的,我为什么说雍正也得听我的呢,这不是狂言。他不是一个穿龙袍的画像,他也是具体的肉身,他所面对的问题,他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面临的问题有许多都是相通的。只要是人,就有对话的可能。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对话中产生。我所面对的,是书是画,又不仅仅是书是画。
文学的故宫是生命的故宫
宁肯:这次对谈叫“文学的故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文学是反映生命的,文学的故宫是生命的故宫。换句话说,祝勇到了故宫,赋予了故宫以生命。我觉得这是祝勇这本书最大的贡献。
赋予故宫以生命,也是赋予历史以生命。《永和九年那场醉》让我想起一首诗,我们和另外一位散文家张锐锋也讨论过这首诗,大家都会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很多时候我们通过窗口才能看清万里千秋雪,从一个窗口看,赋予它一个形象。
祝勇:千秋雪、万里船,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气概大到极致,但它们却是通过一扇窗、一扇门表现的,在杜甫笔下,那扇窗、那扇门,都是一个取景框,这个取景框,叫个人视角。个人化是写作的重要路径,很多年中,我们忘记了这个路径。假如写千秋雪,就直接写千秋雪;写万里船,就直接写万里船,看上去气势磅礴,但失去了个人视角,也就失去了时空上的纵深感,失去了文学的弹性。我们看二月河的小说,看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那么火,但是它们缺乏一扇门,一扇窗,缺乏个体生命的观照,那一部分写作应当是过时的。
宁肯:每个人都应该提供他的窗,提供他的门。不同的门、窗,提供了不同的世界景象,这才有文学世界的姿态万千。杜甫用了“窗含西岭千秋雪”,这就是创造。祝勇通过故宫角度看文学,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比如《兰亭序》,尽人皆知,但是对它我们已经没有反应,但祝勇写得非常好。《兰亭序》包含了多么丰富的生命的信息。而后世的大部分人都是盲者,就知道它好,而丧失了体验力,丧失了对话的能力。祝勇对固化的信息进行了重新编码。当我读到祝勇第一篇稿子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存在这么个《兰亭序》。他带来的那种感动从来没有过,它使我认识到《兰亭序》是王羲之在那样一种状态之下,在灵光一闪中完成的一件不可重复的杰作。从某种意义上,《兰亭序》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神经末梢,什么时候看它都存在,它都活着。什么時候看这个作品都活着,就是在字里行间它那么活跃地活着。谁解读过这种活跃性,这种活性?祝勇重新感知了它,解读了它。他几乎还原了那个现场。
祝勇:有一个读者说,她没有想到一篇写书法的文章居然让她如此感动。这个读者不是外人,是我太太。
宁肯:所以读完之后,我确实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深入感受到《兰亭序》的伟大。《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一个“醉”字,就把《兰亭序》那种生命的状态囊括了,非常的文学,非常的生命。我们通过故宫看到了《兰亭序》,通过《兰亭序》我们感知到了一千多年前的生命,而且那个生命是那么高级,那么鲜活,现在还在感染我们。它呼唤一千年之后可以跟它对应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祝勇。除了是祝勇,也可以是每个人,因为读了祝勇的文章,再去看《兰亭序》,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感受,找到自己的解读。这就是艺术的伟大。
另外一个例子,也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就是《韩熙载:最后的晚餐》。祝勇的写作也非常惊艳。祝勇对韩熙载做了精神分析,用现代最前沿的理论,包括福柯的精神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文学的核心是生命,生命就是直觉,也是思想。没有思想的高度,我们很难与古代的东西对应起来。
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他说,某种意义上是后人使前人变得伟大。什么意思?就是前人已经在那存在了,后人始终认识不到他,体会不到他的价值,没有对他进行继承和发扬。只有当后人继承和发扬之后,前人的伟大才能真正实现。卡夫卡就是一位使得前人变得伟大的人。卡夫卡认为生活存在很多荒诞和悖论,把荒诞彻底进行了建构、深入的表现,因为对荒诞的表现而驰名世界。后来人们研究,卡夫卡受谁的影响?如果没有卡夫卡,那个人就会永远埋没在时间长河里边。由于卡夫卡,那个人被发现了。他使那个东西产生新的意义。
祝勇重新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让我非常地惊讶,我没想到《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包含了那么多的现代性。我本来以为它就是属于古代,是封闭性的。但祝勇让它充分敞开了,我在《韩熙载夜宴图》里看到了现代性的东西,那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和悖论。
比如,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品,竟然是以一种腐朽的方式产生的,而且这种腐朽、这种糜烂,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一颗伟大的果实,居然结在腐烂的根上。我们过去觉得一棵很健康的玉米,结出一个健康的玉米棒子,这是事物的正常性。但是历史上很多文化现象不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东西可能是结在很烂的东西身上,善和恶是剥离不开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韩熙载夜宴图》是那么的神奇。祝勇看到了其中好几层关系,在作品中一层层地讲述,写作过程完全是哲学思辨的过程。这里边包含着的思维方式极其丰富。完全可以用福柯的理论去阐释它。同时我觉得可以阐释出更新的东西出来。
我下面还要跟祝勇聊福柯,聊法国当代哲学,我觉得祝勇已经具备了思想前沿的理论背景,所以他看事物能够把过去、现代和前沿的东西打通,游刃有余。我觉得祝勇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更加自觉和深入地利用当代前沿思想。我觉得最能体现现代性意义的作品就是《韩熙载:最后的晚餐》,是特别前卫的一个作品。重述历史,让古典作品和现代人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范本。
祝勇:为什么说是“文学的故宫”呢?从宁肯刚才的阐述来讲,我们会发现,当你换了一种眼光,它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杜甫说的“门泊”或者“窗含”,是换了一种眼光。有人说文学是不是不靠谱啊,因为文学使人首先想到虚构,你的文章里边是不是有很多不靠谱啊?我想说的是,刚才我们讲的对学术的研究是需要的,学术研究本身需要一个规范性,比如名词术语的规范性,我们要对它表示敬意。但是在这之上,我强调文学性,也不回避虚构,我认为虚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它考验着写作者的创造力。
具体谈到这本书,我认为没有虚构的成分,这部书它还不是一部虚构作品,它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所以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注释,很多人看了注释之后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书。假如说是文学作品,怎么还有注释?假如说是学术著作,又不是按照那样的套路去写的。
关于注释的功能,第一,我想把某些史实和论证的部分,单独提出来作为注释,作为我行文的证据,证明我不是瞎编,我不放到文章里面去,是不愿用这些生硬的史实打断行文的连贯性。
对于文本本身,我强调它的文学性。有人问我你又不去虚构,怎么强调文学性?
历史本身它就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历史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历史把它原有的文学性掩盖起来,我们看到的是芜杂的历史信息,实际上,历史中很多戏剧性情节本身,是小说家虚构不出来的。
我为什么对史料这么津津乐道?因为在这些貌似枯燥的史料中,我们很够发现很多无法想象的事实,就是上帝导演的一出大戏。比如韩熙载,刚才宁肯做了一个简单的叙述,如此杰出的一部美术作品,居然是从一个毒瘤上长出来的。还有宋徽宗,书中有一篇《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写到他的艺术和他的悲剧。宋徽宗赵佶,创造了瘦金体。尽管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有人写瘦金体,但只有在他的手里,这种极端主义的字体才臻于完境,出神入化,成为美轮美奂的一种字体。宋徽宗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怎么评价也不过分。我们看《水浒传》,知道宋徽宗是一个昏君,任用小人。后来北宋被金国所灭,昔日至高无上的皇帝被绳子所绑,带着几千宫女,被押解到北方,最后到达五国城,东北荒寒之地,坐井观天。
一方面,宋徽宗是个强者,在艺术领域里纵横捭阖,天下无敌;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政治上的弱者。真正的戏剧性在于——征服了北宋的金朝,他们的皇帝居然全都是宋徽宗的粉丝,而且是铁杆粉丝。金朝的几任皇帝,他们虽然在武力上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但文化上面他们跟在宋徽宗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宋徽宗是占领文化最高点的,所以金朝几任皇帝都想学瘦金体,但没有一个写得好的。尽管宋徽宗是一个阶下囚,连饭都吃不饱,但看到金朝皇帝写的字,鼻子里一定会喷冷气的。这种历史戏剧性,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在宋徽宗的身上,也体现出十足的戏剧性。他在北国当俘虏的那些年月,之所以能活下去,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还能写字,这是精神支柱。遗憾的是,他写的字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金朝让他写,拿到宋、金边境去卖,可以换外汇。金朝人要用宋徽宗的字去挫败宋朝人抗金的信心。意思是说,你们从前的皇帝是金国的阶下囚,他的每一顿饱饭都是金国赐予的,金国皇帝说一,他不敢说二。
第二个原因,是他梦想着有朝一日继续回到宋朝,继续当皇帝。很不幸,这个皇帝他永远当不了了。不是别人不让他当,是他儿子——南宋高宗赵构不让他当。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你回来了我怎么办啊?就是说天底下万千众生,只有一个人是最不希望他回来当皇帝的,就是他的亲儿子赵构,这又是一个悖论。
宋徽宗最后含恨死在北国。和他一同被俘的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之死,戏剧意味就更强了。当时金朝的皇帝俘虏了两个末代皇帝,一个是宋朝的宋钦宗,一个是辽朝皇帝。有一天金朝皇帝心血来潮,把那两个皇帝押上来,三个皇帝会一会。金朝皇帝想干什么呢?他想过把瘾,让这两个皇帝决斗。两个奴隶决斗,二者必死其一,这就是这两位末代皇帝荒淫误国的代价。
两位末代皇帝在马上PK,显然辽朝皇帝更胜一筹。但他觉得这是逃跑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想纵马出逃,金朝皇帝下令射箭,金兵把辽朝皇帝活活射死,宋钦宗看到这种场景,吓得从马背上跌下来,被马蹄活活踏死了。宋、辽、金,三个皇帝中一天死了两个,这种戏剧性很像是小说家编出来的,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在注释中注明了出处,正是为了把它的史料来源告诉读者,让读者相信这些是有记载的,历史的戏剧性本身往往超出小说家的想象。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大戏,史学本身就是跟文学紧紧相连的。我们如果不是用文学方式来表达历史,而仅仅用公式化方式来看待历史的话,我觉得是无比大的损失。
文学一直在模仿历史
宁肯:刚才祝勇谈到关于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说得非常好。先有历史,才有文学。比如小说,发展得非常晚。中国严格说从唐朝才有小说,唐传奇。假如以小说代表文学,文学一直在模仿历史。
除了小说,还要有文体,比如散文,在不断地发现历史的文学性。祝勇是“新散文”的主力,我也是“新散文”的一员,所以我这里想讲一讲这本书和“新散文”的关系。
我们一提到散文,都是指传统散文。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给我们,散文有抒情散文,有记叙性散文,到中学最简单,就是议论文和记叙文。多年来,这样的观念充斥整个文坛,基本上没有脱开中学语文教育的定义。
新时期小说发展了,詩歌也发展了,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探索,唯独散文一直停滞不前。小说有很多派别,有写实,有超写实,各种各样,诗歌也有很多,唯独散文没有。许多专注于散文文体的写作者,对此非常不满。因为散文从它本意来讲,最接近语言。从世界文学的潮流来看,包括哲学的潮流来看,都在向语言看齐。包括哲学也开始转向语言。
祝勇:语言是21世纪西方哲学三大关键词之一,另一个是身体,还有一个是他者。身体、他者、语言。
宁肯:哲学有一个转身,就是转向语言,从语言角度认识世界,语言不再是工具,语言就是本体。很多哲学著作都写得很像散文,不再是建构体系,建构范式,通过深入对语言研究,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
祝勇:比如罗兰·巴特的哲学著作,我们看起来很像散文,还有本雅明,不再是黑格尔那套硬梆梆的东西。
钱锺书先生曾说,哲学的价值,并不在于体系的建构,而在于深度。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就不是体系性的,而是碎片式的。其实,中国先秦主要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庄子,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通过片断来表达的,像《论语》《老子》《庄子》这些著作,既是哲学,又是文学(散文)。
宁肯:我们点到为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现代的散文,我们理解的散文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散文,包括对人类生存的整体哲思,而不仅仅是微小的记叙文、议论文。
祝勇:简单说,散文不只是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小橘灯》。
宁肯:散文所承载的精神性的东西,是历史、是散文、是诗歌,是非虚构,除了虚构他什么都是,也应该都是。这就是散文。散文是什么?散文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就是发现,就是通过语言去面对一切。这是我们意义上的“新散文”。我们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传统。每一个人都要依附在整体世界里边,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在祝勇这本书里,我发现了这种个人主义。祝勇写倪瓒,写他的洁癖,甚至如厕的时候,在下面覆盖了羽毛,让他的排泄物被鹅毛掩盖。但他最终的结局,却是在王朝鼎革之际,被新的皇帝弄死在粪坑里头。专制制度在消灭个人的时候是毫无情面的。正是因为意识到个人的价值,祝勇才写下这样的一幕。
注释
①: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3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