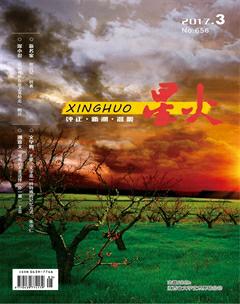故宫记
祝勇
方位在天
有一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几乎每一代中国人都可以从这部华语动画经典里找到自己的童年。它的创作设计者张光宇先生,被孙悟空的光环所掩盖,至今知者甚寥。但张光宇先生对此定然不会介意,因为他创造的孙悟空的视觉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长生不老。这就足够了。
那个被孙悟空搅得七荤八素的天上仙宫,应当是我最早在记忆里确立的宫殿形象。
其实我早在1971年就参观过故宫。那一年我三岁,家住在沈阳,父母带我来北京,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后来又参观了故宫,也在故宫照了相。后来进故宫工作,查看院史,才知道那一年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一年。三年前,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天,红卫兵要闯入故宫破“四旧”,周恩来当晚召开会议,故宫从此关闭。红卫兵冲不进去,就把神武门上“故宫博物院”牌匾换上了一个新的牌匾,上写“血泪宫”三个大字。1971年,造反的浪潮早已平息,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至今90周年,只有这三年关闭过。但我们要感谢这闭馆的三年,因为周恩来的一纸命令,故宫躲过一劫。今天我们在神武门上见到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郭沫若先生在1971年写成,放大刻上去的。
因此,我在那个夏天游历故宫,就有了历史性的意义——我应当是故宫重新开放后的第一批游客之一,只是除了几张黑白照片,脑海里什么印迹也没有。相比之下,还是张光宇先生描绘出的天上宫殿更令我感到新奇和兴奋,因为《大闹天宫》重新上映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已上了小学,对美术有了格外的兴趣,张光宇先生对天宫的想象,那种既华美又奇幻的气息,令我如痴如醉。后来来北京上大学,我重游故宫。重重的宫门,让人感受到它的深不可测。站在空阔的太和殿广场,两边的廊庑把天际线压得很低,凸显了太和殿的高度。其实太和殿的总高度只有35.05米(含台基高度),在现代都市里,摩天大楼野蛮生长,三四百米的高度,也在不断被刷新和超越。相比之下,太和殿的高度实在不值一提。但在我心里,太和殿依旧是最高的建筑。它的高度是感觉上的,不是数字上的;是心理上的,不是物理上的。它犹如一座高峰,屹立在群山之巅,让人产生一种置身天堂的感觉。
故宫从前的名字叫紫禁城。可以说,这座紫禁城就是一座落实在大地上的天宫,与天宫有着相同的结构与属性。古人讲:“方位在天,礼序从人”,所以人世间的一切秩序,都是与上天相对应的。天上有什么,地上就有什么。《史记》中说,“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①天帝——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玉皇大帝,住在天宫里,是宇宙间最高行政长官;那么在人间,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事,他就是皇帝,我们也称天子,意思就是天帝的儿子。明朝以后,圣旨的第一句话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说他的权力,不是靠武力抢来的,而是老天给的,叫“君权神授”,他管理的范围,我们称作天下,就是天的下边。
因此,假如有人从天上看皇宫,看到的不是起伏错落的宫殿,而是无数的点与线,代表着星与星阵。紫禁城的“紫”,不是指颜色,而是指紫微星垣,就是北极星。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宇宙的中心并不是太阳,而是北极星。太阳是会落的,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都不怎么拿太阳当回事。但古代中国人对北极星毕恭毕敬,因为北极星位于天空中央,永恒不动,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它动。有一首歌颂领袖的歌曲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实际上是歌词作者缺乏天文知识,弄错了。他想说的是北极星,北斗星和北极星是两码事儿,北极星是恒定不动的,北斗星的斗柄则是因季节而变的,所以天帝选择住宅时,只会选北极星,不会选北斗星。奉天帝之命统治人间的天子,行政官邸也应该用这颗星来命名。
紫禁城里也有太阳,但太阳没有北极星重要,因为太阳只是众星之一。用作家阿城的话说,中国人“不会崇拜之一,只会崇拜唯一。”②只有北极星才是唯一。《史记·天官书》开篇就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③天极星就是北极星,太一就是天帝。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④那个一,说的就是太一,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是天帝。屈原《九歌》第一首就是《东皇太一》,因为在先秦楚国,有祭祀太一的特殊风俗。中国人的太阳崇拜,直到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以后才有。
紫禁城里有日精门和月华门,是乾清宫区的东西两座门。在这里,日和月是平起平坐的,太阳的级别,并不比月亮高。乾清宫、中圆殿(交泰殿)、坤宁宫这后三宫,加上东西六宫,总数为15,刚好与紫微星垣的星辰总数相等。所以从皇帝到妃嫔,都住在紫微星垣上,就像住在宇宙飞船里,让所有人仰望。
当然,在紫禁城的天体世界里,倘少了北斗七星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北斗七星是天帝的权杖,是天帝统御天庭的象征,天地的运转、四时的变化、五行的分布,都是由北斗七星决定的。《甘石星经》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意思是说,天帝坐在北斗七星组成的车里,定四时,分寒暑,定纲纪,所以北斗七星也是重要的,而紫禁城里,最活跃的数字除了九这个最大的阳数以外,七这个数字也反复出现,就是为了和北斗七星的数字暗合。比如,中轴线上,有七座殿宇,分别是:三大殿、后三宫,加上钦安殿;还有东西七所,数字也都是七。此外,游客们很少注意到,紫禁城建筑的顶端,还有七颗圆球,对北斗七星进行更直观的呈现——在午门城楼上有四座重檐攒尖阙亭,每个尖顶上有一个圆球,午门城楼上就有了四个圆球,刚好构成北斗七星的斗形,而在紫禁城内,三大殿中间的华盖殿(中和殿)、后三宫中间的中圆殿(交泰殿),还有最北部的钦安殿,屋顶都有一个圆球,这七颗圆球组合在一起,刚好是北斗七星。皇帝坐在奉天殿(太和殿)里,眼前是一条天河,也就是内金水河,内金水河外围是北斗七星里的四颗,另外三颗在他的身后,这样构成的一幅天象图,一定会让他腾云驾雾,生出许多幻觉,遗忘了遥远的人间。
气脉之源
早年读《山海经》,读到这样的文字:“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⑤那是中国古人对昆仑山的地理描述。那时我并不知道,正是那座崛起于中国荒凉西部的山脉,决定了今天紫禁城的位置。
这看上去有些荒诞不经,但又不能不佩服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纵深感。那时还没有望远镜,更没有遥感卫星,古人的目光却能够穿透万里河山,获得一种地理上的统一感,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中国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古人在地理上的空间感是分不开的。
或许,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简单、干净,没有雾霾,所以纵然有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硝烟四起、血肉横飞,但那样的自然环境,那样的空气质量,让每个人的心胸都是开阔的,视线都是透明的。所以,尽管孔子周游列国都没找到工作,老子只留下一个骑驴出关的模糊背影,司马迁的下半身都被汉武大帝废了,但他们文字里的空间依旧是广大的,他们的视野依旧是浩瀚的,推窗一望,就能望见星沉海底,雨落河源。
但皇帝们更愿相信术士们的话,赋予了风水先生很高的话语权。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话语权,超过了所有的奖赏。所以,他们才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爬山涉水,无私奉献。在历朝历代,风水先生都是最辛苦的一批野外工作者,有诗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我看来,这诗就是形容风水先生的。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入古代的山川还是大河,在黄河青山、西风古道之间,除了可以看见落在哪朝哪代,还会看到风水师踽踽独行的身影。
所以,在那个名叫廖均卿的江西风水师眼里,北京距离昆仑山的距离并不远,放眼一望,远处近处的山山水水就尽收眼底、了然于胸了。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五月,他站在天寿山里,看到天寿山主山格局如紫微星垣,傲然排列,他的心里或许就映出七百多年前,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里对天寿山的描述:
大龙巨干,万仞千峰,俏然而来,幽然而止。其顿也,若降众山而臣之;其伏也,若怀万宝而藏。掀天揭地,襟江带海,幽奇远秀,依稀天汉之间。
杨筠松是唐代最著名的风水师之一,曾任唐僖宗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之乱后,他归隐山林,也将宫廷中所学之风水术带到了乡野民间,使这门帝王之术,开始为人民百姓服务。
“失礼,求诸野。”这话是孔圣人说的,朱棣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所以他刚刚登基,就开始在民间寻找通风水、懂阴阳的风水先生,为他确定陵墓和都城的位置。那时的朱棣,一门心思地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天下初定,迁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朱棣只能曲线救国,下令礼部寻找风水先生,为他选择陵址。朱棣知道,帝王的阳宅与阴宅要在同一条龙脉上。假如陵址选在北京,那么把皇城迁到北京就顺理成章了。
廖均卿神态庄重地接过皇帝的任命书,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腊月初九。第二天,他就匆匆赶到县衙里报到,那个县,就是江西赣州府的兴国县。县长说,事不宜迟,你这就向京城进发,我给你送行。这是腊月十一。十三日他就到了州里,二十一日就到了省里,布政大人对他说的话,与县长没有区别。他又一路北行,路过徐州时,赶上一场大雪,雪深五六尺,他涉雪而行,抵达当时的都城南京。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之所以落到了廖均卿的手里,原因是廖均卿是当时风水行业的佼佼者,他的祖上廖瑀,就是杨筠松的学生。杨筠松把他的庙堂风水术藏入赣南的山林,七百多年过去,又被廖均卿带回庙堂。
廖均卿跋山涉水,抵达北京勘察地形,是在第二年的五月。站在天寿山上,视线变得无限绵长。面对群山,他开始思考天下的格局。不是政治的格局——那是皇帝的事,而是地理的格局,具体说,就是天寿山与昆仑山的位置关系。思考的结果,却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让一意迁都的朱棣喜不自禁——天下龙脉,正汇聚在这天寿山里。
现在得解释一下龙脉是什么意思。《地理大成》云:“龙者何?山之脉也。”龙脉盘桓在大地上,有起有伏,绵延不断,像是气在其中运行,又像人身体的经络,彼此相通。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山不是一些纯物质的石头,而是气血畅通的脉管。
那么,龙脉的根源在哪里?就在昆仑山。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我们一直习惯于把河流当做我们文明的动脉,但天底下所有的水脉都发源于山脉,而天底下所有的山脉都发源于昆仑山,于是,在这块广袤的国土上,昆仑山为观察所有山脉的坐标原点。《河图纬·括地象》说:“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⑥《青囊海角经》里,杨筠松写道:
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形,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⑦
意思是说,所有的山脉皆发脉于昆仑山,支脉分明。昆仑山秉五气,合五形,天气从这里下降,地气从这里上升,阴阳相配,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这一观念,从早期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一直到清代,都从没有改变过。徐霞客跑遍南北,就是为了给他的家乡金陵与昆仑山接上组织关系。
发源于昆仑山的天下山脉,主要分成三大支脉,也叫三大干龙,成为撑起天下的骨骼。所有的经络筋肉,都附着在这三大骨骼上。三大支脉中,北方的那条最长,它从昆仑山出发,一路向西,沿阴山、贺兰山进入山西,沿太行山逶迤向北,形成燕山,再向东,潜入大海。天寿山,就在这条龙脉终结之处。
起自昆仑山的龙脉,抵达天寿山后潜入地下,建紫禁城时人工堆起的万岁山(景山),又把潜入地下的龙脉再引出来,成为王朝的护佑之山。所以说,小小的万岁山,与苍茫绵延的昆仑山,是彼此连通的。在它的斜阳草木间,感受得到昆仑山的风雨脉动。前面说过,帝王的阳宅与阴宅要在同一条龙脉上,有了这座万岁山,作为皇帝阳宅的紫禁城就与天寿山里的陵寝(十三陵)连通了。
有了这些山,紫禁城就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存在着一条通往上天的秘密通道,尽管这条通道,路途遥远,要从北京城,穿越黄土高原,顺着由倔强的山脊连成的天际线,一路向西,奔向西部的雪山大漠,才能抵达昆仑山,但至少在明清两代皇帝的想象中,它是存在的。有了它,紫禁城才气韵流畅,它的千般威仪、万般美丽,才有了依凭。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上看,起自昆仑山的圣山组合,横亘在帝国版图的北方,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天然屏障,成为帝都和紫禁城的真正靠山,皇帝背靠龙脉,面南而王,俯瞰天下,中原的泰山、南方的五岭,都在他的视线的正前方。皇帝视线的延长线,无形中成为一条更长的中轴线,把万里江山,都统摄在一起。那是一条真正的地轴,紫禁城位于地轴的顶端,一如北极星位于天轴的顶端,被泰山、黄河以及天下山水所拱卫,“合天下一堂局”⑧,孔夫子“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空间理想,终于变作现实。
想起来蛮有意思,假若没有廖均卿为皇陵和皇宫点穴、定位,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紫禁城,就没有明清两代五个世纪的沉浮沧桑,就没有皇城根下芸芸众生的风雨悲欢,也没有我这一介书生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一生的饭碗。在我与廖均卿,甚至与朱棣之间,也有着一条看不见的命运连线,就像那条发轫于昆仑山的命运连线一样。实际上,现世中的每个人,都与历史有一条这样的连线,古时的风里雨里,酝酿着今天的细胞血肉,没有前面发生的一切,后来的一切也都将胎死腹中,这才是一条真正的龙脉。无论历史纯洁还是肮脏,我们每个人,原本都是历史的产物。
大地之轴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对后代帝王影响至深。
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⑨
一个皇帝,必须像北辰那样,居于世界的中心,人们才能像众星一样,环绕着他。他之所以能够居于世界中心,是因为他的道德,天下第一。
那么,到底哪里才是世界的中心,可以安置人世间的那位道德冠军呢?
《尚书》说,“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秦朝的时候,咸阳就是大地的中心。《时遗记》记载,秦始皇在咸阳筑云明台,号称“子午台”,就有中央子午线的意思。后来他修建阿房宫,正殿的前面,就有一条子午线——当时叫“阁道”,一路向南,贯穿秦岭。⑩ 它正对的那条秦岭山谷,被人们称为“子午谷”。当年刘邦被迫前往汉中就任汉王,就是从子午谷通过,道路的艰难激发了汉军士兵对抗项羽的决心,最终,他们杀回了关中,夺取了天下。到了东汉,这样的传奇,依旧激励着汉中太守王升,让他在《石门颂》里,写下了这样的话:“高祖受命,道由子午,兴于汉中……”
从夏商时代建都中原,周秦汉唐进入关中,两宋回到中原,金元明清定鼎燕京,被称为中心的地方太多了,这难免让人对皇帝的道德产生怀疑——假如每一座京城真的是天下的中心,那中心怎么可能忽左忽右、忽东忽西?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代王朝都城的移动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必然使版图的几何中心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各民族的融汇史,“边缘”民族不断融入,既证明了这个“中心”吸附力之强悍,又使原来的“中心”无力负荷,随之而来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只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改朝换代带来的都城转移,必定会让他们感到迷惑甚至眩晕。
不论怎样,到了元明时代,北京被认为是最完美体现“天下之中”思想的都城。早在南宋,朱熹就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輥?輯?訛。北京,刚好是北极星(紫微星垣)在大地上的投影位置,乃天之中,是天下最尊的地方,而关中、中原、齐鲁、吴越都在南面,定都北京,完全符合“以北为尊”、“南面而听天下”的原理,是顺意天意之举,北京也因此而改名“顺天”。
北极星的投影点,就是太和殿,穿过这个点,划一条南北轴线,作为天下的中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子为北,午为南,那条线,也叫子午线。在执政者看来,国家的秩序,正深藏于子午线的意义中。子午线的存在,不仅使宫殿成为王朝时间的启始,也成为空间的启始。这条子午线,不仅穿过紫禁城,穿过整座京城,更一路向南,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是天寿山,正南依次是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皇帝坐在太和殿上,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他视野的延长线上展开,万里江山奔来眼底,让他感觉到江山永祚,天地合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和”字,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
北京的皇宫的正门是午门,午门,就是站立在子午线上的南方之门。午门的功能,一般是皇帝在这里颁发诏书。军队凯旋时,还要在午门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我们常听戏文里说: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在历史上,午门并没有用来斩首,如此神圣的位置,是不会用来砍头的。
但是,午门之外,的确举行过廷杖。明代时,如果大臣触犯了皇家的尊严,便以“逆鳞”之罪,被绑出午门前御道东侧打屁股。廷杖也比斩首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没有斩首痛快。廷杖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刑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还要包上铁皮,铁皮上还有倒钩,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鉤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手下不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也会被撕成一片烂麻。不少受刑官员,就因廷杖而毙命。即便不死,十之八九也会落下终身残疾。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因为打到七八十下,人就已经死了。很少听到有人坚持到廷杖一百的记录。
廷杖开始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后来发展到打死人。明太祖时代,就有了廷杖。明成祖永乐时期废除了廷杖,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又恢复了。被廷杖的官员,一般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107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34人,其中16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皇极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正德皇帝乘法算得精,但常常不等完成定额,人就断气了。
这表明皇帝不仅代表天命,哪怕一根手指、一截盲肠都代表着真理,也表明他的拳头也硬,午门外所有的刑杖,时时刻刻听命于他。宫殿里的皇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然,廷杖的厉害,在于它不仅要命,还要脸,因为身为朝廷命臣,被当众脱裤子,是何等的有损颜面。当然,剥夺大臣们的尊严,是显示皇威的一种手段。一个统治者的威严,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对他人的矮化实现的。廷杖,以剥夺他人尊严的方式,来强调和捍卫皇家的尊严。
但这样的矮化也未必总是很顺利,假如皇帝遇到有脾气的大臣,事情就可能会麻烦。而大明王朝,唯独不缺偏执的大臣。比如,在万历朝,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大臣们发生纠纷,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大臣们极力反对。双方僵持不下,万历一气之下,下令将上疏干涉皇帝立太子的礼部尚书洪乃春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但是万历没有想到,皇帝任性,大臣们更任性。廷杖这一刑罚,不仅没有让大臣们俯首帖耳,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前仆后继,主动申请廷杖。面对廷杖,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荣耀,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皇帝要打大臣屁股,他们干脆齐刷刷地露出白屁股,让皇帝一次打个够。对他们来说,露屁,就等于露脸。在明朝,甚至有很多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皇帝不论说什么,他们都投反对票,以便用皮肉之苦换来冒死直谏的好名声,在今天看来,不免教条主义,但在他们眼中,却是他们超凡入圣的通天梯。很多年中,廷杖几乎成了万历与大臣们对话最主要的方式。实际上,在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君臣之间基本上形成了虐待狂与受虐狂的强强联合,大家一起玩SM。皇帝越是凶狠,大臣们越是痛快。
这一场君臣斗,竟然一直玩了十五年。十五年中,午门广场可谓无比忙碌,被杖打的大臣不计其数,最后的结局,却是万历皇帝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他虽贵为天子,却寡不敌众,根本不是官僚系统的对手。他终于玩腻了,干脆罢了工,几十年不再上朝。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就是万历,明朝的江山,就是在他的手里玩完的,崇祯不过是为他背了黑锅而已。总的来说,明朝的皇帝,道德上过硬的并不多,无论是“为政以德”的政治口号,还是“天下之中”的建筑意识形态,都无法掩盖他们的变态与荒唐。假如皇帝真的是天底下最大的道德楷模,为什么王朝终究都逃不过一场败亡?假如天子真的代表天命,为什么天命总不长久,老天爷总是朝令夕改,朝秦暮楚?
王朝消失了,紫禁城仍在。即使在今天,每一个站在午门前的游客,也会被王朝的余威所震慑,对午门以深的浩瀚宫殿充满遐想。午门在建筑上沿袭了唐朝大明宫含元殿和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来的。正中开三门,两侧各有一座掖门,俗称“明三暗五”。中间的门一般只有皇帝才能走,中侧门供文武官员出入。西侧门供宗室王公出入。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可以从中门进宫,通过殿试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在宣布殿试结果后可从中门出宫。当年慈禧选秀女入宫,是从紫禁城北门,也就是神武门入宫的。没有从午门入宫,成了她一生的最大心结,所以她力荐自己的侄女隆裕做皇后,让她从午门抬进宫,才了结了自己的心愿。
在午门的背后,深藏着重重宫门,如太和门、乾清门、坤宁门、天一门、顺贞门、神武门,它们不仅分割着宫殿的空间,也制造了宫殿的神秘效果。在它们后面,是广场,豁然开朗的宫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依次浮现,那气势,没去过的肯定想象不出,也不用想象,买张票,去故宫看看就行了。
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IMAX影院,它的里面,上演着长达五个多世纪的超长剧情。
注释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1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阿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第1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1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 《老子》,第10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⑤ 《山海经》,第237—23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⑥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影印版,山川典第一卷,第6235页,北京: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⑦ [唐]杨筠松:《青囊海角经》,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影印版,第六五三卷,第57946页,北京: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⑧ [明]章潢:《圖书篇·皇明南北两都总叙·南北两地山川》,第三十五卷,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⑨ 《论语》,见《论语·大学·中庸》,第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⑩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